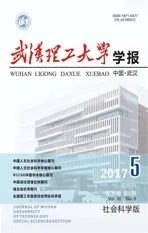东方舞蹈的美学特征
2017-03-08朱宇翔邱紫华
朱宇翔,邱紫华
(1.华中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东方美学与文化艺术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东方舞蹈的美学特征
朱宇翔1,邱紫华2
(1.华中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东方美学与文化艺术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东方舞蹈积淀着人类舞蹈历史形态的生成过程,具有历史的丰厚性。在东方多民族的舞蹈中,保存了人类历史以来的各种舞蹈形态,展现了人类舞蹈史上主要的、典型的、丰富的形态。因此东方舞蹈称得上是人类舞蹈博物馆中的“活化石”。同近代以来的欧洲舞蹈相比,传统的东方舞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东方舞蹈的美学特征主要包括混生性、原生态的自然性和民间性、象征性以及以性感而典雅的“扭姿”(“三道弯”)为美的特征。
东方舞蹈;美学特征;混生性;自然性;民间性;象征性
20世纪世界著名的美国音乐史家和舞蹈史家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es)曾说:“人类生活中和自然界的大事以及部落在求生存中的重大事件构成舞蹈的起因。”[1]109他指明了,舞蹈是人们对生存中重大事件的关注和表态的重要形式,在舞蹈的多种形式中表达出了人们对于那些事件的观念及情感。
早期人类欢庆节日和喜乐的事件时,少不了歌舞,舞蹈使欢乐的情绪达到高潮。从这个角度来说,“舞蹈实际上是拔高了的简朴生活——这种说法道出了舞蹈固有的全部特征和最完整的定义。”[1]3什么是“拔高了的简朴生活”呢?所谓“拔高”就是用舞蹈形式对原生态的生活事实加以创造性的提升和精炼化。一方面是对生活中芜杂的事实、事件本身加以简化和提纯,使事实或事件显得更加清晰、突出和鲜明;另一方面“是从本质上把一个人的惯常状态升华到另一世界。”[1]90即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的感情迸发出来,让情感汹涌澎湃,达到火热的或疯狂的状态。这种情感上的激发和释放,正是舞蹈所特有的或者说最擅长的功能。库尔特·萨克斯指出:“狂热对于舞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是一种能使人脱离生活现实,把自我卷进并贯穿于整个舞蹈世界的力量。”[1]208狂热的激情迸发是舞蹈的重要标志,正是狂热和迷狂,把舞蹈艺术同其他艺术鲜明地区分开来。
中国古代秦汉时期的人们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舞蹈的激情特征。例如: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正义·诗大序》
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礼记·乐记·师乙》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礼记·乐记·乐象》
上面的典籍中谈到了人类不同的表达情感的形态,从心志、言、长言、嗟叹、歌咏到舞、蹈,情感越来越激烈,难以把持和控制;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也不断变更,最终表现为狂热的激情和疯狂的舞蹈。舞蹈“是极度兴奋和剧烈活动在身体上的反映。”[1]113所以,舞蹈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激情的艺术。人类早期的舞蹈同巫术一样,大多都终止于迷狂的状态。
在舞蹈的世界里,个人的激情就像汹涌翻腾的大海中的一小颗水滴,群体的舞蹈才是大海的汹涌翻滚的波浪。群体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舞蹈形式,远远早于个体的独舞。个体性的双人舞蹈或独舞是社会文明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意识确立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舞蹈形式。
可以说,在人类舞蹈史上,随着人类的思想观念越来越文明,舞蹈中的理性因素越来越充分而非理性的迷狂成分才日渐淡薄。古代至20世纪之前,东方各民族的民间舞蹈一直持续着古老的舞蹈形式:以群体性的环形舞蹈和队列舞蹈为最主要的舞蹈形式;这些舞蹈以狂欢化的形式表达着部落、氏族和乡镇全体成员共同的激情和愿望。我们只有非常偶然地在古代埃及、波斯、中国唐宋时期和中世纪阿拉伯的阿拨斯王朝的宫廷舞蹈中,才见到少许的、并不纯粹的双人舞和独舞。这说明,古代东方民族的舞蹈主要是古老的、群体性的舞蹈形式;这些群体性舞蹈具有全体成员狂欢化的色彩。
东方舞蹈积淀着人类舞蹈历史形态的生成过程,具有历史的丰厚性。东方多民族的舞蹈中,保存了人类历史以来的各种舞蹈形态,展现了人类舞蹈史上主要的、典型的、丰富的形态。东方舞蹈称得上是人类舞蹈博物馆中的“活化石”。东方舞蹈按舞蹈动作划分,它保持着人类舞蹈最古老的形式——“痉挛式舞蹈”(巫术中的迷狂舞蹈)和群体的环形舞蹈。在人体的协调型舞蹈中,又同时保存着“伸展型”舞蹈(开放四肢、伸展肢体及跳跃)和“收缩型”舞蹈。在收缩舞中,又可分为立式舞蹈和坐式舞蹈。立式舞蹈又发展出站立式舞蹈和旋转舞蹈;从坐式舞蹈发展出了东方民族丰富多彩的手语舞姿。如果按舞蹈动作的形象性来划分,东方舞蹈一直保存着古老的模仿型舞蹈和观赏型舞蹈。
传统的东方舞蹈同近代以来的欧洲舞蹈有着明显的差异性。那么,东方舞蹈有什么特色呢?本文正是从东方舞蹈与西方近代舞蹈的比较中来凸显东方民族舞蹈的独特性。
一、东方舞蹈的混生性特征
东方舞蹈同音乐、戏曲、说唱等其他艺术一样,到晚近时期才获得了独立自主的艺术地位。在历史上,东方舞蹈始终同诗歌、音乐、说唱、戏曲、民俗、杂耍等艺术形式搅和在一起,它们一直处于混合生成的发展状态中。在古代东方,舞蹈者必须同时具备诗、歌、说唱、杂耍、戏曲等综合表演能力,“印度的戏剧演员承认自己是舞蹈者,因为他们的职业在印度北部的方言称为‘那塔’。而这个字眼在梵文里为‘那第亚’,意即‘跳舞’。”[1]187东方音乐、舞蹈、戏曲艺术的混生性特点一方面使东方古代原生态的民间艺术的传统得以比较完全地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东方音乐、舞蹈、戏曲的分化与独立的进程显得迟慢。艺术分化的迟缓是与历史上东方农业社会向来缺乏明确的、细致的社会分工是同步的。东方国家的城市文明及其商业化进程迟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分工和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门艺术的独立发展。
东方艺术的混生状态要求东方艺术家必须拥有杂七杂八的、众多的才艺,例如“领舞者不但指挥着唱歌还领着大家跳舞。”[1]225但是艺术家却缺乏对某一门艺术专门的、精到的研习和创造,也就缺乏专门的教师和专修的学生,各门类艺术就很难独立出来。东方艺术的混生性状态和东方舞蹈的群体性特点导致了东方艺术继承多于创新的传统,限制了舞蹈的独立发展和个人创新的可能;因而致使哪一门艺术都难以脱颖而出,独立发展。
中国直到唐代以后的宫廷舞蹈中偶尔才有少许的独舞出现;印度的独舞同样出现较晚。独舞是舞蹈独立的最鲜明的标志。从舞蹈史上看,尽管舞蹈最终还是从其他艺术之中独立出来,但混生形态的痕迹却一直延续到晚近时期。东方独舞只是稀少地、羸弱地存在于古代宫廷舞蹈之中,作为东方舞蹈主体的群体性歌舞则一直存在于民间生活中,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东方艺术的混生性不仅造成了后来艺术的繁复性、多样化,而且使各门类艺术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甚至可以促成新的艺术品种的产生。例如,“跳形象型舞蹈都会进入角色,他们再现人物、动物、鬼怪、神灵时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变成所再现的动物、鬼怪或神灵。他们的动作必须像所扮演的角色,必须劳动、赠赐或祝福他人。”[1]61为了替代这个角色,舞蹈者都采用脸部戴面具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替代,“面具舞促进了这种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已孕育了观赏性舞蹈的胚胎。”[1]181东方民族不同的艺术种类和艺术形式数不胜数,丰富多样,这同东方艺术的混生性特点是分不开的。东方舞蹈是东方戏剧艺术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和推手。
二、东方舞蹈的原生态自然性和民间性特征
东方舞蹈拥有人类舞蹈历史形态的丰厚性。从历史的眼光看,东方舞蹈继承传统的舞蹈元素较多而变更与创新显得不足,东方舞蹈更多地保留了古代原生态生活的鲜活性和自然性特点,模仿性元素非常丰富。当然,东方舞蹈的这一特点是相较于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欧洲舞蹈的特点而言的。
近代以来,欧洲舞蹈在充分继承和保持了各民族民间原生态的舞蹈形式和基本元素的同时,又从宫廷舞蹈和中世纪各城市的商业观赏性舞蹈中发展并提炼出了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舞蹈——芭蕾舞。芭蕾舞现在已成为欧洲舞蹈的典范。东方舞蹈同西方芭蕾舞之间最大的或者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东方舞蹈具有非科学性和非人工的自然性,其思想基础建立在巫术的模仿性、象征性和生活劳动的再现性上。库尔特·萨克斯指出:东方“绝大多数模仿型的舞蹈是表现愿望的舞蹈,通过这些舞蹈来表达人们的需求,并且希望通过跳舞去获得部落和大地的繁衍、万物的生长、星宿的赐福、身体健康、生机不衰、强壮有力、狩猎走运和取得胜利。”[1]185东方舞蹈旨在表现群体的宗教愿望以及这种愿望的最终达成。东方舞蹈既是情感性的,又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
芭蕾舞是超越了欧洲各民族民间舞蹈的、独树一帜的舞蹈形式,也是欧洲文化艺术的卓越的代表。芭蕾舞的舞蹈形式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文化观念的产物,也是近代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成果。芭蕾舞的美学思想是建立近代欧洲个人主义思想观念和新的、科学的人体美观的基础之上。芭蕾舞既表现了现代欧洲新型的、静态的人体美理想,又展现了美的人体动态和变化之美的全部神韵。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变革运动。20世纪世界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将文艺复兴描绘为‘第一次启蒙运动’。看来,说启蒙运动是‘第二次文艺复兴’至少同样恰当。”[2]251文艺复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世界著名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指出:文艺复兴的巨大功绩在于“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宣扬:人是上帝的杰作,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然而赞美人体美、欣赏人体美对于基督教禁欲主义来说又是一个重大的罪恶,这是非常矛盾的观点。文艺复兴思想运动中,人的地位和价值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万尼·比科说:“人就像上帝,人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和关键,人是大自然的解说者。”[3]234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借剧中人之口说:“人是万物的灵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罗伯特·伯顿在其著作《忧郁剖析》(1621年)的开场白中说“人,世上最优秀和最高贵的生灵。”[2]250在这一思潮中,中世纪被看作是“邪恶”之源的人体成为新的最美的审美对象。文艺复兴的艺术家重新发现了自然中的人体美,由此开拓了展示人体美艺术的新的天地——雕像、绘画和舞蹈。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上帝造人”的理论,来复活希腊的艺术传统,把完美的、理想的人体之美当作神圣的理想。德国著名画家丢勒写道:“上帝按照人应有的样子一劳永逸地铸造了人。我认为,完美的形式和美都包含在一切人的总和之中。”[3]249由此,追求“完美”成为艺术家创造人体美的目标。冰层既然被冲破,人体美的表现就蔚然成风。无论是表现基督教思想的题材或者是古希腊罗马传说的题材,裸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形象。尽管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所画的裸体人像也遭受到教会人士的猛烈的抨击,但是艺术家们关于人体美是自然天成之美,是最难表现之美、是最高境界之美的信念已坚定不移了。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威尼斯的画家提香成为了卓越的创作女性裸体画的大师。
在某种程度上讲,静态的人体画和人体雕像成为欧洲艺术家创作的最高境界。理想中的最美的人体在生活中难以寻觅,这些范型之美的人体只能通过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创造。为了创作出最美的人体,必须仰仗数学的比例计算来测算。艺术家们把数学的比例关系大量用于人体比例,力求寻找到人体的最美的模型。“在文艺复兴晚期,人的身体像动物的身体一样被‘发现’了。说人体‘被发现’,是指它被解剖、研究并得到了更准确的说明。”[2]234他们从自然人体中提取基本数据,再以实验手段去总结出最美的人体比例和数据系统。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就曾大胆运用实验方法探索符合视觉美的人体比例,“他塑造的人物,身长为头的九倍、十倍、甚至十二倍,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在把躯体各部分组合在一起时,寻求某种在自然形式中找不到的优美;而且他说道,艺术家所需要的量度工具,不是手,而是眼睛,因为手仅能操作,要判断就得要眼睛。”[3]245这说明科学试验精神已经融入了艺术家的意识之中。其结果,是理想化、顺应视觉美感的真实替代了自然的真实,科学性排除了自然性。
人体动态之美的展现只能由舞蹈来承担。从此,数学和物理科学中的比例、匀称、平衡、对称、对比、空间、时间等等观念成为芭蕾舞动作设计和创作的思维基础。人体肌肉的收缩和舒展、人体的跳跃、静止、平衡等的力学关系,人体几何体造型之美等等成为学习舞蹈和研究、创作舞蹈的基本内容。芭蕾舞从意大利的城邦王国宫廷走向法国露易十四的宫廷,再从欧洲各国宫廷走向城市商业演出的过程中,拥有了一批专门的舞蹈教师和学生,有了专业的研究者和演出团队,也就逐渐形成了经过精心设计制作的规范、程式和审美标准。这些动作规范和程式都是欧洲贵族化的人体审美观念的表现。我们从芭蕾的人体“开、绷、直、立”的动作特征可以看到贵族化的高贵的审美趣味:那挺直的躯干、高昂的头颅、绷紧的脚背、外开的下肢、笔直的双膝、舒展的双臂等,无不显示着对完美的、理想人体的想往,透露出渗透在芭蕾舞中的欧洲贵族高贵的宫廷气息。
此外,芭蕾中有大量的跳跃和伸展动作。“芭蕾动作的感觉是离心的、星射的、双臂与双腿从躯干突出向外伸长,形如从躯干飞离出去。”[4]美国舞蹈评论家珍妮·科恩指出:芭蕾“如果没有那种尽力向上的感觉,没有那种‘征服天地般’的直立,我们就无法确认。”[5]芭蕾的外开、跳跃、冲刺、飞腾、托举等动作,都是近代欧洲社会所追求“张扬个性”、“凸显个人价值”观念的体现。时代的大变革呼唤着开放的、张扬的、舒展的舞蹈艺术,芭蕾舞应运而生。相比较,“在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除少数几个地区例外都缺乏跳跃式舞蹈,或者说得确实些,一个民族其耕耘文化特色越浓,他们的舞蹈越属收缩型。”[1]23芭蕾舞的动作舞姿只是生活动作典型化的提纯而不是生活中动作的本身。所以,芭蕾舞是人工制品,非自然性是其根本的特征。
此外,芭蕾舞中不仅包括了人类所有的舞蹈形式——群舞、几人舞、双人舞、独舞,而且独舞、双人舞、三人舞成为了最主要的表演形式。舞者所追求的技巧性、表现性和欣赏者所追求的悦目性、刺激性和观赏性成为了新的舞蹈的“艺术目的论”。这种追求舞蹈的悦目性、观赏性、技巧性、表现性的美学目标,只能通过专业人士的创新性思维和舞者技巧的创造才能实现。加之作曲家精心制作的舞蹈音乐,这种音乐无论是节奏、速度、情感上都必须同舞蹈情境水乳交融,成为一体,这更加增强了芭蕾舞创作的人工性和技术性。芭蕾舞是人类精神精心制作的舞蹈形式,大自然永远不能创生出芭蕾舞。可以说,近代欧洲的芭蕾舞是一种建立在近代科学原理和人工性、技术性基础上的、充分人为化了的、专业化的舞蹈体系。
比较而言,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东方民族的舞蹈依然保持着古代舞蹈的原生态特色。东方舞蹈主要还是模仿性、再现性的舞蹈。其动作、形象主要还是对日常生活和劳动、战争场景的模仿和再现,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这种模仿与再现性的舞蹈,严格说来,就是从古老时代的原始巫术以及宗教的生活内容一直沿袭至今的舞蹈形式和内容。东方民族的舞蹈延续了群体性舞蹈的“非表现性”;环舞与队列舞依然是东方民族舞蹈最主要的形式。直至20世纪末,东方民族的舞蹈依然以节日的欢庆型舞蹈为主,除少量的旅游景点外,很少有表演性和专供观赏的舞蹈。此外,在东方,除了印度、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国家如日本、韩国外,大部分东方民族几乎没有专职的商业性舞蹈演出团体。
三、东方舞蹈的象征性特征
东方舞蹈是东方民族所采用的动态的、表情达意的“符号”和“语码”。东方舞蹈大量运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姿态语、手势语、表情语、眼神语、动作语言来传情达意。这些舞蹈语言属于“非声音语言”。由于“非声音语言”是非概念性、非语词的形象化语言,因此,所传达的思想感情都必须借助肢体、姿态、动作等媒介来表达。携带着情感性的模仿、比附、比喻是舞蹈语言的特点,可以说,舞蹈语言本质上是象征性的。舞蹈语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缺乏清晰性和准确性。舞蹈的肢体语言属于“模糊语言”。模仿、比附、比喻是象征式表情达意的基础;非理性、模糊性和多义性正是象征性语言的特点。东方舞蹈更是充满了象征意味。
(一)东方舞蹈队形的象征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原始文化和大部分初步得到发展的文化水平在空间概念上只要求圆形。”[1]118原始先民们为自己建造了圆形的小屋“环舞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和圆形茅屋的形成和发展有关。……正如圆形小屋被当作火堆或中心位置看待,环形群舞于是围绕着一堆篝火、一个地坑或一个中心物移动,连黑猩猩的环舞也有中心物。”[1]118库尔特·萨克斯指出:“环舞是群舞的最古老的形式,甚至类人猿也跳环舞蹈。今天世界各大陆的人依然跳此舞。……成行或成线的舞蹈形式起源于较晚的阶段。……神话传说里也谈到舞蹈是以圆形开始的。”[1]117可见,群体性的环形舞蹈不仅是最古老形态的舞蹈,而且也是早期人类的群体精神的反映。
东方舞蹈的主要形式都以群体舞蹈为主。群体舞蹈有两种基本的形式,即环形舞蹈和行列(队列)舞蹈。群体性的环形舞蹈不仅是最古老形态的舞蹈,而且也是早期人类的群体精神的反映。环形舞蹈的象征意义在于以下几点:一是环形舞意味着群体共同占有、控制或者放弃某一东西;二是环形舞蹈象征着部落、部族内部的团结以及对它者的排斥;三是环形舞蹈象征着天体的运行节奏和规律。东方环形舞蹈中常有多层的环形舞蹈,有时几层环圈的舞者同时呈顺时针方向旋转;有时,其中的某一二圈则呈逆时针旋转。
(二)东方行列舞蹈的象征含义
行列式舞蹈的排列行数同环舞的圈数一样是有象征含义的。行列舞蹈根据人数的多少而排列为不同的行列,有二行、三行、四行或更多的行列;行列舞蹈有时会变形为二、三列彼此交叉的链条等。就东方的行列舞来说,其队形的象征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行列舞蹈蕴含着明确的社会的等级观念;二是象征着敌我格斗或者两性之间恋爱的“性”吸引过程;三是当行列舞蹈的队形变形为“编织带”、“链条形”或“桥形”、“拱形”队列时,它既象征祈求生殖、生育丰产,又是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愿望表达。上述行列舞蹈的队形象征着东方民族所坚守的宗教信念:用生生不息的生命去超越死亡,达到生命永恒的轮回。
(三)东方舞蹈动作的象征性和虚拟性
自古以来,东方舞蹈都同生活息息相关,所表达的情感和生活内容都直接同人的生命、生殖和生活安康紧密联系在一起,东方舞蹈同人们感性的生活需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很少有纯精神思想的表现或纯粹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享受的成分。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
在少数东方国家的舞蹈中才有所改变。东方舞蹈动作的象征性有几个方面:
第一,舞蹈使舞蹈者的角色身份发生转换,舞者替换成了所表演的那个对象。舞者成为了那一事物或对象的象征。“跳形象型舞蹈者都会进入角色,他们再现人物、动物、鬼怪、神灵时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变成所再现的动物、鬼怪或者神灵。他们的动作必须像所扮演的角色。”[1]61古代东方民族在舞蹈或戏曲中,为了表明这种转换或替代,就让舞蹈或戏曲演员头脸上罩上面具,面具就成为新的角色身份的象征。“面具本身具有双重意义。……它在外向的形象型文化里刻画被模仿的动物或其他生物的模拟形态。”[1]108
第二,在东方民族的舞蹈中,很少有那种大跨步跳越、向上的跳跃的舞蹈。库尔特·萨克斯指出:“在亚洲的东部和东南部除少数几个地区例外都缺乏跳跃式舞蹈,或者说得确实些,一个民族其耕耘文化特色越浓,他们的舞蹈越属收缩型。”[1]23然而,在东方舞蹈少许的大跨步和腾跃式舞蹈中,这些动作都具有特定的生命、生殖崇拜或者说具有丰产巫术的象征性意念。“在日本踩高跷是和印度尼西亚的跳跃舞蹈一样为农事节日的活动所采用。”[1]69同样,中国东北、华北广为流行的踩高跷舞蹈就是象征植物的增产或者说人类的生殖丰产。
第三,东方舞蹈中有着较多的象征性力的题材和动作成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的资料表明,古代以来的东方民族中,盛行种种象征生殖或表现性力的舞蹈集会形式。在这些舞蹈中,“男人们在地上掘一个大洞,……地洞的挖法和小树枝的装饰非常像女人的阴部。在跳舞的过程中,他们在身前握着一根长矛以代表阴茎,绕着地洞跳舞时用长矛刺进洞内象征着他们的生殖能力,并继续唱:‘不是地洞,不是地洞,是阴户!’。”[1]70在文明充分发展的时代,表演形式演变为求爱者围绕女性舞蹈。时至今日,中国四川、云南等地的彝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在每年火把节前夕,村子里那些生育了儿子的男子们上山挖下一棵高大的大树;生育女儿的男人们则在村中的广场上挖一个深坑。然后由生了儿子的男子们把大树插进深坑里。晚上开始,全村人围着这棵大树做成的“大火把”通宵狂热舞蹈。此外,云南白族的“插秧节”歌舞也象征着生殖与性力的过程。在插秧节中,村里凡是生育了儿女的妇女们都要在秧田中拔出秧苗,背到其他田里插秧。男人们则在田边敲锣打鼓,吹号高歌,以表示“助产”。这一过程中,一直载歌载舞。东方舞蹈中的双人舞蹈几乎都有着象征两性爱情、性吸引、性活动的含义。世界著名的美国文化史家威尔·杜兰指出:“舞蹈在印度历史的大多时期,乃是一种形式的宗教崇拜,是一种动作与韵律之美的展示,以荣耀神并且陶冶神的性情。……对于印度人,这些舞蹈不仅是肉体的展示,它们在某方面是宇宙间韵律与过程的模仿。湿婆便是舞蹈之神,而湿婆的舞蹈正象征着世界的律动。”[5]
第四,东方舞蹈的手势和姿式中有着丰富的象征含义。东方舞蹈中有着丰富的手势语和姿态语。舞蹈者通过手势、身体姿势来表情达意,这些手势和姿态语汇都不是简单的模仿性或指示性语言,仅仅指示意义的作用,其中包含着“言外之意”,传达着“弦外之音”。如印度舞蹈采用手势语和姿式语最频繁,最丰富,它是印度各派宗教和古典舞蹈用来传情达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是手舞之家,手舞从这里随着传授佛教来到东方,远至佛教盛行的地区日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波里尼西亚;也可能从印度西移至古希腊,很可能传至更远的地区。”[1]29“手势”是手的姿态、状态;分单手势和双手势。每个手势都有特定的名称,每个手势相当于拼音语言文字中的一个字母,因此,每个手势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意思。但是通过单个的手势形态的变化或双手势的不同样态的组合就可表达不同的含义。就相当于拼音语言文字,就那么二三十个字母,却可以组合成丰富的词汇一样;也像音乐中的音符,就那么七个音符,却可以千变万化,创作出无数优美的旋律一样。仅单手势就有28种手势,双手一起可做出24种手势,单手势同双手势组合成的形状、样态形成丰富的表意符号,这就是“手语”。手语是印度各派宗教和古典舞蹈用来传情达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东方舞蹈的虚拟性开拓了象征和想象的空间。所谓的虚拟性,就是在特定的舞台或演出空间的情景中表现出多种不同时空中的动作情景。例如表现划船的舞蹈:排成两行的舞蹈者代表小船,三个领舞者代表划浆的水手,水手手中并没有实物的船浆,只是通过虚拟的划浆的动作来表现小船和水手同风浪搏斗的场景。虚拟性是古老的模仿性的歌舞、戏曲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根本是用虚拟性的模仿和再现性的动作,来唤起观赏者记忆中的各种生活印象。虚拟性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模仿。它“似是而非”,所模仿的动作处在“似与不似”之间。舞者通过虚拟的表现手法来充分调动观赏者的想象力和记忆力。古代歌舞、戏剧中演员所佩带的面具以及所表演的人物动作就是所扮演的人物身份的“虚拟”。模仿性舞蹈或戏曲动作本质上都是虚拟。东方戏曲和舞蹈中保留着大量的虚拟性动作。例如,在中国和日本的戏曲和舞蹈中,“舞蹈者也能单凭手中扇子来表现一切必须加以表现的东西。它可用以取代剑和矛,也可以给他们当朝圣进山的拐杖用。……舞蹈者把扇子挥向前,让扇子小心翼翼地向下滑,然后用一种激动的表情把扇子举至空中,在我们眼前便出现了一位钓鱼者;他们若温柔地把扇抱在怀里,便可看到抱着婴儿的慈父……”[1]193同样,中国戏曲和舞蹈中的每一种道具,都可以虚拟为各种各样的器物,表现各种各样的动作情景。如一条红绸,既可以横在肩上充当扁担,又可以当毛巾擦脸;既可以当拉车的绳索,又可以当作一条蛇来戏耍。人物站在一张方桌上,可视为站在城墙城门上;两张旗子中站一个人,可视作人物乘坐马车;舞台上几个人不断地跑来跳去,可视作是千军万马……
东方舞蹈的虚拟性特点,大大增强了舞蹈的想象的穿间,丰富了舞蹈的诗意和韵味,使东方舞蹈更加显得优美含蓄,情意绵绵。
四、东方舞蹈以性感而典雅的“扭姿”(“三道弯”)为美
东方舞蹈中最性感而典雅的女性的舞姿是“三道弯”,它集中体现了东方舞蹈的美学特色。所谓“三道弯”的舞姿是指在舞蹈动作中的头和胸、腰和臀、胯和腿以逆反向度呈S状的形态。
东方舞蹈文化的传统是“收缩型”舞蹈,它与西方“伸展型”舞蹈不同。东方“收缩型”舞蹈最重要的形体姿态是“拧扭式”舞蹈。什么是“拧扭式”舞蹈呢?根据世界著名的美国舞蹈理论家库尔特·萨克斯的说法:拧扭式舞蹈“是和我们早已谈论过的巫师的痉挛式舞蹈同出一辙。……拧扭式舞蹈的生理基础很可能是令人感到愉快的转动和全身的扭动。……动作几乎无例外地是跨前与退后的短步,站一脚,摆动,转动和收缩肌体等。”[1]32“在南亚,拧扭式舞蹈已进展到了更为严谨的艺术领域,舞者的四肢以一定的方式扭离关节。……跳舞者的双臂和双腿都要能弯曲到一定的角度,两片肩胛一起屈前或扳后,腹部收缩,全身处于‘扭曲姿态’。”[1]32
拧扭式舞蹈源远流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拧扭式舞蹈具有浓厚的生殖、生命崇拜的象征意味。拧扭式舞者的“臀部在弯曲着的腿上下左右摆动,……(他们)臀部做着狂热的、挑逗性感的动作。临结束时,其中一人扮演女角,表演了性爱情景,他们描摹得越淋漓尽致,旁观者的喝彩声越高。”[1]14肚皮舞通常指的是混合的扭胯动作。舞者胯部的扭动是肚皮舞最具典型的动态,但它不是单纯的扭胯,而是属于混合抽搐的扭胯动作。通常在节奏强拍时动胯,弱拍时则为臀部的颤抖,连带着头、肩、臂、腿、脚的配合动作无论弱拍连续出现多少次,其动律都不变。当舞到高潮时,舞者大幅度的扭动胯部,舌头在口中迅速横向摆动。
拧扭式舞蹈所象征的生殖、生命崇拜意识相联系,尤其是其中的“三道弯”的身体造型是对自然植物藤蔓生长样态的模仿,舞者通过模仿长势茂盛的花朵、植物和藤蔓,可以获得与植物同样的繁殖能力和生命力。世界著名的法国艺术史家雷奈·格鲁塞指出: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古典美学派别“所喜好的身体姿式,尤其女性的,则是‘三道弯式’——即头向右倾侧(女像),胸部则转向左方;同时,由于印度人偏好臀部向旁耸出的姿式,两腿遂又转至右方。男像则与此相反,即头向左侧等等。这种对模仿花朵及动物曲线的关心,和对上述‘相补式’的姿势的偏好……给印度美学典范注入了新的生命。”[6]
这就是东方舞蹈中“三道弯”舞姿的造型的双重象征含义。
“三道弯”是东方“扭拧式”舞蹈最典型的样式。东方舞蹈中有多种多样的“三道弯”姿态。如南亚的印度舞蹈、斯里兰卡舞蹈;西亚的阿拉伯舞蹈——尤其是自古以来就流行于埃及和阿拉伯的“肚皮舞”;又如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舞蹈中都具有丰富多彩的“三道弯”的舞蹈造型。
此外,自古以来,中国舞蹈就有多种多样的“三道弯”的造型。我们从文学和诗歌的记载中,在秦砖汉瓦、汉代砖画和敦煌乐舞中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三道弯”舞蹈的造型。现今,中国各地的民间舞蹈仍有多种舞姿的“三道弯”。例如,在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舞中,傣族、藏族舞蹈具有较强的“三道弯”特点,汉族民间舞中,胶州秧歌和安徽花鼓灯也具有三道弯的特征。傣族舞蹈包含有三种三道弯形态,即手臂的三道弯、躯体的三道弯和腿部的三道弯。手臂三道弯指“肩、肘、手腕”,躯体三道弯指“头、胯、膝”,腿部的三道弯指“髋、膝、脚腕”。藏族民间舞中的“谐”(青海玉树称为“依”),以轻踏、甩舞长袖、扭胯、转动胸腰等为动作特点。有胯和胸腰的动态即是三道弯的体现。
五、结 语
20世纪中叶以来,东方舞蹈在西方舞蹈,尤其是芭蕾舞原则的冲击和影响下,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日本、中国、韩国及东南亚等一些东方国家效仿西方芭蕾舞的科学化、技术化、规范化的训练和教学方法,不仅建立了芭蕾舞团体和学校,而且采用芭蕾舞的教学和训练方法培养民族、民间舞蹈演员,开始把西方舞蹈的元素引进并融入东方舞蹈之中;更主要的是把支撑芭蕾舞的文化基础——科学性、技术性、人工性、规范性引入东方舞蹈之中。东方舞蹈逐渐摆脱古老的、原生态的形式,舞蹈技术和表演水平、编创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东方舞蹈形态也出现了变化。尽管这一变化还在路上,但是东方舞蹈的美学特征依然会发出灿烂光芒。
[1] 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M].郭明达,译;恒思,校.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
[2] 彼得·伯克.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M].刘耀春,译;刘 君,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3]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卷[M].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 于 平.舞蹈形态学[M].北京:北京舞蹈学院内部教材,1998:138.
[5]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下)[M].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713.
[6] 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M].袁 音,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271.
(责任编辑 文 格)
J701;J709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09
2017-03-02
朱宇翔(1983-),女,湖北省武汉市人,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 邱紫华(1945-),男,重庆市人,华中师范大学东方美学与文化艺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西方美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