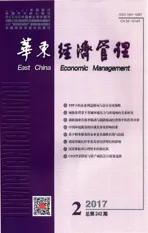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分析
——基于华为和吉利案例
2017-02-23申俊喜
申俊喜,陈 甜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分析
——基于华为和吉利案例
申俊喜,陈 甜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文章基于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受管制程度和国际化经验程度两个情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华为和吉利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指导。结果表明,当行业受管制程度较高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较低时,企业宜采取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当行业受管制程度较低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较高时,企业宜采取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当行业受管制程度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高或都较低时,企业宜采取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
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华为;吉利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促使我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产品的生命周期变短,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了其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全球化的要求,我国提出了“走出去”和创新驱动等发展战略,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向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以提高本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同时由于我国国内的创新环境还不够成熟,所提供的科技研发资源有限,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通过海外直接投资来有效利用国外的技术创新资源,获取技术溢出。根据商务部公布的对外投资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 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并且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企业以获得技术、品牌和市场份额为目的的海外并购项目数量占比增长到75%左右①,这说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增长、调结构、重质量的新阶段。然而,与此同时,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发布的报告称,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②,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依然严峻。可见,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是否能够有效识别各种进入模式的适用性,结合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正确选择进入模式,成为其能否成功获取技术从而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
众所周知,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受到企业自身条件和东道国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们[1-11]已经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吕萍和郭晨曦(2015)利用中国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OFDI的837家上市公司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个方面研究了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对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的影响机制[4]。Diego Quer等(2012)则通过分析2002-2009年139个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数据认为跨国公司的整体规模与其选择全资方式的股权结构模式负相关,即企业的整体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模式进入,而且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进入模式时也较少会考虑东道国因素[5]。与之相反,Kogut和Singh(1988)基于228个外国对美投资的数据实证得出东道国非正式制度文化因素对绿地投资、合资新建和跨国并购三种进入模式选择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6]。周经和刘厚俊(2015)也利用中国跨国企业近十年的OFDI数据实证探讨了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和人力资源距离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作用[7]。綦建红和杨丽(2014)则用KSI指数测度文化距离,基于82家中国大型企业267次OFDI数据实证研究了文化距离对OFDI进入模式的直接影响,得出结论文化距离通过母公司因素对进入模式的选择能够产生显著的间接传导作用,并且母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8]。同时,对于企业微观因素和东道国宏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也有不少学者(赵晶、王根蓓,2013[9];López-Duarte和Vidal-Suárez,2010[10];周经、蔡冬青,2014)[11]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合已有研究发现,影响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不胜枚举,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此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仍然有值得补充之处。其一,在研究对象方面,上述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关于整体OFDI进入模式的,而较少有关于更高层次的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的针对性研究,从而探究旨在获取技术的企业海外投资模式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和精准性程度不够。其二,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文献中大多数都是采用建立数理模型和计量统计来分析的,而对于典型海外OFDI企业的案例研究则较少。相比于大样本数据的数理模型和计量统计分析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如何”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具有信息获取更加丰富、详细与深入的特点,而且也能为其他类似案例提供易于理解的和生动的解释。同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翔实研究,研究者可以对现存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发展,还可以对某些现象、事物进行描述和探索(孙海法、朱莹楚,2004),从而能够更直观、更细致、更深入地探讨和理解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针对更为具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被管制程度和国际化经验程度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提出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为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进入模式选择提供指导。
二、情境因素对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
(一)行业被管制程度对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
企业所属行业的特性不同,在东道国的被管制程度也不同。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往往出于某些政治目的、保护本国的关键产业不受外国控制或扶持本国弱小新兴产业发展等原因,对国外跨国公司在投资进入时可能会采取某些管制措施,比如包括经济法律方面的限制、税收政策的管制、金融市场的资金管制以及当地人民的情感抵制等,这会导致某些国际化进入模式管理和运行的成本与风险增高,增加了企业获取技术的难度[12]。因此,如果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被管制程度较高,则企业能够选择最直接获取技术的跨国并购进入模式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并购东道国当地有重大影响力和关键效用的企业更是难上加难。而如果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被管制程度较低,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偏小,则其选择各种形式进入模式的自由度更大。
可见,行业被管制程度较高的企业面临着更多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管制和规范带来的压力和阻力,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所运行的成本和风险偏高,甚至于在某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明确禁止外国企业并购关系国家安全的本国重点企业,此时企业更偏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或合资模式进入;而行业被管制程度较低的企业面对的投资风险和管制规范压力偏小,可以选择更易获取技术的合资新建或跨国并购进入模式。
(二)国际化经验程度对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
在研究影响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众多微观因素中,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国际化经验是指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国际经营市场知识、国际先进技术知识、国际先进管理知识和实践、各国制度文化知识和投资信息等,具有海外经营的高管、普通员工的个体经验知识也包括在内(曾德明等,2013)[13],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学派认为企业国际化成长是自发和持续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所感知的经营不确定性是其在该国经营经验的减函数。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较高的企业对东道国的市场、法律、政策和文化等有较为深入透彻的了解,能够增强对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把握,提高对风险的掌控能力以及对外在环境变化的识别能力和适应能力[9],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从而可以驾驭各种形式的进入模式来获取技术溢出。而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较低的企业则对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缺乏敏感,应对风险的技术能力和经验知识储备不足,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较弱,从而影响战略决策的判断和制定。此外,由于国际化经验不足的企业正处于“体验式学习”的过程中,对制度的学习成本、信息的搜集成本和谈判的交易成本都相对更高一些[13]。
可见,国际化经验较为丰富的企业能够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能够更好地与东道国企业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因此选择进入模式形式的自由度较大,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新建或跨国并购的模式进入;而国际化经验较为不足的企业缺乏积极响应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对于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难度较大,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或合资模式进入市场。
(三)基于行业被管制程度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综合分析框架
在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充分考虑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技术寻求型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划分为以下四种情境:行业被管制程度较高而国际化经验程度较低;行业被管制程度和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高;行业被管制程度和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低;行业被管制程度低而国际化经验程度较高。
行业被管制程度较高而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较低时,企业面临更为严苛的准入制度,却又缺乏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和管理经验,对东道国相关的制度文化知识也了解不足,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更倾向于选择“试探性”的绿地投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不容易直接获取技术溢出,但是在准入门槛上更容易得到东道国的政治许可,并且管理方式的自主性强、容易操作,可以主动监测当地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市场动态从而进行技术追踪活动,通过搜集和传递信息以及充分利用当地的专业技术人才、科技研发设施等研发资源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在行业被管制程度较高而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较低的情境下,企业宜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
行业被管制程度较高且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也较高时,虽然投资进入门槛较高,但企业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国际管理技术人才,对东道国相关的制度文化等知识也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已经具备了规避和处理政治风险及国际合作风险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和应对东道国的管制举措,合资新建便成为企业获取技术溢出最有效的方式。建立合资企业可以在两国企业间搭起相互充分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的桥梁,使得企业能够充分学习和利用东道国合作伙伴的人才资源、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因此,在行业被管制程度和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高的情境下,企业宜选择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
行业被管制程度较低,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也较低时,跨国公司的投资进入门槛较低,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虽然合资新建也会面临合作伙伴存在技术保密的防范风险,但它相比于绿地投资模式来说,技术溢出的获取更为方便直接。而且相比于跨国并购模式来说,合资对企业自身条件要求略为宽松,而且还能够通过向合作伙伴交流学习以实现自身的国际化经验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行业被管制程度和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低的情境下,企业宜选择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
行业被管制程度较低但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较高时,企业跨国经营经验充足,跨国并购是最为理想的进入模式。跨国并购是获取技术知识最直接的方式,能够有效规避东道国的技术寻求壁垒,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获得被并购企业的科技研发设施、专业人才及技术。但由于跨国并购涉及不同制度文化的两个企业的直接融合,因此对企业克服和处理双方显性和隐性差异的能力和国际化管理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行业被管制程度较低但企业的国际化经验程度较高的情境下,企业宜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综上所述,四种情境下的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见图1所示。

图1 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
三、技术寻求型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案例研究
根据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的企业海外投资实践,本文将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进入模式分为绿地投资、合资新建和跨国并购三种模式。
(一)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被管制程度较高的情境下进入模式的选择
行业被管制程度较高情境下,东道国政府可能为了保障自身国家安全和保护弱小产业发展对投资企业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竭力避免外国企业并购本国关键企业。比如,华为所属的基础性和支柱性的通信设备行业是兼具商业利益、技术安全和政治效应的特殊高科技行业,对国家经济和信息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受政府管制的政治阻力极大,行业的准入制度更为严苛。从北美市场对外资通信设备商设置很高的认证门槛,思科起诉华为侵权后美国法院发布初步禁止令,与贝恩资本联手收购3Com被委员会否决,对三叶系统公司专利资产并购以可能存在网络间谍活动为由遭拒,到美国政府以安全为由强制干预华为在当地的其他并购活动等,华为的运营商网络业务在北美始终难有斩获[14]。面对这种严控管制的情况,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和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但是,企业在进入时具体选择何种模式,还取决于企业自身所处阶段的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主要从事通信网络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固定网、移动网、数据通信网和增值业务领域的网络解决方案,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还未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已连续五年进入世界500强[15]。
华为自1996年正式踏入海外市场拓展的征途,采取“稳中求胜”的战略,首先有意避开管制程度较强的发达国家,以低价战略迅速打入正在热切寻求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扩大海外规模,积累国际经验,为之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寻找机会并积蓄力量。1997年华为成功获得孟加拉电信公司的投标项目,1998年与巴基斯坦电信公司正式签约,1999年开始大规模进入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区域,2000年成功进入俄罗斯和印度市场。到2000年底,华为的海外市场销售额达到1亿美元[14-15]。在逐步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并积累了一定的国际化经验后,华为终于将目光盯向了通信设备市场占全球80%的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由于还处于国际化经验的初始积累阶段,华为还缺乏国际关键技术和管理人才,全球化经营经验和管理经验也相对不足,对东道国当地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还未能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异国人员间的沟通还相对困难,所以华为选择以独资新建的进入模式在发达国家和技术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技术溢出。华为的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情况见表1。1999年,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建立研发中心,2000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建立研发中心,截止到2001年,华为已经在美国建立了四个研发机构,2002年的海外市场销售额已经达到5.52亿美元,比两年前翻了五番多,同年专利申请量增长率也达到136%。独资新建研发中心是一种“养精蓄锐”的方式,相对更容易取得东道国的投资许可,并且自主性强,可以继续部分沿用国内的管理体制,管理较为容易,风险较小,使华为不仅可以间接追踪技术前沿和学习当地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还可以渐进式积累丰富的国际经营管理的经验,学习现代管理方法,改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培养一大批国际化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之后深入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表1 华为的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在具备了丰富的国际化经验、本土化适应力和全球化人才储备后,华为开始尝试更易获取技术的合资新建模式。2003年开始,华为与美国3Com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专注于企业数据网络解决方案的研究,2004年与德国西门子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开发TD-SCDMA解决方案,到2005年华为的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2007年与德国赛门铁克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开发存储和安全产品与解决方案,同年与英国Global Marine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提供海缆端到端网络解决方案,在2007年底成为欧洲所有顶级运营商的合作伙伴。2008年,华为全年共递交1 737件PCT专利申请,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在当年专利申请公司(人)排名榜上排名第一,LTE专利数占全球10%以上,移动设备市场领域排名全球第三②。合资新建的技术获取模式可以使华为规避东道国的某些限制措施,缓和东道国人民的抵制情绪,与合作伙伴共享知识技术进步,形成优势互补的共赢局面。比如华为与3Com的合资可以使3Com直接利用华为在国内的销售渠道和成本优势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可以使华为直接利用3Com的国际品牌和地位继续拓展海外市场,不仅如此,除技术与市场的合作外,在思科诉讼华为案例中3Com也为华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与支持,有效防范和化解了竞争风险。华为利用在世界各地设立的23个研究院,以及与领先运营商成立的36个联合创新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创新合作,推动技术进步。可以看出,华为与发达国家技术领头企业的合资合作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其国际影响力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华为每年至少将销售收入的10%投入科技创新与研发,在近17万的华为人中,超过45%的员工从事创新、研究与开发工作。2013年,加速成长的华为终于超越行业领头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讯厂商。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华为累积共获得专利授权50 377件,累计申请中国专利52 550件,累计申请外国专利30 613件。其中,90%以上专利为发明专利③。
(二)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被管制程度较低的情景下进入模式的选择
行业被管制程度较低情境下,东道国政府可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对投资企业的限制程度不大,甚至还会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外资企业以各类形式进行投资。比如,吉利所属的汽车行业涉及的国家安全和政治目的程度微弱,同时又能解决东道国当地人民的就业问题,所以汽车行业所受东道国的政治管制较少,在很多国家并无准入限制,与当地制造商享有平等待遇,甚至有时政府还会提供低息贷款、削减税收等优惠政策条件。因此,技术寻求型企业选择对外投资模式的自由度相对更宽泛一点,在此情形下,企业通常会选择较易获取技术溢出的进入模式,如合资新建和跨国并购,但这依然要取决于企业自身所处阶段的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吉利”)始建于1986年,1997年进入汽车行业,旗下拥有吉利汽车、沃尔沃汽车、伦敦出租车等品牌,连续四年进入世界500强,连续十二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连续九年进入中国汽车行业十强,是国家“创新型企业”和“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④。
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吉利国际化经营人才和管理经验不足,而东道国对汽车行业的外资进入管制宽松甚至有所鼓励却使得吉利选择难度较小的合资新建模式来获取技术溢出成为可能。2002年,吉利与韩国大宇国际株式会社技术合作开发CK-1项目,掌握了结构设计与工艺设计同步进行的“同步工程”技术。同年12月,吉利与曾为法拉利和奔驰设计过车型的意大利汽车项目集团马吉奥拉公司正式签约,合资设计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家用轿车系列。2003年6月,与欧洲著名车身设计公司德国吕克公司合资开发新车型。8月,第一批吉利轿车出口海外,实现零的突破。2005年,与香港工业支援机构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资合作开发中高档新型轿车体系,2007年,合作研发可使用石油或汽油的TX4发动机及燃料供应系统。同年,吉利与海域印尼PTIGC公司合资开发自由舰CKD组装项目。2009年,与中国台湾裕隆汽车合资开发锂电池电动车[16-18]。与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合资使吉利的国际化步伐迅速加快,通过与特定技术领先的知名企业的合资开发,利用合作伙伴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吉利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显著的互补和提高,不断自主研发出新车型,其技术和产品领先于国内同级其他汽车企业。
随着国际化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吉利的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也不断加强,成功发展了一批可进行国际化交流和运作的人才队伍,增强了处理并购后文化整合的能力。为更为直接地获取技术溢出,吉利开始尝试采用最快速直接的跨国并购形式。2009年3月,吉利汽车100%收购了福特、克莱斯勒、韩国双龙等公司的长期动力传动系统供应商、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箱公司澳大利亚DSI自动变速器公司,使之迅速获得了DIS的大扭矩自动变速箱技术,与其已经拥有的4速自动变速箱技术形成互补,增强了吉利掌握中高档汽车的核心技术能力[16]。2010年8月,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以及欧盟向吉利发放低息贷款等优惠条件下,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瑞典高端汽车品牌沃尔沃的全部股权,获得包括沃尔沃品牌商标,整车厂、发动机、混合动力等方面的4 000多项技术专利在内的无形资产以及沃尔沃大量包括安全和环保技术的知识产权使用权,更为重要的是,吉利收获了包括研发、管理、财务和市场等方面的4 000多名高素质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这是此次并购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1]。然而,“小伙娶贵妇”、“小蛇吞大象”型的并购获得成功,与吉利拥有很强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无关系。七七定律指出,在跨国并购中,有七成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而其中的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问题,如上汽收购韩国双龙(2004),TCL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2004)等,均因为并购后文化整合处理不当而以失败告终。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已有83年历史的瑞典高档品牌沃尔沃拥有成熟典型的西方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而当时仅拥有13年历史的中低档品牌的年轻吉利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具有典型中国企业的文化特征和管理方式[18]。并购后两种差异巨大的文化必然会出现交流和碰撞,这是吉利面临的最大挑战。对此,吉利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一是选派技术与管理人员到瑞典进行学习和交流以获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知识,同时邀请沃尔沃方面的相关人员来中国进行培训和指导以加强相互间的沟通、理解与合作,实施人才交流,减少人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增进双方的情谊;二是实行“沃人治沃”的管理理念,在品牌管理、产品研发与市场布局等方面给予沃尔沃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薛琴、申俊喜,2015[19]),声明吉利和沃尔沃并非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的兄弟关系,使沃尔沃的核心技术管理人才都得以保留;三是成立“沃尔沃—吉利对话和合作委员会”来协调双方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企业管理风格和未来战略愿景的差异,使并购后的高层能更好融合。由此可见,吉利拥有大量的国际化管理人才和丰富的国际化管理经验是此次并购成功的必要条件。吉利的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情况见表2所列。

表2 吉利的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四、结论
本文基于企业所属行业在东道国的受管制程度和国际化经验程度两个情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华为和吉利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决策矩阵。研究结果表明,当行业受管制程度较高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较低时,企业宜采取绿地投资的进入模式;当行业受管制程度较低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较高时,企业宜采取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当行业受管制程度和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都较高或都较低时,企业宜采取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方面,技术寻求型OFDI的企业首先应该充分了解本行业特性,了解其所属行业在投资东道国的受管制程度,不仅包括是否存在经济法律方面的限制、税收政策的管制和金融市场的资金管制等正式制度管制,也包括是否存在当地人民的情感抵制等非正式制度管制,企业要根据其技术获取程度的要求和自身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如国际化经验丰富程度)巧妙避开和化解矛盾冲突,选择适宜的进入模式。同时,企业要在“体验式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自身的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知识,培养全球化管理技术人才,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跨文化整合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继续采取税收激励和政策支持等措施,积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全球科技人才资源获取技术进步。同时,政府也应该做到扩大与加强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东道国政府的摩擦冲突,努力谈判以降低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入门槛。此外,政府也要利用其国际政治优势搜集并公开世界各国的各类信息,减少或避免企业进行重复搜寻,降低企业获取东道国相关制度的信息成本,为技术寻求型企业创建全面服务支持的平台。
注释:
①波士顿咨询公司“迎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新时代”(www.bcg. com.cn),2015-09-24。
②资料来源于华为公司介绍(http://www.huawei.com/cn/abouthuawei/milestone)。
③资料来源于华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④资料来源于吉利汽车公司介绍(http://www.geely.com/intro⁃duce/intro/index.html)。
[1]Bo Bernhard Nielsen,Sabina Nielsen.The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The Choice of Foreign Entry Mode[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1,46(2):185-193.
[2]Aekerman Abraham.The Effect of the Target Country’s Le⁃gal Environment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Working Paper,2005,3:1-26.
[3]Andrea Martinez-Noya,Esteban Garcia-Canal,Mauro F. Guillen.International R&D Service Outsourcing by Technol⁃ogy-intensive Firms:Whether and wher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12,3:18-37.
[4]吕萍,郭晨曦.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J].财经研究,2015(3):88-99.
[5]Diego Quer,Enrique Claver,Laura Rienda.Chinese Multi⁃nationals and Entry Mode Choice:Institutional,Transac⁃tion and Firm-Specific Factors[J].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2012(6):1-24.
[6]Bruce Kogut,Harbir Sing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3):411-432.
[7]周经,刘厚俊.制度距离、人力资源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J].财贸经济,2015(1):73-79.
[8]綦建红、杨丽,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基于大型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2014(6):55-61.
[9]赵晶,王根蓓.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2):100-112.
[10]Cristina López-Duarte,Marta M.Vidal-Suárez.External Uncertainty and Entry Mode Choice:Cultural Distance,Po⁃litical Risk and Language Diversity[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0,19:575-588.
[11]周经,蔡冬青.企业微观特征、东道国因素与中国OFDI模式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14(2):124-134.
[12]孙海法,朱莹楚。案例研究法的理论与应用[J].科学管理研究,2004(1):116-120.
[13]曾德明,张磊生,禹献云,等.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国际化进入模式选择研究[J].软科学,2013(10):25-28.
[14]许晖,万益迁,裴德贵.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风险感知与防范研究——以华为公司为例[J].管理世界,2008(4):140-149.
[15]谢文新,严永怡.华为公司国际化战略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0(9):72-77.
[16]孙林杰,康荣,王静静.开放式创新视域下民营企业技术能力的发展演进[J].科学学研究,2016(2):253-259.
[17]冉龙,陈晓玲.协同创新与后发企业动态能力的演化——吉利汽车1997-2011年纵向案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2(2):201-206.
[18]于洋,李壮壮,杨雯月,等.并购沃尔沃对吉利竞争力的影响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4):45-47.
[19]薛琴,申俊喜.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人力资源融合吉利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5(11):173-179.
An Analysis on the Entry Mode Choice of Chinese Firms for Technology-sourcing OFDI—Based on the Cases of Huawei and Geely
SHEN Jun-xi,CHEN Tian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comprehensive role in two situational factors—the industry regula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firm’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combined wit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two typical cases of Huawei and Gee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ecision matrix on the selection of entry mode for Chinese firms of technology-sourcing OFDI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decisions.The results shows that when the industry regulation is high bu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s low,the entry mode of greenfield investment should be chosen.Conversely,when the industry regulation is low bu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s high,firms should choose the entry mode of cross-border M&A.However,when both the industry reg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re high or low,the entry mode of joint venture is a better choice.
technology-sourcing OFDI;entry mode;Huawei;Geely
F272.1;F276
A
1007-5097(2017)02-0178-07
[责任编辑:张青]
10.3969/j.issn.1007-5097.2017.02.024
2016-12-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JY084);江苏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2012SJB790036);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计划(15CX_003G);江苏省创新经济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申俊喜(1969-),江苏东台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陈甜(1991-),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