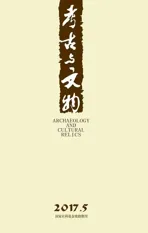释“”*
2017-01-28单育辰
单育辰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金文中有个常见字,字形及辞例如下(字形下或代称A):
(1)《集成》2331: 父作姜懿母A鼎。
(2)《集成》2692:戴叔朕自作A鼎。
(3)《集成》3766.1:伯几父作A簋。
(4)《集成》3886:散车父作 姞A簋。
(5)《集成》4441.2:鲁司徒仲齐肇作皇
考伯走父A盨簋。
(6)《集成》4596:作皇考献叔A盘。
(7)《集成》10305:燕侯作A盂。
(8)《集成》10338:黄大子伯克作其A盆。
(9)《集成》3939:禾肇作皇母懿恭孟姬A彝。
(10)《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新收》1452):丙公献王A器,休亡谴。
(11)《集成》4623:邾大宰朴子 铸其A(簠),曰:余 (毕)恭孔惠,其眉寿以A,万年无期。
(13)《集成》4161:伯康作宝簋,用飨朋友,用A王父王母。(A下加皿,可参《集成》4160同铭铭文)
(14)《集成》3827:敔作宝簋,用A厥孙子,厥丕吉其祼。
可看出,A可做食器的修饰语,如在(1)-(11)中,A后接鼎、簋、簠、盨、盘、盂、盆;其后也可接食器的统称如彝、器;后面还能连加上两个食器,如(5)的“盨簋”。同时,A还可做动词,从(11)-(14)可以看出,A是用为飨一类的意思的,如(13)“用飨朋友,用A王父王母。”“飨”、“A”互文,即是明证。
不过,A是什么意思,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好的说法。旧多从《说文》释为“”,训为“滫饭也”[1],但“滫饭”是蒸米的意思[2],而“鼎”、“盘”、“盂”、“盆”无以用来蒸米,并且用“滫饭”的意思也无法解释(11)-(14)的辞例。
为了分析其构形以便做新的释读,我们暂且把这个字放到一边,先看看和A具有相同偏旁的字。
第一个字用为曹国的“曹”,第二个字是“奏”,第三个字是“拜”,这些都是没有疑义的。
第四个字是近来才被考释出来的字,其考释过程如下:
郭店《缁衣》简18+19: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18】,亦不我力。”
从“ ”之字在《说文》中其出现了多次(按,小篆“ ”旁并未写得完全一样):
由上可知,《说文》中这些从“ ”的形体与古文字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所以《说文》“”的来源一定是古文字中的“”。
金文中还有一个字,作下形(下或代称B),是在“枣”形加两“屮”:
它们主要做“较”或“鞃”的修饰词,其辞例为:
《集成》4318.2:金车:B较、朱虢鞃、靳、虎幂熏里、右厄、画 、画 、金甬。
《集成》9898:金车:B鞃朱虢、靳、虎幂熏里、B较、画 、金甬。
《集成》2841:金车:B较、朱乱鞃、靳、虎幎纁里、右轭、画 、画 、金甬、错衡、金踵、金豙(轙)[10]、约軧、金簟笰、鱼服。
《集成》4302:金车:B较、B鞃朱虢、靳、虎幎朱里、金甬、画 、金轭、画 。
B字旧多释为“贲”、“雕”等[11],孟蓬生认为它们也从“”,而把B读为幽部的“髹”,我们认为孟先生所考释很可能是正确的。同时,也有些学者释之为“漆”[12],我们认为也可能是正确的。“髹”和“漆”可能是一字分化,如在秦简中,“ ”做“”(睡虎地《效律》四六)、“”(睡虎地《秦律杂抄》二一),即是“髹”与“桼(漆)”的合体状态[13]。在更早时期读为晓纽幽部的“髹”,后来大概由于某些原因,演变为清母质部的“漆”音了。《周礼·春官·巾车》:“駹车,雚蔽,然,髤饰。”郑注:“故书駹作龙,为。杜子春云:‘龙读为駹。 读为桼垸之桼,直谓髤桼也。’玄谓:駹车边侧有漆饰也。”《周礼·春官·笙师》“髤”《释文》读为“香牛反,或七利反”,这都是幽部的“髹(髤)”向质部的“漆”转化之证。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些字形,其所从的屮形与U形可能取像割划漆树的割口,现今取漆割口仍与这些形状很相类,不过金文中的“”、“”是以“枣”为声符的。目前所知最早的“桼”见于春秋早期的《曾伯 簠》(《集成》4631、《集成》4632),作“”、“”形(上雨下桼),所从之“桼”已有变化。秦文字中的“漆”作“”(《集成》11405.1)、(《新收》986)等形,则与西周金文的“”较一致,但省去屮形(或U形)又加了水旁而已。
在金文中还有B与衣服连言的情况,似乎有读为“裘”的可能。
《集成》9456:矩又取赤虎两、麀B两、B韐一。
《集成》4268:赐汝朱黄(衡)[14]、B衬、玄衣黹纯。
《集成》4260:赐汝B、朱黄(衡)、玄衣黹纯。
《集成》9722:赐几父幵B六。
《文物》1998年第4期(《新收》62):赠匍于柬:麀B韦两、赤金一钧。
与上面字形相近的还有一个字,多用在甲骨文及西周早期金文中(下或代称C):
C以前多释为“求”,后来陈汉平、冀小军发表文章,认为甲骨文已经出现了“”(字形出自《合集》2119)这个“求”字[15],所以C再释为“求”就不合理了,他们认为C即《说文》的“ ”字,从“夲”得声,读为“祷”[16]。经上面论证,我们可以知道,C其实就是“枣”的本形,验之以金文、郭店《缁衣》中的“”、“”与“仇”、“逑”相通,即可知C以读为“求”更直截,它和甲骨文中的“”字形不同,主要是来源不同,但都可以用为“求”[17]。 不过,陈、冀二先生之说也不能算错,因为上文已经说过,《说文》的“”本来就从“枣”演变而来,并且,“求”、“祷”音义皆近,二字本出一源[18]。我们也不能否认,C或有用为“祷”的情况的存在。
《集成》550:仲姞作羞鬲。
《集成》581:郑井叔蒦父作羞鬲。
《集成》2443:伯氏作 (曹)氏羞鼎。
《文物》1994年第8期(《新收》889):杨姞作羞醴壶。
在金文中,同一含义的词用不同的字表示是很常见的,这不能成为否认“”可读为“羞”的理由。
《尚书·酒诰》: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
《国语·楚语下》: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仪礼·有司》: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妇,内羞在右,庶羞在左。……其荐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傧礼。……卒,乃羞于宾、兄弟、内宾及私人,辩。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战国文字里,各国“枣”字的写法已与甲骨文及西周金文的“枣”有着不小的差别,但在秦系文字里,“枣”的这种早期写法一直存在,如《石鼓文·銮车》:“□□銮车,真□。”(因残缺过甚,“”含义无法解读,不知与金文的“逑即”有无关系[21]。)睡虎地《日书甲种》六○背贰+六一背贰:“人无故而发挢若虫及须眉,是是恙气处之,乃煮【六○背贰】屦以纸,即止矣。”《说文》系统中的“()”正与它们一脉相承。
[1]参看:a.周法高,张日升,徐芷仪,林洁明.金文诂林[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4:3358-3364.b.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9:457-476.
[3]陈剑.据郭店简释读金文之一例[C]//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378-396.又,陈先生亦言:“‘枣’其实也应该是由‘’分化出的一个字。”
[4]a.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4.b.黄德宽,徐在国.郭店楚简文字考释[C]// [1]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98-111.c.颜世铉.郭店楚简浅释[C]//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379-396.
[5]刘钊.释甲骨文中的“秉棘”[C]//书馨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2-57.
[7]参看a.李家浩.楚简所记楚人祖先“ (鬻)熊”与“穴熊”为一人说——兼说上古音幽部与微、文二部音转[J].文史2010(3):5-44.b.史杰鹏.由郭店《老子》的几条简文谈幽、物相通现象及相问题[C]// 简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7.c.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9:473-474.
[8]“古代玛雅人所举行的自我献祭仪式中,献祭鲜血的仪式可以说无处不在。”古玛雅人常在手掌、双颊、嘴唇、舌头和阴茎上放血,其工具有黄貂鱼脊骨、黑曜石小刀、骨椎、带刺的绳子、草弦、草片等。参看[美]林恩·V.福斯特.探寻玛雅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60-265.环太平洋地区先民的生活祭祀习俗极为相似,可相模拟。
[10]“轙”从吴红松释,参吴红松.西周金文车饰二考[J].中原文物,2008(1):85-86.
[11]参看a.周法高,张日升,徐芷仪,林洁明.金文诂林[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4:6127-6153.b.冀小军.说甲骨金文中表祈求义的字——兼谈 字在金文车饰名称中的用法[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1):35-44.
[12]张亚初,姚孝遂,刘桓诸先生已把此字释为“漆”,参看a.张亚初.古文字分类考释论稿[C]// 古文字研究(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242.b.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76-1477.c.刘桓.甲骨征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398-403.
[14]“衡”从唐兰释,参看唐兰.唐兰先生金文论集[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86-93.
[15]参看裘锡圭.古文字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2:59-69.
[16]a.陈汉平.屠龙绝绪[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52-56.b.同[11]b:35-44.
[17]具体论证可参看a.同[4]a:76-77.b.孟蓬生.释“”[C]// 古文字研究(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67-272.
[19]“奏”、“拜”二字是会意字,是例外。
[20]“羞”字含义参看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04-1805.
[21]董珊.石鼓文考证[C]//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