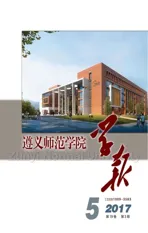笼络与控制: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建立及首次朝觐
2017-01-28邹建达杨晓燕
邹建达,杨晓燕
(1.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2.云南警官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笼络与控制: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建立及首次朝觐
邹建达1,杨晓燕2
(1.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2.云南警官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金川之役”后,为确保包括大、小金川在内的川西北土司地区的长治久安,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将之前成功施行于内外蒙古和回部王公的“年班制度”用于川西北土司,仿照回部年班之例建立起川西北土司的“年班制度”,使得川西北土司成为西南众多土司中唯一享受朝觐殊荣者。而川西北土司的首次朝觐,人数之多,在京时间之长,接待规格之高,参与活动之丰富,获得赏赐之丰厚,都是极其罕见的。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建立和首次成功朝觐,既是清廷对在征剿两金川战争中支持清军各土司的奖励,并藉此加以笼络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各土司实施控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年班制度”的实施,对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川西北;土司;清高宗;年班制度;朝觐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金川之役”,以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投降而告结束。为确保包括大、小金川在内的川西北土司藏区的长治久安,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其中仿照回部年班之例所建立的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以及各土司的首次成功朝觐,既是清廷对在征剿两金川战争中支持清军的川西北各土司的奖励,并藉此加以笼络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各土司实施控制的重要制度安排。之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均失之于简,未能深入。①相关研究,参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等等。本文通过对档案史料的细致梳理,对此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清廷建立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情形,并透过对首次成功朝觐的揭示,能更深刻地理解清廷为控制该地土司以及为保持该地区长久稳定所做出的努力。
一、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确立
何谓“年班”?《大清会典》记为:“凡朝正于京师,内扎萨克王以下各以其班至,曰‘年班’。”①嘉庆《大清会典》卷68《理藩院·王会清吏司》。《中国历史大辞典》则解释为:“清制,蒙古各王公、首领及回部伯克、四川土司、蒙藏喇嘛等,各按人数多寡编订若干班次,每年各以一班于年节时轮流进京朝觐,称为‘年班’。”[1]P1046戴逸则根据实际运作中朝觐对象身体情况和觐见地点的不同,分出“年班”和“围班”:“凡少数民族的上层,已出痘症、不怕染病者,定期轮番到北京朝觐皇帝,叫做‘年班’。凡未出过痘症,到北京因气候与水土关系,易染天花,因此不宜进京,则轮番到木兰围场,随同皇帝打猎,在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叫‘围班’。”[2]212赵云田则根据年班制度实际运作情形,做了更为细致的解释:“有清一代,居住在我国北方及西北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王公以及四川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每当旧历年前,多要前来清王朝宫廷觐见皇帝,瞻仰‘圣颜’。他们轮班来朝,年年如此,这就是清代的‘年班’制度。”[3]
而土司朝贡,在明代曾施行过,对此,明政府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湖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腹里土官,遇三年朝觐,差人进贡一次,俱本布政司给文起送,限本年十二月终到京庆贺,限圣节以前谢恩,无长期,贡物不等。”②(明)申时行《明会典》卷108《朝贡四·土官》,中华书局,1989年。“年班制度”以朝觐为主,旨在建立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之间的联系。而“朝贡制度”则以贡赋为主,除加强双方的联系外,双方的经济交往也是一大考虑因素。但土司进京朝贡,给朝廷和土司都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因此入清以后,于顺治十七年(1660),云贵总督赵廷臣上奏“请停边贡,以省解送之”③民国《贵州通志·食货志·土贡附言》,贵阳书局,1934年铅印本。,即停止了土司进京朝贡,土司将贡品交到省里,由各省布政使司统一上交朝廷。此外,在明代实行的土司袭替“亦必亲身赴阙受职”的规定,也于康熙十一年(1672)停止。是年,清廷规定:“土官袭职,停其亲身赴京。”④《新纂云南通志》卷7,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春龙点校本。此后,土司再难有机会进京觐见皇帝。
作为笼络和抚绥少数民族上层的一项重要举措,清代年班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施行的对象也逐步扩展。清代的年班制度始于顺治六年(1649),是年开始,清廷准蒙古王公进京朝觐,并逐步规定了朝觐的时间和班次。此项制度开始仅施行于漠南蒙古各部,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清廷将此制度推行到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并设有蒙古地区的喇嘛年班。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后,又将年班制度推行到回部,将回部王公伯克分为六班,一年一班,轮流到京朝觐。⑤《钦定回疆则例》卷3。
将年班制度推行于土司地区,则是在“金川之役”结束前后,且一直仅限于川西北土司。还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第二次征剿金川的战争已进行三年有余,清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逐步取得优势,战争可望结束的时候,清高宗就已开始筹划善后事宜。他指示金川前线的统帅、定边将军阿桂:“欲俟两金川平定后,令各土司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入觐,使其扩充知识,得见天朝礼法。”⑥《清高宗实录》卷963,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己巳。首次提出将川西北土司纳入年班体制。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当清军攻下大金川土司的第一大官寨勒乌围,开始围攻其最后一个据点刮耳崖官寨,即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时,清高宗谕军机大臣,再次提出筹划善后事宜设想,内容也涉及土司入觐,甚至虑及细节和展望取得的效果:“至善后事宜,亦应豫为筹及……至于各土司,经此番辑靖之后,务须使之怀德慑威,上下维系。所有各土司,应令将军、总督一体管辖,在内属之理藩院,方为妥协……至阿桂,于扫穴擒渠之后,即应振旅还朝……并须酌带土司数人来朝,令其瞻仰天朝礼法,承受恩典,将来即照新疆年班之例,轮流入觐。除巴旺、梭磨现系土妇,不便轮班外,此次着先带绰斯甲布土司雍中旺尔结、布拉克底土司阿多、沃克什土司雅布泰随同来京,事毕再令回巢。伊等共相传播,久之,必以入觐受恩为荣,亦如准部之永承恩泽也。”①《清高宗实录》卷898,乾隆四十年八月癸卯。
首次进京朝觐,清廷之所以选择上述三土司前往,是因为有功于清廷的巴旺、梭磨两土司系土妇管理,不便进京朝覲,而绰斯甲布土司雍中旺尔结曾经临阵督兵,布拉克底土司和沃克什土司也有功于清廷,沃克什土舍雅满塔尔及布拉克底头人俱属奋勇着绩,上述三人均被列入紫光阁功臣像后五十功臣之内。②(清)阿桂等撰《平定两金川方略》卷101,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61册。除上述三土司及巴旺、梭磨土司外,明正、木坪、瓦寺等土司也随清军从征有功,与清廷的联系也相对紧密,因其靠近內地,暂未列入。
之后,清高宗又考虑到“该土司等从未进京,恐其见将军等掣此数人入朝,虑有他意,心生畏惧”,要求阿桂将明正土司和瓦寺土司也一并随同带至京城,因为“明正土司于内地礼仪最为相习,向为各土司总领;而瓦寺土司亦于内地为近,伊等若闻准其来京觐谒,必皆欣然乐从。……绰斯甲布等见有明正、瓦寺土司同来,自必心安意得,对仪节亦可视明正等为效法”③《清高宗实录》卷989,乾隆四十年八月乙巳。。由此可见,清高宗对建立川西北土司入觐制度的重视及对各土司首次入觐效果的期许。阿桂接旨后奏称:“瓦寺土司故后,伊应袭之子年幼,尚未袭封,布拉克底土司阿多,本系跛足,令人背负而行,自不能远赴京师。至番人,有生身、熟身之分,与蒙古无异,未经出痘者心多畏惧。请令明正、沃克什等先来。此后有愿输忱瞻觐者,再行办理。”④《清高宗实录》卷991,乾隆四十年九月戊辰。清高宗命将阿桂所奏交军机大臣讨论,经讨论后,乾隆四十年十月,军机大臣议奏:“边外各土司,令仿照回部伯克之例轮流入觐,以理藩院为之典属,俾扩充知识,以革其犷悍之风。据阿桂奏,布拉克底土司腿患瘫疾,巴旺子幼未袭,系土妇管理,不能进京外,其木坪、瓦寺、明正、沃克什各土司,率皆倾心向化,恳请入觐。应同绰斯甲布土司,均令将军阿桂于凯旋时先行率带来京,共与盛典。其余各土司,仍令酌量远近,定以年限,轮流入觐。”⑤《清高宗实录》卷994,乾隆四十年闰十月辛亥。清高宗特谕:“此亦特使伊等仰觐天朝礼法,以悛改伊等狡性之至意!其众土司等所处地方远近,酌量派定年班,着其轮班来京瞻仰。”但考虑到土司与蒙古各部、回部的体制并不完全一致,仍有所区别。因此,理藩院奏称,各土司番子等承袭,原归兵部承办,此制行之久远,不便更易。理藩院则专办土司纳贡,并请圣安,并年班来京瞻仰等事。并称土司年班朝觐既拟定照回部之例一体办理,理藩院也不再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土司年班朝觐事宜,而交由管理回部年班朝觐的徕远司一并管理,每年务必于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到京。土司来京,必须预为奏闻。未到之先,由该地方报部,所经过地方,官员将伊等照料,由驿遣发至京,俟年节后,仍由驿遣回原处。⑥《金川案》(亨)10《理藩院咨复有关金川土司进京朝觐事宜》。
至此,清廷明确了将川西北土司年班朝觐纳入理藩院管理,并规定了各项制度内容,其年班制度得以正式确立。其后,清廷开始着手筹划和安排川省土司首次朝觐事宜。
二、首次朝觐的筹划和安排
川西北土司首次进京朝觐,并未按照清高宗之前要求的随阿桂振旅还朝时一同前往。且如何排定班次,此时也仍未确定。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在接受大金川土司索诺木的投降,金川战争结束时,阿桂等奏称:“查木坪、沃克什、党坝等各土司、土舍,均已束装预备赴京,绰斯甲布、三杂谷、布拉克底、巴旺,亦遣土舍、头人随往。但番人深畏内地炎热,若令随同官兵于四月望前抵京,其归途正当五六月,倘有事故,转不免指为畏途。应请令至十一月内,本省提督派出谙练将领带领,于年前至京。彼时正直入觐之各蒙古及土尔扈特王公、扎萨克并回城大小伯克等俱集京师,在各土司等,见王会辐辏,既益生其震迭,而轮班之王公、伯克等亦知无远不服之盛。”清高宗认为阿桂等“所见甚是”,谕令军机大臣:“其应行入觐之土司,统俟阿桂办理善后事宜时,酌定如何分班,照回部轮流入觐之例,与外藩等同与朝正。仍知会沿途督抚一体照料。”⑦《清高宗实录》卷1002,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癸卯。
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清廷仿照第一次金川战役结束后的做法,用清、汉、西番三种字体缮写敕谕一道颁发给川省土司,其中有再次重申对川省土司施行年班制度,藉此以奖赏各土司的内容:“尔土司等年来出力随征,共效恭顺,甚属可嘉,已节次加恩奖赏,并命照回部之例轮班入觐。除土妇及土司中之未曾出痘不能至内地者毋庸轮班外,其余土司、头目,俱按应行入觐之期,令于冬间,由将军、总督、提督等照料进京,俾之随班朝贺,瞻仰受恩。尔等并得身受宠荣,增长闻见,岂非尔等之大幸欤?”①《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为明确职责,妥善安排好川省土司进京朝觐事宜,清高宗又谕令军机大臣:“各土司内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等职,其每年轮班入觐时,应作何按次轮班,并听(成都)将军核定,会同总督、提督料理送京。至该土司到京后应照年班回部之例,归理藩院管理,使土司、头人各遂其瞻仰之情,承受恩泽,倍加荣耀。其土司袭职等事,亦由将军、总督咨报理藩院办理。”②《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癸未。军机大臣议覆:“明正、木坪等土司,现令于半年冬间进京。统俟土司入觐后,再照回疆例,定以年班,应令(成都)将军明亮等妥为酌派,为均体恤。”③《清高宗实录》卷1004,乾隆四十一年三月丙戌。也就是说,川西北土司的首次朝觐,并非是按班排定的,而是经清廷指定和各土司自愿参与而组成。
之后,定西将军阿桂、定边右副将军丰升额、成都将军明亮奏报:“霍尔章谷、纳林冲、孔撒三土司恳请进京谢恩。”并补充说:“查此三处,自军兴以来,派令土兵在革布什咱、甲鲁一带防守,并仍派乌拉輐运军粮,亦为出力。”获此信息,清高宗非常高兴,谕令:“霍尔章谷等土司既诚心感戴,自应准令同众土司入觐。着交明亮等妥协经理,将应行朝觐之各土司,按其序次、大小、远近,分派平允,仿照回部年班,仍遵前旨,于冬至月启程,岁底到京。”并进一步强调:“今年系初次朝觐,自应多派数人!此后按年均匀轮派。其来朝者承受恩宠,回巢传说,众土司闻之,自必倍加踊跃。”④《清高宗实录》卷1005,乾隆四十一年三月癸巳。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望前,川省入觐土司分18处,其中土司8人,即明正宣慰司甲尔参得沁、木坪宣慰司甲尔参纳木、瓦寺安抚司桑朗遇春、霍尔章谷安抚司汪尔甲策尔丹、绰窝安抚司朋楚克拉布丹、孔撒安抚司策丹纳木扎尔、巴塘宣抚司衮布甲木沁、理塘宣抚司丹津衮布,土备、土舍、头人21人(原定16人,后增为21人),即下孟董寨土游击穆塔尔、杂谷脑土守备阿旺帛噶尔、角克碉土守备二等侍卫穆塔尔、别斯满土守备阿忠保、管理金川河西暂充土守备丹比西拉布、管理金川河东暂充土守备达固拉得尔瓦、鄂克什土舍斯丹怎甲木错、绰斯甲布土舍绰尔甲木灿、梭磨土舍阿拉从、噶克土舍彰布木、绰沃土舍色纳木达尔结、鄂克什大头人赖兴、革布什咱大头人达尔结、巴旺大头人雍中太、布拉克底大头人雍中尔结、丹坝大头人策旺称拉、卓克采大头人阿结、麻书大头人登珠及头人诺尔结德尔、格忒头人色楞拉布、坦策旺邦,于十月望后集于成都,分起进京。成都将军明亮将沿途的需用和应付上奏,清高宗谕令理藩院仿照回部伯克入觐之例参酌办理。理藩院经过讨论,提出细致的意见:第一、土司自备骑驮来至成都,沿途州县各照所带骡马,每匹每日给予空草十斤,不计豆料。抵省之后,未启程前,有暂留乘骑者,仿照此支给。启程赴京后,即令将原带马骡出口,自行牵回,俟土司等回川,预期赶赴成都应用,仍照来时一体支给草料。第二、朝觐人数较多,川省额设马匹不敷应用,仍照例办给夫马,雇佣民马应用,并雇民夫抬送行李。第三、仿照回部伯克朝觐分品定级,口内沿途支食口粮,每伯克一员,日支羊肉二斤、白面二斤、米八合三勺、柴三斤、清油二两一钱之例,土司、土守备、土舍、头人自成都启程,按数支给。行令川省并陕西、山西、直隶各省一体遵办。⑤《金川案》(亨)10《理藩院咨复有关金川土司进京朝觐事宜》。一切准备就绪,众土司头人等按计划由成都启程。
三、首次朝觐的主要内容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二十日(丁巳),成都将军明亮率领川省土司、土守备、土舍、头人及番众、通事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抵达京师,清廷给予高规格接待。自是日抵京至正月二十日离京,各土司头人在京30天,辄蒙召见,天天宴席,赏赉缎匹、荷包、器具、食物殆无虚日。
在各土司头人抵京的第二天,即二十一日(戊午),清高宗就御驾瀛台,明亮率甲尔参得沁等二十九人叩仰天颜。清高宗于瀛台赐宴,并赐巴塘宣抚司衮布甲木沁孔雀翎。二十二日(己未),清高宗上谕内阁:“四川边外各土司,于此次征剿两金川,或多派土兵协同攻剿,或拨乌拉馈运军粮,均属奋勉出力。现在趋附阙庭,共抒瞻就之诚,尤为可嘉。着加恩赏戴二品红顶,并令其子孙承袭后一体戴用。其随来之土舍、头人等,向有越级戴用帽顶者,亦着加恩,仍旧赏戴,以是优奖。”当日,赐予甲尔参得沁等二十九人朝帽、帽顶、朝珠、蟒袍、补褂。二十三日(庚申),赐予角克碉土守备二等侍卫穆塔尔默克赞巴图鲁名号,同之前已获巴图鲁的别斯满土守备阿忠保一起,各赏银一百两。三十日(丁卯),清高宗于保和殿筵宴,甲尔参得沁等皆与宴。四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戊辰),正值元旦令节,甲尔参得沁等随清高宗至皇太后行宫行礼和至太和殿行庆贺礼。初六日(癸酉),清高宗于紫光阁筵宴,众土司头人皆与宴。初九日(丙子),各土司头人等随清高宗于阅武楼阅兵。初十日(丁丑),清高宗于山高水长幄次赐宴众土司头人。之后,屡蒙召至幄次,令观火戏。十五日(壬午),清高宗于正大光明殿筵宴,甲尔参得沁皆与宴。当日晚间,清高宗御山高水长幄次,甲尔参得沁及番众五十三人表演歌舞,清高宗赐缎匹有差。正月十九日(辛卯),各土司、土守备、土舍、头人及番众、通事等启程回川,清高宗命派官护送。①(清)阿桂等撰《平定两金川方略》卷101,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61册。
清高宗柔远绥遐,真可谓是无微不至。即便是剃发易服,也都详细指示。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在接到四川巡抚文绶奏报“新疆番众久经剃发,并半已穿戴内地人民衣帽。至西、南、北三路沿边土司番众,亦均已遵制剃发,并无仍沿旧俗之事”后,斥责其“所办未免过当!”强调“两金川番众,自收复以后,隶我版图,于屯土练兵一并遵例剃发,自属体制当然。至沿边土司番众,如德尔格、霍尔等处,自可听其各仍旧俗,毋庸饬令一体蓄发,更换衣饰。将来伊等轮班进京朝贡,衣服各别,亦可见职贡之盛!何必令其换衣服以生其怨也!即现在收复之两金川番众,亦止须遵制剃发,其服饰何妨听其旧俗。何况沿边土司番众,何必更改服饰耶?”②《清高宗实录》卷1103,乾隆四十五年三月辛丑。
川省土司的首次朝觐大获成功,自此之后,川西北土司每年轮班到京师朝觐,直至清末。
清廷将之前成功施行于内外蒙古和回部王公的“年班制度”用于川西北土司,仿照回部年班之例建立起川西北土司的“年班制度”,使得川西北土司成为西南众多土司中唯一享受朝觐殊荣者,表明清廷对此地区的重视。而川西北土司的首次朝觐,人数之多,在京时间之长,接待规格之高,参与活动之丰富,获得赏赐之丰厚,都是极其罕见的。川西北土司年班制度的建立和首次成功朝觐,既是清廷对在征剿两金川的战争中帮助支持过清军的川西北各土司的奖励,并藉此加以笼络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各土司实施控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清廷通过年班制度的施行,藉以笼络该地各土司,加强朝廷与各土司之间的联系,使他们知国家幅员广阔、民富物丰,知朝廷有礼有德。各土司在感受皇恩的同时,亦被强大的国威所慑服,从而畏威怀德,输忱向化,倾心归附,其好勇斗狠之狡性得以悛改,相互之间的倾轧争斗得以消弭,最终达到了对各土司实施有效控制,使川西北嘉绒藏区这个原来难以治理的地区得以长治久安之目的。
[1]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2]戴逸.简明清史(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赵云田.清代的“年班”制度[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32-35.
Cajolement and Dominance:The Yearly Shift System and the First Audience with Emperor
ZOU Jian-da,YANG Xiao-yan
(1.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Ya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2.Yunnan PoLice office Acaclerny,kunming 650092,China)
In order to keep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Tusi District in the northwestern Sichuan,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took a series of after the “Jinchuan Battle”.Among them,“Yearly Shift” that had worked well in outer and inner Mongolia was used in the Tusi of the Northwestern Sichuan,thu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Tusi to have an audience with an emperor.And as for this audience,it was terribly unusual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the longest time for stay in the capital,the richest activities,the highest level and the most precious rewards.The establishment of yearly shift system and their first audience with emperor was not only a kind of reward to the supporters of Qing soldiers,but an important policy taken as an kind of dominance over the Tusi leaders.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stabilizing and developing this region.
Northwestern Sichuan;Tusi;Gao emperor in Qing Dynasty;audience
K249
A
1009-3583(2017)-0018-05
2017-09-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12&ZD135)
邹建达,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清代政治制度史、西南边疆史地;
杨晓燕,女,云南昭通人,云南警官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魏登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