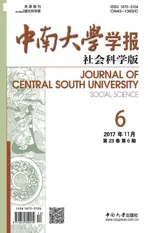对宏大话语的颠覆与挑战
——论20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早期电影研究的转向
2017-01-11宣宁
宣宁
对宏大话语的颠覆与挑战——论20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早期电影研究的转向
宣宁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界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语言学、文化学转向。受其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降,美国电影学界围绕早期电影的研究也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型。语境化的研究背景、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搭构了更开放的研究框架,推崇更细腻的言说方式,不仅让这一时期的电影研究在电影史述与理论思考两个层面不断挑战传统的宏大话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也为后续的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开拓了新的思路与空间,可谓影响深远。但是研究转向所暴露出的淡化电影本体、电影研究泛文化化、以现代性为阐释核心等问题,也应引起学界的批判与反思。
美国早期电影研究;研究范式的转变;电影史;电影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打破单线的宏大叙事而突出差异、动态与微观存在的研究转向。这场由诠释学、语言学、结构/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不断推动的研究转向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电影研究自然也包括在内,而尤以对未受规范(叙事)束缚而呈现多种发展形态的早期电影的研究所受影响为巨。研究风习的扭转,让美国电影学界围绕早期电影的研究在电影历史的建构与电影理论的思考上都出现了重大转变。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具体的研究方法有异,但是强调广阔的研究语境,跨学科的交叉视角,以更开放的研究架构和更微观的研究视点,突出对象的动态与差异,从而冲破僵化的宏大叙述获得新见的研究路径确是相同的。
一、重写历史的早期电影史研究
二战以来的历史研究深受这场方法论转向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开启了由地窖向阁楼的转变,放弃宏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论述,转向多样的微观描摹,深入而细致的心态史成为研究新宠。历史学界由经济而社会,继而进入心态(文化)的第三层次研究。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美国史学界的心理史学便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构成。故而,有美国学者将近几十年国内历史研究的发展概括为由思想史而社会史,由社会史而文化史。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展、深化,纷杂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必须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于是以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审视多样的边缘对象,在广阔的语境里描绘对象的具体存在,从而建构更为丰富、多层乃至动态的历史图景成为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转向必然深刻影响有关早期电影的历史论述。在1974年国际电影档案联合会蒙特利尔论坛之后,论坛主席艾琳·鲍泽撰文写道:“电影史,如同所有历史,总是根据我们此时此地的独特视角而被重构着。”[1]继而指出,这种重构对新方法的需要,“仅仅探究一部电影自身,或是一个导演的所有影片,甚是一个国家的所用影片都是不够的。……影片既不能孤立于它的时代,也不能孤立于其他文化、社会和政治事件和理念。问题是找到聚集所有这些资料并加以组织,以一种新视角来揭示电影历史的方 法”[1]。作为一种回应,美国著名电影史学者杰伊·莱达在同期以“朝向一种新电影史”为题,指出了电影史研究里的弊病,展望一种更为合理的电影史书写。在他看来,传统电影史研究将电影窄化为影片文本,“在技术与艺术,或艺术与金钱之间竖起了隔墙……如此分割不能反映当下或过去实际的电影制作过 程”[2]。此外传统的电影史研究也将电影与其他社会活动分割开。种种弊病导致“电影史学者犯了与19世纪历史学家简单组构事件的方法同样的错误,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再现为一个理性的序列”[2],由此遮蔽了历史发展里种种错讹、偶发导致的“戏剧”。而对这充满偶然与矛盾的真实历史的探询也便成为随后美国早期电影历史研究的主调。
电影学者查尔斯·马瑟和道格拉斯·戈梅里曾有过一次火药味十足的争论,充分表征了当时美国电影学界在早期电影史研究上的一些特征。1983年马瑟在《电影研究》上发表了长文《美国的维塔格拉夫: 1897—1901》,在考证了维塔格拉夫公司的早期历程之后,马瑟出乎意料地将批判矛头直指戈梅里,指责其电影史研究方法为“技术决定主义”,“将技术革新直接转译为商业策略、信息模式,而这并不总是有效和准确的”[3]。马瑟从而强调电影制作本身及影片的社会文化属性。戈梅里在回复里则批评马瑟过于将自己的研究窄化在单一公司的限度内,忽视了大众娱乐产业这一研究语境,且其对所谓“新经典主义”(“技术主义”)方法的回避,更是将他的研究局限在维塔格拉夫公司的早期,而没有随着技术扩展进入该公司更具产业活力的后期。而且马瑟的论述缺乏对马克思理论资源的引用,也并没有回应他对电影文化属性的强调。针对马瑟揶揄自己对资料的引用不够严谨,戈梅里也从方法论的视角提出了早期电影史研究里史料挖掘与运用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对史料运用方式的思考应与挖掘史料本身并重[4]。马瑟继而反驳,再次指责技术主义对电影文化属性的忽略,明确自己的研究基于电影制作与放映的产业背景[5]。
看似剑拔弩张的争论,细致分析却不乏偏颇。马瑟批评戈梅里强调技术,忽略影片本身,是技术主义的局限,却忽视了戈梅里的论述试图打破艺术、技术的区隔,将电影放置于更广大的娱乐消费(技术、产业)的广阔视野里。戈梅里反驳马瑟回避所谓技术主义,拘泥于单一公司某一时期的电影制作,却忽视了其研究所基于的产业背景,及其对电影作品文化属性的强调。因此尽管言辞激烈,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真正交锋,对具体细节自说自话似的纠缠,不仅颇有一叶障目之感,还遮蔽了两人在研究方法上的趋同,即打破疆界的研究路径与跨学科的开放视野。
而在他们之后的著述里,这一方法上的共性表现得更为凸显。2004年,马瑟发表了论文《历史编纂方法与早期电影研究》,提出了早期电影史研究方法上的五大挑战,即:“探寻电影文本的状态”“探讨电影与其他文化作品的关系”,思考“电影实践变化的本质”,构建“银幕实践的历史”,以及“探究电影(和其他文化作品)与其社会基础的关系”。其中不乏超出传统电影史研究范围,跨越学科,更具语境的新向度[6]。戈梅里和罗伯特.艾伦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的序言则强调:“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机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即无论何时电影都同时是所有上述四个范畴的综合:它是一个系统。理解这一系统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是怎样随时间进程发生变革的,意味着不仅要理解电影中个体成分的运作情况,而且也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7]
透过他们对史料引用的相互揶揄,也可以发现他们资料来源的丰富与多样,举凡影片名目、新闻报道、法庭判决、公司合同等等,都成为他们引述的资源。正如有学者所言,“早期电影的媒介互文,娱乐和休闲产业带来了丰富的发现,也打开了全新的研究领域。”[8]
与此同时,论述语境里多力纠缠的磁力场,需要研究者更细致地分析对象。于是微观细致的深入解析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征。微观视点和广阔语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的。正因为微观,则更容易体现出牵扯其间的各种影响;正因为在广阔的语境里,以跨学科的交叉视野进行探究,才更可能全面地描述微观对象的存在状态。美国电影学者约翰·贝尔顿在《宽银幕电影和历史的方法论》一文里考察了电影史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其一是以巴赞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历史研究的经验主义,突出电影发展中的技术因素,将电影发展看作趋向完善的进化之旅。其二是科莫利的唯物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电影的发展是多力角逐的结果,尤其以技术、经济与意识形态扮演的角色为重。然而在贝尔顿看来,不管是理想主义的电影进化论,还是唯物主义的电影多力影响说,“仍然是一种再现的模式,作为一种再现,仍为它们描述真实历史变迁的复杂性的能力所束缚”[9],它们对于历史的梳理也都是“预先设定”的。继而贝尔顿提出以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而特别强调细致分析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内部差异性的研究方法。这一微观深入的研究路径,有力地打破了线性历史的论述逻辑,将电影发展重新放置于充满偶然的复杂的图景里。
史学研究的转向凸显了单线进化历史的贫乏与虚妄,为新的历史书写提出了挑战,同时这一方法论的更新也塑造了新一代的电影史学者。诚如电影学者托马斯.埃尔塞瑟尔所言:“主要在美国的一代新电影史学者担负起了这一任务,开始对那些将电影史敷演为无畏的先驱、关于“第一次”、历险和发现、大师与杰作的故事的历史论述进行彻底的反省。”[8]以查尔斯·马瑟、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大卫·鲍德韦尔、克瑞斯汀·汤普森、珍尼特·斯泰格、汤姆·甘宁、乔治·普拉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怀疑一切的精神,在广阔的视野里不断探索电影发展里的各种“戏剧”,以一大批视角不同却同样深入的力作,拼贴出繁杂的电影图景。
二、重新认识电影的理论思考
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转向不仅为捆缚于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松绑,在跨学科的广阔语境里探询微观对象的具体存在,也质疑着宏大理论的阐释能力。结构/解构主义所凸显的话语建构性质与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接受主体的能动性,为打破宏大理论不断提供动力。在此基础上,各种理论思考不再试图建构单线霸权的阐释话语,而表现出更开放、更平和的阐释姿态。
当代电影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倚重于各种人文社科的理论资源,二战前后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学说,纷纷将电影纳入自己的阐释视野。电影不仅成为这些理论学说的影像注解,更据此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流派。而这些打着各种主义的理论话语,以霸权的姿态左右着对电影的理解,强调电影的功能与接受的单线不可逆性。学术转向有力地冲击着这种理论阐发里的宏大姿态,对话语建构性质的凸显以及文化研究视野下对动态交互的强调,让电影理论的阐发更显灵动。虽然依旧要借重各种理论资源,但由于更开放的论述框架,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具体性和能动性的强调,理论阐发被表述得更动态而包容。转向后对美国早期电影的理论思考即突出地表征了这些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微观细致的思考路径,开放灵活的阐释姿态。美国电影学者汤姆·甘宁与米莲姆·B·汉森的电影研究无疑是极具分量的例证。
如果说1972年布加勒斯勒国际电影档案联合会年会拉开了对电影史研究方法的探讨,那么1978年在布莱顿会议上放映的珍稀影像则激起了诸多学者对早期电影的理论兴趣。随后几年,在早期电影研究中,最引人注目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无疑是美国电影学者汤姆·甘宁和加拿大学者安德烈·戈德罗所提出的“吸引力电影”的概念。甘宁对这一概念做了更为深入持续的阐释、推广。甘宁认为:“吸引力电影是直接诉诸观众的注意力,通过令人兴奋的奇观……激起视觉上的好奇心,提供快感。……它是对观众的直接致意……戏剧展示凌驾于叙事吸引之上,强调震撼或惊慑的直接刺激,置故事的展开或虚构世界的建立于不顾。……将能量向外倾注于得到认可的观众,而不是向内着力于经典叙事中实质以人物为基础的情境。”[10]
吸引力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对宏大理论的反驳。在后来追述这一概念的形成时,甘宁反复表示观众接受的角度是这一概念产生的基础,并由此驳斥了当时宏大理论对观众接受的单线限定。“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高理论’(High Theory)依然束缚并限定了有关观众接受学的观点,……把电影观众接受学机械地概称是毫无意识的沉迷过程,关注的只是本能固有的反映和退化了的心理状态。”[11]而劳拉·穆尔维关于视觉快感的论述则给他以极大的启发,“如果对一位有着性别身份意识的观众需要进行特别考察的话,那么一位历史上的观众同样是不是也需要讨论?”[11]正是基于历史化的、经验的观众接受,甘宁提出了迥然不同于经典电影叙事模式的以展示为核心的视觉传达机制作为早期电影的形态特征。此外,对早期电影吸引力特征的阐释也基于包括综艺游乐场、杂耍、博览会等20世纪初广阔的现代生活语境,调用了瓦尔特·本雅明式现代性体验的言说方式。正如他在《作为客观一课的世界:电影观众,视觉文化和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1904》一文里所言:“早期电影研究的新路径必须小心地将其置于表征着世纪之交的视觉文化和技术文化之中,并且避免将电影作为这些文化的顶峰看待。电影在这一驳杂的领域里不是作为一个顶峰出现,而是作为一个偶然的边缘参与者出现的。”[12]在其看来,世纪之交的整个现代生活与体验是理解早期电影品格的必要背景。
同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米莲姆·B·汉森则从其他角度强调早期电影的现代性特征。而在她的研究里同样体现了开放的阐释姿态,以及跨学科的理论视野。汉森借用其导师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阐释早期电影的现代性特征。不同于哈贝马斯对“中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界定,汉森对早期电影公共领域的理解更接近德国电影导演、理论家亚历山大·克鲁格,强调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包容性与个体体验和表达的可能性。这种在公共领域里对不同体验与表达的关注本身即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驳,而在理论阐释上则是对意识形态电影理论无缝询唤的一种逆转。不仅如此,相较于克鲁格,汉森对早期电影公共领域的理解要更为开放和包容。克鲁格所谓“公共领域”是与“代表的”“抽象的”“排外的”“经典公共领域”与“虚假公共领域”相对的“抵抗的公共领域”(“普罗”),以“开放性,自由接触,多重关系,交际互动与自我反省,为要义”[13],可称之为“政治的工厂”,在其中“政治及其交流第一次成为可能”[14]。因而克鲁格的公共领域概念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图与意识形态色彩,这也让他的论述不时流露出决绝而武断的排外性。如,针对美国早期电影存在向中产阶级浪漫小说学习的倾向,克鲁格完全否定了其公共领域的反抗性。于此,基于现代性视角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汉森则表现出更动态、开放的阐释姿态。汉森强调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的美国早期电影在试图吸引各阶层的观众时,也许为多层的,乃至敌对、反抗的公共领域留下了空间[15]。
这种对研究对象细致而包容的阐释姿态也体现在她对鲍德韦尔维尔等人的批判中。在肯定鲍德韦尔等人用实证打破劳工阶级与早期电影的自然联系这一经典的影史神话的同时,汉森也敏锐地指出他们的研究将早期电影观众预设在阶级话语中,将他们简化为经济身份,而忽略了其中所含有的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身份。在理论实践上,汉森更是不遗余力地阐释早期电影公共领域里女性的观看体验,将被长期忽略的女性观众(女性观看)概念化[16]。
汉森另一个将电影与现代性体验联系起来的概念是“白话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最初是针对经典好莱坞电影(其中的大部分时段并不属于早期电影范畴),但是随后却引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的研究中。其学生张真的后续研究,更让这一概念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森直言:“选择‘白话’(vernacular)一词,以其包括了平庸、日常的层面,又兼具语言、习语、方言等涵义,尽管词义略嫌模糊,却胜过‘大众’(popular)一词。后者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而在历史上并不比‘白话’确定。”[17]而对于“白话”这一术语的选择也尽显其对各种宏大理论与区隔的反叛,以及对动态差异的强调。白话是俚俗习语,因而它打破了经典艺术与通俗艺术、先锋电影与叙事电影、思想表达与物质体验的区隔,将现代性的思考与表达由经典艺术、先锋电影引入通俗的叙事电影里,以物质直觉代替抽象概念,强调电影所提供的现代性感官机制。白话又是方言,因此即使面对美国经典电影(美国主义)的侵入,现代性发展不均衡的不同区域对美国电影的接受都会有转译与差异的主动一面。这种对所在地主动性、差异性的强调甚至被有的学者批评为“因其过分的灵活性和多元性而显得模棱两可”[18]。
从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电影公共领域”研究到世纪之交的“白话现代主义”,20余年的时间跨度似乎很难将这两个研究项目联系起来。但是汉森1991年所著的《巴别塔和巴比伦:美国默片里的观看》的名称却表露了其间的关系——正是“观看”,观众的观影体验与表达,成为延续在其电影学术历程里的研究逻辑。从分析公共领域里不同观众的观看与体验,到强调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所组织的“视觉与感官认知的新模式”,所传达的“关于美感、匀称、和谐、平衡的永恒意义”[19],观众的“观看”(体验)一直是论述的基点。而这一阐释基点的确立则源自汉森对电影功能的理解。在她看来,“观看”本身即是电影功能的实现之途。在《媒介为何是美学》一文里,汉森详细地论述了她的电影功能观,借用本雅明的“人类学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汉森赞同电影的主要功能在于“训练人们使之具备应对在其生活中不断扩张的大量设备所必须的知觉与反应”,即“在人类与技术之间建立平衡”的观点[20]。显然,公共领域里的观看与白话现代主义里的观看,都必然基于电影的这一感官调节功能,只是后者对这一功能的表述更为直接。
与甘宁一样,汉森的电影研究也跨越了多个学科,而她的学术经历本身即是绝佳的说明。师从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电影研究的起步伴随着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齐格弗里格·克拉考尔的深入思考。这些来自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与电影学的理论资源,有力地支撑着她的电影研究,使其在现代性的广阔语境里来去自由,而多学科的视角,也让她的早期电影研究新见频出,深入透彻。举例而言,汉森对早期电影现代性体验的直觉感官方式的强调显然受到了本雅明“单行道”及“拱廊研究”里印象式书写的影响。
三、研究转向的意义与局限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这次围绕早期电影的研究转向,在影史与理论两个方面挑战了传统的宏大论述,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影响深远。但是其自身的研究局限与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与 思考。
就早期电影的历史书写而言,研究范式的转向以多线复杂的历史图景突破了单线发展的历史叙述。汤姆·甘宁指出:“虽然早期电影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完全理论化,但是我相信我们仍能提炼出三种支撑着我将称之为连续性模式(the continuity model)的设想。”[21]这些趋向进化、发展的单线逻辑支撑了路易斯·雅各布斯、乔治·萨杜尔、让·米特里与克里斯蒂安·麦茨等几代电影学者关于早期电影的思考,成为书写早期电影历史的主导模式。研究范式的转变无疑极大地突破了这种单线发展的电影史观。跨学科的开放视野不仅将众多被忽略、遮蔽的边缘现象纳入议程,也努力探寻历史塑形过程中众多的幕后推手。而微观聚焦的切入方式,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充分、可靠的文献资料放大这些相互博弈的影响源,凸显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两相作用,早期电影史单线的时间流程被扩展为多力共存的空间战场,向善的进化之旅被偶发的错讹戏剧性地打断。早期电影史严密整合而动力十足的宏大叙事不断被撼动,而历史也开始以多线、迂回、甚或难以把握的方式展露真面目。二十多年后,这次研究范式的转变获得了来自中国电影学界的回响。在对中国电影史学的局限与前路的思考中,学者们感叹电影史的研究方法已然落后于历史学的发展,指出影史研究在史述体裁上的陈旧单一,在专题研究上的粗疏。“微观史观”“生态史观”等研究路径渐成学界共识。
就理论思考而言,转向后的研究凸显“观看”与“观看主体”的经验,以此挑战宏大话语机械论述,寻求对早期电影的全新理解,建构动态、灵活的理论阐发。在大卫·鲍德韦尔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主体-位置理论”是电影研究里典型的“宏大理论”,而其宏大阐释的立足点则基于对观众主体的建构。“根据这一概念常见的理论化形态,主体既非个体的人,亦非有关个体身份或自我的直接观念……主体性通过表达系统而建构起来。”[22]这种对观看主体单一、超验的限定支撑起宏大理论的霸权姿态。基于此,米连姆·B·汉森在研究中对经验的、多样的、主动的“观看主体”与“观看”的强调就不乏挑战宏大理论的战略意义。汉森指出:“对于电影学或其他学科的发展,探讨公共领域中的观看问题都很重要。”[23]甘宁也追溯了激发吸引力电影概念的观众接受视角。正是从观众主体这一基石出发,转向后的理论思考不断用历史的、主动的观众主体与观看,撕裂封闭、僵化的主体限定,寻找对早期电影的全新理解,在现代性的广阔语境里以更动态的理论阐发挑战宏大话语单线机械的论断。在这一研究思维的启发下,电影的理论思考不断越过现代电影理论里的各种宏大藩篱,出现多路发展的态势,重燃电影本体思考的理论潮流即是一例。
在新的研究范式的指引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电影学界围绕早期电影的研究不论是历史著述还是理论探讨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鲍德韦尔、汤普森、甘宁、马瑟、艾伦、戈梅里等人的电影史著述不仅引领了影史研究的热潮,并扩展了电影史研究的领域,更为后续的影史书写提供了范式。在理论建树方面,甘宁的“吸引力电影”则在电影本体研究沉寂多年之后,提出了迥异于“叙事”的以“展现”的视觉传达为特征的电影形态,无疑是涉及电影本体的研究成果;汉森关于“早期电影公共领域”“白话现代主义”的思考,其将早期电影作为现代性(现代生活方式、文化)表征的研究路径与甘宁的“吸引力电影”研究,一道被誉为电影的“芝加哥学派”,深刻影响了当代美国电影研究的整体面貌。这些成果迅速成为经典,为欧美高校里电影学科的建立贡献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晋学者及其研究都与中国渊源颇深,不少学者进行过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被译介后,更是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学术热情。鲍德韦尔较早进行了有关香港电影的研究;汉森也以早期上海电影作为其白话现代主义的理论注解,并为中国早期电影研究培养了两位出色的华人学者;英国学者裴开瑞则借用“吸引力电影”概念解读中国戏曲片。而随着成果的译介,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更是推动了国内电影研究的发展。电影史书写的文化化,电影研究的物质化、语境化,将中国电影研究推向纵深。
当然,这次电影研究的转向也并非毫无瑕疵,电影学界也不乏批判反思的声音。张英进先生指责“白话现代主义”概念由于缺乏界定(意识形态)而导致分析缺失标准、过于灵活的问题。曲春景先生则对“感官主义”研究路径边缘化电影本身满怀忧虑。这一忧虑在不断模糊边界、泛文化化的电影研究路径渐成主流的研究背景下显得更为紧迫。查利·凯尔质疑“吸引力电影”概念与“现代性”论述过于粘合,以致当现代体验成为常态后,对电影吸引力模式后续发展的阐释将陷入困境。此外,随着研究转向的影响日隆,尤其是汉森与甘宁的研究成果及方法的流行,早期电影的现代性论述会不会成为电影研究里的又一种宏大理论,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鲍德韦尔、戈梅里等人的电影史研究也尚未弥合“重写电影史”的宏愿与零散的案例研究之间的鸿沟,研究方法的更新、转向很难沉淀进影史(尤其是通史)的书写里。而在铺展电影生存语境的历史书写中如何拿捏“本体史观”与“生态史观”的论述关系,既不失广阔视野,又聚焦电影本身,也需要更谨慎的思考。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学者内部也是争议不断,如前所述汉森批判过鲍德韦尔等人的研究,马瑟与戈梅里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就连出身同门的甘宁与马瑟之间,围绕“现代性”在早期电影研究里的地位也不乏争论。然而,正如马瑟所言:“电影研究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术团体,其中创造性的摩擦不仅产生对话和关于电影在历史里如何运作的更深刻的认知,也产生了友谊。”[23]正是这些批判反思与相互诘难,延续着这次研究转向的学术活力,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新的灵感。
[1] Eileen Bowser. Introduction[J]. Cinema Journal, 1974(2): 1−2.
[2] Jay Leyda. Toward a New Film History[J]. Cinema Journal, 1974(2): 40−41.
[3] Charle Musser. AmericanVitagraph: 1897−1901[J]. Cinema Journal, 1983(3): 4−46.
[4] Douglas Gomery. Historical Method and Date Acquistion: Douglas Gomery Replies to Charles Musser’s ‘American Vitagraph:1897-1901’[J]. Cinema Jounral, 1983(4): 58−60.
[5] Charles Musser. Charles Musser Responds[J]. Cinema Journal, 1983(4): 61−64.
[6] Charles Musser. Historiographic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Early Cinema[J]. Cinema Journal, 2004(1): 101−107.
[7] 罗伯特·C·艾伦, 道格拉斯. 戈梅里. 电影史: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7: 3.
[8] Thomas Elsaesser. Early cinema : from linear history to mass media archaeology[C]//Thomas Elsaesser, Adam Barker, eds. Early Cinema: Space Frame Narrative. London: BFI, 1990: 3.
[9] John Belton. CinemaScope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y[J]. Cinema Journal, 1988(1): 22−44.
[10] 汤姆·冈宁. 吸引力电影: 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J]. 电影艺术, 2009(2): 61−65.
[11] 汤姆·甘宁. 吸引力: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J]. 电影艺术, 2011(4): 71−76.
[12] Tom Gunning. The World as Object Lesson: Cinema Audiences, Visual Culture and the St.Louis World’s Fair, 1904[J]. Film History, 1994(4): 422−444.
[13] Miriam Hansen. Reinventiong the Nickelodeon: Notes on Kluge and Early Cinema[J].October,1988(46): 78−198.
[14] Alexander Kluge, Thomas Y. Levin, Mriam B. Hansen. On Film and the Public Sphere[J]. New German Critique, 1981(24/25): 206−220.
[15] Miriam Hansen. Early Silent Cinema: Whose Public Sphere?[J]. New German Critique, 1983(29): 147−184.
[16] Mriam Hansen. Pleasure, Ambivalence, Identification: Valentino and Female Spectatorship[J]. Cinema Joural, 1986(4): 6−32.
[17] 米莲姆·不拉图·汉森. 堕落女性, 冉升明星, 新的视野: 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J]. 当代电影, 2004(1): 44−51.
[18] 张英进. 阅读早期电影理论: 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J]. 当代电影, 2005(1): 29−34.
[19] 米莲姆·不拉图·汉森. 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J]. 电影艺术, 2009(5): 125−134.
[20] Mriam Hansen. Why Media Awsthetics?[J]. Critical Inquriy, 2004(2): 391−395.
[21] Tom Gunning.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The Temporality of 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J]. Velvet Light Trap, 1993(32): 3.
[22] 鲍德韦尔, 卡罗尔. 后理论: 重建电影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9.
[23] 米连姆·汉森. 电影观看与公共生活[J]. 艺术评论, 2010(7): 14−21.
Subversion and challenge to grand discourse: The turn of American early film study since the 1980s
XUAN N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The paradigm of study in the western humanities has turned towards linguistics and culturology since the 195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tendency, American early movie stud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taken the same turn in research paradigm since the 1980s. Contextualized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constitute more open frame for research and emphasize a more exquisite way of telling, which not only makes film study during this period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grand discourse from such two levels as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movie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chieving rich fruits, but also supplies new paradigm for the subsequent film study, thus expanding thoughts and space for research. All of these are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But, the turn discloses such problems in film study as desalinated ontology, pan-culturalization, modernity-oriente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like, which should invok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American early film study; turn of study paradigm; film history; film theory
[编辑: 胡兴华]
2017−04−28;
2017−06−30
宣宁(1981−),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四川音乐学院戏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理论与批评
J902
A
1672-3104(2017)06−01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