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与季羡林的两场“论战”
2016-12-01庞旸
庞旸
周有光与季羡林的两场“论战”
庞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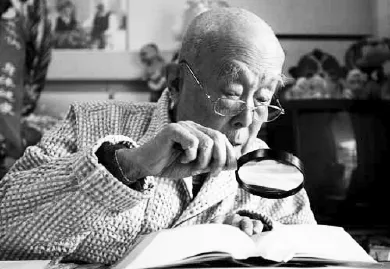
周有光和季羡林两位老先生,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颇为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
“双文化论”是周老的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河东河西”论是季老的观点。季老认为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
季老的“河东河西”论发表时,正是上个世纪末,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周老的“双文化论”。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他认为“河东河西”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关于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汉字该不该简化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周老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说,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老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老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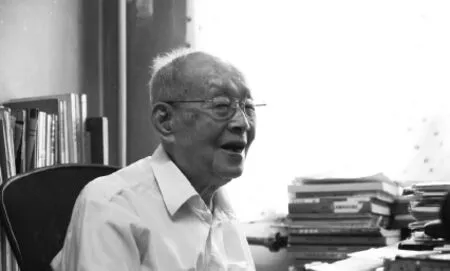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周老说,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他认为,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他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老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对于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张,周老说,繁体字是恢复不了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共识。
周老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还要对汉字进行一次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