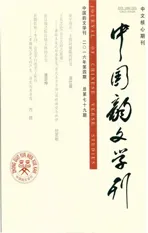诗债论
2016-11-26王雪
王 雪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诗债论
王 雪*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唐前虽无“诗债”一词,但是文人的诗歌创作中已出现与之相关的观念。“诗债”一词最早出现于白居易的诗歌,最初单纯指欠他人之诗,后来内涵有所扩大——欠万物之诗、欠自我之诗。对不同的欠债对象,诗人们的创作态度也是不同的,欠他人的诗债大都需要偿还;欠万物的诗债,本质上是诗人作诗来报答自然界赋予的感官享受,是诗人主观的自我加压,有时可以不还;前世今生所欠的宿债,实则就是欠诗人自己的诗,是他们喜爱作诗的托词,这类诗人往往将作诗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大都创作量巨大。
诗债;唱酬;催诗;宿债
《毛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P637)情感一直被认为是诱发诗人创作的关键原因,但是文人创作心理纷繁复杂,有些时候并不是在情感的触动下写诗,而是因为“负债”而创作。“诗债”最初的意思是指答应了他人的要求写诗但还未写的亏欠,宋人多认为“诗债”一词出自贾岛,林逋《诗筒》诗下注“诗权出薛许昌”,“诗债出贾司仓。”[2](P54)《北山诗话》亦云:“诗权出薛许昌,诗债出贾常侍,故有‘诗债隔年还’之句。”[3](P413)(案“诗债隔年还”是贾岛的诗,但他并未做过常侍之类的官)据张伯伟先生考证,《北山诗话》当为南宋初人所作,但作者失考。二者所说极为相似,《北山诗话》可能是参考了林逋之诗。贾岛的原诗为:“树阴终日扫,药债(一作诗债)隔年还。”(《寄钱庶子》)*[唐]贾岛著,李嘉言校《长江集新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长江集》作“药债”。《文苑英华》所录此诗作“诗债”,下注“集作药债”。《瀛奎律髓》作“药债”。《全唐诗》作“药债”,下注“一作诗债”。经笔者考订,此处的异文当作“药债”*其一,林逋《诗筒》最先指出“诗债”一词出自贾岛,但是其诗中所指多有讹误,如诗中注释“诗权出薛许昌”,薛许昌指唐代诗人薛能,有《许昌集》,但是遍检薛能之诗,并没有发现“诗权”二字,故“诗债”一词的可信度也有待商榷。其二,钱庶子名徽,字蔚章,是大历十才子钱起之子,两唐书有传。元和十一年(816),“以论淮西事忤旨,罢职徙太子右庶子,出虢州刺史。”钱徽无诗名,亦无诗作传世,故贾诗中如果说欠他的“诗债”实属牵强。其三,贾岛多次在诗中表明身体孱弱多病,《寄李辀侍郎》:“此身多抱疾。”《咏怀》:“经年抱疾谁来问。”而且其生活潦倒贫苦,诗中多有向他人求药的经历,如《酬栖上人》:“松姿度腊见,篱药知春还。”《送胡道士》:“却从城里移琴去,许到山中寄药来。”由此推测《寄钱庶子》一诗中当指“药债”。,“诗债”一词最早来源于白居易*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一诗中提到:“老偿文债负,宿结字因缘。”开成二年(837),他又在《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诗中云:“顾我酒狂久,负君诗债多。”这是关于“诗债”一词的最早记载。。
经笔者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未有“诗债”一词,但与之相关的创作已经出现了。白居易之后,中晚唐诗人的诗歌中也开始陆续出现“偿诗债”的例子,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开始蔚为大观,诗债的意义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大。因为关于诗债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所以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是从一些具体的创作中确实能够发现,这种观念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从诗债说产生的渊源,按照欠债对象来分类,分析不同类型的诗债对诗人创作的影响。
一 “睡余强起还诗债”——欠他人之诗
《韩诗外传》卷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自此“登高必赋”便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九种才能之一。《三国志》卷一称赞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从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但并不是每个人每次登高都能赋诗,有些人文采不济,自然赋不出来,《南齐书·文学传论》:“卿、云巨丽,升堂冠冕;张、左恢廓,登高不继,赋贵披陈,未或加矣。”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写得宏大华丽,张衡、左思的赋继承二者的优点,博大开阔,后来者即使“登高”也难以为继。孔子云:“诗可以群。”诗歌是文人交流感情、切磋诗艺的一种方式,但是在酬唱赠答的过程中,如果一时答不上来,不仅愧对诗友,而且会有负债感。江淹《郊外望秋答殷博士》:“频赠既雅歌,还怀谅短书。”江淹用了一个“还”字,可见他意识到自己欠殷博士诗歌,对于以一篇短章来答谢殷博士多次赠诗感到非常惭愧。何逊《酬范记室云》:“林密户稍阴,草滋阶欲暗。风光蕊上轻,日色花中乱。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清谈莫共理,繁文徒可玩。高唱子自轻,继音予所惮。”他劝范云不要妄自菲薄,对于范云的继诗他还是非常畏惧的。这就反映出,在酬唱赠答过程中,一方文采过于出众会给另一方造成压力,因为他不一定能作出和诗,如果写不出来,就会欠下对方的诗债。
魏晋南北朝时期联句盛行,何逊喜作联句,但是有时难免文思受阻,也会有作不出的尴尬,江革《赠何记室联句不成》题下注:“嘲以诗。”诗云:“龙鳞无复彩,凤翅于兹铩。畴昔似翩翩,今辰何乙乙。”诗的大意为:你以前文采是多么出众,怎么现在却作不出来了呢?何逊联句不成因而受到江革的嘲笑,江革的诗即有催债的意味。而后何逊作答诗一首《答江革联句不成》:“日余乏文干,逢君善草札。工拙既不同,神气何由拔?”自己缺乏文采而又偏偏遇到江革这样善于作诗的人,所以不免一时答不上。由此可见,魏晋时期虽没有“诗债”一词,但文人们在创作中已经有了诗债的意识,酬唱赠答时对方文采太高或是自己一时诗思困厄都会给自己留下诗债。
文人唱和之风古已有之,但直到中唐时期才开始逐渐兴盛,唱和之时你来我往,如果一时没有继作,难免欠下诗债。白居易是中唐唱和之风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与元稹的“通江唱和”可谓是当时的代表。白居易在诗中多处提及“诗债”,如《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
病容衰惨澹,芳景晚蹉跎。
无计留春得,争能奈老何?
篇章慵报答,杯宴喜经过。
顾我酒狂久,负君诗债多。
敢辞携绿蚁,只愿见青娥。
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
此诗作于开成二年(837),这是关于“诗债”一词的最早记载,沈四著作名述师,沈传师之弟,白居易在诗中自注:“沈前后惠诗十余首,春来多醉,竟未酬答,今故云尔。”[4](P2565)沈述师再三赠诗,是自己的疏懒嗜酒导致欠下诗债。又如《自咏老身示诸家属》:“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4](P2818)张祜是元和时期著名的诗人,与当时的元白、韩柳两大诗派都有联系,其诗《忆江东旧游四十韵寄宣武李尚书》:“酒徒穷不破,诗债老相仍。”穷困潦倒也要喝酒,年事虽高仍然欠人诗债。晚唐时期诗债之说依然盛行,如刘得仁《和郑先辈谢秩闲居寓书所怀》:“把笔还诗债,将琴当酒资。”牟融《题朱庆余闲居四首》其二:“近来疏懒甚,诗债后吟身。”陆龟蒙《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其十:“酒材经夏阙,诗债待秋征。”贯休《酬杜使君见寄》:“心疼无所得,诗债若为还”等。这些诗歌都为次韵酬唱之作,诗债说最初就是从唱和诗中产生并流传开来的。
北宋元祐时期文人士大夫之间唱酬更加频繁,以苏黄为例,苏轼现存次韵诗785首,黄庭坚有566首,围绕在其周围的文人也多参与唱酬,频繁的唱和必然会出现“偿诗债”的例子,如黄庭坚《次韵张秘校喜雪三首》其一:“睡余强起还诗债,腊里春初未隔年。”急忙赶在腊月里还诗并没有留到来年,这里化用贾岛“药债隔年还”一句。又《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镇》:“传语濠州贤刺史,隔年诗债几时还?”陈师道《夏日书事》:“穷多诗有债,愁极酒无功。”秦观《拟白乐天》:“北里酒钱烦屡索,南州诗债懒频酬”等。南渡之后继承了酬唱赠答的风习,文人也常为诗债而恼,如张孝祥《将如会稽寄曾吉甫》:“诗债未还缘懒拙,宦游如此竟危颠。”杨万里《又追和功父病起寄谢之韵》:“忽忆约斋诗债在,自吹灯火起来看。”陆游《闲思》:“闭门旋了和诗债,卖药不偿沽酒资。”刘克庄《答庐陵彭士先》:“昔牧昌黎州,尝负君诗债”等。
有一种情况,诗人们不是在唱和之时欠下他人之诗债,而是以诗歌作为娱乐活动的筹码。北宋初年文人徐铉的诗《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即是以诗歌作为下棋的赌注,输的一方就要作诗来惩罚,就是欠下对方的诗债。梅尧臣《题腊药》诗下自注:“尚书晏相公腊日投壶,输诗七首,便以腊日所用物赋,先成四首上呈。”《语鸩》诗下又注:“此以上三首补前投壶所输七首。”诗人因为投壶而输给对方七首诗,所以在诗中自注说明这些诗是为还债。《冷斋夜话》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曰:‘华发寻香始见梅,一株临路雪培堆。凤城南陌他年忆,杳杳难随驿使来。’”[5](P40)以作梅诗为下棋的赌注,输的一方就欠下对方的债务,要写诗以偿还。陆游《东篱三首》其三:“陪客投壶新罚酒,与儿斗草又输诗。”诗人投壶罚酒,斗草又欠下儿女的诗歌。这些输诗的例子也属于诗债。
正如黄庭坚所云“睡余强起还诗债,腊里春初未隔年”,欠他人的诗歌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多数情况下需要偿还,所以诗人们经常搜肠刮肚来偿还诗债,如吕本中《长葛道中遇周原仲》:“僧房夜语久不眠,更摩枵腹偿诗债。”曹勋《和次子耜久雨韵》其三:“吾儿诗有债,老我韵劳心。”王之道《和张文纪咏雪二首》其二:“诗债恼人眠不得,夜寒残管亦须拈。”如果久不还诗,有的诗友甚至会来要债,如司马光《昌言见督诗债戏呈绝句》:“学餧才贫杼轴劳,逾年避债负诗豪。”友人来诗催促所以不得不作诗还债。冯时行《索友人赓和》:“诗债迟迟不见还,只缘草赋动天颜。”从诗题即可看出这是一首催债诗。葛胜仲《喜宗丞侄病愈》:“径须营度还诗债,要看笔端翻峡水(侄有围字韵诗未和)。”邓深《寄徐广文并序》:“可能忘旧债,五字当追须。”序云:“予客长沙,用之亦寓居,春闲忽告别往宾州,暨予还家,闻渠复返所寓,寄四韵索诗债云。”诗人寄诗即是为了催债。但是有些诗债确实是诗人无力偿还,因为一些诗人在唱酬之时为显示自己的才能而故意压险韵,令他人难以为继。为此,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三专门论述了还诗债有一定的技巧:“凡诗债丛委,固有缓急,亦当权变。若先作难者,则殚其心思,不得成章,复作易者,兴沮而语涩矣。难者虽紧要,且置之度外。易者虽不紧要,亦当冥心搜句,或成三二篇,则妙思种种出焉,势如破竹,此所谓‘先江南而后河东’之法也。”[6](P66)“先江南而后河东”之说出自吕中《大事记讲义》卷二:“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后难,先近而后远,先瑕而后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为先江南而后河东。”[7](卷二)简而言之,就是要先易后难,这样才能够“势如破竹”,否则有可能徒费心思却一首也作不出。
欠他人的诗债需要偿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唱和诗的创作,充分发挥了“诗可以群”的社会功用。而文人受诗债思想的影响推敲琢磨,也能够锻炼诗歌写作才能,提升诗艺,赵蕃《途中每息,必索砚笔抄诗,作廿八字》云:
望望青山乱作堆,行行身到白云隈。
偶逢道店聊休歇,又被匆匆诗债催。
观察诗题,诗人在旅途中每次休息都要作诗,这是因为总有诗债“逼迫”,这样的日锻月炼必会提升诗歌写作水平。但是有时候为了偿还诗债,诗人们往往绞尽脑汁,容易形成苦吟之风,范成大《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北邻亦复淡生活,要我忍寒吟此诗。”为了偿还诗债,诗人在苦寒之夜还在搜句吟诗。陈造《次韵王知军雪》:“未办壶天陪一笑,夜深空敛索诗眉。”诗人为答友人赠诗,夜深人静时还在搜肠刮肚地思考。苦吟往往导致文人过多注重字句而忽略情韵,甚至出现有句无篇的情况。而且以诗偿债有时会影响诗人创作态度的严肃性,郑板桥论述杜甫和陆游的诗题时说道:
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放翁诗则又不然,诗最多,题最少,不过《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兴》而已。岂放翁为诗与少陵有二道哉?盖安史之变,天下土崩,郭子仪、李光弼、陈玄礼、王思礼之流,精忠勇略,冠绝一时,卒复唐之社稷。在《八哀诗》中,既略叙其人,而《洗兵马》一篇,又复总其全数而赞叹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时,君父幽囚,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皆流连诗酒,沉溺湖山,不顾国之大计。是尚得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诗歌而劳吾赠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诗债而已。[8](P188-189)
他认为陆游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耻于与之唱和,所以大多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等题目了却诗债。这是赞其清正廉洁,但从反面亦可说明陆游为还诗债有时会随意拟题作诗,综观《剑南诗稿》,单以“遣兴”为题的诗歌就多达30余首,这样大面积的重复令陆游诗歌招致许多诟病,钱锺书就批评他:“其制题之宽泛因袭,千篇一律。”[9](P128)这就反映出,如果诗人对于欠债对象有微词而不愿覃思还债,就会出现随意拟题的情况,这是诗债影响过犹不及的一方面。
二 “平生欠汝哦诗债”——欠造化之诗
诗债本是指欠他人之诗,但是有些时候文人往往把欠债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司空图《白菊杂书四首》其二:“此生只是偿诗债,白菊开时最不眠。”他自认欠白菊的诗债,所以每到白菊开时都忧不能眠。洪适《得洛中牡丹》:
洛花天下选,千里湊三园。
望岫方缄恨,凭莺忽践言。
群葩俱退舍,胜日便开尊。
莫惜诗偿债,真同香返魂。
诗人酷爱牡丹进而认为欠之诗债,要作诗偿还。杨万里《黄雀食新二首》其一:“诗债被渠浑索尽,醉乡邀我不容归。”黄雀来索诗,诗人只得苦思还债,连喝酒的工夫都没有了。
据程杰先生统计,《全宋诗》收诗约25万4千多首,梅花题材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亭题咏等相关题材)4700多首,占1.85%。[10](P29)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这个比例都不可谓不大。宋人深喜梅花,所以诗中常常出现“偿梅债”“梅催诗”等例子。活跃于两宋之交的李处权《梅二首》其二:“可怜映竹深深见,似为催诗特特开。”梅花仿佛就是为了索诗而开。刘克庄在《葺居》诗中亦云:“旋移梅树临窗下,准备花时要索诗。”作者认为梅花开时定会催促自己作诗,因此早早地将梅树移到窗下。韩元吉、范成大、陆游和赵蕃等人都曾在诗中表达欠梅诗,要“偿梅债”。韩元吉《晖仲惠梅花数枝四首》其四:“诗人每负梅花债,屈指今年第一篇。”范成大《海云回,按骁骑于城北原,时有吐番出没大渡河上》云:“天于麦垄犹悭雪,人向梅梢大欠诗。”在《春怀》诗中亦云:
柳颦梅笑各相恼,诗债棋仇俱见寻。
莫道幽居无一事,春来风物总关心。
作者虽幽居无事,但是对春天的事物还是十分上心,因为柳树发芽、梅花开时也就是自己偿还诗债之时。范成大喜爱梅花,不仅在诗中反复提及(约35首咏梅诗),而且还编有《梅谱》一卷,所列之梅凡12种。他每见梅花开时都要作诗,仿佛是在还梅花之“诗债”,在《新岁书怀》诗中曾云:“岁华书户笔,年例探梅诗。”每年都有咏梅花之诗,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陆游亦酷爱梅花,在《阆中作》其二中云:“平生剩有寻梅债,作意城南看小春。”他的咏梅之作达159首,《次韵张季长正字梅花》一诗云:“倚桥临水似催诗,戏伴鹅黄上柳丝。”他亦认为梅花盛开即是在向自己索诗。范成大在诗中曾提到:“陆郎旧有梅花课”(《古梅二首》其二),可见陆游也是十分自觉地咏梅,并把它当做一项功课来作,这与范成大“年例探梅诗”的态度是一样的。另一位嗜梅如命的诗人赵蕃,现存咏梅诗123首,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云:“赵章泉日作梅课。”[11](P391)他每天都要写咏梅之诗,虽未免有些夸张,但他的确是认为自己欠了“梅债”,要生生世世咏梅来还,如《梅花六首》其一:
平生欠汝哦诗债,岁岁年年须要还。
未至腊时先访问,已过春月尚跻攀。
直从开后到落后,不问山间与水间。
却笑渊明赋归去,庭柯日盼自怡颜。
作者认为自己一生都欠梅花的诗债,所以要时时吟咏之以偿还,从梅花开前到落后,他都是兢兢业业地追随它、赞美它,并且乐此不疲。
方回《瀛奎律髓》云:“以雨催诗,自老杜作古。”[11](P772)“催诗”说最早见于杜甫的诗《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一:“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天气突然变化,仿佛是急雨来催促诗人作诗。“催诗”说在唐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是到了北宋时期人们的仿作才零星出现,如苏轼《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另一首《游张山人园》:“纤纤入麦黄花乱,飒飒催诗白雨来。”诗人认为雨水并非无故而来,而是为催促诗人创作而下。署名孙莘老的《题阎求仁虚乐亭三首》其二:“春深鶗鴂催诗句,夜静蟾蜍入酒舟。”春天来临,杜鹃鸟亦来向诗人索要诗歌。南宋时期“催诗”之说更为兴盛,除却雨可催诗,如范成大《雨凉呈宗伟二首》其二:“说与骚人须早计,片云催雨雨催诗。”洪适《次景裴席上韵》:“酒未举杯风逐客,诗方拈笔雨催人。”陆游《初春二首》其二:“漠漠春寒罢对棋,霏霏春雨却催诗”等,其他万事万物都可以来催促诗人创作,雪可催诗,如陈与义《又用韵春雪》:“急雪催诗兴未阑,东风肯奈鸟乌寒。”又《舍弟逾日不和,雪势更密,因再赋》:“密雪来催诗,似怪子不作。”陈造《呈程帅五首》其二:“连朝积雨前宵雪,总为催诗陆续来”等。花草树木亦可催诗,如杨万里《答章汉直》:“雨剩风残忽春暮,花催草唤又诗成。”陆游《枕上闻急雨二首》其一:“枕上雨声如许奇,残荷丛竹共催诗。”尤袤《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其一:“把酒问花花解语,定应催促要新诗”等。此时诗债的欠债对象已扩大到自然万物,万物皆可来向诗人索诗。
万物皆可催诗,而春天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所以每到春季诗人们总会感叹欠万物之诗债无处可躲。《诗话总龟》云:“卞震,蜀人……《春日偶题》云:‘诗债到春无处避,离愁因醉暂时无。’”[12](P125)范成大《丙午新正书怀十首》其二:“莫言此外都无事,柳眼梅梢正索诗。”又《春晚卧病,故事都废,闻西门种柳已成,而燕宫海棠亦烂漫矣》:“诗债无边春已老,睡魔有约昼初长。”张镃《南湖二亭落成各书长句一首》其一:“多病半春诗债满,经旬无客酒缘轻。”但是这只是诗人主观的诗债,并非是欠他人的诗歌,所以有些只是口头说说,并不是都会作诗偿还。
南宋时期,从“雨催诗”发展而来的万物催诗,诗人们还将其改造为以诗催物,如范成大《中秋后两日,自上沙回,闻千岩观下岩桂盛开,复檥石湖,留赏一日,赋两绝》其一:“金粟枝头一夜开,故应全得小诗催。”诗人认为桂花一夜之间开放就是自己作诗催促的结果。杨万里《旱后喜雨四首》其一:“旧日催诗元要雨,如今雨却索诗催。”这里化用杜甫“雨催诗”的典故又加以重新翻案,认为雨要用诗歌来催促才能下得下来。又《遣人探梅翟园,云尚未开》:“传语翟园千树梅,不应藞苴索诗催。”诗人调侃翟园的梅花,不要等到自己写诗去催促才开放,应该早些盛开。陈造《早春十绝呈石湖》其五:“杏羞桃涩要诗催,客子情钟倍费才。”诗人调笑杏花与桃花都太过于羞涩,一定要作诗催促才肯开放。这种以诗催物是在万物催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诗人是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来提升诗歌的艺术境界。
笔者看来,诗人认为自己欠万物之诗债,一则是为报答自然界所赋予的审美愉悦,就如同尤袤所说:“无钱可办罗浮醉,报答春光只有诗”(《德翁有诗再用前韵三首》其三),如果没有好诗都愧对于大好春光,“诗无杰语惭风物,赖有丹青传小笔。”(范成大《万景楼》)二则是以诗歌报答自然造化的恩惠,感谢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题诗弄笔北窗下,将此功夫报答凉。”(范成大《八月二十二日寓直玉堂,雨后顿凉》)“恩深到骨吾能报,急赋新凉第一诗。”(范成大《明日复雨凉再用韵二首》其二)中国传统的“诗缘情”观认为必须在情感的激发下才能够作出好诗,而负债则显然不会写出好作品。但是诗人认为欠万物诗债而积极作诗,这是他们的自我加压,在客观上也能够锻炼诗人的写作技巧。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论述“勤读多为”与“艺熟必精”条时,都曾提到“梅圣俞日课一诗”的例子,并引胡仔的一席话:“旧说梅圣俞日课一诗,寒暑未尝易也。圣俞诗名满世,盖身试此说之效耳。”[13](P157-158)陆游的“梅花课”和赵蕃的“日课梅诗”也是这样的一种境界,长此以往的艺术训练必然能够提升写作技能。另外,诗人既认为万物时刻催诗反过来也说明自然造化全都成为诗人笔下的诗料,正如杨万里所云:“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14](P3260)南宋诗人在万物催诗之说的敦促下把眼光投射到大自然,努力发掘新的创作题材,这对南渡诗歌摆脱江西诗派的桎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 “多生债负是歌诗”——前世所欠之诗
有些诗人认为自己前世今生欠下宿债,因而毕生都要努力作诗偿还。笔者考察白居易诗中出现“文债”“诗债”的例子共有6例,其中4例都是指前世所欠之债务,他在《自解》诗中云:
房傅往世为禅客(世传房太尉前生为禅僧,与娄师德友善,慕其为人,故今生有娄之遗风也),王道前生应画师(王右丞诗云:“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
世传房琯上辈子是禅僧,而王维前世是诗人,我审视自己的宿命,生生世世都欠有诗债。佛家讲究生死轮回,前生犯下的业债要到今世偿还,他显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白居易将“负诗债”作为一种宿命坦然接受,将诗歌作为自己所犯之“业债”来偿还,这种负罪心理导致其病中作诗比未病时更加认真刻苦。他在《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中亦云:“老偿文债负,宿结字因缘。”今生所欠之“文债”都是因为自己宿世与文字结下因缘关系。《斋戒》诗中认为自己在斋戒中不仅降服了酒魔,而且还清了诗债:“酒魔降伏终须尽,诗债填还亦欲平。”他在《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中又云: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
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
渐伏酒魔休放醉,犹残口业未抛诗。
君行过到炉峰下,为报东林长老知。
“口业”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由口而说出的一切善言恶语,妄语、绮语、两舌和恶口等都包括在内,诗歌亦属于口业的一种。他笃信佛教,但是在这里却说自己虽然还有“口业”但也不放弃写诗,这可能就与要偿还诗债有关。白居易不仅将“诗债”说宿命化,还试图将其与“口业”不相协调的地方合理化:作诗犯“口业”只是因为要偿还前世之诗债。他一直将诗歌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直到晚年都是老病相仍,仍不废诗*白居易有诗《老病相仍,以诗自解》,见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第2653页。。
口业之说一直存在,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记载了一则趣事:“元丰癸亥春,余谒王荆公于钟山,因从容问公:‘比作诗否?’公曰:‘久不作矣,盖赋咏之言亦近口业,然近日复不能忍,亦时有之。’余曰:‘近诗自何始?可得闻乎?’公笑而口占一绝云:‘南圃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嫋嫋垂。’此真佳句也。”[15](P99)王安石认为赋咏之言是“口业”的一种,但是又觉得自然美景总是撩拨自己写诗,实则这不过是自己一时技痒的托词,他是太爱作诗而顾不得口业之说了。无独有偶,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口业”不断是因为要偿还诗债,他与白居易一样,为自己找到了“口业”与“作诗”更好的契合点。又如《孙莘老寄墨四首》其四:
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
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
今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
先生不讥诃,又复寄诗械。
幽光发奇思,点黮出荒怪。
诗成一自笑,故疾逢虾蟹。
诗人称自己听从朋友的劝戒而闭口不作诗,但是内心又受不了这样的煎熬,今日友人寄来“诗械”——墨,终于忍不住又赋诗一首。他在《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其二中又云:“口业向诗犹小小,眼花因酒尚纷纷。”苏轼将“口业”之说淡化,认为其不可与作诗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口业”之说已丝毫不能阻碍诗人们的创作热情。
晚唐的司空图也曾表达过这种宿命论:“此生只是偿诗债,白菊开时最不眠。”陆游的祖父陆佃亦曾云:“几时诗债许蠲除?直待金鸡放赦书。”(《依韵和双头芍药十六首》其十二)古代大赦时,立一长杆,杆头设一黄金冠首的金鸡,口衔绛幡,击鼓,宣布赦令。诗人认为自己是欠债有罪之人,要等到朝廷大赦之日诗债才能解除。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宿命思想更为强化,许多诗人都在诗中表示要毕生作诗来偿还诗债,陆游也化用了“金鸡放赦”这一典故:“赦书虽未除诗债,盟府犹当策酒功。”(《遣兴》)虽然他的态度较为旷达,但也是认为自己一生都背负诗债。杨万里《送彭元忠县丞北归》:“我欠天公诗债多,霜髭捻尽未偿他。”刘克庄《壬戌首春十九日锁宿玉堂四绝》其三:“老去未偿文字债,始知前世业缘深。”元好问《德禅师清凉草堂》:“多生负诗债,秋物苦催索。”方回《辛卯元日三首》其二:“一生酒债兼诗债,数亩花园半菜园。”经过白居易的改造以及苏轼的论述,诗债已不再纯粹是指欠他人之诗歌,而是成为一种宿命,诗人应该坦然而自觉地接受这一宿命,更加积极主动地作诗。
这些将作诗视为宿命的诗人,无论是在重大节日还是寻常生活,总是兢兢业业、刻苦不怠。范成大说过:“但逢节序添诗轴。”(《满江红·冬至》)每年的七夕、除夕和元夕他都会写诗,每年也都有诗描写梅花与大雁,“岁华书户笔,年例探梅诗。”(《新岁书怀》)“每岁有诗题白雁,今年无酒对黄花。”(《重九独登赏心亭》)即使公务繁忙也要创作,《甬东道院午坐》:“忙里有诗偿日课,老来无赋为秋悲。”这类诗人总是认为自己欠有宿债,至老都是笔耕不辍,所以他们往往创作量巨大,白居易、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刘克庄等人都可以说是著作等身(范成大的作品多有散佚,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16](P540)可见其总量之多),陆游更是迄今为止存诗最多的诗人(约9300首)。
但是不难看出,将作诗视为宿债的诗人其实是在为自己热爱作诗找托词,他们是把诗歌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范成大就特别重视诗歌创作,“官减不妨诗事业”(《与正夫朋元游陈侍御园》),“诗情不浅任尘官”(《峰门岭遇雨泊梁山》),“何物与侬供不朽,西征卷首石湖诗”(《杨少监寄西征近诗来,因赋二绝为谢,诗卷第一首乃石湖作别时唱和也》其一)。陆游亦云:“史限虽严不废诗。”(《示子聿》)这种欠宿债的观念表面看去是压迫诗人们作诗,实则这是诗人主动的自我加压,是他们爱作诗的表现,就如同杨万里所云:“老子平生有诗癖,为君焚却老陶泓。”(《跋姜春坊梅山集二首》其一)两宋之交的王之道(1093—1169)《追和东坡梅花十绝》其六:“醉眼昏昏午倦开,不堪诗债苦相催。”诗人追和苏轼的咏梅之诗,自述不能忍受诗债的催促,实则他与苏轼根本不是同一时代之人,这里所提到的诗债当是他的自我加压,是为还自己的“宿债”。又如范成大《寒夜观雪》:
静极孤鸿响,寒疑万籁喑。
眼花灯下字,髭断雪中吟。
颇似偿前债,非关惜寸阴。
可怜蝴蝶梦,翩作蠹书蟫。
老眼昏花的诗人在苦寒之夜还在搜句吟诗,自言是为偿前世之债。其实不过是因为喜爱作诗才会在寒夜苦吟,但是诗人却将之归之于欠下宿债。
喜爱作诗并把诗歌作为宿债来偿还自然会提升创作数量,然而,过于热爱作诗亦容易形成苦吟之风,上述诗人都曾在诗中提过自己的苦吟经历,如杨万里:“更长酒力短,睡甜诗思苦。”(《夜雨不寐》)陆游:“社栎终无用,秋虫漫苦吟。”(《自警》)刘克庄:“每对忘甘寝,频挑伴苦吟。”(《书灯》)而且作诗过多还会有不经拣选率意为之的情况,沈德潜就曾批判杨万里作诗草率、以多为贵:“苏李数篇,老杜奉为吾师。不朽之作,不必务多也。杨诚斋积至二万余,周益公如之。以多为贵,无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简金,几于无金可简,亦安用多为哉?”[17](P72)陆游诗作近万首,也是瑕瑜互见,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论:“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少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9](P125-126)作诗太多自然免不了意境句式趋于雷同。
结语
虽说诗债说对诗人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类诗人却与之关系较小,李白的诗中就从没有关于欠他人之诗的表述,苏轼虽然与人唱酬交往颇多,但是诗中提到的诗债大都是指欠自己的宿债,与他人无关。笔者看来,李苏二人是属于天才型的诗人,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就将二人归为一类,属于“子列子之御风”,“无待者神于诗者”[14](P3231-3232)的天才诗人。赵翼称苏轼:“其犹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18](P56)他们写作时往往文思泉涌,很少会出现一时语塞而欠下诗债的情况。
值得提出的是,诗债题材的创作多集中于次韵唱酬、咏物遣兴和日常闲适之作,基本与社会现实无涉,这是因为文人提及诗债或是为切磋诗艺或是咏物言情或是苦吟锻炼,多是创作于闲暇之时,所以很少提及严肃的社会现实。
诗债由单纯的欠他人之诗歌演变为一种创作观念,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表述,但是大量的诗歌创作都与之相关,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理应受到重视。三种类型的诗债在一定程度上都敦促诗人积极作诗,诗人们一改传统的等待诗情萌动才开始创作的路数,而是在诗债的鞭策下主动作诗还债,这不仅能够提高诗人的写作技艺,也使得其创作量大大提升。但是,任何一种创作观念的影响都是双面的,以诗偿债有时也会造成苦吟之风,而且对于那些致力于毕生作诗偿债的诗人来说,这种宿命观往往会导致他们作诗过于率意而忽视情韵,清代蒋鸿翮就曾批评杨万里的诗歌:“粗直生硬,俚词谚语,冲口而来,才思颇佳而习气太甚。”[17](P68)不经深思熟虑而信口作诗,必然会出现许多平庸甚至粗俗之作。
[1]〔梁〕萧统.文选[M].〔唐〕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宋〕林逋.林和靖诗集[M].沈幼征,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3]〔宋〕佚名.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张伯伟,编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4]〔唐〕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M].谢思炜,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宋〕释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明〕谢榛.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宋〕吕中.大事记讲义[M].四库全书本.
[8]〔清〕郑燮.郑板桥全集[M].卞孝萱,编.济南:齐鲁书社,1985.
[9]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上)[J].阴山学刊,2001(1).
[11]〔元〕方回选.瀛奎律髓汇评[M].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M].周本淳,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3]〔宋〕魏庆之.诗人玉屑[M].王仲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宋〕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校注[M].陈应鸾,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
[16]〔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湛之.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64.
[18]〔清〕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 徐 炼
王雪(1992— ),女,安徽凤阳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I207.22
A
1006-2491(2016)04-005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