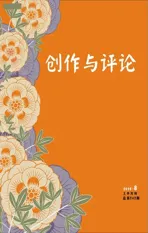李子园春色
2016-11-21石光明
○ 石光明
李子园春色
○ 石光明
秋光渐老的季节,却想起了雪峰山边邵水河畔的李子园春色。
其实,在资江和邵水河双清荟萃的宝庆古城,李子园并非胜景,坐落在这里的邵阳师范专科学校也并不知名,享誉盛名的只是傲居城南的“六岭春色”。然而,三十年前,四季的河流游走到邵水河口处,春雷挟带春水,把河曲山梁上这个叫李子园的地方漂染得春色满园,春意盎然,春景常在,成为了恢复高考后一代学子永远的念想。
在我的记忆中,李子园的春色是可憧憬,可阅读,可回味的。它萌发于改革开放、百废俱兴的时代,蓬勃于师德馨香、青春浪漫的校园,永生于学脉相连、心结绵绵的情怀。
清晰地记得,这一年的早春,料料峭峭,乍暖还寒,三月初了,还没听到布谷的欢鸣,也看不到杜鹃的霞锦,厚实的冬衣仍不敢脱去,裹着少年那颗余悸未平的心魄。刚刚散去的雨雾,把雪峰山中千峰万壑田园村社浸泡得潮潮润润,阴阴凉凉,恍恍惚惚。抬头却已见,一柱柱清光撕裂厚厚阴霾,穿透重重云层,照射到了莳竹古地的山岭河流,敞亮了山中少年久被遮蔽的视野,温暖了刚从寒雨连江漂泊不定中登岸的心灵。经过了欣喜、等待又几近绝望的煎熬,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终于听到了来自遥远北方春雷震响的黄钟大吕,收到了高校扩招后那温暖心窝的补录通知。许多年后,我成为了“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清理干部档案时,高考试卷退还给了我,才明白当年差点“落第”的真正原因。拂去梦中的天潮地湿,收起沾满寒风冷雨的油布伞,心情如清爽的蝉翼飘举蓝天。不禁也如余光中当年在香港新界半岛沙田中文大学一样激动欢呼,“毕竟是春天了”。
怀揣着入学通知书,搭乘一辆拖运原木出山的卡车,开始了新的求学寻梦之旅。车开行的那一刻,我不忍看的是,母亲的笑容显然被泪水浇湿,父亲挺直的身影依然难掩沧桑。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绵绵的大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何况是这个生我养我,晴雨交集,冷暖相伴的家山家园,是这座尘封了孔明南征历史,千年后依然古朴的莳竹小镇,是这方萦绕着知青生涯余韵悠远的绿水青山。带着对父母家园的眷恋不舍,带着逃离隆冬围困挣脱春寒纠葛的激动不安,带着对雪峰山外烂漫春光向往的锲而不舍,兴奋与悲凉交织,眷恋和思量混响。我就像一只雏燕,惴惴而欢快地飞向山外广阔无垠的天地,飞向被资江和邵水滋润了数千年,在甘棠古渡载渡了数千年的宝庆古城,飞向那将任我畅游书山学海的美丽校园的无边春色。
车奔驰着。我憧憬着。远远近近重叠萧瑟的横岭侧峰,总想重演“春风不度”的古人嗟叹,车一近跟前,却猛地出现豁然洞开的山峡河谷,在重重屏障上破开一道裂口,让春的信风循着峡谷吹入。春风过处,一座座青山绿岭,一排排树影如云,一个个集镇村庄,一处处炊烟氤氲,鸡鸣犬吠一阵阵,樵夫牧童一群群,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春的色彩一下子明朗了许多。难怪有人说,春天存于人的心间。心中注满了春日阳光,眼前便也春光明媚了。细看时,森林翠绿得翻出黛色的波浪,树叶青绿得滴落清亮的天光,小草也嫩绿得招展养眼的初妆。毕竟是春天来了,“吹面不寒杨柳风”啊。感悟中,对李子园春色的憧憬愈加强烈。
春天是大自然的一件服饰,春色是人们心绪的一个季节。看着景物在车窗边不停地变换,忽然想起曾经读过的庾信《春赋》中的句子,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俳赋大家,《春赋》是他前期赋作的代表。“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这景象,这感觉,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就说过了。但赋中的“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的妙处,不身临乡间春景,是难以领悟得到的。
初见李子园,很平常的一个山头,正在建设中的景象。据说,学校创建于1958年,其间,几经废立搬迁,前两年才又从数百里外魏源故里迁回古城原址。一幢新建的理科教学大楼,撑起了学校风雨之后弱冠之年的岁月,一片刚平整的环绕八百米跑道的运动场,铺展了刚从十年文化禁锢中放飞出来的一代青年的学步翱翔之路。没有茂林修竹,也没有桃李成行,道路旁稀稀落落看到些新栽的幼株,绿色依然萧瑟。竟没有想象中高等学府的神秘幽深,从大开敞的校门口一眼便看到了后山河岸。在我依然激动着的心海,只是微风吹过,涟漪轻起。确没有后来入读岳麓山下千年学府,面对其悠久历史油然而生的震撼,也没有新世纪初到中央党校进修,与友人漫步未名湖畔北大燕园,留连人文胜景起于心底的肃敬。然而,它带给我的却是春寒料峭中的丝丝温暖,春雨萧瑟后的盈盈温馨。现在想起来,仍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已然从眼前不多的绿树看到了蓬勃的生机和浓浓的春意了。我如同饥渴已久的沙漠跋涉者,远远望见了绿洲,急切地渴望着亲近这早存于梦中的绿色,阅读这已萌芽在心里的春色。
山里孩子没坐过火车,没开过眼界。看电影《铁道卫士》,每当看到大智大勇的公安战士驾着小车与火车赛跑,然后飞身跳上火车与敌特搏斗,火车长啸如飞奔的烈马,拉起的长烟如马鬃一样飘曳,我们的心也便风驰电掣,神往着御风而行的快意。到校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不怕城里同学笑话,就是要去城东的火车站,一睹火车的真容。当时火车路只修到邵阳,一截盲肠路,曾让邵阳人遗憾激愤不已。但在山里孩子眼里,高阔修长的车厢,高昂雄壮的车头,高扬啸叫的汽笛,那气派真叫人惊奇感慨。跟随着远去的火车,平行的双轨一路向远处飞伸而去,连接韶山,连接长沙,连接北京,把天边的春风和春色牵引来邵水河边的甘棠古渡,染新六岭春景双清秀色,在我们这一代人寒窗苦读的李子园种下了生生不息的春光。回到寝室,天已向晚,兴奋不已地向同学说起现在看来非常幼稚可笑的观感和满足。夜色中,一阵悠扬的笛声从宿舍楼不知哪个窗口飘出,带着杨花柳絮的春风,带着穿林打叶的春雨,带着桃红李白的春色。
李子园的春色在哪里?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问老师,问同学好友。得到的答案也有无数个,似乎有答案,又似乎无答案。仿佛这春色氤氲在禅风之中。在李子园的几年学习参悟,我终于读到了满园春色。她,与朝露辉映在墙外桔园邵水河边的晨读,与灯光陶醉于阶梯教室图书馆里的晚课,伸枝展叶于授课老师的声情并茂,蝶舞蜂飞在文学美苑的千古绝唱,风生云起于社会实践的多姿多彩,瓜迭绵绵在同学师生无穷回味的粗根细蔓。
李子园每天都醒得很早。晨光熹微中,九曲的邵水河宁谧如镜面,雾气飘荡,水气淋漓,像一帧刚洗印出水的照片。依稀显影出,数千年前西周周武王之弟周召伯追踪舜帝南巡之路,在这条河边甘棠树下布施王政的情景,显影出两千年前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白善督率士民筑城建堡的场面,显影出一千年前北宋年间,理学宗师周敦颐以永州通判摄邵州事时,迁建学宫,兴办教育,流连爱莲池的故事。早起晨读的男女学生,或坐或立或徘徊,惊起树丛一只只宿鸟。露水未晞的橘叶草丛,在潮湿浪漫的晨氛中醒来,随着学子们来来往往的游走,大气小声的吟诵而前俯后仰,像极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写的,书塾先生诵读古文时神痴可掬的形态,“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俯仰之时,却把露水偷偷沾湿了学子的裤脚鞋袜,也把湿湿的春天的记忆,留在了学子们的心底。
“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真羡慕唐朝诗人宋之问,一日之内,朝夕春景,都收眼底,俱描笔下。而李子园的春夜,窗户依然是寒窗,主题依然是苦读。所有的教室,都是灯火通明。明亮的日光灯下,三三两两散坐着不同系科专业,或捧卷静读,或埋头笔记的男女学生。晚自习的时光,格外安静。在专心攻读的学子眼前耳旁,门外没有杨柳风,窗外没有桃李月,室内也很少窃窃私语。然而,寂寂的夜风总是挟着草木的清香和醒人的凉意,闯入教室,旋着华尔兹舞步,偶尔翻乱几张书页,招惹得冷冷的灯影似乎想蠢蠢欲动,让本在静心研读的年轻学生也生出些异样的情愫来。
生于晚清的祖父,少年时只上过几年书塾。听说我在学古文啃古籍,一本新华字典已不够用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那个荒僻的乡村,在那个“文革”洪流刚刚退去的年月,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踩了多少门槛去寻找,也许还把父亲寄给他的不多的生活费也花掉了,却让我喜出望外地收到了他亲手寄来的一本康熙大辞典。后来才听说,祖父的宗亲里曾出过不少读书人文化人,有大学教授,有达官显贵,乡下没有旧书铺,祖父就是从一位族人家里,很费了些功夫把这本辞典淘来的。这本康熙大辞典很有点年头,好像是民国时的版本,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封页掉了,前后一些页面也有缺损。经过十年“文革”浩劫,能保存下来就属不易,又焉能奢求完好呢。捧着厚如砖头的大辞典,如登山得到一根拐杖,行船得到一把橹桨,执着的访客得到了一块敲门砖。我徜徉在李子园,安坐于明灯下,去寻芳历史的春天,访胜春天的历史。敲开被岁月尘封的门窗,一抬腿,一探头,就与先秦两汉的春天撞了一个满怀,与春天的唐诗宋词共同葳蕤欢唱。
不经意间,我来到了《诗经》里的郑国,清澈浏亮的溱洧河边。“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你看,三月的上巳节到了,溱洧水流淙淙,欢畅春游的男女们纷纷来到水边,采摘芳香的泽兰;情思缱绻的情人,相互赠送着美丽的芍药花。文学史家曾说,郑风绮旎。是啊,一幅欢快明丽的春景,永远刻画在溱洧河上。几千年后,人们读来仍感到香风拂面,春意盎然。
走进汉乐府的园林,只见:“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前面一段写景比兴,最后两句点出主旨。劝谕人生应抓住青少年的黄金时期,努力学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老来才不会怨悔。一曲《长歌行》,两千年前就把市井流传妇孺皆晓的民歌,唱成了一首春天畅想曲,一章青春励志篇。乐府的春天竟如此的蓬勃向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成了历朝历代千家万户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
唐诗宋词是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这里的春色更是多姿多彩,浪漫绚丽。攀登途中,可随手采摘韩愈的“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可随处观赏杨万里的“不如卧听春山雨,一阵繁声一阵疏”,还能随心品味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千古佳境。当然,唐宋诗词史的春光也有凄美悱恻的一页。“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二月二日》是李商隐描写踏青节的一首七律,也是其诗集中很有特色的一首。李商隐惯以深沉凝重的笔调,婉曲晦涩的用典,描写恋情爱情,吟咏历史,酬唱应和,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名句,风流千古,光照诗坛。而他晚年在东川柳仲郢幕府写作的这首律诗,却一反过去风格,通过对春天踏青欢快节景的描写,表达了在陷入牛李党争,长期潦倒困顿中,得到正直惜才的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扶助信任,荐为检校工部郎中,用为幕府判官之后,轻缓舒畅的心情。思接千年,我不由得也为李商隐舒了一口气。然而读完后四句,方觉得生活磨难对诗人的影响太深太深,“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前面几句所写的美好春景,所用的欢快笔调,却是为了反衬出诗人压抑郁闷的情怀。那沉重的春愁,让诗人一背就是上千年。
春光旖旎中,又看到苏轼的《蝶恋花》了。苏轼是宋词中豪放词的领军人物,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句“大江东去”,就激起古今多少文人万丈豪情,千年惊涛。俞文豹曾把苏词与柳永词作比,说“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折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在我看来,他的婉约词也不比柳词逊色,《蝶恋花》就是代表作之一。你看,岭南的暮春景色被他写得多么灵动美丽,景中含情:“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前几句寄寓了春光渐逝的伤感,然后词意一转,表明了坡公相信天涯到处都有春天,不管自己身处何地,也能处之泰然的旷达。但到下阙最后一句,却又一转,“多情却被无情恼”,那一份无奈和自嘲,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又把春天弄得有点凄切伤感。浓重的伤春情绪,令人唏嘘不已,难怪尽管词很美,跟随词人身边的侍妾王朝云竟不忍歌唱它。
阅读中,历史和文学的春色,移植成为心中的春光,又把李子园的春意装点得愈加明媚,也愈加迷濛,愈加鲜艳,也愈加沧桑,愈加晴阔,也愈加幽深。
在李子园的春色里,我们阅读寒暑,阅读四季,想象着把四季都染成和煦美艳的春色,让四季美如画,神州春常在。走出李子园的日子里,我们阅读自然,阅读社会,期盼着把社会建设成生态和谐的家园,让李商隐的春愁,苏东坡的伤春不再重演。多少次,车过邵水桥,总忍不住伏窗南望。望穿一曲春江秋水,望透几重绿丘红楼,李子园的春色,母校的温馨,便袅袅升起在视野上方,直到车已驶远。
石光明,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岳麓山下》(作家出版社出版)、七绝诗集《潇湘听雨》(岳麓书社出版)、诗集《难忘是乡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等。散文、诗歌作品多次被收入多种作品年选、获奖和被选刊转载。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