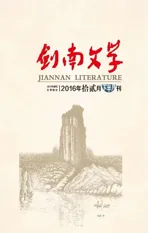乞丐意识的潜隐表达
——论《钟鼓楼》中环境与人物设置的共性
2016-11-21杨高强
□杨高强
乞丐意识的潜隐表达
——论《钟鼓楼》中环境与人物设置的共性
□杨高强
引言:刘心武的《钟鼓楼》通过集中描写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不仅丰富了现代化转型语境中社会文化反思的横截面,还借助环境和人物形象的共性设置渗透出一种“庸俗的、功利取向的、苟且偷安的”底层民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本文以“乞丐意识”作为切入点,考察作品中环境及人物设置的共性特征,揭示作品对底层小市民阶级精神文化状态的叩寻与关切。
“乞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且有着悠久的存在历史。乞丐文化的独特内涵,在文学再现说的视域中,颇为符合塑造“典型”的美学要求,在文学书写的发展史中,不仅能够“形而上”地抽离出独具规模的“乞丐”人物群像,还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符号话语介入有关文学形象的认识活动。
“乞丐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以周德钧的《乞丐的历史》较具代表性。据其表述,“乞丐文化”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边缘性的亚文化类型的文化,一种底层民众的文化,一种弱势群体的文化。”周德钧认为,由“贫困、天灾人祸、差别与不平等、文化张力”四种社会根由产生的乞丐文化,在集体性的精神层面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为:“庸俗的、功利取向的、苟且偷安的、消极无为的、放浪自任的”。自五四以来,有关国民性探讨的问题内涵与“乞丐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特征既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义性,也可以将后者视为前者的表现内容。
刘心武的《钟鼓楼》集中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日常生活,渗透出一种“庸俗的、功利取向的、苟且偷安的”底层民众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态与周德钧关于“乞丐文化”的定义不谋而合。一直以来,刘心武的《钟鼓楼》倍受民俗学和叙事学研究者的推崇,其精神意蕴和文化意识层面较少受到关注。本文着重探究作品的环境和人物设置方面具有的共性,即“乞丐文化”意识形态的体现。
一、环境设置中的乞丐意识
《钟鼓楼》中,“鼓楼”和“钟楼”以跨越时空的文化权利象征和时间发展的指涉意义构成了颇具文化意蕴的文学形象,与鼓楼周边的底层社会生活环境构成社会转型发展中现代与传统、发展与变革的映照关系。“改革开放”的驱动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小市民阶级的生活并没有大幅提升(“乞丐文化”成因中的“贫困”和“差别与不平等”的体现);而在饱尝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及“大跃进”带来的苦果、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之后,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随着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呈现出滞后问题(是人祸、也是文化张力不足的体现)。人们在寻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满足无果的情况下,一种“庸俗的、功利取向的、消极无为的、放浪自任的、苟且偷安的”的“乞丐意识形态”不禁滋生出来。
对“社会大环境”和“四合院的特定场景”的描写是《钟鼓楼》中呈现的主要的环境空间。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和逐步实施阶段,但是,基于各种文化心理成因,为之后人民群众所诟病的一些社会现象已渐露矛头,诸如“官僚主义”、“走后门”、“干部子弟特殊化”等社会风气形成了不言自明的社会暗潮。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之下,人物命运的复杂性由此生成。狭窄闭塞的四合院环境和一个新旧事物不断碰撞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乞丐文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刘心武解释写作《钟鼓楼》的初衷即是追求“一种原始的历史流动感”。“四合院”,尤其是北京城内、建于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四合院当年的主人看似与今天的九户居民毫无瓜葛,但通过作者对四合院详尽的描绘,我们似乎在空间的连接中找到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今日四合院居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丝丝缕缕的联系,使我们不禁感到昔日的四合院文化竟还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沉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以至于这种安详的、独门独户的、不被打扰的四合院生活仍然是小市民们生活追求的最高奢望。原本雕栏画壁的四合院虽早已成为了狭窄闭塞、堆满各种杂物、“鱼龙混杂”的大杂院,但却在文化特征上摆脱了原有的单调色彩。作者通过描写当时人们的住房条件以及生活设施,表现了这一批底层小市民生活的窘迫,从而为解释“乞丐文化”的产生做好了铺垫。
从父母双亡后路喜纯在小饭馆里保守排挤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就业分配难”、“走后门”、“干部子弟特殊化”的社会大环境。由于路喜纯贫贱的出身,即使手艺远在“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之上,却也只能屈居做主食的白案。跟路喜纯年纪相仿、出身相似的青年人荀磊也受到了同时代大背景的限制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在他自信满满地将一部“不走后门、不拉关系、不靠取巧、不凭侥幸”且具有“敏而适时的选题、通达而流畅的译笔、必要而准确的注释”的译稿交给了编辑部,却惨遭退回,原因仅仅是他二十二岁的年纪不具说服力。在经历了出国留学和外事部门的工作之后,他的英语事业看似已经开始风生水起了,但终究也还抵不过当时社会的“惯性思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小子不配在译作上署名。从这两个年轻人饱受时代制约个人发展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一个阿谀奉权贵、论资排辈的时代环境就是“乞丐文化”的“培养基”。
二、人物设置中的乞丐意识
《钟鼓楼》在对人物形象的概括中,有一个与“乞丐文化”特征呼应的词语——“浅思维”。所谓的“浅思维”是指“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思维方式”。这一群出身与低文化水平家庭、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的人,在面临世界和人生的流逝时,往往并不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无论是在动荡不安的旧社会还是在温饱有靠的新社会,他们所关心的也还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会不会动摇。这种“浅思维”就是造成他们消极无为、放浪自任、苟且偷安的根本原因。
卢宝桑这一人物形象较为集中体现了“乞丐文化”中的消极无为、游手好闲和放浪自任的特征。卢宝桑出身于一个乞丐世家,爷爷曾经是丐帮的一个“杆头儿”,父亲也是一名职业的“硬乞”。他行为的粗俗与野蛮和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卢宝桑在宴席上那种颐指气使地吆喝路喜纯的行为与其父卢胜七在浴池中指使服务员泡茶的举动简直如出一辙。乞讨时的低声下气和支配人时的耀武扬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信奉着弱肉强食的生活信条,而又弄不清自己是弱者还是强者。在有机会指使别人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自己的支配欲。但当他处于屈辱地位的时候,也并没什么屈辱和沦落的窘迫意识。文化大革命中,当卢宝桑由“红五类”变成“黑五类”任人批斗时,他也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还甚至“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占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臀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可以斗人,也可以被人斗,可以糟践人,也可以被人糟践,这无疑是人格缺失的突出表现。
《钟鼓楼》中体现的“乞丐文化”不仅渗透在环境中,而且引申到作品中每一个人物形象身上: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荀磊在向机遇乞讨,敢爱敢恨的慕樱在向真爱乞讨,柳暗花明的澹台智珠在向名利乞讨,凡事都讲究名牌的潘秀娅在向欲望乞讨,四合院的院里院外的每一个人都在向生活乞讨……实质上,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向命运乞讨的众生并不是个例。藉此反观刘心武创作《钟鼓楼》的初衷,纵览近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底层市民的命运沉浮,一种根植于国民文化深处的人性本质似乎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改头换面。自“五四”启蒙文学揭示出国民性问题以来,以此为中心展开的探讨不仅在问题的深度上渐次开掘深挖,还在问题涉及的广度上不断探索发现。《钟鼓楼》中浸透的“乞丐文化”意识形态即是在这一问题广度层面的重要铺陈。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