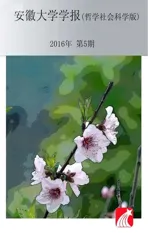清代皖江流域的徽商
2016-10-09张绪
张 绪
清代皖江流域的徽商
张绪
清代的皖江流域是安徽境内极具经济活力的一个地区,其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徽商等客籍商人的推动。作为当时的一支商业劲旅,徽商遍布于皖江流域的重要市镇,从事盐、典、粮食、牙行、棉花、布匹等生意,经营领域甚为广泛,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徽商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在皖江流域广施善举,诸如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济灾民、主持正义等,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儒家的“仁”“义”思想,推动了地方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
清代;安徽;皖江流域;徽商;徽州;徽学
皖江流域*近年来,安徽学界围绕皖江流域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于“皖江流域”这一概念仍没有统一的定义。程必定、朱洪、汪谦干、汪军等在相关论述中探讨过皖江地区的空间范围,基本上指安徽沿江地区。“区域”这一经常被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术语,正如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并不是指一个由一些关键因素如语言、宗教或大宗经济产品所构成的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的地带,而是指由一些层次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一个区域,其主要的特点并不是内部的同质性(尽管在一些次等因素如方言上会相同),而是在功能上的差异性”([美]林达·约翰逊主编:《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本文所指的“皖江流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界定的,即基本包括了安徽沿江地区,具体而言有安庆、池州、宁国、庐州、太平、和州、滁州等府州。地处安徽沿江地带,在清代是安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张绪:《清代皖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概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张绪:《清代皖江流域市场的发展概况、特点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也是文化昌盛的地区。从水系看,皖江流域基本上是一种以长江为主干,两岸众多湖泊、河流向中心汇聚的“枝干状”水道格局,皖河、裕溪河、菜子湖水系等由江北向长江汇聚,黄湓河、秋浦河、九华河、青弋江、水阳江等由江南向长江汇聚。这些河流与长江相连,依赖于水道这一天然纽带,在物资贸易的强化下,各地区之间具有一种经济上的自然联系,又进而融于更为宏阔的长江流域经济区。降至近代,这种经济联系又随着芜湖米市的崛起和芜湖的开埠,更趋紧密,区域性经济特征更加凸显,正如前人指出的:“芜湖扼中江之冲,南通宣歙,北达安庐,估客往来,帆樯栉比,皖江巨镇,莫大乎此。光绪初,创建新关,外商纷至,轮舶云集,内外转输,沪汉之间此为巨擘。”*查钟泰:《芜湖新修县志序》,民国《芜湖县志》卷首。“皖中、皖南各县产品之输出,与外货之输入,莫不以芜埠为转运吐纳之总汇。”*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1933年,第1页。在这一区域,不仅存在着芜湖这一区域中心市场,还存在着其他具有不同经济功能的市场层级,它们在区域内部及与外部区域的商品交换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地位并相互依赖的地区系统。从这一意义上说,皖江流域可谓当时安徽乃至全国一个较为重要的经济区域。
皖江流域曾经聚集许多客籍商帮,作为商界劲旅的徽商也是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商业力量,他们在促进当地商业发展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推动了地方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在现有徽商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多选择徽商人数较为集中的“江南”作为讨论的空间范围,对于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也仅仅将目光投注于汉口、芜湖、南京、上海等沿江一些重要商业都市,进行点状式的分析,对于徽商在明清长江流域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则缺乏总体考察。以安徽皖江流域为例,该地区是明清长江流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米谷输出贸易是其主要商业特色,而其商业的发展主要为包括徽商在内的客籍商人所推动。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徽商在皖江流域活动的考察尚不充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点状式的局部研究,讨论的地区仅限于芜湖、巢湖等地*王廷元:《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陈恩虎:《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缺乏对徽商在安徽沿江地区经营活动的全面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所用史料多为地方志,对于徽州族谱、文书等史料的利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在努力爬梳多种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地方志、族谱、文书等文献资料,对徽商在清代皖江流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进行研究,以揭示徽商在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化对徽商与明清长江流域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
一、徽商在皖江流域的商业经营活动
清代的皖江流域在参与长江流域经济贸易的同时,当地的城镇经济非常活跃,农商业发展兴盛。因与徽州相去不远,此地亦成为徽商开展经营活动的一个理想据点,在当地许多城乡市镇都留有他们的足迹。
芜湖是清代安徽沿江的重要商埠,地理位置优越,“东借长江可达镇江、南京,西南溯江以上可达安庆、九江、汉口,西北恃内河与淮南大平原之巢县、无为、庐州等处连接,南经鲁港与南陵、宁国相通,为全省水道中心”*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交通篇》,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1930年,第15页。。早在北宋时期,芜湖就已经发展成为沿江重要的都会和手工业、商业兴盛的港口城市*马茂堂:《安徽航运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至明清时期,芜湖的商业发展更趋兴盛。明人黄礼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民国《芜湖县志》卷8《地理志·风俗》。清康熙年间,芜湖“市衢蕃殷,货财辐辏,肩摩毂击之盛,甲乎寰宇”*寿以仁:《新建江防公署记》,乾隆《芜湖县志》卷19《艺文志·记上》。。乾嘉时期,“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嘉庆《芜湖县志》卷首。。这座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吸引和聚集了不少外地客商,“居厚实,操缓急,以权利成富者,多旁郡县人。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即使“同光以来,邑人以商业致富者颇不乏人,较之旧俗,大有进步,然城镇乡各处,大率业砻坊者居多,此外各业,仍不若客籍之占优胜”*民国《芜湖县志》卷8《地理志·风俗》。。显然,客籍商人群体在芜湖城市的商业发展中占据着优势,而这种情况又造成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外来商业性移民人口日渐增多,“五方杂居者十之七”*光绪《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在这些客商中间,徽商是一大商人群体,他们是参与芜湖商业市场竞争的一支劲旅,来此从事贸易的徽州商人不在少数。如黟县岭下人汪文雅,原是一名邑庠生,因为家庭贫困,“后赴芜湖,为商号司笔札,谨慎自饬,善居积,以此致小康。后营商业,获利益多”*民国《黟县四志》卷6《人物志·质行》。。婺源理田人李上葆,“家故贫,弱冠,佣工芜湖,备尽辛劳,中年贷本经商,家道隆起。……性慷慨赴义,芜湖建会馆,倡输千余金,秉公任事,交游咸器重之”*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十·义行七》。。作为皖江流域中心市场的芜湖成为徽商从事商业活动、追逐商业利润的一个理想之地。
在皖江流域的其他府县,也有徽商的足迹。如在庐江县,“民悉土著,故为商贾少。厥产惟谷,厥货惟矾,皆外来之人兴贩,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之人开设铺号”*光绪《庐江县志》卷2《舆地·风俗》。。在全椒县,“民安耕读,不习外事,客商多麇集于此,若闽、若苏徽等帮商,业最巨”*民国《全椒县志》卷4《风土志·风俗》。。在天长县,有婺源查氏族人来此经营商业贸易,除查文濂外,本为塾师的查公集亦“弃儒就商,偕其兄荣商于天长铜城镇”*光绪《婺源查氏十一修族谱》卷尾之三《文翰·行实》。。黟县环山余氏有不少族人曾在皖江流域的许多城镇从事商业活动,如光禄公,在咸丰兵燹以前,“初学贸于棕阳”;世勋公,“习商怀宁石牌,勤谨经营,常为商人所奖许”;祥元公,“服贾大通(皖江),勤谨经营,其筹划有如老成,最得资本家信用”*民国《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18《懿行》。。荻港镇为繁昌县境内一座商业重镇,余氏族人亦多选择在此经商。如光标公,“性诚朴,年十五,习商荻港。咸同匪乱,店中伙友星散,公以食人之禄,义不忍避,力为店主护持货财,备历艰险,颇为商界所推重。乱平,店主人两分其店相酬谢,不受。年六十,以老病辞归,店少主以巨金为公修养之费,又谢不受”*民国《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18《懿行》。。余光标从十五岁到荻港经商,一直到六十岁才归老故里,他寄身荻港镇的时间确实很久。族人朝旺公,“幼孤,事母孝。及长,作贾荻港,有能名。嗣见汽轮通驶,预测芜湖商埠当兴盛,乃献议于资本家,往芜营业。是时,芜埠荒凉,远不及荻港。未几,果蒸蒸日上,商界咸服其卓识”*民国《黟县环山余氏宗谱》卷18《懿行》。。身处时代变迁大潮中的余朝旺没有故步自封,对于新式交通背景下芜湖和荻港镇的商业发展前景做了很好的预判,体现出敏锐的商业战略眼光。黟县黄村人黄澜,“贾于安庆,有信行”*同治《黟县三志》卷6下《人物志·质行》。。该县紫阳里人朱照开,亦“商于安庆”*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志·尚义》。。休宁人汪琼生“年十一丧母,父先义久出未归,遂肩贩四方,访寻其父”,后“至池之大通镇,与父遇,因赁居居其父,仍小贩以供菽水”,在大通镇经商长达二十余载,至其父离世,仍“日市贩,夜守柩”三年*道光《休宁县志》卷14《人物·孝友》。。歙县人汪良蛟,“服贾青阳”*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江长遂为光大家声,“与长兄季弟共相筹划,业鹾宛陵(宣城古称),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赀累万”*乾隆《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布政司理问长遂公按察司经历长遇公合传》。。
即使在交通不畅的山区,亦有徽州人在当地经商。宁国位于皖南多山之地,与徽州毗邻而处,当地不乏徽商身影,徽州的周氏家族就有不少族人在宁国的一些重要商镇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如周创顺,“旅商宁邑河沥溪镇,历充本镇总董、筹议公所,议民团总长,卓著能声”*民国《周氏族谱正宗》卷9《鱼龙川》。。周顺定则“创业于宁国之港口镇,体恤人情,得同事心”*民国《周氏族谱正宗》卷12《传记·顺定公顺春公合传》。。周兴维亦“客贾宁国之港口镇”,“能自谋商业,久,乃信用渐著,远近争与通往来,商业日益盛”*民国《周氏族谱正宗》卷12《传记·兴维公传》。。在咸同兵燹后,绩溪鱼龙川周氏族人在周永顺的率领下,来到宁国经营油业生意,“艰难缔造,备极辛勤”,颇有开创之功,“今其遗业基址巩固,获利丰厚,族之与股者咸享幸福,公与有力也”*民国《周氏族谱正宗》卷12《鱼龙川传·永顺公传》。。绩溪坦川洪氏族人则在旌德、泾县等地开设商肆。如在咸同兵燹之后,洪会昌投身商海,获得成功,“所业骎骎日盛,闻于一乡焉”。此后,又进一步向外拓展业务,“广设商肆,遍及旌城三溪、泾城、芜湖、扬州各埠,商业之盛,一时无比”*胡祥木:《洪会昌太翁家传》,民国《坦川洪氏纂修宗谱》卷2《列传》。。洪荣章,曾“服贾旌城”,后又“转商三溪”,经过几番打拼,“不数载间,习知商场情伪,操奇擅赢,遂为商界翘楚,以此营业日增,今更推及于泾、芜各埠矣”*王鸣:《赠绩溪洪荣章国珍昆仲序》,民国《坦川洪氏纂修宗谱》卷2《文苑》。。
随着徽商经营活动的频繁,清代皖江流域出现不少由徽商创建的商业性会馆。如在怀宁县,“徽州会馆在大墨子巷,徽州人公立”*民国《怀宁县志》卷4《会馆》。。芜湖县的徽州会馆,“康熙间建,在西门内索面巷”*民国《芜湖县志》卷13《建置志·会馆》。。在合肥、南陵等县亦有徽商所建会馆*吴介五:《合肥的外籍同乡会会馆》,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肥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182~185页;民国《南陵县志》卷10《营建》。。这些会馆的兴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在此地区经商的活跃。
由上可见,清代徽商在皖江流域的活动范围甚广,他们既聚集在沿江重要商业都会城市芜湖,也大量散布于其他城镇。可以说,在清代皖江流域的市场发展过程中,他们有着颇高的显示度,是该区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关于此点,我们还可以从其经营行业中予以佐证。在清代皖江流域,一些关乎民生或代表当地主导产业的重要行业领域基本上都有徽商涉足其中。明清时期,盐、典、茶、木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四大行业。皖江流域属于淮盐售销区,在这一地区从事盐业生意的则主要是徽州商人。如在巢县,“商所货竹木、布帛、钉铁、油麻,皆外商所贩,巢民性惮远涉,无行货者,即为行货,亦土产、稻米、鱼、薪而已,而盐策独徽商巨贾司焉,巢之市贾要皆取诸外商,以资贸易”*康熙《巢县志》卷7《风俗志》。。可见,巢县的商业主要为外地客商所把持,在盐业生意方面,徽商独擅其利,居于垄断地位。无为州亦“食卤于淮,濡之引皆徽商行掣分销,四民取给而已”*嘉庆《无为州志》卷2《舆地志·风俗》。。在和州,徽人江仲馨自二十一岁就“代扬商领销和州引盐”,“在岸辛勤四十余载”,并在当地购置店屋、庄田等产业*江氏:《二房赀产清簿》,复印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资料室藏。。
相近色的搭配,不像撞色那般猛烈,反而会更耐看、温婉,和煦如冬日暖阳,给人不凛冽的感觉,是十分“治愈”、闲适、可人的搭配。
粮食行业也是徽商在皖江流域十分看重的一个商业经营领域。在明清时期,皖江流域是参与长江流域米谷贸易市场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巢湖流域、沿江宣芜平原等地,稻米贸易极为兴盛。如无为,“县无异产,以地多平原,水道如网,夏日炎热,雨量丰沛,故农业盛,而尤以为米为最。圩田之多,甲于全皖,即巢湖五属舒、庐、无、巢、合,亦无与拟者。……所产二分之一供民食,余皆输往芜湖销售,为全县生计之所赖,或以无为为皖省产米中心,由此观之,并非过誉”*民国《无为县小志》第四《物产》。。在米粮贸易的推动下,皖江流域的市镇经济呈现出显著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粮食贸易市镇众多。如位于舒城、庐江、合肥三县交界之地的三河镇,汇舒、庐、六诸水,“河流宽阔,枝津回亘”*嘉庆《合肥县志》卷3《疆域志·关口》。。地理位置的优越,加上当地及周边盛产米谷,使得该镇迅速发展成为安徽境内一个重要的米粮集散市场,“米廪比栉,商贾至,负贩不竭”*左辅:《重修〈合肥县志〉序》,嘉庆《合肥县志·序》。。在产粮重镇无为州,其辖境内的襄安镇、黄洛河镇也是两个重要的米谷集散市场,据称:“襄安镇为西河、永安水汇流处,且为陆路往桐、庐之渡口,昔汉襄县治也,在城西南四十里,为西部米粮集中地”*民国《无为县小志》第六《城镇略述》。。黄洛河镇,“在治北三十五里,当外河、濡须水汇流之冲,东往含山、北入巢境必经之地,米之出口多由是,故成市集”*民国《无为县小志》第六《城镇略述》。。这些市镇都因粮食贸易的发展而兴盛,它们成为编织和构建皖江流域粮食流通网络的一个个重要节点*张绪:《清代庐州地区的米谷贸易与商业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在清代皖江流域的粮食市场中,徽商的表现十分活跃。如黟县商人郑嘉莲,“字濂若,上轴人。……尝于桐城金山墩卖米,自江西运之”*嘉庆《黟县志》卷7《人物志·尚义》。。歙县商人吴无逸,“席先业,鹾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于运漕,致富百万”*民国《丰南志》卷9《艺文志·建置·松石庵》。。又如“采石有某大姓者,家畜舟,募水手撑驾,以是取利。有徽商某于其家雇舟载米,往吴门粜之,价适腾贵,二三日即尽,获利且倍,趋还,再贩之京口”*《旧小说》己集《诺皋广志》,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196页。。绩溪人章传仁也是一位在粮食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商人,原先他的家庭十分贫困,“初执艺以养父母,嗣偕兄弟兴贩稻粱于宛陵,亿每多中,不数十年,遂以起其家”*民国《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
此外,还有不少徽州商人在皖江流域从事典当行业。如在乾隆时期,裴宗锡抚皖时,为了疏浚怀宁县境内漳葭港河道,“假藩库城工余款四万七千两,以二万两为浚河之费,以二万七千两分给安、徽、宁三郡典商,宽期十稔,起息以偿”*裴宗锡:《浚漳葭港河道碑记》,民国《怀宁县志》卷2《山川》。。在安、徽、宁三郡典商的协助下,最终顺利了完成此项工程。除了政府大兴工程需要借助典商之力外,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与典当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结构上,清代的皖江流域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百姓主要从事农耕生产,米谷是市场流通的大宗商品。农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调剂以及粮食贸易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典当、钱庄等传统金融行业给予支撑,因此,这些行业在当地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不少徽州典当商人聚集于此,以追逐其中的商业利润。如在巢县,就有徽州典当商人在一些重要商镇开典设铺。黟县人汪国玺,中年时被“休邑陈姓聘往巢县主持典事,克称厥职”*民国《黟县四志》卷6《人物志·质行》。。再如,在遗存的徽州商业文书中,也有徽商在巢县商镇开设典当铺的相关文书。为说明问题,将文书内容照录如下:
时调巢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王为谕知事案,据烔阳典商陈谦益以地僻易稀,所质当本不及他典之半,力不能撑,陈情收歇,请示召顶等情到县,本县留心体察,该典开设烔镇,西接合界之长龄河,北接柘镇,东达巢城,南属焦湖,其长龄河与柘镇近添数典。该典乡址甚窄,皆系乡僻村庄,质当货物尽系粗布农具。该商所禀地僻易稀,架本无多,委系实情。若遽准收歇,又恐一时召商乏人,有妨民便。查邻境典铺有一典、半典之分,当经批饬典承,悉心查议。兹据该承禀称,查得巢境魏家坝地方向有典铺朱允升,因易稀疲闭,随召陈肇祥接顶。开张未及数载,即据陈肇祥以地窄易微,不堪承领全典发典生息款项,禀请减半输税等情,禀蒙前宪,议将该典原领奉发生息本银提回一半,归于同县各典,均匀摊派。以后凡有一切捐输、盘查、捐派公事等项,悉照半典承应,稍抒商力,详奉藩宪批准,遵行有案。今陈谦益所禀情节,与陈肇祥典事同一律,可否援照办理等情。据此,并据抄呈陈肇祥原案,前来本县查核,议禀仿照陈肇祥典调剂成案,以抒商力各情,尚属允协。除批准照议饬遵外,合亟谕知。谕仰县境城镇典商公凝泰、陈裕丰、白义兴、鲍恒裕、孙源丰、任庆源知悉,所有烔阳典铺陈谦益原领巡江、颜料、快丁三项生息本银,各皆提出一半,归于该商等均匀摊派,营运缴总。其以后凡有续发生息本银及一切捐派、盘查公事,咸以六典半均派,永远遵守,以资调剂,而抒商力。仍即换具领状,同遵照缘由,禀覆备案,毋违,切切!特谕。
道光拾年七月日谕*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从这份官府文书中可知,在道光年间,徽州典商陈谦益在巢县烔阳镇(今作烔炀镇)开设了一家典铺,但因生意欠佳,“所质当本不及他典之半,力不能撑”,于是向巢县官府请求歇业。对于陈谦益的歇业请求,巢县官府担心“若遽准收歇,又恐一时召商乏人,有妨民便”,于是仿照陈肇详典成案,以“半典”方式,即将陈谦益典铺原领巡江、颜料、快丁三项生息本银,各提出一半,分摊到该县其他典商的典铺中,以缓解陈谦益的经营压力。这份文书表明,在清代,巢县的重要商镇烔阳镇曾是徽商开展商业活动的一个聚集点,典当行是他们在此投资经营的一个重要商业领域。
在巢县另一商业重镇柘皋镇,则有徽州杂货布商在此贸易营生。《休宁汪姓誊契簿》中有一份康熙年间的包揽承管合约:
立包揽承管议墨人吴隆九,今自情愿凭中包揽到汪嘉会、全五二位相公名下新创汪高茂字号在于柘皋镇市开张杂货布店一业,计本纹银五百两整,当日凭证,是身收讫。三面议定,每年一分六厘行息,其利每年交清,不得欠少分文。其店中各项买卖货物等务,俱在隆九一力承管,其生意立誓不赊押,其房租、客俸、店用、门差悉在本店措办无异。凡店中事务,以及赊押并年岁丰歉盈亏等情,尽在隆九承认,与汪无涉,但每年获利盈余,尽是隆九独得,银主照议清息,不得分受。自立包揽之后,必当尽心协力经营店务,毋得因循懈怠,有干名誉,责有所归。所有事宜,另立条规,诚恐日久弊生,开载于后。今恐无凭,立此包揽承管议墨存照。(中略)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
日立包揽承管议墨人吴隆九(押)
凭中证人 汪起龙
诸位朝奉同见程子有
佘子衡
汪永清
依口代书人吴学贞*《休宁汪姓誊契簿》,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3页。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徽商在清代皖江流域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动,不仅经营地域广阔,而且在当地的主要商业领域都很活跃,有的甚至居于垄断地位,其商业势力不容小觑,这些也反映出清代徽商与皖江流域商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
二、徽商在皖江流域的义行善举
徽商“贾而好儒”,素有儒商之名,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强调以“义”取“利”,“义”“利”并重。如黟县商人吴国珍,“贾于桐城枞阳镇,为人悫直,经商垂五十载,一介不苟取,事人及自
营业皆能以义为利”*民国《黟县四志》卷6《人物志·质行》。。王国椿,“贾于太湖徐家桥,垂五十年,信义素著”*民国《黟县四志》卷6《人物志·质行》。。在安庆开设磁铺的婺源人詹元甲因擅长诗词,与知府陈其崧交好。后遇大祲之岁,“陈槖金二十余万,力请采办米粮,谋再三,乃诺。既至其地,逆旅主人曰:‘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也。’元咈然曰:‘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十·义行七》。詹元甲没有按照成例,为满足一己私利进行抽息,而是舍利取义,克己奉公。在儒家义利观念的深刻影响下,徽商在追逐和收获商业利润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他们广施善举,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据称:“我江南言乐善好施者必曰徽人,言多财善贾者必曰徽人,徽人遂好施善贾名天下。”*周赟:《义仓序》,光绪《绩溪县南关惇叙堂宗谱》卷8《序》。在清代的皖江流域,徽商的义行善举亦不胜枚举。
1.捐资兴修基础设施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财力所限,除城池、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主持兴修外,其他如桥梁、道路、渡口等基础设施一般多由民间自行建造。在这些基础设施的兴修过程中,商人们常常会有所作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建设*张绪:《清代皖江流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安徽史学》2008年第5期。。在皖江流域,徽商出资兴修基础设施的情况十分常见。如婺源人江起辛,“服贾孝养,喜周利济,尝……在澛港建渡舟,置田永济”*光绪《婺源县志》卷36《人物十一·质行二》。。来往于吴楚之地的婺源籍商人程待诏,“性好施,尝多义举”,曾在芜湖建造义渡*光绪《婺源县志》卷32《人物十·义行四》。。在巢县橐皋镇东三里许有座古探花桥,“岁久倾颓,一遇淫雨,山溜遄发,接路泥沙没胫,行者病焉。邑侯马公税驾时临,心甚恫然,谋所以新之,捐俸以先众。时大歉之后,民力维艰,新安诸商人雷成美、谢鏊、吴良采等仰体侯意,各输金助工,僦石鼎新之,竖以木楯,桥前土埂萦以石甃,近二百余丈”*阎銶:《建弘济桥碑记》,雍正《巢县志》卷19《艺文》。。在徽商的慷慨捐助下,这座古桥得以重换新貌。在宣城从事牙行业的章健德亦乐善好施,曾“与歙方君某合钱修治宛陵路,自五里亭至于妙音寺,凡五里有奇”*汪泽:《国子监生章君健德墓表》,民国《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6《幽光录·墓表》。。
因为长期在外经商,徽商深知人身安全的重要性,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对于安全设施也会积极捐资兴修。如在滨江城市芜湖,“大江西有驿矶,石骨嶙峋,水涨落不时,行楫偶不戒,害立见”。于是,“邑人议起台矶上,用为标识”。但因所费甚巨,只能通过劝捐来完成此项工程。听闻此事后,侨寓芜湖的徽州人吴昂说:“众擎固易举,道谋恐难成也。”于是“白于令君张,独力建造。雍正六年十月兴工,八年三月竣事。垒石为台,上立庙,名其矶曰‘永宁’,商舶皆利赖焉”*乾隆《芜湖县志》卷15《人物志·流寓》。。这一工程为过往船只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休宁珰坑街人朱德粲也是一位义商,为人慷慨好义,广施善举,“贾于皖,尝成潜山县石梁,造救生船于大江以拯溺,制水桶于皖城以救火灾,并置义地,施茶汤,保姜氏子,赎许氏女,义行甚众”*道光《休宁县志》卷15《人物·尚义》。。
2.扶危济困,助赈灾民
徽商好义乐施,扶危济困、助赈灾民也是常有之事。在灾荒年份,徽商往往不惜财力,积极助赈。如歙县许村人许仁,“贾于芜湖”。嘉庆十九年,安徽境内发生旱灾,“饥民就芜湖索食,且酿乱。仁拟章程十条,上大府,资流民出境,事乃已”。“芜湖有凤林、麻浦二圩,为南乡诸圩门户。道光十年,大水,仁董振事,以工代振。明年夏,水又至,复倡捐巨金以振。又议二圩通力合作章程十六条,农民称便。”*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黟县人王廷璧,乐善好施,“尝贸易东流县,值水灾,居民纷纷流移,有年老艰于行者,璧出三百金于城隍庙给发。越二日,金尽,适县令请赈,难民得老幼完聚,至今东流人犹称廷璧之德”*道光《黟县续志》卷7《尚义》。。休宁人叶天育,“贸易庐江,适患蝗,民多乏食,育捐重资助赈,活人甚众”*道光《休宁县志》卷15《人物·乡善》。。徽商积极出资助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府的赈灾压力,也有助于安抚灾民,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有的徽商还捐资置办义冢,施棺助葬。如黟县人朱照开,“商于安庆,赈饥施棺,置义冢”*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志·尚义》。。婺源商人王启仁,幼年读书,长大后代父经商,“足迹所经,见义必为,仁声四达”,曾“置芜湖澛港田亩,瘗暴埋枯”*光绪《婺源县志》卷28《人物九·孝友二》。。绩溪人章健德,“持身颇俭约,至有义举,辄踊跃从事”,曾在宣城“买山一区,营义冢,瘗穷民及行旅之死无所归者”*汪泽:《国子监生章君健德墓表》,民国《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6《幽光录·墓表》。。
乐于助人、解人之困也是徽商的一大美德。如婺源商人方尚赐,“尝贸易池州,宿洗马,闻有妇人哀泣达旦,囚夫债迫,将鬻以偿。其家两代单传,妇已孕数月,赐知恻然,以所买棉花数担赠之,抵还债主,悉允服,夫妇得全,赐空囊而归”*光绪《婺源县志》卷32《人物十·义行四》。。在方尚赐的无私帮助下,这对夫妇得以相守,避免了分钗破镜之痛。
3.伸张正义,维护市场环境
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徽商往往会面临各种考验,除需要承受正常的商业竞争压力外,他们还会遭遇各种制度、人为因素的干扰,诸如欺行霸市、官吏盘剥等等。对于这些商业陋病,徽商一般会直面以对,据理力争,不惜全力维护市场秩序、伸张正义。如婺源商人胡之震,“薄游江湖,为木商条陈芜榷利弊,及创立澛港停泊规制,公私交赖焉”*光绪《婺源县志》卷31《人物十·义行二》。。婺源商人查文濂,“商于天长,县吏侵商,公举首以惩之”*光绪《婺源查氏十一修族谱》卷尾之三《行实》。。
其实,徽商在皖江流域的义行善举远不止以上所举。如婺源人俞焕是一位实力雄厚的商人,“以赀雄吴楚间”,为人乐善好施,“积而能散”,曾“于饶州、苏州、金陵输建会馆,于芜湖立蟂矶庙,修澛港堤”*光绪《婺源县志》卷32《人物十·义行四》。。黟县人李肇柏曾“创业芜湖”,后“旅和悦洲,乐输同仁局,倡设公德趸船,又助建石埭老鸦滩石桥,捐本县积谷”*民国《黟县四志》卷6《人物志·质行》。。乾隆十四年,芜湖城隍庙动工兴修,徽商亦共襄其事,“邑人与徽人合力输赀,更番董事,阅五载告竣,殿庑肖像成巨观焉”*乾隆《芜湖县志》卷3《祀典志》。。徽商的义行善举难以尽述。
三、结 语
自明中叶以后,徽商走出家乡,贾于四方,经商之风炽烈,以致形成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序》,明万历五年(1577)王氏经堂刊本。的浩荡场面。在安徽的重要经济区——皖江流域,也聚集着大批徽州商人,他们在此从事盐、典、粮食、棉花、布匹、牙行、木材等生意,经营领域十分广泛。以儒商闻名的徽商,在进行商业竞争、追逐利润的同时,还自觉地以儒家义利思想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商业活动,强调“义”“利”并重、以“义”为先,在皖江流域广施善举,诸如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济灾民、主持正义等等。徽商促进了清代皖江流域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成为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创造者。
责任编校:张朝胜黄琼
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5.013
◇徽学:徽商研究专题◇
K295.4
A
1001-5019(2016)05-0100-08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2YJCZH28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12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70008)
张绪,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安徽 合肥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