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所意象到场所认同:景观艺术的场所情感体验
2016-09-24赵刘
赵刘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2141531)
从场所意象到场所认同:景观艺术的场所情感体验
赵刘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无锡2141531)
作为综合性的空间艺术,城市景观艺术的情感体验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场所情感体验由场所意象与场所认同共同组成。场所意象是场所情感的基础,有助于建立积极的艺术空间。场所认同是情感体验的深化,意味着场所对于人具有意义,并产生“定居”。景观艺术通过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的存在揭示,从而为公众集结了一个富有魅力的世界,使公众产生场所认同感。景观艺术的场所情感在更深维度上表现为帮助城市建立一种“美学共同体”。
景观艺术;场所情感;场所认同
情感体验在艺术审美中具有鲜明的表现和重要的地位,任何真正领略过艺术之美的人都会由衷地赞叹作品对人的情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罗宾·乔治·科林伍德将情感表现看作是艺术至高无上的目的;苏珊·朗格认为人类文化都是一种符号的表现,而艺术就是一种非语言的情感符号。但是,作为由雕塑、壁画、建筑、绿篱、园林等组成的综合性空间艺术,人们的情感体验另有特色。
一、场所情感体验的提出
从艺术存在的形式上来看,一个极为鲜明的区别表现在城市景观艺术是以综合性的空间区域出现,而传统艺术大多以单体形式出现(建筑除外)。虽然传统艺术可以分为时间艺术、空间艺术、时空艺术各种形式,但是在审美过程中我们始终是对某一个艺术对象进行审美,所产生的审美情感也与这个艺术对象紧密相关。但是在对综合性空间艺术——公共景观的审美过程中,人们即使对其组成部分的单体艺术会产生某种情感,但总体而言这种审美情感必然是对于整体公共景观艺术的情感综合,也必然是对于它所占据的这个区域和空间的情感集成。此时,我们将对于一处城市景观艺术的整体所产生的审美情感称为场所情感体验。这种场所情感体验与以往常见的艺术审美体验表现出很大不同。比如,可以说听一首歌曲感到很振奋,看见一幅画感到很美妙,读一首诗感到很悲伤,但对于城市公共景观艺术的审美似乎很难产生这种令人激动和深刻的情感。此时产生更多的是方向清晰感、温馨感、依恋感、归属感之类的感受。如当人们处于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或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时,会产生这样清晰而深刻的情感体验。优秀的城市景观艺术以鲜明的场所感提醒人们它自己的存在,而失去场所感的公共景观艺术则令人感到苦闷和彷徨,凯文·林奇将其定义为“不经意地彻底消除有特点的场所”和“标准景观的建造”。
城市景观艺术蕴含的情感价值对于主体表现为一种场所感,一种类似于“家”所带给我们的那种空间与主体紧密相连的感觉。此时,景观艺术不再以一种客观的“空间”形式向公众显现,而是以一种主客体紧密联系的“场所”而存在。段义孚认为:空间是抽象的、宽泛的、开放的、空洞的,是一种客观的、冷峻的存在,它体现为具有长宽高固定数据的体积;而场所则是人与空间融合的产物,是空间渗入人的感知、情感后的结果。由于人的主观情感的渗入,主体对于同一处公共空间往往产生不同的反应,这样空间就对人产生出不同的意义。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能带给人们场所感,空间要成为场所并不容易。对于景观艺术来说,它的价值不只体现在为人们提供视觉形式美,还在于为公众提供意义思考和场所情感,从而加强公众与空间的关联。真正的景观艺术必然带给人们主体鲜明的场所感,而对于场所情感体验的研究也将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城市景观艺术带给人们的重大价值。对于那些杰出的景观艺术,人们往往产生鲜明的方位感、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因此也可以相应地将其情感体验分为场所意象感和场所认同感。
二、作为场所情感体验基础的场所意象
场所情感体验首先以方位感的维度呈现给人们,即那些给予人们深刻场所情感体验的景观艺术空间必然在人们意识中产生清晰的方位感,本文将这种方位感称为 “场所意象”。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指出,无论城市有多大都应该给人可感知的形象,能否给人一种鲜明的印象是城市价值的一种重要体现。所谓“意象性”指“具形对象使每个特定观察者产生高概率的强烈印象的性能。对象的色彩、形状、排列促成了特征鲜明、结构坚固和相当实用的环境心理图像。以一种更高的意义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可识别性或可见性。就是说,目标不但可见,而且鲜明地呈现在感觉之中”[1]8。实际上林奇所要探讨的核心命题是:从人的知觉角度出发,如何理解城市空间在人的意识中所产生的深刻意象。相比于林奇对意象特征的不厌其烦的描述,给人们更大启发的可能是他揭示出人对于空间方位感或意象感的依赖性。当一位飞行员迷失了高度定位,这将成为他人生最可怕的经历;当非洲土著迷路时,他们将会惊恐万状,狂乱地闯进灌木丛中去。因此,“找寻道路是环境印象的基本功能,也是建立感情联系的基础,但意象的价值不只限于这种作为指示运动方向的地图的直接意义,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它可以是个人的行动和运动知识的广泛的参照架。”[1]118由此看来,人对于场所的方位感不仅是一种识路的需要,而且是一种适应周围环境从而生存的前提,人们需要将方位感或意象看作人与场所结成紧密关联的一种表现。如果环境能够产生好的意象,那么就会在人的心理产生安全感,如果有机体无法在环境中确定方向,就会产生失落感和恐惧感。能够对于一处场所或空间产生意象,这正是建立情感的基础,换句话说,这种场所意象正是人与场所紧密关联的表现,即一种场所情感体验的表现。
意象理论不仅适用于一个城市,它也适用于任何一处空间,因此景观艺术所存在的空间也会使人产生场所意象。如果说城市意象指的是居民对于城市所产生的一种方位感,那么城市景观艺术所产生的场所意象也是公众对其所产生的明晰的印象与方位。当人们说自己对于某处景观艺术有清晰的意象时,是从两个层面来表述的。首先指的是以城市为背景,可以感到这处景观艺术具有鲜明的印象,它醒目地占据着自己大脑中城市感知地图的某处位置,自己对于它在城市中的方位、乘坐几路公共汽车、坐几号线地铁、如何开车到达十分清楚。一些公众甚至以著名的景观艺术场所为方位参照来处理城市地理信息,如有的北京市民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来将王府井大街、颐和园、中关村等地方纳入基于广场的距离与方位的整个城市定位系统,这些市民不一定采用城市地图式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位置,而是以自己距离天安门广场多少距离什么方位来自我定位。第二个层面指当自己现实地位于这处景观艺术空间中时,对于它的实际布局、路径、内部小品、休憩设施等十分清楚,它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是某处陌生的地方,而是类似于家一样的温馨熟悉的场所。比如对于哈普林所设计的爱悦广场(见图1)来说,由于广场的杰出设计和便捷的实用性,波特兰市民频繁地进出和长期地使用这处公共广场,以至于喷泉、演讲堂、观景平台、休憩的椅子等都非常醒目和自然地显现在公众的脑海里。当公众来到喷泉下淋水时,他们不用看也能清晰说出演讲堂位于自己脑后何方、有多少距离。类似于爱悦广场这样的具有良好意象的公共景观艺术,为公众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空间而不是消极空间。所谓积极空间,指空间从人的视野背景中凸显出来,自己形成一个世界从而吸引人们关注。而消极空间,指人们将之作为经过的地方而不是逗留和欣赏的地方。由于景观艺术场所往往位于城市中心,与许多建筑相邻,所以二者往往共同处于人们的视阈之中,它们都力争成为图形而避免沦为对方的背景。对于那些提供积极空间的景观艺术场所,人们将旁边的建筑或街道视为背景,而将景观艺术作为图形去仔细观看或沉浸其中;对于那些提供消极空间的场所,人们会忽略眼前的景象将之视为背景,却将远处的建筑视为图形来观察欣赏。显然,人们在积极空间所体会到的是安全感、清晰感与温馨感;而在消极空间人们体会到的只是失落、陌生,只想尽快离开。形成积极或消极空间差别的原因正在于这处场所能否予人深刻的场所意象。

图1 波特兰的爱悦广场
在如何产生场所意象这个问题上,城市景观艺术一方面遵循林奇所提出的五大因素(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影响理论,但是又不仅仅受这五大因素影响。作为一处空间来说,景观艺术毕竟也由土地、道路、绿化、中心等组成,在客观物质组分上它与其他任何空间没有区别。但是景观艺术并不只是类似于街道、广告牌、灯柱那样的普通物质,它更具有独特的形式与丰富的艺术内涵,它始终以超出普通客观物质的方式向公众显现。景观艺术与普通空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许多构成元素都具有深刻的符号意义和艺术价值。那些给予我们深刻意象的公共景观不仅仅因为它的道路或区域设置因素,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其的理解与认同所产生的力量。史密斯的《螺旋防波堤》(见图2)远离市中心,但是人们以崇敬和浪漫的眼光去看待这幅作品,这是因为人们觉得它具有震撼的视觉形式和深刻的意义。野口勇所设计的耶鲁大学贝尼克珍藏图书馆下沉庭院并没有清晰的标志或结点,人们之所以被它吸引主要还是在于庭院中的立方体、金字塔或环状造型引起人们哲学上的玄思与联想,从而赋予这组作品极大的价值和鲜明的意象。因此,景观艺术并不仅仅以道路、边沿、区域、结点、标志这些客观空间因素来产生场所意象,更依靠它的思想与意义来打动公众,从而与公众结成密切的关联,产生深刻的场所意象。

图2 螺旋防波堤
三、作为深度场所情感表现的场所认同
场所意象感是场所情感体验的基础,更为深刻的情感表现为场所归属感和认同感。挪威建筑现象学家诺伯舒兹认为,场所方位感与认同感既有关联又相对独立,“晓得自己所在的方向,却没有真正的认同感是有可能的;一个人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但不一定感觉很舒服。对场所的空间结构没有很清楚的认识,然而感觉很舒服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场所的体验是一种令人满足的一般特性。然而真正的归属就必须是这两种精神功能的完全发展。”[2]20在诺伯舒兹看来,场所并不表现为一种空洞的客观空间,而与人具有深深的意向性关联。那么场所认同感到底是什么呢?诺伯舒兹认为,在人们的环境脉络中,认同感意味着与环境为友。“人类的认同必须以场所的认同为前提。认同感和方向感是人类在世存有的主要观点。因此认同感是归属感的基础。……真正的自由必须以归属感为前提,‘定居’即归属于一个具体的场所。”[2]21“意义是一种精神的函数,取决于认同感,同时暗示一种归属感,因此构成了住所的基础。我们必须重申人最基本的需求是体验他的存在是具有意义的。”[2]167这样舒兹就构造了这么一个关于认同感的公式,“场所认同感=场所归属感=场所对于人具有意义=人在场所‘定居’”。在他看来,当人对一处场所产生认同感时,就会产生归属感,就会产生“定居”的感觉,也即意味着场所对于人具有意义,这四个方面几乎可以用等号连接。所以,诺伯舒兹是用一种存在主义视角来表述认同感的,在此认同不仅表示同意或赞许,而是在更深的维度上表达主体的“诗意地栖居于某处场所”。
在海德格尔和诺伯舒兹的概念中,“定居”意味着充满价值和诗意地栖居,这完全不同于那种生存式的居住。那么人如何才能实现这种定居呢?诺伯舒兹认为只有当建筑集结世界时才能使人充满意义和认同感,“人类是经由定居熟悉他所能理解的一切。集结是一个具体的现象,使我们获得定居最终的含义。……我们可以获得结论,定居意味着集结世界成为具体的建筑物或物,而建造最早的行为是包被。……当人能将世界具体化为建筑物或物时便产生定居。”[2]22此时的建筑不仅是个遮风挡雨的处所,而是使人通过它了解到周遭的世界,用诺伯舒兹的话说就是“形成一个小宇宙”。他用埃及人的建筑来进行证明,埃及人将建筑视为他们宇宙概念的一种模型,通过天花顶、柱子等建筑细节,埃及人试图重现一个微型宇宙,正是在这种建筑里生活才使埃及人由衷地感到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实现一种诗意地栖居。诗意地栖居意味着建筑不仅是砖石的集合物,而是使人感到更多的意义。所谓的“定居”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不仅住在砖石构成的空间里,而且住在由意义所编织成的场所中。诺伯舒兹认为对于那些失去场所精神的处所,人们将不会具有认同感,取而代之的是疏离感。特别是二战以后的许多场所都失去了一直传承下来的场所精神,表现出“场所沦丧”。只有当人们重新在场所中发现意义和产生认同感时,才能真正遏止这种破坏性的发展。
一处成功的城市景观艺术也必然具有自己独特的场所精神或氛围,公众在这种场所中也必然会感受到强烈的认同感。置身于林缨所设计的越战碑景观中,人们感到莫名的伤感与哀愁,迷惘与失落,生发出对“生死”“成败”“此岸彼岸”的丰富思绪与感怀。在巴拉甘设计的马戈花园中,人们感受到的是喜悦、悠远与沉寂的气息。在哈格里夫斯设计的拜斯比公园木桩阵中,人们感受的则是类似英国巨石阵般的神秘、寂静,生发出对时空流转、宇宙天地的感叹。而在安藤忠雄设计的水的教堂(见图3)中,人们体验到的则是神圣、安详、深沉与平和。这些或喜悦、或伤感、或神秘、或安详的感受正是体现了景观艺术所具有的独特的氛围或场所精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景观艺术创造场所的手段比建筑更为丰富和多元,人们在公共景观艺术场所中感受到的认同感也更加深刻。如果说建筑是通过墙、柱子、天花板、装饰等来集结世界,那么景观艺术则通过雕塑、壁画、景观、绿化等来表现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景观艺术场所中的各种惯常元素似乎都被场所精神所磁化,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比如上海衡山路上有个以雕塑《蓝调》为中心的公共场所,《蓝调》表现的是两个男子:一个手持萨克斯的男子正在自我陶醉地演奏着爵士乐,似乎完全融进了音乐世界当中,而另一个倚靠在灯柱上的号手则在独自想着心事,显得有点寂寥而又优雅。整个场所虽然简单,却表现出不俗和优雅的怀旧氛围,反映了那种小资式的生活态度和精神世界。在这处公共场所的影响下,原本是普通的街道也被渲染上了类似的文化性格与气质。雕塑的视觉形象与周围的环境格调显得如此的融合无间,就像雕塑的怀旧风格一样。

图3 安藤忠雄设计的《水的教堂》
既然景观艺术也鲜明地表现出一种场所精神,那么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传达场所氛围,并使人们产生认同感的呢?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中提出的最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莫过于将场所认同与“定居”“意义集结”联系起来,这大大拓展了人们关于场所情感的认识。他认为,建筑正是通过集结功能,向人们揭示了更多的东西,因此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变成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家,使他能居住。他得出了关于艺术与定居的观点,“我们晓得艺术主要的功能便是集结生活世界中的矛盾与复杂成为一种宇宙意境,艺术作品帮助人类达成定居。”[2]22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景观艺术通过揭示周围环境和城市的存在,集结了一个世界,人们在这个小宇宙中感受到强烈的场所精神和认同感,从而实现“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场所之中。具体而言,城市公共景观艺术通过以下三种揭示存在的方式来达到集结世界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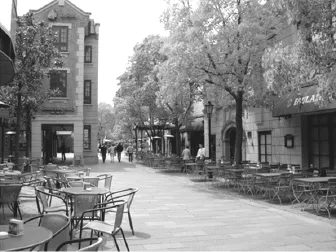
图4 上海“新天地”园区
首先,景观艺术集结世界的方式就是揭示城市文化与历史,使人们感受到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文蕴含。上海“新天地”园区(见图4)是在尽可能尊重和利用上海城市中旧有的“石库门”民居样式和里弄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商业化、时尚化的改造和艺术的再创作。该处场所大量保留了20世纪初期建筑形式,而对其内部格局、使用功能、周边环境、公共设施等进行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改造。通过对建筑景观、装饰风格、家具陈设、商业项目等融入传统符号元素,营造出兼具传统上海消费文化与当代白领消费文化、欧美工业文明与地域特色文化的“海派文化”氛围。人们在表面陈旧的街区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形式的水体艺术、植栽艺术和立体化的环境设计。整体场所传达出一种主题明确的传统怀旧氛围,但是却并不显得呆板和单调,现代化的设计点缀其间,赋予其新潮感。传统与现代、形式与功能在这处场所达到了很好的融合。无论是老上海市民、当代年轻人,甚至外来游客,都可以在“新天地”园区感受到那种独特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所精神。
其次,景观艺术集结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揭示当代生活的现实,使公众产生认同感。《深圳人的一天》(见图5)是此种类型的典型作品。18位模特分布在整个公共广场中,完全取自于深圳百姓的生活实际境况。整个活动仿佛一个摄取的平台,让城市人群自己在上面显现自己。公众在这个场所中所发现的是完全来自于现实而又被镜头定格的艺术作品。它要求公众不再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去对待现实,而是重新以一种新鲜的视角来看待日常生活。《深圳人的一天》实际上通过这18个取材于真人的模特,再现了深圳这座城市和深圳人的生活世界,无疑它将激起公众强烈的认同感。

图5 深圳人的一天

图6 曼哈顿银行广场的下沉式庭院
再次,景观艺术集结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揭示未来或生命,引导公众在反思中产生认同感。如野口勇为曼哈顿银行广场设计的下沉式庭院 (见图6)就是这种作品。他在直径为18米的波浪形地床上不对称地放置了七块黑色石头,花岗岩铺装铺成环状花纹和波浪曲线,隐藏的喷头喷出细细的水柱和神秘的水雾,这些石头在水雾的衬托下好像成了大海中的孤岛。公众在对这个场所景观的欣赏中,会联想起大海、高山、和未来的生命终点,从而在反思生命的过程中认识到作品的真正价值,产生一种由衷的认同感。由此可见,景观艺术通过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的存在揭示,为公众集结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宇宙,展现出独特的场所精神,使公众产生场所认同感。
四、场所情感体验与美学共同体的建立
由场所意象和场所认同组成的场所情感体验表现了景观艺术对于公众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了景观艺术与公众所结成的深刻意向关联,反映了艺术的力量。如果人们将景观艺术对于公众之间交流的促进、对于城市公共文化背景的宣扬等视为公共性的表现的话,那么这种公共性不是源自于其他原因,而只能来自于城市景观艺术的艺术性之中。正是在公众对于艺术的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公众对于景观艺术产生了场所情感等深层次体验,才真正实现了城市景观艺术的公共性。学者们往往将景观艺术有助于产生城市的认同感视为公共性的重要表现,如马钦忠先生认为,“公共景观艺术对城市空间的体验起到推动和提示的作用,增强人对城市性质和品格的了解,加强浏览者和居住者的美学亲密情感的联系。”[3]287
景观艺术的公共性在更深维度上表现为帮助城市建立一种“美学共同体”。这种美学共同体不同于一般社会群体的最鲜明之处在于具有相似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认同,它们潜在地指挥着人们的审美体验,帮助人们自觉地建立融洽的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阿诺德·伯林特认为建立在对场所情感认同和自觉维护基础之上的 “美学共同体”远胜过建立在个体强制上的“理性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是通向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倡导的联系世界的更好选择。所谓“理性共同体”是指基于利己主义理念而构成的共同体,其中指导个体行动动机的是谨慎的动机、对代价和利益的仔细计算,这样的共同体中的自我与他人始终处于对立的焦虑之中。所谓“道德共同体”指的是基于道德良知而形成的共同体,此时道德责任超越了欲望和私利成为约束性的力量,但是这种共同体中的成员放弃了独立的判断和个人决策,表面上的统一掩盖了连续性经验的缺乏。而“美学共同体”保证了成员个性的存在以及体验的连续性,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惠代替了其他模式的界限和分离。显而易见,这种美学共同体不是通过对城市功能的科学分区或生态建设就能达到的,而必须经由文化交流、艺术审美等方式体现。那么景观艺术是如何帮助建立这种“美学共同体”的呢?
作为一种非监控的、愉悦性的交流场所,景观艺术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之中。无论景观艺术的主题、形式为何,它们都直接诉诸人们的感性经验,让人们在审美体验中产生相应的场所情感。由于景观艺术主题的公共指向性以及公众相似的文化背景,公众所产生的场所情感体验总会有交错合集的地方,当这些情感体验通过作品的提炼被呈现给市民的时候,当市民在体验和思考这些作品的时候,原本分离的个人世界便经由情感联系到了一起。“我”发现自己对艺术产生的共鸣和情感与“你”一样,公众对于该处场所产生同样的认同体验,虽然公众没有经过语言这种更加清晰的方式,但却要比言语交流达到更深层经验的沟通与认同。“我们对艺术最丰富、强有力的参与能创造一种连续性体验,这种体验在一个具有不同的持续影响力的领域中将艺术家、欣赏者、艺术对象和表演者结合起来。”[4]115-116它真正使公众的生活世界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了关联。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人们从自己的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他人的主观世界发生了关联,并在进入一个共同语境的过程中构筑起一个共同分享的世界。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经由语言沟通,而是经由审美体验而产生,那么经由这种场所情感体验而构筑成的共同分享的世界也就是“美学共同体”所带来的世界。
[1]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M].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2]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3]马钦忠.公共景观艺术基本理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4]阿诺德·柏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编辑:张雪梅)
From Place Image to Place Identity:Affectiv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Art
ZHAO Liu
(Wuxi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erce,Wuxi,214153,China)
Unique is the affective experience of urban landscape art,a comprehensive space art.The affective experience of a place includes place image and place identity.Place image i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affection of the place occurs,which helps establish a positive artistic space.Place identity in turn engenders more affective experience,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lace is of value to human beings,and implies a sense of settlement.Landscape art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three time dimensions—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and thus constitutes a charming world in which the public has a sense of identity.In a deeper sense,the affection of a place engendered by landscape art helps a city set up a kind of aesthetic community.
landscape art;place affection;place identity
TU 984.1
A
1671-4806(2016)04-0096-06
2016-05-05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SJB345);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项目作者简介:赵刘(1980—),男,安徽凤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景观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