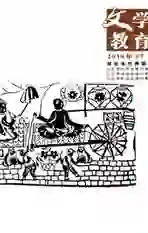卡利古拉与堂吉诃德的疯癫比较
2016-08-15田开
田开
在古希腊,迷狂作为疯癫的早期形象,被人们认为是“神力凭附”,这是一种荣幸而不是丑闻。柏拉图认为“诗性的迷狂”乃是诗人的创作灵感源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虽没有如此神圣的地位,但也在世俗之地自由存在着,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之中指出这一时期“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迷恋”。这里最常被提起的文学中的疯癫不外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一种浪漫化的疯癫,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因为18世纪还在承认它那刚刚被抹掉的形态”,而这种浪漫化疯癫的特征是由塞万提斯确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三种类型的疯癫,分别是:狂妄自大的疯癫,道德领域中正义惩罚的疯癫以及绝望情欲的疯癫。在随后的古典时期疯癫完全被理性禁闭,在社会的边缘沉默独处。福柯认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所谈到疯癫时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我思故我未疯”,但我惊奇地发现到了现代,非理性哲学的崛起对此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嘲讽。加缪的《卡利古拉》中,作为和传统意义上截然不同的暴君,卡利古拉是一个“我思故我疯”的形象。卡利古拉的疯癫不属于以上四种任何类型,福柯在《疯癫于文明》中并没有对疯癫做出清晰的界定,因为正如德里达指出的一样,言说“沉默的疯癫”这种行为本身就不能成立,用理性来定义疯癫同样也是一种悖论。 历史一直在悖论中前行。疯癫在理性的废墟上起舞。当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在西班牙的大地上横冲直撞,卡利古拉在古罗马的皇宫里开始流血的盛宴,这是个人对于世界的对抗,在不同的背景下同样悲壮,不论以重造还是以毁灭的形式,这种努力都让人致以敬意。本文试图依托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比较二人疯癫的机制与过程。
一.疯癫的开始:表面上不需要理由的自我狂欢
《卡利古拉》第一幕开始,我们得知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在惊慌失措地寻找他们走失的皇帝。这个有些忧郁的文艺青年在失去了自己的爱人(他的亲妹妹)之后开始下落不明。爱人的死亡让他突然领悟到这样一个真理:“人是要死的,人是不幸福的。”其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关键是他对此的态度和众人不同。绝大多数人在知晓自己必死的结局以及对命运的无能为力之后都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卡利古拉却拒绝如此。于是他开始追求月亮,这种现实中的不可能之事。事情到现在也不稀奇。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惨死在世人不可能体验过的强烈的光与热中。卡利古拉的追求代价之大在于他的身份。他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那个人,是所有人必须服从的那个人。于是飞向太阳的不只是一个人,他想让谁去,谁就必须成为真理之光中的灰烬。众人都以为他只是简单的受了乱伦之爱消逝的打击,即福柯所说,只是暂时处于绝望情欲的疯癫状态,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疯癫的长久性与破坏性才让他们明白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只有卡利古拉唯一的对手舍雷亚才明白,他们的皇帝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暴虐疯子。对于不明就里的众人来说,卡利古拉的疯癫没有理由。
如果说卡利古拉的疯癫还有爱情消逝作为外在的一个契机,那堂吉诃德的疯癫则完全没有征兆。我们只是知道这位老乡绅读了如此之多的骑士小说,所以某一天他突然开始积极行动准备自己要进行的骑士的光荣历险。相比于卡利古拉的顿悟式疯癫,堂吉诃德的疯癫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这种泯灭现实与虚构界限的例子其实现实中并不少见,何况在文学中。乌纳穆诺认为堂吉诃德的发疯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单调的生活与苍白的想象力。这样说来任何一个文学人物的疯癫抛开什么具体的理由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所有现存或潜在的读者。不少学者推测过堂吉诃德发疯的具体原因,甚至跑偏到这位老单身汉是被对自己侄女的压抑性欲逼疯的。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妄图为疯癫找到生理学的基础。这里我们只探究精神层次。在《西方正典》中,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堂吉诃德的疯癫乃是一种自由、无功利性、排他性和限定性的游戏行为,因而不算是疯癫。与之相比,卡利古拉的行为更加自发、无功利,但他的行为不仅没有排他性反而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并且有一种要突破底线打破限定的肆意。所以我更倾向于在疯癫的领域内让堂吉诃德和卡利古拉相逢,而不是游戏领域。
无论如何,在开始卡利古拉和堂吉诃德就都陷入一种疯癫状态,随即开始了不需要解释的自我狂欢,虽然前者实质是一种表演,而后者实质是一场战争。疯癫的齿轮一旦转动,就开始了不可逆的过程。
二.疯癫的机制:从幻觉的解放到无法反驳的逻辑
疯癫的过程之所以不可逆的进行着,因为不论是卡利古拉还是堂吉诃德都有一套强大而顽固的疯癫的机制。
由福柯之说来关照堂吉诃德和卡利古拉,我们不难发现堂吉诃德的疯癫以幻觉的解放为主要形式,而卡利古拉的疯癫则,依托严密的推理,即一种无法反驳的逻辑。下面分别探究二人的疯癫机制。
堂吉诃德,毋庸置疑,他的疯癫在于他有一套自己虚构的法则取代了现实世界的真实。而且这种虚构的真实强大到让桑丘也自然而然的加入。疯癫的话语言说出骑士的世界,理性的话语言说出现实的世界,在两个世界无法和谐共存的冲突下,堂吉诃德注定要一败涂地。他让幻觉无比自由地驰骋在沉重的大地,所到之处一片荆棘。这种纯粹解放幻觉的疯癫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的主体性,所以到后来桑丘也乐此不疲地相信,因为个体价值的释放是一种美妙的过程,无论它以何种形式,所以就算屠夫也会在精准地挥刀结束生物生命的瞬间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快感。更何况堂吉诃德是以骑士道之名来执行的自己的疯癫。对堂吉诃德来说,事物所成为的比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本身固有的更为重要。所以理发师的铜盆成为了曼布力诺头盔。这种感觉类似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堂吉诃德说,这是曼布力诺头盔,于是有了曼布力诺头盔。只不过前者从虚空之中创造,后者从现实中取材加工。乌纳穆诺将《堂吉诃德》奉为西班牙的“圣经”,将堂吉诃德视为俗世的“上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
卡利古拉的疯癫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无法反驳的逻辑。从一开始,总管对他禀报国库的事情,他便得出了以下结论:“既然国库重要,那么人命就不重要。这是一目了然的。凡是同你看法一致的人,既然把金钱看成一切,就不能不同意这种推论,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总而言之,我决定要遵循逻辑。既然我有这个权力,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逻辑要让你们付出多大代价。”在之后的行动中,卡利古拉果然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种逻辑。最淋漓尽致的一回在第二幕第九场:“人应当死,因为他们有罪。他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当了卡利古拉的臣民。既然帝国上下全是卡利古拉的臣民,那么人人有罪。因而得出结论,所有的人都应当处死,问题只在于时间和耐心。”这种推论的逻辑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列举的疯人逻辑如出一辙,只是前者的范围大大扩张,因为卡利古拉有这个权力。这种逻辑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的绝对性和彻底性。在世俗生活中,绝对逻辑无法存在,因为人们总要靠谎言和假象才能更好地生活下去。人民认为自己自由,掠夺者认为自己慷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其乐融融。而绝对逻辑拒绝妥协和折衷。所以卡利古拉认为,对于他的臣民来说,被真相伤害总比被谎言伤害要好。但是真相的伤害来的直接尖锐,造成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而谎言的伤害往往缓慢异常,从而使人无法察觉到痛苦。绝对逻辑强迫人们面对真相,从而使人陷入绝望。
堂吉诃德选择用幻觉虚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幻觉就是真相;卡利古拉选择用绝对逻辑刺穿现实世界的谎言之布,从而使世界只剩下真相。
三.疯癫的实质:反抗死亡与反抗荒诞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道,乌纳穆诺的“愁容骑士”是生存的探索者,他仅有的疯狂举动就是对死亡的圣战:“堂吉诃德的疯癫真伟大,原因在于产生疯癫的根源也伟大,即永不熄灭的生存渴望,这是最张狂的傻事和最英勇的行为的源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疯癫总是伴随着谋杀和死亡,而在《堂吉诃德》中,疯癫变成了一种反抗死亡的方式。拉曼查的乡绅年过半百,似乎过不了几年就应当过上一种安享晚年的生活,但他却选择了成为堂吉诃德,为自己瘦削的身躯添上累累伤痕。在常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找死的举动。但恰恰相反,这不是加速死亡的过程,而是追寻永恒的过程。
反抗死亡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可笑,因为在现实领域,在生理学上,永生是不可能事件。即便我们所说的永恒,也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既为永恒,便无始无终,但人的生命都是有起点的,历来帝王术士所追求的也只是长生而已。堂吉诃德所追求的不在于这水平方向的生命长度上,而在于垂直方向,在生命的纵深处。据乌纳穆诺解释,堂吉诃德的动机来自于要获得不朽的声名,或者可以解释为“时空里的一种人格扩张”。布鲁姆认为这是耶和华文献作者的“福音书”的世俗版本:向无垠的时间中引入更多的生命。堂吉诃德的做法就是自己构造出一个世界,在无法摧毁现实世界的前提下。不管是塞万提斯还是堂吉诃德,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毁灭世界的隐秘愿望。因为这个世界太不美好太不友善,无论是对塞万提斯还是堂吉诃德,是对改宗的摩尔人还是对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毁灭世界听起来太恐怖,于是堂吉诃德采取了了一种迂回的方式,他不承认这个世界,他只承认自己的世界,于是他成了疯子。
而对于卡利古拉来说,反抗死亡只是表面的借口。死亡只是荒诞的一种表现。我们看到卡利古拉并没有历来帝王所表现出的对长生的欲望,相反,他有一种不在乎生死的态度,不仅是自己的生死,还有整个帝国所有人的生死。他要反抗的,是荒诞,是大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的荒诞。反抗荒诞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但他的方式太过残酷。加缪在《文论集》中考察了对空虚和渺小、对人的不幸命运进行反抗的种种形式。有一种似乎使个人摆脱一切羁绊的超现实主义的反抗,这是一种绝对的反抗,一种达到尽善尽美境界的虚无主义。而这种反抗终将变成报复性的歇斯底里,变成颂扬杀人和自杀,变成震惊人心的造反。——“你们都是诗人,而我但求一死。”这种超现实主义居然说,超现实主义者最简单的举动,就是拿着手枪,走上街头,朝人群射击。卡利古拉的方式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豪华升级版。
他所追求的月亮,幸福或是永生只是一种象征。这些都是现实世界之外的美好。而现实中的美好,如大自然,卡利古拉以前也深爱过的大自然,“罗马丘峦的轮廓以及黄昏带来的短暂的、令人心潮平和的恬静……只听湛蓝天空中雨燕的叫声……还有在那微妙的瞬息间,天空变幻:看上去还是万道金霞的天空,猛然翻转过去,向我们展示它星斗灿烂的另一副面孔……还有炊烟,树木和流水的混杂气味,从大地袅袅升上夜空……蝉声入耳,暑气减退,犬吠声、迟归马车的隆隆声、庄户的话语声 ……黄连木和橄榄树之间的路径,隐没在暮霭中……”这一番与西皮翁的对话甚至几乎化解了这位年轻诗人的杀父之仇,但这种转瞬即逝的温情却表现出卡利古拉非但不是一个铁血的人,反而拥有诗人一样的敏感与纯情。这些美好的真实事物只构成了生活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他看到的是整个世界的荒诞,人类整体命运的无常。既然他选择了用自己所制造的荒诞来反抗世界固有的荒诞,那他就不得不成为“恶之纯粹”。于是他执行杀人的绝对逻辑,即使他杀的人比发动战争所死亡的人要少的多,他仍然不能被理解。他的所有行为都像是一种表演,他扮演着荒诞,扮演着命运。但他终究只是一个人,即使他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他也有很多无法做到的事情。人为的荒诞终究还是没那么强大。
堂吉诃德的疯癫是自发的,他的清醒却是被动的。我相信一旦有人体验过疯癫便不会再想恢复正常。但他在被打败后顿悟式的恢复了理智,幻觉构建的世界瞬间土崩瓦解。于是他死去了。对于被幻觉支撑的生命来说,这是必然的宿命。他对死亡的反抗最终还是以死亡来收场。
卡利古拉最终也走向毁灭。他的逻辑不可摧毁,所以他的人必须被摧毁。他的自由伤害了太多人,而人为的荒诞更不可能持久。这个世界不可能只是真相,这样的世界犹如真空无法有人类生存。求真的前提是谎言的存在,如果绝对逻辑取得胜利,那么胜利之日也是它的终结之时。对荒诞的反抗本身也很荒诞。
参考文献
1.福柯.《疯癫与文明》
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绛译
3.加缪.《卡利古拉》.李玉民译
4.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王念宁译
5.吴奇,福柯的疯癫史【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5
6.涂险峰,“透明的荒诞”与“纯洁的逻辑”——论《卡利古拉》中的暴虐启蒙【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5
7.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