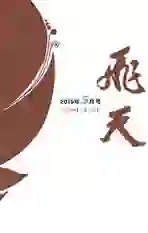痴翁,一块煤的持续燃烧
2016-05-21李云鹏
李云鹏
在我们其后要说到的一本名为《画苑英萃》刊物封二的一则百字短文后,署名的“痴翁”,当时未询,我信是陈伯希。
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少年为兵时从一本杂志上知其名的军旅画家,其后竟同在一个单位服务,并有幸做了他的下属,尽管所从事的具体业务不同。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在我退休后,应他之约,又有了几年愉快的合作,其实是出乎我预想的我的一次进修。
我要请出的人物是:陈伯希。
1950年代,兰州军区战士文化读物社出版有一本《人民战士》。其上,书画方面多见陈伯希,还有黄胄、钟为、王天一的笔墨,《人民战士》忠实读者的我,始知伯希其名,也记住了别几位画家的名字,为文者至今还记得的有军旅作家尉立青。他们同在这本杂志效力,而伯希时任文化读物社总编辑。
1970年代初第一次与伯希见面时,先生亮在我眼里的形象:一米八以上高挑的身个,骨骼峭劲,略显瘦削,行步如丈量,很有些这位当年擅长木刻的画家峻厉刀笔的走势。
还有另一面。那是人们神经紧绷的年代,我们身处的省群文室、刚刚复刊的《甘肃文艺》编辑部,也如置身一艘波荡的陋船上,难有安静的作息。人们头顶总像悬着一件什么物器(我编辑部的大哥郗惠民就有“《甘肃文艺》是一个‘帽子提在手中的角色”一说),逼你惶顾左右。时势使然,一些无端飞来的议题,多被引入同志间无谓的争论甚乃争斗,堂而皇之归谓“路线斗争”。陈伯希这位从延安走来的艺术家,他的革命经历,他后来的坎坷境遇,绝不想再见同志之间鸿沟的加深。印象中有一种扫不去的愁郁隐约呈现在他的眉宇间。那时会多,我记得,与会的伯希烟抽得狠,指缝间似乎常有一支烟的明灭;掌中口杯,也似乎多是调理意绪时的汲取。我记得,在某些火花喷溅的批判会上,他多取沉默;偶有不得已的表态,也选择了一种平抑、弥合裂痕的温婉,措辞调理得十分得体。
这其中其实深含着一种难言的苦衷。我记起《画苑英萃》创刊号伯希以“痴翁”撰写的一则百字短文,记述有这样一件轶事:“在十年动乱中的1971年秋天,石鲁、赵望云两位画坛大师在西安北大街陕西美协住所会见了前来探望他们的老友(陈伯希)。三人见面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但他们当时都被诬为‘黑帮,受到冲击,有千言万语不便多说。”话不宜多说,石、赵二位便挥笔写兰花,以谢伯希探望之情。石鲁的题句有深意焉:“芝兰之宜于人也会以高朋。”伯希有忆:“画毕三人相视大笑,尽在不言之中。”
这“千言万语不便多说”,这“尽在不言之中”,便可以理解伯希们当时难言的沉默了。有一句话说:沉默是金。那年代的这“金”的成色中,我以为,无奈和痛苦是沉重的含量。
那个令人惶悚的年代我不想提说。但我敬重伯希在那个特殊年代放低身姿的温婉甚至沉默。我们当过兵的人知道:某种境况下的匍匐前进,终极是为了前进的继续。在风险多多的那个年代,我把这看作一位智者选取的一种理智的方式,一种不失尊严的藏锋。我确信,伯希内心自有他的尺度。
我眼里,伯希其实是一位性格独卓、谈锋甚健的长者。新时期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兼美协主席的陈伯希,与当时省文联的领导班子,具体肩负着重新集结打散的文艺队伍、激发他们创作活力的重任。他们热情喷发,他们苦心经营,我见到了伯希异于往昔的活跃身姿,以及他高亮的语腔。笑声敞亮又带了磁力,特别是有了争论时的高调的坚持。烟依旧抽得紧,那烟云缭绕处是为事业谋划的沉思;口杯里的汲取则是适意时的散淡。环境及境遇就这样重塑了、或者说恢复了一个真实的三八老兵的伯希,我看到了一块沉默日久的煤的燃烧。应该说,他们杰出地完成了那个时段甘肃文艺队伍的恢复调整工作。甘肃美术界散兵的重新集结、重新勃发生机,领军人陈伯希功不可没。
那长长两个迥异时段的伯希,被我缩略为以上几行文字。我只取一点儿印象,只能说是对其背影的匆匆一瞥。
这块煤的持续燃烧,是在陈伯希离休之后。因了一段时间更近距离的接触,他给了我一个更清晰的形象。
是在我已决定退休而尚未离岗的某次省文联设的饭局上(似乎是2001年春节前的某个时段吧),我向在座的老前辈们敬酒时,伯希老在象征性的唇触酒杯后,一个手势招我近前,有问:“退休后打算做什么?”我的回答是含混的,仅以“休闲”一类词搪塞,此前确未想过这个问题。伯希却直奔主题:“来帮我做些事吧。”
这才知道,伯希离休后,由他主持的甘肃省书画研究院拟创办一份书画刊物,已得出版部门核准。伯希老希望我在刊物的编务方面做点儿事。
做过近三十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对编刊已经生出些疲倦感;心下盘算的是退休后好好消散些时日,然后来一番在岗时想去却没能去成的地方的自由行;加之,我与书画不在行。以上几点,使我无法给陈老一个确定的答复。陈老看出我的犹疑,用“你回去再想想”点了个分号。
果然没有画上句号。时隔不久的春节,似乎已过初五,接到陈老的亲笔短函:“过年时去文联家属院,曾去拜年,并想与你详细谈谈,但未见到,今由三子幼珀前去拜见并汇报。”并言画刊经费、事务已大体办理就绪,之后是:“请你出山,主持此事。”
我文联的老领导、我敬重的老前辈的这“请你出山”,令我惶然不安。我只能应命。我把这看作老班长对一个新兵的不容置疑的操令:出列!
这就有了我随伯希老创办的书画季刊《画苑英萃》几年的伴行。我最初的允诺是,只在文字方面做些审读的细事。未料,创刊号出来,版权页上我的名字前竟加有“主编”二字。书画专刊,我显然是承当不起的。这当然是伯希老对后生我的厚爱,我只能以进修的谦谨尽力而为了。
伯希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给《画苑英萃》撰写创刊词。匆匆草就,欣得伯希认可。其实第一期的编辑,此时伯希已不止成竹在胸,并有了具体内容的构想,且已一一书列于纸。清茶水果的第一次编务会议,轻松地议定了创刊号的编目,编委中几位曾在多家报刊效力的画家熟练地编排画板,画刊半已成形。伯希是1950年代兰州军区战士读物社的总编辑,后又任《甘肃画报》总编辑,是编辑界的前辈。他一定理解我于书画是生手,便有了画刊第一期编辑的示范,是师范。这解除了我如何入手的最初的惶惑。于此可见伯希细密的拳拳之心。
我在参与《画苑英萃》的编务后,始知所在办公地的“百蹊画室”,及画刊诞生的由来:这是一个故事。这是缺了伯希便不能讲得完整的故事。我确信世间的故事,应有一些是偶然的机遇;但它的完成,必有一颗素心的痴迷。
这本画刊,以及与画刊相伴而生的“百蹊画室”,扯出了一段与台湾同胞的交谊,也成就了甘肃美术界跨越海峡在祖国宝岛的第一次书画交流。陈伯希是此中的主角。
时间归到1998年。早在1988年就来大陆投资的台湾町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文相先生、总经理吴上财先生,素好书画艺术,经朋友介绍,在兰州结识了陈伯希先生,得临伯希居舍,得赏伯希书画,赞赏之余,有意请伯希老去台湾“走走看看”。遂有了应台湾创价学会邀请之宝岛三人行(陈伯希、杨丁东、杜时象),有了醒目的冠以“庶民心·艺术情”的三人书画联展。首展台北,移展新竹,历时月余。归途中,又应广东东莞台商会盛情邀约,在东莞市展出数日。
这是甘肃省书画艺术第一次与台湾同胞见面,是第一次的书画交流。尽管参展作者不多,展出画幅有限,但老艺术家们展拓中国书画艺术传统的矫健功力、吸纳塞上绮丽于胸怀的笔下生花,仍给众多参赏的台湾同胞留下了新鲜的、独特的印象。台湾创价学会理事长林钊先生特为撰文评介:“三位书画家虽年届古稀,仍充满了旺盛的斗志与创造力。从作品的苍劲挺拔、抒情寄意、有乐人间的意境,深刻感受到作者的真挚流露、回归自然的赤子之心。”
对于甘肃书画界,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书画家在宝岛的这次画展,也可以说是一次艺术交流的“踩路”之行——从此便有了二次三次……以及相关的运作。陈伯希为此与台湾友人有多次细密的沟通,极力促成了启幕于2000年元月的、含有西部19位知名书画家60余幅作品的“庶民心·艺术情——名家邀请展”。台湾创价学会理事长林钊先生盛赞为“美的飨宴”。
这飨宴的背后,书画界朋友知道,有着伯希特别的用功。痴翁的伯希对此默默。能为同行们做成一件事,他视为享受。
两次画展的台湾热心人吴文相,感于台湾公众对画展出乎意料的热忱,发出了“那份感动,让我们更有信心继续走下去”的愿想。这意味着新的运作。
删繁就简。不多说两岸热心人这期间的情来意往,这交流最终成就了两桩雅事:一是台胞出资购赠画室——兰州市中心的一栋高层大厦内,装修一新宽敞又雅致的330平米的“百蹊画室”,举行了有数十位台湾同胞到会助兴的隆重启砚典礼仪式;二是为新创画刊《画苑英萃》提供启动资金,并有继续资助之忱。
伯希先生多年来为画界公益事业奔波不疲。退居二线以来,尤为画家们、特别是退休的老艺术家们有个活动场所而劳心。而台胞吴文相先生们的赠画室,起意于吴先生到伯希家室的初次造访。他见陈老家室窄扁,兼客厅的画室,一方桌子,几把座椅,加上书架、画具,就没有多少空间了。想见这位颇有声望的老画家伏案作画的局促,探知创作桌案上无法展伸的大幅画作时,陈老竟是宣纸铺地躬身作画,许多精美的画作竟是在这样的斗室里造出来的。吴先生深为老画家安守清贫、刻苦自励的精神所动,隔年再次访晤陈老时,恳切表达了在兰州买一块地方赠作画室的盛意。一为老画家换新一个宽便的创作环境,二为甘肃省书画家提供一个群体活动的场所。
伯希特殊珍重这渗透着台湾同胞心意、凝结着两岸艺术家心血的画室,和对《画苑英萃》提供启动资金、并有意持续资助的厚情。许多人没有料到的是,伯希处理此事的我谓之伯希的方式。对于台湾朋友购赠的画室,伯希有一条坚持:谢不受赠;得使用权足矣。产权仍归出资购房的町洋公司。对于画刊的资助,只纳取启动资金;之后的经费,由画院自己筹措。
这是痴翁伯希的选择。这其实是为自己肩上加砝码的选择。痴翁此处之痴,或可能被误为傻?我眼里,这痴是痴守,痴守自然于心的某种信条。在伯希,他视为寻常的礼拒;我读出的是一种境界——这伯希的方式,这三八老兵的襟怀。
伯希的珍重是行动。一再强调并力行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空间,多办些事、办好实事。许多美好的艺术活动构想便源源不断地自伯希先生脑海涌出。每隔些时日,就有精心筹办的某一类书画展,或书画笔会,或书画研讨会在这儿举办。看着画家们特别是年轻辈在这儿挥毫,伯希老更像一个果园的守望者,时时关切着花蕾的绽放、佳果的坐枝。一杯清茶的氤氲里(当年吸得颇狠的香烟似乎很少见到了),有对别人成果的惬意的享受。
画院有个规矩在壁的例行聚会:周四笔会。画家可依自己的方便,来画室作画,笔墨纸砚俱全。可以挥笔抒怀,可以品茶清谈。我有几回临室观赏,这里有另一番境界。宣纸上走笔者,或有柔曼的勾画,或有潇洒的泼墨,书性尽在不言间。不言之静,能听到毫端触纸的细微。一纸画成,挂起来,就有几多目光的品评。总是到场的伯希,依旧一个果园守望者的姿态,一杯清茶的氤氲里,享受着画家们笔下的鸟鱼花卉、山光水色,一脸欣然。
在壁的规矩是:此日所作画归为画院资产。那些年,在画院书画家们的同心协力下,伯希先生和画师们以卖画所得资助画室画刊,使筹划的各项活动得以顺利开展。这就是伯希回应台胞捐资时“我们自己筹措”的一策,也是为自己肩上所加的砝码。其实画院同仁们心里有谱:在画室及画刊的形成及发展的整个运作过程中,有伯希老关键性的、多方面的付出,不只是力之劳顿。换言之,没有已届耄耋之年的伯希忘却年龄的操劳和付出,画室、画刊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在兰州的土地上生出。伯希似乎不觉得自己是在付出,只把这当作应尽的本分。淡泊如浅草间汩汩滑过的一溪清流。
他为此快乐着,最使他快乐的是得以与众多同道分享快乐。这块煤是为更多人燃烧的。
“更多人”视这个画室为温馨的家。一位退休老画家说得朴实:有这个家和没这个家感觉就是不同。多了一个去处多了一个家,多了一份念想,脚步不由地想往这里跑一跑。就闲聊几句,也畅快。
退休是人生的一个节点。多有人取一种“难得悠闲”的姿态,无可非议。忙促半生,舒缓喘一口气,情在理中。
继续唱着前进的有,伯希是一个。伯希是名著画坛的老八路,离休后,本可以借有较多的余暇,在宣纸上挥洒激情。画界有评:伯希的画愈到老年愈是风采卓然,愈显大家风范。这位早年木刻见长的画家,后来转攻花鸟,笔底挥洒出缠绵的诗意,甚乃历史的厚重。我读伯希大多作于“望九之年”的画册,大有“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感慨。画品显人品。你看这画题:“清风”(丛竹),“清净无垢”(百合),“苇繁不掩秋荷香”、“本色”(荷),“雄鸡高歌 蓬雀唧唧”……他有多幅百合画作,85岁时,最巨一幅题名《和谐之春》,整幅画面是百姿盛开的百合,“烂漫”二字写不尽。我有一个行外人的读画:从“斗争”年月过来的人,最珍重的当属“和谐”了吧?先生之属意百合,隐约似能觅见画家幽婉的心曲。署“八六逸叟”、题名《风尘》的大幅画作,视野里整个一地向日葵。题句:“五十年前遇此景,五十年后忆绘图”,两枚肩章,其一是“阅尽人间春色”。我有一个行外人的读画:离画作时的五十年前,应该是1957——1958年了。联系到伯希们的遭际,我有面对岁月《风尘》时良久的沉思。
伯希本可以在他画笔“老更成”之时,潜心于一案一纸上的挥洒,淡远窗外余事。他的唱着前进,是挽着更多画友的方队式的前进。他有画写君子兰,画题:“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伯希先生离休后之作为,这一命题已将其内核说得透透。
陈伯希九十大寿,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他文艺终身成就奖。领军人的劳绩更彰显于众多文化界朋友们的口碑。
《画苑英萃》的运作十分顺利,出刊后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必须说,年逾八旬的伯希老仍然着力最巨。每期总的架构基本都出自他的思考;却总是谦和地征询编委们的意见,听取大家的七嘴八舌。不薄名人爱新人。伯希对新人和基层书画家的关注,给我留下深的印象。每期都推出新人,伯希多有具名或不具名的亲自撰文,绍介评析。助力年轻辈,见着他们出了成果,伯希总有一种明显的享受感。对画笔矫健的新老画家,不惜篇幅,专辑着力推举。
惟他不在辑内。多位编委提议,应有他的专辑,伯希总是一笑推之。我也有两三次提请,伯希似乎有些松动:“随后吧,随后吧。”这个“随后”之许,一直到四五年后我离开兰州、离开画刊也未践诺。只在画刊创办第四个年头的某期的近乎结尾,因介绍一次四人画展的讯息,伯希等四人共占了仅只一个页面的局促!而这时,大约已有二百多位新老画家在画刊亮相。这就是甘肃画坛领军人、《画苑英萃》编委会主任的我们敬重的陈老陈伯希。
我一再强调了我的“进修”,于书画,我缺乏那方面的细胞,爱着,却没有本事入进;我的“进修”仍然有我珍重的收获——伯希老处事的我谓之的“伯希方式”: 他的谢不受赠,他的以卖画之资办刊,他的为更多人谋取利好;耄耋之年,一块煤的持续燃烧的精神……一些细事,在我眼里反而特别鲜亮。
在我离开画刊那年,伯希老用六尺长宣为我挥毫,一幅书体古朴苍劲的隶书墨宝,至今增辉于我小小的客厅:
竹瘦独存节 家贫惟有书
书画界,画案旁,年逾九十的伯希依旧瘦骨劲挺,依旧有煤的持续燃烧。忽然就想到藏族诗人丹真贡布《流沙河的背影》中的几行诗句,也可以是我眼里伯希先生瘦削背影的写真:
这里面没有脂肪
只有骨骼和韧带 还有
曾经被误认了的最好的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