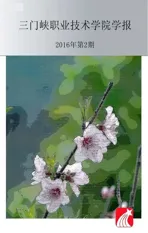女性话语的困境与突围
——新时期女性文学话语策略研究
2016-04-12高娓娓
◎高娓娓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文史哲专题研究
女性话语的困境与突围
——新时期女性文学话语策略研究
◎高娓娓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河南三门峡472000)
文章以新时期女性小说为文本对象,从话语策略的角度剖析了女性话语模式的阈限性,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并结合具体作品,探索了走出女性话语困境、实现两性对话的方法路径。
女性话语;话语策略;空间位置;美学转换;困境
在新时期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话语呈现出反叛性和性别差异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文本中差异性的叙述声音或叙事形式。但是,女性话语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是很难以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形而上概念量体裁衣地构建起来的。例如,这种话语是以女性的生理、心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小女人”话语,抑或是指类同于西方女权主义的特立独行、宏大叙事式的“大女人”话语呢?女性话语是以形式技巧、叙事手段的精致华美见长呢,还是以抵抗父权制度的决绝态度、抗争内涵取胜?这样的话语体系只能把女性的交往行为孤立起来,把话语实践行为在性别角度抽象起来,最终把社会领域和性别范畴内的性别对话、斗争、理解和包容简化为两性之间的差异对立,把内容的形式和形式的内容粗暴地加以分割,进而陷入本质主义的困境和被边缘化的危机之中。因此,笔者尝试着以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为例,力求能够较为准确、深入地探讨女性话语这一概念在女性文学中从对父权话语的依仗、借用到女性声音自身的张扬、外显,再到两性声音走向对话、渐趋和谐的整个过程,揭示女性话语策略的运用过程和运行轨迹,力求从性别二元对立的僵局中再次寻回两性和谐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一、女性话语模式的阈限性
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来看,女性文学对于现成话语的改装与改写,并不可能构成对既定话语传统的完全排斥与否定,而有可能在破坏现成话语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因袭和依赖;也不可能以女性的性别立场重构话语系统,而有可能在改写现成话语系统的基础上体现出某种性别立场和话语诉求。当代女作家张抗抗曾经这样表示,“作为一个女人,怎么会没有女人的感觉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除非这个女人不健全。但如果执意非要用女人的眼光去衡量一部作品,难道就是文学作品的阅读目的?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女性眼光不会是全部,不然,女人为什么还要去读男作家的作品呢?”[1]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追问一直处于两难的尴尬境遇之中,或者说,用女性话语模式去解决人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阈限性:当人们用人的标准去权衡性别问题的时候,人们担忧性别问题在大写的“人”的旗帜之下会失去应有的分量;当人们用性别问题为人的价值祛蔽的时候,人们同样担忧人的标准会在女性话语的蛊惑之下变得暧昧不清。正如张抗抗所言,“女性叙事角度、女性话语、完全女性化的文本,建立起一个完全女性化的文本。但这里随之产生一个问题:女人也同时把自己限制在了女人的天地之中,把一个原本共同的世界拱手相让了。”[1]打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相关的女性文学文本,就会发现,有关性别立场的话语表达正在一步步受到女性话语模式的限制和剥夺,一个两性共存的宽广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一种具有深厚底蕴的人文内涵正在变得越来越肤浅和趋于表面化,从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身体写作,到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以沈浩波、尹丽川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再到以木子美、春树、九丹、盛可以等为代表的美女写作,有关女性身体、女性生活、女性空间等描写越来越繁琐细腻,但是由这种话语模式呈现给读者的女性世界却越来越呈现出漂浮性、无根性和短暂性,有关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的表述越来越明确和坚定,但是由这种话语模式呈现给读者的女性立场却越来越暗淡和模糊。
纵观1980和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现状,作家和读者大都关注作品文本“言说了什么”的问题,而对于作品文本“怎样言说”的问题,均未引起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与对立都已超越了纯生物学的意义,日益显露出其文化建构的形式特征,女性话语模式即来自于这种文化建构,这一形式特征才是应该引起读者足够重视的关键问题。“所谓的男人和女人、‘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都是社会文化的杰作,是表意系统给他/她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特定含义。如果说传统保守不是女性写作的固有特征,那么前卫的实验性写作同样不是女性或女性主义的特色,更不是她们的‘专利’。”[2]在这里,笔者更愿意把女性特征的建构归之为女性文学的一场话语策略,归之为来自于文本自身的话语诉求。话语策略、话语诉求与女性话语有着根本不同,它强调的是话语的表达方式,侧重于从女性的生理、心理、气质、个性等多方面表达女性的生命经验和个体情感,从叙述模式、空间分布、美学风格等方面重新分配性别资源,进而重构女性在文本实践和话语言说活动中的立场并从观念上完成女性对于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话语策略、话语诉求将会疏离从具体的言说活动中去探求思想内容、道德内涵、价值取向等环节,更加关注话语活动的言说立场和相关语词的语法构成和存在形式,通过某种或某些结构法则、形式美学、风格特色从女性话语的困境中突围出来,切切实实地走上一条能够实现自我救赎的有效路径。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借助于新时期一些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加以展开,在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一些早期作品中,例如在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陆星儿的《呵,青鸟》,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万方的《在劫难逃》等作品里,叙述人都是以话语诉求的方式来表达女性意识的觉醒,以求在日常生活、政治、伦理、审美等领域有所突破。其中《爱,是不能忘记的》在一场婚外恋情的表述与探讨中,女性叙述人声音的发出虽然力求体现出某种差异性,女性叙述人的声音虽然常常有意无意地凸显出来,但从整体上看,女性声音主要借重于男性化声音加以个性化的表达,这种表达仍然是以承认父权话语为先在条件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开始表现或关注女性声音的独立性,如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五香街》,王安忆的《长恨歌》、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徐小斌的《双星鱼子座》、《迷幻花园》,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起》等作品已经先在地预设了女性话语同父权声音的反叛态度和弑父情结,这除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之外,更多地源自于作家的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女性立场,当然也与国内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的译介和批评有关。一些学者如熊薇、彭晓玲甚至从发音部位、音调、音高、音质等语言学层面指出了两性话语的生理差异,以及基于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差异,要求从点点滴滴的语言学工作扎实做起,建立起一种有别于男性话语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女性话语体系。
二、女性话语的突围:空间的位移和美学转换
应该说,降低叙述人的声调和叙述姿态,将话语陈述的动作尽量向内敛,模糊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界限,尽量转换叙述视角以期融入社会视野,已经成为新世纪女性文学创作的普遍诉求和策略转向。这种现象与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叙述权力,越是紧紧抓住不放并企图以此彰显弱势者的身份或力量,越容易形成强烈的本质主义、性别主义诉求,女性写作在文学格局中破‘蚕’而出的过程就是一个通过诉诸本质化、性别化的叙述人声音来表达女作家个人身份、个人言说的。”[3]可以这么理解,一种有关性别的话语存在显示和澄清了女性的性别、身份、意识和立场,然而女性话语离开了存在形式,其作为物的存在的立场也便丧失了,这正是哀伤地弃绝它的根本原因,也是远离本质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根本要求。
声音低调、风格内敛的女性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存在,近年来更是多有出现,如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迟子建的《伪满洲国》、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笨花》等作品基本上都采取了中性的立场和格调,叙述人在文本中所居位置较低。例如铁凝的《永远有多远》以白大省的表姐“我”为叙述人进行叙述,而“我”实际上是作为局外人存在的,这样“我”的声音和标准就未必靠得住,更何况“我”的声音和标准本身就矛盾重重,故事的末尾“我”居然声称自己对白大省并不了解,这样作品便产生了复调式的艺术效果,一贯以“仁义”著称的白大省内心却否定了“好人”这顶帽子,非常渴望能够变成像西单小六那样的女人,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仁义”的道德价值要远远大于作为女人的性别价值,而在白大省个人来讲,也许她更需要的是作为女人的性别价值;然而,白大省既然以做女人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为什么每每在关键时刻动起“仁义”之心呢?笔者想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仅在于思想内容的深刻和富于启迪性,也来自于叙述人位置的处理和安排,来自于超越女性话语的策略转向和形式创新。
与艺术形式的创新相适应,作品的美学效果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也显得格外突出。在早期的作品中,王安忆的《长恨歌》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作品中,抽象的历史现象通过具象的人物得以诠释,个人的生命体验附着历史的灵魂。女性细碎而实在的生命感受着变幻的历史,以生命铭刻历史成为作品文本中叙述人、主人公与历史“对话”的叙述策略。这种“琐碎”的历史感充溢着女性的主体性、情感性和过程性,以女性个体在历史时间中的悲剧存在演绎出一曲长恨不息的生命挽歌,也使历史的反思上升到了生命本体论的高度。王安忆的成功之处即在于把女性话语策略定位在历史的大构架中,把个体女性经验融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在对性别视野的超越中实现对女性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和美学观照。
这种叙事风格在蒋韵的《隐秘盛开》中也有所表现,即使灾难降临在主人公潘红霞头上,叙事节奏仍然丝丝相扣、有条不紊:“她把包存了,包里,有那个致命的诊断——要是能把它丢了就好了,她突然闪过了这么一个孩子气的念头,要是能把它弄丢让它消失多好啊!她又笑了笑。”[4]让舒缓的节奏和恬静的微笑来面对命运之神的不公,或许这种美学转换比起孤立的、静止的女性话语更能让人领会存在的意义。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强调,“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它的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5]打破传统的文化惯例,建立一种不受父权话语制约的女性话语体系,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而且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未来的社会是两性和谐共存的社会,未来的话语是以两性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为特征的话语体系;而且,性别的界限由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也会在社会和心理层面得以补偿,作为个体的性别主体也会打破二元对立界限,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容纳两种或多种性别元素。因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种形式和美学意义上的探索,女性文学能够通过话语实践的自适与调整,实现对性别话语的人文科学和美学观照,从而有利于整体话语体系下两性的和谐发展乃至多元化性别因素共存,以推动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1]张抗抗,李小江.女性身份与女性视角[J].钟山,2002(3):101.
[2]禹建湘.徘徊在边缘的女性主义叙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3]孙桂荣.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蒋韵.隐秘盛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5]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倪玲玲)
The Plight and Transcendence of Female Discourse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Strategy of Femal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
GAO Weiwei
(Sanmenxia Polytechnic,Sanmenxia 472000,China)
Taking female novels in the new period as an exampl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strateg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minality of female discourse patterns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feminine literature works since 1990s,and also,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works,it tries to explore the path.of out of the plight of femal discourse and gender dialogue.
female discourse;discourse strategy;spatial location;aesthetics transformation;plight
I207.4
A
1671-9123(2016)02-0085-04
2016-04-20
河南省教育厅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10—281)
高娓娓(1971-),女,河南洛阳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主义、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