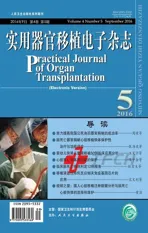心脏死亡供体肾功能的保护
2016-04-03韦中余韩永仕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北京100039
韦中余,韩永仕(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北京 100039)
近年来,我国器官短缺形势日趋严峻,严重制约了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目前,供肾短缺的矛盾日益加剧,自从我国取消死囚供体以来心脏死亡供肾已经成为解决供肾短缺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我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肾移植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时间短、数量少,有关供肾肾功能保护的报道较少,尤其是供肾获取术前肾功能保护方面的报道更少。现将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3年9月至2016年6月完成的268例可控型DCD供体在供肾获取术前肾功能保护方面的临床体会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在268例可控DCD供体中男性211例,女性57例。平均年龄40.7岁,自发脑出血120例,脑梗死13例,脑外伤70例,脑肿瘤35例,心肺复苏术后11例,其他疾病19例。
1.2 纳入标准: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1995年荷兰Maastricht(马斯特里赫特)国际会议定义的DCD分类标准。Maastricht分类:Ⅰ类:入院前死亡者,热缺血时间未知,属于不可控制类型;Ⅱ类:心肺复苏失败者,这类患者通常在心脏停跳时及时给予心肺复苏,热缺血时间已知,属于不可控制类型;Ⅲ类:有计划地撤除心肺支持治疗后等待心脏停跳的濒死者,热缺血时间已知,属于可控制类型;Ⅳ类:确认脑死亡的患者发生心脏停跳,热缺血时间已知,属于可控制类型。该类中的特殊类型:已诊断患者脑死亡,但家属不能接受心脏未停跳情况下进行器官捐献。在这种情况下,以心脏停跳供者捐献方式实施捐献,即撤除呼吸机,待心脏停跳后再进行器官获取。2011年2月,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分为三大类 :① 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BD);② 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大多数心脏死亡供体不符合器官捐献条件,临床上很难实施;③ 中国三类(C-Ⅲ):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与Maastricht标准的Ⅳ类相似,属可控制类型,符合脑死亡诊断标准。由于脑死亡法尚未建立,且家属不能接受在心脏跳动状态下进行器官捐献,对于此类供者,应按DCD程序施行捐献,即撤除生命支持,待心脏停跳后实施捐献。采用可控制型 DCD(MaastrichtⅣ类或中国Ⅲ类)。
1.3 脑死亡诊断:根据2013年9月发布的《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标准,由本院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ICU)3名教授同时结合正中神经短潜伏期体感诱发电位试验及脑电图检查结果确认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12小时后再次确认脑死亡。
1.4 撤出支持治疗及器官获取:在两次确认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后,与供体家属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按照美国器官移植分配网(UNOS)评估系统和威斯康辛大学评分系统评分,预计供体在撤出支持治疗1小时内发生心脏死亡。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ICU 教授共同见证下,将供体转运至手术室,撤出支持治疗,供体在 10~30分钟内发生心脏死亡,观察2~5分钟,宣布供体死亡。器官获取组织进行器官切取手术。
1.5 供体入科时及器官获取手术前主要参数对比(表1):供体在入科时平均尿量155.6 ml/h,切取术前平均尿量159.0 ml/h,肌酐入科时平均96 μmol/L,切取术前平均114 μmol/L,白蛋白入科时平均32 g/L,切取术前30 g/L。入科平均动脉血气氧分压143 mmHg,切取术前平均动脉氧分压157 mmHg。
1.6 合并症情况:268例可控型DCD供体中合并有发热的54例,需要升压药维持的85例,血培养阳性的4例,尿崩症24例,高钠血症61例。
2 结 果
在268例供体中入院时少尿者46例,血浆白蛋白偏低者134例,经过积极补液扩容,补充白蛋白纠正低蛋白血症,使中心静脉压(CVP)维持在8~12 mmHg(1 mmHg=0.133 kPa),其中有15例在术前尿量较前有增多,总有效率达32.6%。同时85例使用升压药者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量有所减少,15例在入院时肌酐高的患者有11例肌酐出现下降,有效率为73%。
3 讨 论
供体器官来源短缺一直是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原因。许多终末期肾病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供肾最终在透析中走向死亡[1]。DCD是公民器官捐献的一种形式,器官捐献必须在公民心跳停止以后(即心脏死亡以后)进行,20世纪60年代,DCD开始应用于临床。20世纪90年代,由于器官移植和器官保存技术的大大提高,以及捐献器官的供需严重不平衡,移植界开始广泛关注DCD。DCD供体可以显著扩大供体池[2]。我国现阶段能利用器官的主要方式是在供体发生脑死亡后,经过积极干预,调整器官功能,在供体达到预期撤除支持治疗后1小时内心脏停跳的标准后,有计划地撤除支持治疗[3]。有研究报道,器官获取时导致供体器官损伤的危险因素如热缺血时间、再灌注损伤、脑死亡等与移植后肾功能恢复不良有密切关系[4]。同时由于DCD供者长期昏迷卧床、基础疾病消耗、营养不良等因素,常出现全身感染、低血压等情况,加上大量应用血管活性药物,亦会造成供肾功能不同程度受损。造成DCD供肾肾移植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急性排斥反应(AR)的发生率明显升高,同时常伴有移植物生存状况差和术后早期移植物丢失[5-6]。因此,对于术前供肾功能的维护格外重要。
3.1 脑死亡对供体器官造成影响的病理生理变化常见的机制主要包括[7]:① 神经源性休克,其主要机制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功能障碍导致血管张力调节障碍;② 大量炎症介质和氧自由基释放导致的各器官损害;③ 脑死亡早期的“儿茶酚胺风暴”、Ca2+超载和过量β受体的激活导致心脏损害和心律失常;④ 甲状腺和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⑤ 尿崩症可能导致水电解质失衡;⑥ 神经源性肺水肿和吸入性肺炎;⑦ 体温调节障碍;⑧ 坏死脑组织释放大量组织纤维蛋白溶解因子和纤溶酶原激活因子导致凝血障碍。
3.2 生命体征维护:在得知患者家属有器官捐献意愿后,应立即开始加强器官功能保护。停用甘露醇、甘油果糖氯化钠等脱水药物,补足血容量。研究表明,对于低血压时间较长〔平均动脉压(MAP)<50 mmHg的时间超过15分钟〕,血管活性药物使用过多过久的供者,会造成捐献肾脏肿胀,包膜下出现瘀斑的发生率增大[8]。尽管有研究显示,小剂量去甲肾上腺素不会降低肾脏的灌注和血流[9],但大剂量和长时间使用α受体激动剂可导致肾血管收缩、肾血流减少,进而影响肾功能恢复。在268例供体中入院时少尿者46例,血浆白蛋白偏低者134例,经过积极补液扩容,补充白蛋白纠正低蛋白血症,使CVP维持在8~12 mmHg,其中有15例在术前尿量较前有增多,总有效率达32.6%。同时85例使用升压药者去甲肾上腺素的用量也较前有减少,15例在入科时肌酐高的患者有11例肌酐出现下降,有效率为73%,因此,对于术前尿少的患者,在监测MAP的前提下给予充分的补液扩容,纠正低蛋白血症,有利于肾功能的恢复。为保证肾脏血流灌注,我中心维持MAP>70 mmHg,尿量> 1 ml /(kg·h)。调整呼吸机参数,维持血氧饱和度(SpO2)在95%以上,动脉氧分压>100 mmHg。同时对于有高热的患者应给予冰毯控制体温。对于合并有感染的患者积极抗感染治疗。
3.3 电解质平衡:血钠水平是我们另一个关注的重点,由于尿崩症及胰岛功能的丧失,脑死亡供体常发生高钠血症。供体发生高钠血症时会造成细胞水肿,加重缺血/再灌注损伤,从而使移植物发生功能不良及移植物失功的风险相应增加[10]。然而最近有研究提出了相反的结论,Khosravi等[11]研究显示,供体血钠>155 mmol/L组与血钠<155 mmol/L组比较,两组受体移植术后肾功能指标无统计学差异。严重颅脑损伤伴有高钠血症、尿量增加> 7 ml /(kg·h)、尿比重降< 1.010、肌酐正常,要考虑中枢性尿崩症的可能性,这时应严密监测电解质,补液原则应该量出为入,必要时给予垂体加压素4~8 U肌肉注射,如无明显效果可持续给予垂体后叶素泵入。61例高钠血症的患者通过限钠、胃内冲洗等处理后均将血钠维持在<160 mmol/L。
总之,积极完善的供体器官功能保护,既提高了供肾的使用效率,同时也可以减少移植肾受者术后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