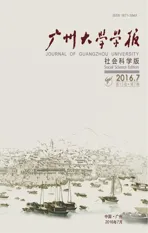认真对待“特赦”的法理言说
——从人权、宪法实施、法治三个层面说起
2016-03-09梁鸿飞
梁鸿飞,张 清
(1.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扬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认真对待“特赦”的法理言说
——从人权、宪法实施、法治三个层面说起
梁鸿飞1,张 清2
(1.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2.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
“特赦”关系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与国家刑罚的执行,绝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偶然性的政治决定来看待,否则会对国家的人权理念、宪法权威以及法治建设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国家正着力推动宪法实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认真对待“特赦”应是我们不可回避更不容小觑的命题。在立宪时代,“特赦”是一个储藏着人权保障价值的法律概念,而人权保障之根本规范为一国之宪法。那么,在法理逻辑上应将“特赦”措置在宪法之人权规范实施的范畴之内,而实施之路径应由以宪法为纲的法治来铺就。
特赦;人权;宪法实施;法治
201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重启已经尘封四十年之久的“特赦”,此一举动引起各界的广泛热议。但是,一阵热议之后官方层面就再无声息,直至今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会”报告中提及共赦免三万余人,“特赦”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就此而言,“特赦”之重启不免有些突兀之感,而且又在悄无声息间施行完成,它留给世人的是一副十分模糊的面貌,似乎仅仅是一个偶然性的政治决定。“特赦”关系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与国家刑罚的执行,倘若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偶然性的政治决定来看待,或是说留给人们这样一种主观印象势必对国家的人权理念、宪法权威以及法治建设都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是故,认真地对待“特赦”是我们不可回避更不容小觑的命题。
“‘特赦’的概念及其作为政治统治术在中国自古至今有之,在西方也同时自古至今并存。‘特赦’是一个跨越东西方、横亘古今的普世概念及政治统治术。”[1]然而,在前立宪社会,“特赦”并不是一个储藏着人权保障价值的法律概念,而只是君主或统治者恩施仁政、聚拢人心的方法、手段,“特赦”的时期具有不确定性,“特赦”的方式具有不规则性,“特赦”的对象难以进行类型的分化。在以宪法为圭臬,奉行法治的国家或时代,国家的治理讲求权利本位的价值宗旨与遵循法律的权力理念。在此语境下,“特赦”应由所谓的“恩施仁政”转向“人权保障”,而“保障”之根本原则与最高依据则在已被奉为圭臬的宪法之中,由以宪法实施为逻辑起点的法治方式推求而出。由此不难发现,现代之“特赦”,其价值宗旨在于人权保障,正当性渊源为宪法之人权规范,实施路径则由法治来铺就。是故,笔者就人权、宪法实施以及法治三个维度顺次而下来审视“特赦”,一方面以更为立体的方式描绘出“特赦”的法理原貌,另一方面亦为如何认真地对待“特赦”提供学理参考。
一、“特赦”与人权
“在当代,就各国政治理念及国内法上的‘特赦’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宽免理念,在形制上则是由国家元首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政令等形式对特定时期、对全部或大部分或一部分特定的犯罪人或不特定的犯罪人,对已判定之罪或正在追诉之罪予以免罪和免于刑罚或免于追诉尚未定狱之罪的政令、法律、政策或措施。”[1]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最高权力机关决定特赦四类服刑罪犯无疑是国家宽免理念的再次彰显,同时也是我国向海内外表达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契机。如赵秉志教授所言,“在新的历史时期施行特赦,充分展示了刑罚人道主义,凸显了国家和社会对罪犯的必要宽容。”[2]
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复读仇恨,而是以史为鉴企望未来。面对深沉的历史,我们时常提及的“殷忧启鉴”在宣扬“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朴素真理外,更是警示人类如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丧失了人道主义情怀,无论再怎么强大也必然坠入地狱的深渊之中。同理,施予痛苦的严苛刑罚是刑事法律乃至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存在的必要手段,但是施予痛苦并不是法律的价值依归,严苛刑罚亦非主宰国家的治理之道。罪行法定之后的人道主义补足是避免法治异化为刑治的重要屏障,以“特赦”为载体的人道主义情怀表达不失为纾解国家暴力氛围,消解社会戾气的善治良方。
具体来说,“反理性的、反社会的和犯罪的行为都被解释为是对人之正常本性的病态偏离,正像自我保护这种内在本能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和在一些人身上被结束自己生命的冲动所趋使而泯灭。”[3]32这种正常本性的病态偏离诚然给予了国家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正当理由,使其隔绝于社会,避免病态之危害进一步扩大。刑罚施予的痛苦与隔绝不仅仅旨在惩罚罪犯,避免危害,同样也有纠正乃至治愈罪犯之病态的功能与意向。也就是说,除非罪犯之病态已无药可救,非死刑不足以抵其罪过,其余之刑罚施予罪犯表明国家仍未放弃这些病态的少数人。当刚性的刑罚是本着“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这就说明国家仍在坚守权利本位的权力理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如同法律固有的空缺结构一样,刑罚矫治罪犯之病态的功能也并非面面俱到、药到病除。一味地固执于刚性严苛的刑罚有时往往适得其反,不顾世事的历史变迁,忽略社会期待的实质正义,完全依凭国家暴力维护稳定的秩序,所谓的法治也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实质上已经异化为刑治。所以,如同法官需要用法律解释方法填充法律的空缺结构一样,国家也需要用人道主义精神调处刚性严苛的刑罚,以致仁爱和宽容成为权力主体的个性与品格,那些病态的少数人也能够感受到人道的温婉理性之光。
事实上,“我们人类自身从来就是在爱与恨、宽容与残忍这两种情感的交织、博弈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全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摆脱邪恶之心逐渐走向理智、不断褪去残忍的本性走向宽容的过程。没有人类的理智和宽容,像‘特赦’之类的最能体现仁爱和宽容的政策或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特赦”所彰显的仁爱和宽容是寄寓于人道主义精神之中的,现代国家行使“特赦”之权并不源于皇恩浩荡式的恩典而是基于权利本位的价值原则。“人道主义(humanism)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即承认自己与他人都是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应享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中。”[4]此后,人道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并集中于人权这一伦理原则之中,成为人权之义。可见,人道与人权有着密切的耦合性。作为一项流行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伦理原则,“人权通过强调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资格、利益、能力和自由,来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防止和扼制任何把人作为手段或工具的功利主义的、结果主义的考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权是一个以人道作为社会进步目标的目的性概念。此其一。其二,人权是一个以个体作为人道主体的主体性概念。”[5]176它不仅把人道要求落实在具体的个体的发展与完善,更加强调个人是人道的主体,而非客体或对象。[5]176也就是说,所谓的人道关怀应当是人作为人而应有的权利,非当权者的恩赐。“其三,人权是一个以权力来推行人道的权威性概念。作为一个法学上的权利概念,人权不仅指承认人们所享有某种实际的符合人道原则的利益和需要,而且,它把享有和满足这些利益需要宣布为人的权力。”[5]177概而言之,人道主义是人权的主旨,现代人权又要求人道主义需要奉行权利本位的价值原则,脆弱的人道主义则需要借助人权概念予以强化、稳定以及发展。
回到“特赦”的命题上来,如果说“特赦”是对特定类型的罪犯所施予的合理的人道主义关怀,那么也可将其称之为国家依从权利本位这一价值原则,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对特定类型的罪犯提供的人权保障。这种人权保障虽不同于落实一般的国家作为义务主体的权利性条款,但就人道主义这一价值出发点而言并无二致,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治愈罪犯的偏离人之正常本性的病态,使之重新回归到理性人的角色,再次获得平等生存与发展之权利。就当下的一般情况而言,“伴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交往方式的愈加多样和交往风险的不断攀升,人权保障要求法律之治从更多层面和更多侧面加以回应。”[6]显然,现代人面临的各种风险在客观上要求人权保障在法律之治的层面向着更为绵延周密的方向迈进,这对大多数一般人适用,对少数正在服刑的罪犯也应同样适用。认真对待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乃至有罪过之群体的权利是拷问一国之人权保障完善与否、正义与否以及是否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关键命题。如范进学教授所言:“考察一个社会的人权实现状况,既要看多数人的人权实现程度,更要看少数人或个体公民的人权实现程度。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多数人的人权容易得到实现,而少数人或个体的人权诉求难以被重视、甚至被忽视或蔑视。如果一个社会建设起了对少数人或个体人权保护的屏障,让少数人或每一个个体的人权诉求基本得到满足,应当说该社会的人权状况就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不顾少数人或个体人权的保护,而一味地以牺牲他们的人权为满足多数人权利的代价,则该社会即会倾向于多数压迫少数的危险,这对于人权保护也是极具危害性的。”[7]认真对待少数人乃至有罪过之人的权利亦应为遵循文明之道的人类的价值共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和第二十六条就分别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可见,现代人权的发展之道应由“认真对待权利”迈向认真对待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乃至有罪过之群体的权利,这既是人权发展更为精进之路向,也是人权保障亟待填补之洼地。
现代国家之“特赦”,从某种角度可以被理解为刑罚人道主义。如果我们顺着人道主义这一关键词超越刑罚领域来看实则是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朝着更为精进的方向迈进。所以,如果说国家用完善人权法的方法来填补现代社会的人权洼地,那么“特赦”就是这一方法的微观缩影,亦或说具体表现。
二、“特赦”与宪法实施
前文提及,由于人道本身过为孱弱,是故需要借助人权概念予以强化、稳定以及发展。“特赦”实质上是国家以人权保障的方式推求人道主义情怀,使其落到实处,有所依归。然而,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四类服刑罪犯以来,多数人都在提及宪法第六十七条与第八十条,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七)决定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这两项条款诚然是国家施行特赦具有最高效力的规范性依据,但其所蕴含的更多的是程序性要素。如果仅仅只是强调宪法的第六十七条与第八十条,而忽视实质之价值依归,所谓的“特赦”势必给人留下灵动之政策或盛世之仁政的印象。尤其是距上次特赦已有四十年之久,又恰逢9·3阅兵盛典,种种因素似乎都在印证我国之“特赦”是灵动之政策或盛世之仁政。“特赦”既然是国家以人权保障的方式推求人道主义情怀,那么必然需要以宪法为纲的法律体系织构起落实人权、推求人道的规范之网。只不过,除了发现程序性的正当依据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探寻与明确法律体系之中的实质价值依归,使得法律实施尤其是宪法实施能够体现出保障人权的应有能效与推求人道的价值取向。
通常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形成与发展的逻辑基础是人的尊严与权利的保障,即人是宪法发展的基础。”[8]“一部宪法,如果失去了对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追求,就丧失了宪法的核心原则,从而也就不能称其为宪法。”[9]155-156可见,宪法作为根本之法应当在人权保障的法律实施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2004年人权入宪以后,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民众对此都有着莫大的期许,希冀“尊重与保障人权”成为法律实施乃至整个国家活动之主旋律。但其结果却乏善可陈,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公民的人权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人权事业能否取得进步,更多的恐怕不是取决于宪法做出什么样的规定。人权是理想和应然性的东西,但更是现实,是实践性的东西,特别是与政治和一国的历史有密切的关联,当其他相关的条件不具备、不成熟的时候,对人权进行过于热烈超前的讨论,有可能不利于人权的发展。”[10]
笔者认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平固然与其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人权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如何对其进行讨论并不影响它的发展。人权保障的法律之治并不需要过多的形而上色彩,公民的人权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宪法做出什么样的规定,因为更加关键的是国家作为义务主体是否切实地履行了公民权利保障书上的承诺。“一部宪法无非涵盖两大部分规范内容,即一部分是权力规范,而另一部分是人权规范——基本权利规范。”[7]而这两部分规范绝不是毫无交集,并列而行。相反,权力规范之实施旨在保障基本权利,也就是将权力主体作为义务主体履行承诺,保障人权规范的实施。[7]这在本质上也就道出了宪法实施的最终指向是人权规范。亦即,人权规范的实施乃宪法实施之鹄的。
张千帆教授有着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宪法实施分为两类:程序性实施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实体性实施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11]我国宪法目前实施之现状是,国家机关对照章办事的程序性实施已是驾轻就熟,而对指向实质正义的实体性实施则视为畏途。是故,所谓的宪法实施成为了程序性正当的走秀,宪法的实体性实施在国家优位主义的压制下被悬置起来,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如同镜花水月之境一般,可望而不可及。对此,林来梵教授有着这样的精辟比喻,“它真的就像一份重要证书所可能获得的待遇那样,被谨慎地装裱起来,悬挂在墙上,几乎成为一种象征性的‘镇国之法宝’。”[12]所以,就2015年施行的特赦而言,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宪法第六十七条与第八十条这样程序性意味浓厚的条款反而颇具讽刺意味。
“特赦”本应是国家基于人权这一伦理原则推导而出正常权力行为,这既是对宪法人权规范的落实,也是排除程序性走秀,推行宪法实体性实施的例证。然而,这却在我国是四十年一遇。我们与其强调程序性意味浓厚的宪法第六十七条与第八十条,或欣慰于局限在刑事政策的领域之内的人道色彩,毋宁省思这四十年一遇的“特赦”是否说明了我国的宪法实施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当然,或许有人会说除了第六十七条与第八十条之外,宪法并无其他关于“特赦”之规定,又何以在宪法之人权规范的实施视角来论及“特赦”,如此又何以认为“特赦”的常年尘封可以印证宪法实施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所谓“特赦”,赦其罪过,允其新生。在皇恩浩荡已过其时,人权理念已入人心的当代,“特赦”作为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这一人道主义情怀的表达本身就是人权发展的应有内容,人权保障的具体表现。宪法的本质就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但无需将各种权利一一列举完毕。再者,“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提纲挈领的原则业已写进宪法,在法律实施和国家活动中就理应起着思维路向与价值指标的作用。所以,可以确证:如果说“特赦”是人权保障的具体表现,那么它就应该纳入宪法实施的范围之内,即宪法人权规范实施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唯有将“特赦”纳入宪法实施的范围之内才能保证其尊重人权的价值取向以及以此为依托的人道主义情怀。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断定2015年施行的特赦的本质是灵动之政策或盛世之仁政,而只是在“特赦”应是人权保障之具体表现这一理论推断以及“特赦”四十年一遇这一事实背景下,反思人权入宪已十余年而人权保障却未有明显之改观这一困惑。反思之结论则可概括为:如果国家能够认真对待宪法的人权规范部分,认真地推行宪法的实体性实施,宪法自然可以由象征性的“镇国之法宝”回归到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提纲挈领的原则亦可在整个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如此,民众对“特赦”也无需啧啧称奇,因为其本身就是宪法实施的正常表现,而其四十年一遇之仁政面相亦转为常态化的人权保障之本相。
最后,如果我们将2015年之“特赦”结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来看,或可将其视为宪法实施之开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全会还提出,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把每年十二月四日正式设立为国家宪法日,进而具有法定效力。显然,面对宪法的长期悬置化处境,执政党中央已经明确表达了推动宪法实施的政治决心,尤其是设立国家宪法日之动议足见其认真对待宪法的政治诚意。国家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重新开启特赦自然有一定的政治考虑,但只要政治逻辑与宪法逻辑相一致,从执政党和国家推动宪法实施这一宏观背景下考量,将2015年施行的特赦视为宪法实施之开端仍然是合乎逻辑的。
三、“特赦”与法治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所以着力强调宪法实施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的法律体系看似门类齐全、日趋完善,实则是各立法主体各行其是、自说自话,难以形成有机统一之整体,所谓的法律之治就成了形式化、碎片化的照章办事。是故,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定,就迫切需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重新凝聚基本共识,以此为逻辑起点开启法治之征程。
所以,有人宣称:“依法治国必定要求依宪治国,如果治国不依宪,那就等于废弃了立国的根本,背离了最根本的国家共识,使法治陷于悖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设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13]宪法之治诚然是现代法治的根基与源脉,法律实施如果没有贯彻宪法之规范意旨,亦或离弃宪法之价值取向,就等同于否定自身“良法”之品格,“善治”随之亦不可期,看似宏伟的法治大厦实已危如累卵。宪法就如同法律海洋中的灯塔,为每一部法律的实施提供从立法、执法到司法的方向航标。但是,我们也要认知到,航标的提供诚是航行最为重要的一环,而仅凭航标再过壮丽的灯塔也不可能将人权、正义、秩序等诸多价值意旨送达至良法善治的彼岸。在法治这一命题之下,一方面,宪法之规范意旨的实现需要法律实施的延展与贯彻,另一方面,宪法之价值取向需要法律实施来提供承载程序。以宪为纲,以法为目,纲举目张方为法治。可见,法治征程的开启固然需要以宪法实施或说宪法之治为逻辑起点,但是这一征程一旦开启,无论是宪法实施还是法律实施皆应有机且统一地规置在法治这一命题之下,为良法善治这一目标而努力。
众所周知,法治与人治相悖,前者追求的是良法善治,后者期待的是王朝盛世。同样是赦免,法治之下的“特赦”必然与人治之下的“恩赦”有着根本的区别。“法治是一系列排列规整的程序,人权是法治程序所要实现的组合本体。”[14]只不过,宪法能否有效地实施决定了这一系列排列程序的规整程度与价值取向,进而关系着人权这一组合本体的内在意涵是否富有人道主义情怀。如果说“特赦”是日益精进之人权保障的具体表现,那么在宪法实施的背景之下,“特赦”也是经由法治程序所要实现的人权这一组合本体的外在形式。是故,“特赦”应被规置在法治命题之下,经由法治程序实现,接受法治原则的制约。国家施行特赦也要讲求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兹以保证其确定性、公开性,符合法治之程序正义的标准,由此实现的人权才是宪法规范意旨中的人权,由此推求的人道主义情怀才具有正义的说服力。要之,没有宪法实施情况下的法律之治不能称为法治,不经法治过滤的赦免亦不可谓为“特赦”。
具体来说,即“法治之下的赦免不应成为特定政治机构灵机一动的决策,或是偶然仁政的外显,而必须稳定化、连续化。对赦免的范围,通常应当交由民主的代议机关来决定,并且只能做到相对正义。对那些没有此次享受此项制度‘恩惠’的罪犯,在制度上还有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救济机会。当然,从制度设计上,也要增加特赦制度的可预期性、公开性等要素。”[15]就2015年施行的特赦而言,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国家元首签署,审判机关裁定,检察机关监督,监狱机构执行等这一系列的过程都要符合既有的法律规定,严守基本的法治原则。当然,毕竟“特赦”已经尘封四十年,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对此都颇为陌生,而且相关的实施规范一时也难以统一周整,具体操作程序势必难免有失精密,法律效果如何亦有待考察。所以,“未来特赦制度的发展愿景是使之常态化、程序化和公开化。比如特赦议案的提起程序、审议和决定程序,特赦的执行监督,特赦人员的帮扶、再适应社会制度,均需建立清晰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在条件成熟时,还可考虑使特赦机构常态化,并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特赦委员会,作为依据宪法和法律,辅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审议特赦议案、监督特赦令执行的机构。”[15]不难发现,施行特赦不是一张主席令那么简单,既要讲求规则化与程序化的系统性构建,又要推求宪法之人权规范的价值取向与人道情怀,其本身就是一项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建构的艺术工程。恰如陈云生老先生所言:“用清晰、明确的思维和体制上固定的建制,将‘特赦’确定为今人处理或调节社会纠纷的多元化选择中的一个选项,或许是一个不容回避和有极高价值期待的政治技术乃至政治艺术。”[1]显然,清晰、明确的思维应是讲求法治方式的法治思维,体制上固定的建制是在合乎宪法与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使“特赦”制度化,用更为具体、公开的程序链接其中,进而赋予其操作上的规范性、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在施行特赦制度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主观的思维路向与方式方法上,还是在客观的规范依据与参照标准上,都体现着规则治理、程序优位的基本原则,进而更有法治上的考量意义。唯具有法治的考量意义,“特赦”才是一项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建构的政治艺术工程,才能具有极高的价值期待。否则,所谓的“特赦”还是逃离不了“恩赦”的窠臼。
“法治方法排斥专断方式,法治思维排斥任意的思维。”[16]金斯伯格指出:“‘正义观念的中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性权力。”[17]可见,法治意味限制权力,排除任意,我们在注重“特赦”法治化以防其成为权力所任意操纵的“恩赦”之同时,也要认知“特赦”本身也应是修补法治不足的一种法治方式。这就如同法律的空缺结构需要法律解释来填补,法律的价值冲突需要法律论证来调处一样。在特定情境下,“特赦”是用法治的方式来修补罪行法定之后的人道主义缺失,但这并不意味宏观的人道主义可以任意地贬损讲求技艺精巧的法律方法,矮化或冲击具有原理性与准则性地位的法律原则。
有人认为,人道主义应作为刑罚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以化解罪行关系法定化的困境。具体而言,就是将人道主义作为司法者的职业道德责任以消解在特殊情境下法律之形式正义所显露的刻薄、残酷。[18]人道主义之所以需要用人权的概念予以框定,一方面是因为其过于脆弱,难以独立成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同样具有普罗透斯之面,如果不以细密的规范化方式推行,反而会泛滥成灾,以增添法治倾覆之风险。法律意义上的正义、公正或许在一定的场景或语境下显得冷酷严苛、不近人情,不符合普罗大众的朴素的实质正义期待,但是作为法律适用者的司法机关并不能用所谓的司法道德去柔化这种冰冷的形式正义。司法者的焦点应集中于法律解释和推定法律事实,过重地赋予其推求人道的价值负荷势必让司法权摇摆不定,事实与规范之间逻辑涵摄反倒成为法庭上的人道宣讲,这样一种不讲求法治方式和法律立场的思维只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贬损程序正义,进而与法治脱钩。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固执于刚性严苛的刑罚,完全依凭国家暴力维护稳定的秩序,但也不可将钟摆推向另一个极端,以人道主义来冲击罪刑法定这一刚性的法律原则,如此以牺牲法治为代价的人道主义进路无异于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罪刑法定作为法治所要求的基本准则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的确会偶然性地牺牲个体的合理权益,所以这才需要以施行特赦来补足罪刑法定之后的人道主义缺失。从某种角度说,“特赦”是由宪法与法律实施生成的产物,但它又是法律实施尤其是刑法实施的矫正器,其矫正之功能并不体现在法律实施之过程中,而是当法律实施之结果有悖宪法之人权规范意旨亦或民众普遍的实质正义期待之时,“特赦”才以法治化的方式予以矫正补足,亦即以法治的方式修补法治的缺漏。
人道主义并不是仁爱泛滥,人权保障不亦等同于恩泽天下之恶。在现代法治视力域下,“特赦”应表现为国家权力机关用法治方式来回应民众的正义诉求,实现宪法的人权保障宗旨,弥补法治的不足与缺漏,依此才能推求出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情怀。
[1] 陈云生.中国的特赦及其宪政意义[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9-33.
[2] 崔清新,等.三大看点解析特赦[EB/OL].(2015-08 -25)[2016-01-11].http:∥news.xinhuanet.com/ mrdx/2015-08/25/c_134552658.htm.
[3]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 黄枬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10.
[5] 夏勇.人权的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 罗豪才,宋功德.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社会科学,2011(3):4-19.
[7] 范进学.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J].学习与探索,2013(1):54-61.
[8] 韩大元.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论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6):5-9.
[9] 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0]刘松山.人权入宪的背景、方案与文本解读[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5):58-64.
[11]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J].清华法学,2012(6):19-25.
[12]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J].比较法学研究,2014(4):26-39.
[13]秦前红.依宪治国:法治的灵魂[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22-25.
[14]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一种人权史的解释[J].学习与探索,2001(4):44-45.
[15]秦前红.四十年后重启“特赦”意义何在?[EB/OL].(2015-08-25)[2016-01-11].http:∥news.sina.cn/ article.d.html?from=qudao&wm=3049_a111&docId= fxhcvrn0511218.
[16]陈金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意蕴[J].法学论坛,2013(5):5-14.
[17]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4):5-27.
[18]孙万怀.罪行关系法定化困境与人道主义补足[J].政法论坛,2012(1):92-104.
[责任编辑 吴震华]
Getting Down to Special Pardon from a View of Jurisprude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ights,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e,and Rule of Law
LIANG Hongfei,ZHANG Qing
(1.School of Law,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China;2.School of Law,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Jiangsu 225009,China)
Special pardon is related to the disposal of civil right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enal system.We can not regard it as a temporary political decision.Otherwise it will cause a considerable negative impact on human rights view,constitutional authority,and the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After 4th plenary session of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China is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building a law-abiding government.So we must treat the special pardon carefully.In Constitutional era,we know that special pardon is a law concept which contains the aim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So jurisprudentially,the special pardon should be within the frame of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norm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and the path of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paved by the rule of law.
special pardon;human rights;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rule of law
D924.13;D921
A
1671-394X(2016)07-0024-06
2016-03-31
梁鸿飞,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法理学、民商法学研究;张清,扬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法理学、宪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