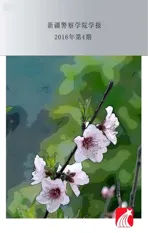完善“污染环境罪”的思考
2016-02-27谯冉李森
谯冉,李森
【法学论坛】
完善“污染环境罪”的思考
谯冉,李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38)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罪状。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立法理念、罪状表述方面仍存在纰漏。从立法上完善“污染环境罪”应增设环境危险犯,完善罪状表述,创新罪名体系。
污染环境罪;环境刑法;立法完善;环境危险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污染物的排放量显著增加,生态环境面临各种潜在威胁,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民生议题,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严惩污染环境的刑事犯罪已成为社会共识。为此,我国于201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修改,新罪名被确定为“污染环境罪”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EB/OL](2011-04-19)[2016-11-24].http://www.court.gov.cn/qwfb/sfjs/201104/t20110429_20043.htm.。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与之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2013年《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立法的修改与新司法解释的出台,使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司法适用上扩大了适用范围,体现了我国对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重视与决心。但是,仔细比较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2013年《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与2006年颁布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司法解释》,笔者发现2013年《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仍然强调打击已然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对环境危险犯、环境法益等理论问题没有较大突破,这就容易造成立法理论与司法适用的脱节,使得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不断发生,但是处罚的案件却非常有限。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试从本罪的立法理念以及环境危险犯的讨论入手,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刑事环境立法有所裨益。
一、本罪存在的立法问题
立法模式是有关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外在表现形式,现行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规定是对当前环境犯罪的立法思想与立法技术的具体体现。如果说近年来污染环境犯罪行为被入罪的数量加大,得益于《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立法的修改,那么针对环境法益保护对象的不同、完善环境危险犯、规范罪状表述,应是下一步从立法方面完善本罪的角度与方向。
(一)立法理念过于保守
立法理念为划定法益范围和确定治理手段能起到指导作用。纵观“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背景与当前的司法实践,本罪仍是针对已然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要求必须发生实际破坏环境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却是我们不能估量的,补救所付出的成本更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此类严重污染环境犯罪的预防远比打击更为关键和重要。部分地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只有给人们的健康、财产造成重大损害时才能引起人们对此类犯罪行为的关注。这种“人类中心”本位主义的立法理念,不利于对环境犯罪的有效打击,而且一旦发生重大环境事故,补救成本巨大,甚至给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严惩此类犯罪势在必行。
目前,“污染环境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的第六章。从立法意图的角度来看,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国家对社会的管理秩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此类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往往是一般犯罪所无法比拟的,危害结果的出现往往会给整个社会和个人带来难以估量的沉重损害。由于污染环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我们有理由提高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避免可预料的污染环境事故的出现,将立法理念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预防,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建议对此类犯罪行为的处罚时间点适当提前,有条件的可将环境危险犯这一概念引入本罪。
(二)罪状表述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法》分则第338条对“污染环境罪”的罪状作出了如下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立法表述追求科学性与准确性,如果把“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和“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为因果关系,那么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就一定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吗?这显然是不科学,因为严重污染环境的确认要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定。如果把“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和“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为并列关系也存在问题。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了14种具体的犯罪行为,但是这14种行为中并没有包含篡改监测数据偷排的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在实践中是比较常见的,同时危害性巨大。这种危害性巨大的犯罪行为与“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犯罪行为不同,同时未被司法解释明确涵盖,使得本罪在打击此类犯罪行为时鞭长莫及。这也暴露出本罪在立法模式上单纯追求犯罪结果,没有分区具体法益之间的保护对象,造成了罪状表述的冗长与不科学,同时也不能有效遏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层出不穷的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理解“严重污染环境的”的概念时,应当从整个犯罪构成的全局考虑,明确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何种行为可能侵害法益,如何界定侵害的种类、程度,以达到在系统认识本罪的基本上,简洁罪状的表述,细化保护对象。
二、完善“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建议
(一)增设环境危险犯
增设环境危险犯主要是出于“预防优先”的立法理念,严重污染环境犯罪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驱动,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实施此类犯罪,因此在一些区域这类犯罪具有易出现而恢复难的特点,一旦发生,会对人们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以污染海洋罪、污染土地罪为例,其具有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破坏力强的特点,有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例如,1986年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毒气泄漏事件,相关受害者生育的子女都患有先天性双目失明症。①张瑞幸.过失危险犯与环境犯罪[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56-58.针对此类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如果本罪的立法理念一味强调对造成结果后的惩罚,而忽略了对环境造成严重危险状态行为的处罚,就有可能放纵犯罪,不利于本罪发挥其应有的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将环境危险犯的概念引入本罪是有必要的,尽管当前危险犯适用于本罪仍会引起司法适用、立法协调等诸多问题,可这一趋势可能会成为本罪今后改革的重点方向。
引入“环境危险犯”这一概念,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明确危险的含义。污染环境犯罪中所指的危险究竟应依据何种标准,是人们对危险的普遍意识、相关专家、学者对环境危险概念的共识还是国家的既定标准?如果将“危险”界定为一种具体危险,由于污染环境犯罪对于环境危害具有长期性、潜伏性等特点,要证明这种危险并不容易,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学理上进行讨论。“危险”指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可以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行为的危险”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作为结果的危险”指行为所造成的对法益的威胁状态。②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6.
笔者认为,环境危险犯中谈论的“危险”指作为结果的危险,指行为已经引起严重污染的危险状态。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依据“侵害的危险”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将犯罪行为分为侵害犯与危险犯,又进一步将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③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1.具体危险犯指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紧迫危险。抽象危险犯指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即可。①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67.在一般社会观念下,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不论是对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对环境法益本身都具有危害的紧迫性。笔者认为应该区分犯罪行为进行具体分类,一方面体现罪刑法定的精神,另一方面发挥刑法精确性的指导作用。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一定区域内危害性不显著的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要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足以造成某种法定危险状态来判断,这种危险状态应该是具体的法定危险,可以由有关部门针对区域内环境承载力,通过统计学与环境学等学科的标准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涉及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核设施、核材料等污染源的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以抽象危险来进行判断,只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该行为造成了自然环境、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处于受严重威胁的危险状态之中,则行为人就要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的“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同样是指根据犯罪地的环境承受力和人们对基本生活环境的需要为依据,并结合国家当前的经济技术水平以及相互衔接的行政责任限度来综合确定。仅仅针对的是保护对象不同,前者是国家生态安全利益,后者是区域的环境承载力。
综上所述,环境危险犯的设立还需要理论上的完善与技术上的支持,但就污染环境罪中设立危险犯本身而言,一方面可以弥补本罪行为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严重污染环境事故的发生,对于防患未然,发挥污染环境罪打击环境犯罪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完善罪状表述
我国的罪状修改一直奉行“治大国如烹小鱼”的慎行传统,针对现实问题,在保证体系完整的情况下,罪状的修改一直以“精、准、少”为目标。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对之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体现了立法者的良苦用心,一方面体现出追求一种保护环境法益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本罪的适用范围。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慎行传统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法律滞后性的缺陷。例如,伪造、篡改监测数据偷排的行为是此类污染环境犯罪中比较常见的手段,但是司法解释却缺少对此类犯罪行为的明确规定,以致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行为。此外,本罪的罪状存在表述不科学的问题,“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与“严重污染环境的”如果是因果关系显然存在问题,如果是并列或者补充关系,在引入环境危险犯概念的大趋势下,“严重污染环境的”的表述有画蛇添足之嫌。
笔者认为,随着人们对环境法益的重视,环境刑法独立成为一类犯罪是一种势趋。在目前仍适用一个概括性罪名“污染环境罪”的现状下,可以按照具体污染对象的不同,积极探索符合实际需求的独立罪名,例如污染水体罪、污染海洋罪、污染大气罪以及污染土地罪四个具体犯罪,并对其罪状作相应设计。
1.污染大气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向大气排放有害物质、造成空气的性质发生不利改变,处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污染大气犯罪客观方面不需要产生具体危险,只要有实际的排放行为即可构成。同时,本罪的入罪门槛与法定刑都不宜设置过高,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坚持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2.污染海洋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向海洋环境排放有害物质,造成内海水域水质发生不利改变,处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较其他污染行为,防治海洋污染的法规繁杂,有《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理条例》等,不胜列举。但是,其主要是根据污染源的不同进行的分类,例如核材料、海洋石油勘探、拆船污染等,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立法形式。此外,海域一般分为内海与外海,考虑到国家生态安全利益,可以把内海水域水质发生不利改变作为入罪的标准。笔者建议,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将配套法规体系化、系统化,以使其能够适用各种污染方式,充分发挥本罪担当打击严重污染海洋犯罪方面的作用。
3.污染水体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向地表水体、地下水体等内水水域排放有害物质,造成水质发生不利改变,处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污染水体犯罪对人身安全与公私财产影响较大,客观方面的认定不需要产生具体危险,但要考虑水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需要相关环保部门以国家生态安全利益为重,制定较为严格的认定标准,只要犯罪行为达到相关标准即可构成本罪。
4.污染土地犯罪
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环境(包括草原、湿地等),排放有害物质,致使土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土地资源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土地本身不具有流动性,一旦污染,很难恢复。因此,对污染土地犯罪行为单独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新罪名体系
目前,我国刑法分则体系的安排主要有两个标准:一种标准是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由重到轻进行排列;另一种标准是按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将犯罪分为十大类。按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进行分类的方法可以突出刑法打击犯罪的重点,有利于司法人员更准确地掌握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但目前由于“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其体系安排主要按照同类客体的方法,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并没有凸显出对此类犯罪危害性的重视。此外,由于我国刑事立法的传统,“污染环境罪”是对于“重大污染事故罪”的延续,本罪的体系安排没有从根本上关注本罪客体在今后社会实践中可能发生变化的特殊性。而且,就目前“污染环境罪”的客体——国家对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其法律规定较为庞杂,主要有《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其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更是不胜列举,这些法规之间并没有形成系统体系,而采用混合罪名形式设立的“污染环境罪”又过于笼统,因此,完善罪名体系是完善本罪的重要任务。
解决“污染环境罪”罪名设置过于笼统的问题,主要包括两种方式:其一,完全采用独立罪名形式,取消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直接依据环境要素的不同,分别参考其各自独立的法律条款,具体规定为水体污染罪、海洋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土地污染罪等环境犯罪行为;其二,继续采用混合罪名的立法模式将有关污染环境的行为纳入统一法条之中,尽力弥补此种模式过于笼统的缺憾,对具体法律条文规定予以细化和优化,补充明确有关犯罪构成、刑事处罚的内容。笔者认为,两种模式各有千秋,第一种模式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一方面可以细化污染环境罪,增强法律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将来在刑法中增加“污染海洋罪”“噪声污染罪”等新型污染环境犯罪奠定基础。第二种模式符合目前我国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现状,能够保证立法体系的完整性与历史传承的统一性。出于对环境刑事立法趋势的考虑,笔者在这里选择了第一种模式并提出了一些设想,希望有助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完善,进一步促进环境刑事立法在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环境中的重要意义。
[1]侯艳芳.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既遂形态的立法思考[J].山东大学学报,2013,(2):65—72.
[2]郭浩,李兰英.风险社会的刑法调适——以危险犯的扩张为视角[J].河北法学,2012,(4):121—128.
[3]陈家林.我国不能犯理论基本立场的再定位[J].刑法论丛,2007,(1):77—139.
[4]李岸曰.新“重大环境污染罪”属结果犯、危险犯还是行为犯[J].环境保护,2011,(11):51—52.
[5]陈家林.论刑法中的危险概念[J].云南大学学报,2007,(2):32—38.
Consideration on Comple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
Qiao Ran,Li Sen
(Law Department,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China)
The 338th article of Criminal Law in operation in China has acc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In June 2013,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joint to release Explanations for the Laws of Handl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ind Cases.Compared with the explanation tha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nounced in June 2006,the new released one has some flaws in legislative ideas and accusation expressions.In order to complet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new system of charges should be set up,and accusation expressions be comple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s;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perfect legislation;environment potential damage offense
D924.3
A
1672-1195(2016)04-0056-(04)
责任编辑:王梅
2016-11-24
谯冉(1987-),男,四川达州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办公室政策研究室民警,主要研究方向:警察法学、刑事法学;李森(1986-),男,北京人,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民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刑法。
【doi】10.3969/j.issn.1672-1195.2016.04.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