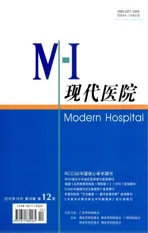术后镇痛管理的现状与展望
2016-02-21谢创波屠伟峰
谢创波 屠伟峰
术后镇痛管理的现状与展望
谢创波 屠伟峰
术后疼痛治疗既是患者的权利,也是麻醉医生的职责。理想的术后镇痛管理有利于手术患者的快速康复。目前,虽然术后镇痛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但镇痛理念不一、管理低效和个体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仍然影响术后镇痛的效果和患者满意度。镇痛管理的全程化、智能化和个体化的全面实施可有效提高镇痛管理质量,缩短患者术后康复时间。
术后镇痛;全程化;智能化;个体化
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快感觉和情感反应,是继血压、脉搏、呼吸和体温后的第五生命体征。术后疼痛(Postoperative Pain)是手术后即刻发生的,其性质为急性伤害性疼痛,也是临床最常见和最需紧急处理的急性疼痛。疼痛是患者术后主要的应激因素之一,可导致患者术后早期下床活动或出院时间延迟,阻碍外科患者术后康复、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因此,有效减轻术后疼痛,是降低患者应激反应和缩短其住院时间的重要措施。
Henrik Kehlet教授[1]在1997年首次提出了ERAS(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ury,ERAS)的概念,在2012年又阐述了快速康复外科的未来发展方向[2]。所谓ERAS是指采用一系列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围手术期处理措施,涵盖了麻醉、镇痛和微创手术等各方面。ERAS可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患者死亡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和降低住院费用[2-3]。提供适合的镇痛是ERAS方案的核心要素之一[4],因此,术后镇痛在患者的快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中尤为重要。本文对目前术后镇痛的现状与镇痛管理方法、存在问题与困惑、镇痛管理的未来与展望等方面作一综述。
1 术后镇痛的现状与镇痛管理方法
1.1 术后镇痛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新型镇痛药物及非药物镇痛方法的应用,术后疼痛治疗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仍有相当多的患者术后疼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在一项调查中[5],术后24 h和48 h,术后疼痛的发生率分别为55.3%和34.7%,其中,中、重度疼痛的发生率分别为13.0%和11.7%。多种因素可致患者术后镇痛不足,目前缺乏有效的术后镇痛规范。术后恶心和呕吐(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PONV)是一种常见的手术麻醉后并发症,约30%手术患者在术后24 h内发生PONV。在一些具有危险因素的患者中,PONV的发生率甚至可高达80%左右[6]。术后镇痛不足和镇痛药物使用过度,可增加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这是目前术后镇痛管理中遇到最棘手问题之一。此外,镇痛用药杂乱、配方不合理、镇痛管理不到位、没有专职急性疼痛服务(Acute Pain Service,APS)队伍、镇痛数据记录不全等也构成了制约镇痛管理效果的诸多因素。
1.2 常见术后镇痛管理方法
从近年来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在术后镇痛管理的实际操作中,主要是按照相关专家共识、管理规范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来进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倾向和做法。目前,主要的镇痛管理方法有:①术后疼痛评估: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数字等级评定量表(Numeric Rating Scales,NRS)、语言等级评定量表(Verbal Rating Scales,VRS)和Wong-Baker面部表情量表等方式进行术后疼痛强度评估;通过评价药物或治疗方法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疼痛治疗结束后由患者评估满意度进行术后疼痛治疗效果评估。②多模式镇痛:术后疼痛的产生是一个多环节、复杂的过程,单一的镇痛机制不足以达到理想的镇痛效果,多模式镇痛通过干预多层面的痛觉感知或传导,实现不同作用机制药物或镇痛方法的相加或协同,在围术期的疼痛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患者术后自控镇痛(Patient Controlled Analgesia,PCA):国内使用PCA已有二十多年,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步。目前主要的PCA方法有硬膜外PCA(PCEA)、静脉PCA(PCIA)、外周神经阻滞 PCA(PCNA)、皮下 PCA(PCSA),其中PCEA和PCIA最为常用。
2 目前术后镇痛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2.1 镇痛理念不一
目前,尚无比较健全的术后镇痛管理规范和制度,是造成术后镇痛不足的多方面因素之一[7]。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术后镇痛管理主要是以各类指南和相关文献报道为指导,并结合麻醉医生自身工作经验来实施。那么什么样的镇痛管理理念才是最优化的?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2 镇痛管理繁琐低效
传统的 PCA泵是分散型的使用模式,管理不便。电子泵报警后医护人员不能及时获得信息进行相关处理,报警声音造成患者不必要的紧张,输出信息不能及时汇总,医护人员管理工作量大;机械泵只是恒速输注,不能随患者病情的变化而随时调节,不能达到个性化治疗的目的,遇有输注管道堵塞等严重影响镇痛质量的问题,医护人员不能及时发现[8]。此外,术后镇痛的数据未能被自动采集建立成数据库,导致术后镇痛工作质量不能持续改进。
2.3 未能实现个体化
急性疼痛管理的目标[9]是:最大程度的镇痛、最小的不良反应、最佳的躯体和心理功能、最好的生活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疼痛与多种个体因素有关,如性别、年龄、心理状态等。然而,目前的镇痛管理中注重考虑病种、术式等因素,较少考虑患者的个体因素。目前的镇痛管理能否到达疼痛管理的目标,如何使每个患者对术后镇痛效果感到满意,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镇痛管理的未来与展望
3.1 全程化镇痛管理
这里所谓“全程化镇痛”,是指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整个围手术期的镇痛干预,主要遵循多模式镇痛原则。
围术期的疼痛管理和应激控制是影响ERAS效果的核心因素,这就需要不断更新术后镇痛的理念、优化镇痛管理模式,得到更好的镇痛管理和加快患者的术后康复。随着对疼痛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术后疼痛的干预不再局限于在手术之后进行镇痛,在整个围手术期进行镇痛干预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因此,术后镇痛管理的理念不再是单一的“术后”镇痛,而是围手术期的“全程化镇痛”。
3.1.1 术前镇痛干预 提到术前镇痛干预,我们很容易能想到超前镇痛和预防性镇痛。这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有学者对两者的含义进行了专门的阐述[10-11]。超前镇痛指的是术前给予某种镇痛治疗比切皮后或者手术后给予同样的治疗更加有效。超前镇痛强调的是手术开始之前而非之后进行疼痛治疗,目的是减少伤害性刺激引起的外周和中枢敏化。然而,有专家在回顾了3篇有代表性的荟萃分析后,质疑超前镇痛的有效性[12]。相比起超前镇痛,预防性镇痛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13],指的是在发生痛觉敏化之前给予镇痛措施以阻止中枢敏化,而不限定给药的时机。随着术后镇痛理念的变化,超前镇痛的概念也向预防性镇痛迁移[10]。预防性镇痛干预时间点可以在术前,但又不局限于术前,而是可以在术前、术中和术后任意时间进行镇痛干预,这与全程镇痛的理念相符。
预防性镇痛可以采用多模式镇痛的方法,具体包括神经阻滞、椎管内镇痛、静脉镇痛、口服给药、皮下或肌肉注射给药、切口局部浸润等[14]。近年来,也不断有研究发现多模式预防性镇痛的有效性,Mario Nosotti等[15]通过一项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发现,术前使用右美沙芬联合肋间神经阻滞进行预防性镇痛,能够减少术后早期镇痛药物的使用量。
3.1.2 术中的镇痛干预 术中优化麻醉管理和镇痛是ERAS策略中重要的一环,区域麻醉、预防性给药、联合不同作用机制的镇痛药物、使用抑制中枢敏化的药物等都是镇痛管理的重要要素[16]。另外,苏醒期停止镇痛药物需提前采用镇痛措施,如使用镇痛药物、切口局部麻醉、神经阻滞、硬膜外给药等,以保证窗口期的有效镇痛。
3.1.3 术后镇痛干预 术后镇痛干预采取以PCA为主要镇痛手段的多模式镇痛方法,并遵循个体化原则。个体差异会影响患者术后镇痛的具体需求,根据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镇痛方式和镇痛药物。值得注意的是,进行PCA的患者撤泵后的疼痛管理常被忽略。突然中断的阿片类药物镇痛可能引起强烈的疼痛,这可能使我们的镇痛工作功亏一篑。
3.2 智能化镇痛管理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信息化技术改进医疗质量的应用越来越多。信息化和智能化可以应用于术后镇痛的管理,如无线镇痛泵的使用[17],有利于减轻医务人员工作量,收集积累形成术后镇痛大数据,促进镇痛管理规范化,这也符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建设和物联网发展规划的要求。
PCA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可实现对镇痛相关数据进行自动采集,重现PCA过程,分析镇痛效果[17];广泛应用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信息,可为制定术后镇痛药物配方、剂量和参数设定提供更好的研究平台,也为镇痛的质量控制提供更真实可靠的数据,不断促进术后镇痛的规范化管理[18]。相比传统的PCA镇痛泵,术后镇痛智能化管理系统可实现院内镇痛泵信息化管理,并使用移动终端进行监控、查房、随访评价和记录等,大大节省人力,又快捷高效。
3.3 个体化镇痛管理
有文献报道,对术后疼痛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药物治疗能够更好地控制疼痛[19]。此外,APS小组对PCIA患者实施全程干预不仅可降低镇痛不全发生率,减轻PCIA患者术后24 h内的疼痛,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还可以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量[20]。APS小组通过有针对性的宣教、调整镇痛用药、进行镇痛查房等方式提高了镇痛管理的个体化程度,从而提高了镇痛服务质量。通过综合评估患者个体因素,进行个体化镇痛管理,将会使更多患者受益。
[1]KEHLET H.Multimodal approach to control postoperative pathophysiology and rehabilitation[J].Br J Anaesth,1997,78(5):606-617.
[2]KEHLET H,SLIM K.The future of fast-track surgery[J].Br J Surg,2012,99(8):1025-1026.
[3]CANNESSON M,KAIN Z.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versus perioperative surgical home:is it all in the name?[J].Anesth Analg,2014,118(5):901-902.
[4]SCHUG S A,PALMER G M,SCOTT D A,et al.Acute pain management:scientific evidence,fourth edition,2015[J].Med J Aust,2016,204(8):315-317.
[5]MWAKA G,THIKRA S,MUNG'AYI V.The prevalence of postoperative pain in the first48 hours following day surgery at a tertiary hospital in Nairobi[J].Afr Health Sci,2013,13(3):768-776.
[6]GAN T J,MEYER T A,APFEL C C,et al.Society for Ambulatory Anesthesia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J].Anesth Analg,2007,105(6):1615-1628.
[7]洪 溪,黄宇光,罗爱伦.术后镇痛的规范化管理[J].中华麻醉学杂志,2005(10):798-799.
[8]韩文军,邓小明,赵继军.手术后患者自控镇痛的管理策略[J].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5,36(1):73-77.
[9]徐建国,吴新民,罗爱伦,等.成人术后疼痛处理专家共识[J].临床麻醉学杂志,2010(3):190-196.
[10]唐 帅,黄宇光.术后镇痛理念新跨越:从超前镇痛到预防性镇痛[J].协和医学杂志,2014(1):106-109.
[11]ROSERO E B,JOSHI G P.Preemptive,preventive,multimodal analgesia:what do they really mean?[J].Plast Reconstr Surg,2014,134(4 Suppl2):85-93.
[12]佘守章,许学兵.超前镇痛有效性争议及预防性镇痛的研究新进展[J].临床麻醉学杂志,2008(6):545-547.
[13]VADIVELU N,MITRA S,SCHERMER E,et al.Preventive analgesia for postoperative pain control:a broader concept[J].Local Reg Anesth,2014,7:17-22.
[14]中国加速康复外科专家组.中国加速康复外科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2016)[J].中华外科杂志,2016,54(6):413-418.
[15]NOSOTTI M,ROSSO L,TOSI D,et al.Preventive analgesia in thoracic surgery:controlled,randomized,double-blinded study[J].Eur J Cardiothorac Surg,2015,48(3):428-433.
[16]HOROSZ B,NAWROCKA K,MALEC-MILEWSKA M.Anaesthetic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ERAS protocol[J].Anaesthesiol Intensive Ther,2016,48(1):49-54.
[17]王浩然,曹汉忠.无线镇痛泵系统的应用效果探讨[J].中外医疗,2015(3):52-54.
[18]杨霜英,于京杰,朱四海.无线镇痛信息系统在麻醉科的应用[J].中国医学装备,2014(1):57-59.
[19]DE LEON-CASASOLA O.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multiple factors involved in postoperative pain course and duration[J].Postgrad Med,2014,126(4):42-52.
[20]刘冬华,陈雪莉,于爱兰,等.急性疼痛服务组织全程干预对患者术后静脉自控镇痛效果的影响[J].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5,36(10):900-903,915.
Th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Progression of 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XIE Chuangbo,TU Weifeng
Postoperative pain treatment is not only a right of patients,but also responsibility of anesthesiologists.Optimal 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can shorten the recovery time after the surgery.Although 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 attracts more attentions than before,being lacking of regulations,in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low-level of individualization decrease the postoperative analgesic effec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Pain management in the whole perioperative period,intellectualized and individualized pain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algesic effects,and reduce the recovery time after surgery.
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Perioperative Period;Intellectualization;Individualization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GuangZhou510010,China
R614;R619+.9
:A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6.12.015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12A080202012);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重大创新专项(编号:201508020253)
谢创波 屠伟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广东广州 510010
屠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