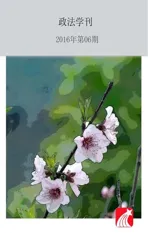论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及其制度完善
2016-02-10黄喆
黄 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论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及其制度完善
黄 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地方公共利益的存在与博弈催生了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是克服跨界污染及其治理外部性的基本途径和持续推进跨界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应当遵循公平负担、损益相当、法定补偿与协定补偿相结合的原则。近年来,我国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它存在的不足亦是显然易见的,如在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多数停留于应然状态、生态补偿的适用存在局限、生态补偿的标准缺失、生态补偿的方式单一等。因此,必须立足于法律完善我国生态补偿的顶层制度设计,拓宽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和实践领域,合理构建生态补偿的标准,充实和丰富生态补偿的方式,以进一步推动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落实和发展。
跨界污染治理;利益关系;生态补偿;制度完善
长期以来所奉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在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环境污染还会超越特定行政区划边界而演化成一种“跨界污染”。不同于在某一行政区划内进行的环境污染治理,跨界污染治理涉及不同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地方公共利益关系的博弈。为此,跨界污染治理的实施必须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平衡为前提。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在跨界污染治理中实施生态补偿并推动其制度完善。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一、跨界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与生态补偿的缘起
利益关系是主体间围绕物质与权利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可能在不同的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或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
当发生人为的环境污染事件时,会存在两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平衡问题:一方面,如果污染者的行为损害了特定公民的财产权、健康权、生命权等,其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以此平衡特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就一定的地区范围而言,即使污染者的行为未直接对特定公民造成损害,或受损害的公民未向污染者主张权利,但污染者的行为却也侵犯了该地区的环境公共权益。为此,地方政府会借助于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的实施,来要求污染者弥补其污染行为对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视为由地方政府作为辖区公民的利益代表向污染者所进行的“求偿”行为,并借此平衡环境污染中污染者与辖区公民群体的利益关系。
然而,当环境污染超出了污染源所在地区而对其他地区造成影响时,由于受到管辖权的限制,污染源所在地区以外的地方政府并不能直接对污染者进行管辖,而这些地方政府管辖下的公民群体的环境权益也难以通过其所实施的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得到保护。为此,受污染地区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从污染源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中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否则,污染者与其他区划公民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将难以协调。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之间发生的这种补偿与受偿的关系,类似于民事主体间所发生的侵权关系,它也是由一定的致害行为所引起,并存在相应的损害结果,因而这种补偿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赔偿”。只不过地方政府是所代表的是抽象的公共利益,与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存在性质上的差异。与此同时,污染者对于其他区划所造成的环境损害,也有可能是通过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间接造成的,与一般的损害存在区别,所以由此引起的“赔偿”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被纳入“补偿”之范畴。
而且,能够引起生态补偿的事实不仅限于跨界污染等致害事件或行为,在某一地区实施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等而使其他区划因此而获得利益时,获益的一方也应当向对方进行补偿,以弥补其为实施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等所支付的成本,以及由此而放弃的经济发展机会。如果将发生跨界污染后的补偿视为一种被动的补救,这则是一种由积极的预防所引起的补偿。一方面,这有可能是由较为单一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如某一地方政府在采取限排减排等措施治理本地区大气污染的同时,大气质量的改善实际上也会超出本地区的地域界限,从而使邻近地区共享了大气治理的成果。这种情况主要是基于大气流动与扩散的客观规律而形成。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是在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人为因素的结果。其典型的例子如在地方政府相互协商或上级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同一流域内的下游地区与上游地区之间,由上游地区对水源采取保护措施,并以此提高下游地区的水质。这种情况则属于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
因此,生态补偿有别于公民等私法主体之间发生的环境损害与赔偿行为,它是由代表地方公共利益的各地方政府之间发生的一种利益调节行为。而且,引起生态补偿的事实既包括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的污染、破坏等行为,也包括对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保护、治理等行为。从本质上看,只要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引起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损益,生态补偿即可能产生。
二、生态补偿之于跨界污染治理的意义
对于跨界污染治理而言,实施生态补偿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生态补偿是克服跨界污染及其治理外部性的基本途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跨界污染及其治理都会应“溢出效应”的存在而具有外部性。其中,跨界污染超越了污染源所在区划的空间范围而损害了其他区划的生态环境,因此,对于这些地区来说,跨界污染的“溢出”具有“负外部性”。而当某一地区进行跨界污染治理时,其行为也可能会使其他地区共享了治理的成果。相对于跨界污染,治理行为“溢出”而产生的是一种“正外部性”。尽管对于由这些地区组成的区域整体而言,负外部性意味着损失,而正外部性则意味着获益,但对于区域内的地区而言,无论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的存在,都意味着特定地区利益的损失。在此情况下,只有由致害地区向受害区划或由获益地区向授益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才能够克服跨界污染及其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性。
其二,生态补偿是持续推进跨界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跨界污染治理必须建立在地方政府合作的基础之上。尽管在跨界污染治理中,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在宏观上作出权力的让渡,而且在具体的事务操作上也可能需要作出不同程度的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合作的某一地方政府应当无限地作出让步,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恰恰相反,跨界污染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寓地方公共利益于区域公共利益之中的行为选择,它不仅应当注重区域整体公共利益的提升,同时也必须关注地方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否则,如果地方公共利益不能随着区域公共利益的提升而增加,或甚至因此而减损时,地方政府必将退出合作。长此以往,跨界污染治理也难以为继。可见,通过生态补偿来平衡各地区之间的地方公共利益,有助于维持稳定的地方政府合作关系,以此为跨界污染治理的持续推进提供重要保障。
三、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原则
(一)公平负担原则
公平负担是生态补偿的首要原则。一方面,生态补偿的产生源于公平原则。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在发生跨界污染及其治理的过程中,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益状况。无论是就本地区形成的跨界污染对受损区划进行补偿,还是因享有了其他地区的治理成果而实施补偿,都是为了实现区域内部各地区在跨界污染治理及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其本质在于保障各地区公民均享有平等的环境权与发展权。另一方面,生态补偿的实施必须遵循公平负担原则。此处的“公平”指称的是一种实质上的公平而非形式上的公平。这是由于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仍很不平衡,且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往往还承担着为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环境质量的任务,这不仅导致它们失去了大规模发展工业产业的机会,也使得它们为保护生态及治理污染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为此,经济发达地区在对经济落后地区进行补偿时,还应考虑到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并适当提高生态补偿的标准。
(二)损益相当原则
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各地区在跨界污染治理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或付出的成本,以维持各地区间利益关系的平衡。为此,任何地区都不应在生态补偿中获得其损失或成本以外的额外收益,或将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创收手段而在额度问题上“漫天要价”。但与此同时,生态补偿也必须起到其应有的利益调节之功能。比如,在对跨界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时,应考虑到生态环境破坏及其引起的各种叠加效应而形成的损失,以及在长期的修复过程中的成本变化等因素。又如,在对部分地区实施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进行补偿时,不仅应对其为实施环境污染治理所付出的资金等实际成本予以补偿,还应对其为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所放弃的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等预期利益进行补偿,以合理弥补其付出的机会成本。
(三)法定补偿与协定补偿相结合原则
生态补偿可通过纵向转移支付以及横向转移支付两种方式予以实现。其中,前者是上级政府对各下级政府进行统筹管理的方式之一,因而此种生态补偿应当是一种法定补偿。具体来说,即对于生态补偿的范围、标准以及资金的分配等问题,都应由法律进行明确的规定,以防止财政资金在生态补偿方面的不当使用,以及保障财政支付补偿在各下级政府间的公平分配。而后者则属于平行的地方政府间通过协商而实施的生态补偿。基于这些地方政府之间的平等性,它们能够对生态补偿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确定补偿的方式、金额等。法定补偿与协定补偿相结合,有利于畅通生态补偿的渠道,从而保障生态补偿的实现。
四、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现状及不足
近年来,我国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从观念上看,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开始成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共识,大部分与跨界污染治理或地方政府合作相关的规划、协议等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提及了有关生态补偿的问题。从实践上看,国家已经在多个流域开始实施生态补偿的试点工作。如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于2011年在跨越安徽、浙江两省的新安江建立。在国家财政部与环保部协调下,安徽、浙江两省达成协议,如果上游的安徽的出境水质达标,下游的浙江将每年向安徽补偿一亿元。[1]又如,2013年1月14日,从河南惠济河排出的氨氮超标水体对安徽涡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导致了安徽亳州境内养殖业的重大损失。为此,河南于2014年3月向安徽亳州支付了首批400万元赔偿款。[2]2013年11月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但总体而言,我国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仍处于起步阶段,它所存在的不足亦是显然易见的。
第一,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多数停留于应然状态。尽管生态补偿在跨界污染治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不少有关区域环境保护的规划及协议中,仍没有涉及与生态补偿相关的内容。而在部分涉及生态补偿的文件中,对于构建生态补偿制度也显得“小心翼翼”。如从《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广佛肇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等文件的用语来看,在有关生态补偿的规定之前,都加上了“探索建立”、“尝试建立”、“加快建立”等,从而对生态补偿作了一定的限制。这不仅表明了地方政府对于生态补偿还持有一定程度上的保留,也导致生态补偿的运行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因此,现有的生态补偿往往还表现出一定的试验性质,甚至是“纸上谈兵”,难以落地。这种情况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反映——如至今为止,广佛肇三地仍未出现有关生态补偿的实践案例。
第二,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适用存在局限。在我国,1998年修订通过的《森林法》首次在法律条文中提及“生态补偿”这一概念,并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予以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我国的生态补偿主要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例如,自1998年以来,国家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生态转移支付等多项森林生态补偿工程。[3]森林生态补偿之所以最早为法律肯定并得以实践,不仅是由于我国自上世纪末起就面临着严重的森林资源危机,也是由于森林资源可以通过覆盖率的计算来得出较为量化的补偿标准,从而使生态补偿具备了较强的可操性。此后,我国生态补偿的试点逐渐扩展至水资源的保护领域。但从实践来看,流域跨界生态补偿已经进入运行轨道的实际上只占少数。而在大气资源保护及其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方面,目前较为典型的只有山东省于2014年通过规范性文件《山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出台,启动了其省内跨市域间的大气资源保护及其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实践。除此以外,我国大气资源保护及其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鲜有出现。可见,我国生态补偿的适用领域仍较窄,尤其在跨界污染治理的适用上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
第三,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标准缺失。生态补偿的标准设定是实施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在我国,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之所以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较大的阻碍,并不一定是地方政府之间对生态补偿行为本身存在争议,而往往是由于对生态补偿的标准未能达成一致。为此,即使地方政府之间对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也未必见得生态补偿就一定能够被最终落实。同时,主要通过纵向转移支付所进行的生态补偿往往也存在标准偏低的情况。从实践来看,一些由上级政府拨付的补偿金并不能有效弥补下级政府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甚至存在下级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而倒贴费用的情况。而且,由于补偿标准的缺失,上级政府对于各下级政府的生态补偿金额也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公平的情况。如自2000年起,浙江省开化县为维护钱江的水质而放弃了大量的经济发展机会,但在它为生态保护作出此种牺牲的情况下,却迟迟未能从上级政府得到相当的补偿,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08年浙江省全面启动生态补偿后才有所缓解。尽管从当前的补偿情况来看,已基本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平衡,但由于开化县较早即开始实施生态保护,为此,开化县有关人员认为,他们先前的付出实际上仍难以得到充分的补偿。[4]
第四,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方式单一。从纵向转移支付与横向转移支付两者的实际运用来看,纵向转移支付仍是我国生态补偿的主要方式。这造成了地方政府在跨界污染治理中实施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并不高,它们更多地为应付上级政府的要求而启动生态补偿,且在生态补偿的支付方面也更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而对平行地方政府的横向转移支付缺乏信心。在生态补偿金的筹措方面,现有的生态补偿金基本来源于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负担,也使得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往往由于财政资金的紧缺而难以落实。此外,当前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基本都通过支付补偿金的方式进行,但较少考虑其他可行的实现方式。
五、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制度完善
现阶段,我国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所存在的种种不足,究其原因在于生态补偿仍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撑与保障。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推动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制度完善。
第一,立足于法律完善我国生态补偿的顶层制度设计。当前我国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所表现出来的实践局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度在推动生态补偿方面的乏力状况。政策与法律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两种正式制度安排,两者在实践中都对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具有规范作用,且当前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更多地是在政策措施引导下得以实施。然而,由于政策自身所具有的短期性[5],使其在稳定性与权威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欠缺,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在生态补偿的实施上摇摆不定。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生态补偿难以在跨界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推行。而且,“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法律应该是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6]对于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而言,亦是如此,尤其须通过法律建立起生态补偿的顶层制度设计。即使《生态补偿条例》的出台进程正在加快,但由于它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效力低于法律,因而难以对当前分散在一些法律中的生态补偿规范予以统一规范。为此,从长远来看,还是有必要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或制定专门的《生态补偿法》,对生态补偿制度予以法律上的规定。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变由政策主导生态补偿的现状,另一方面有助于对不同法律法规中有关生态补偿的规范进行“统领”,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完备的生态补偿法律规范体系。以此为基础,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适用也必将得到有效的推进。
第二,拓宽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和实践领域。首先,应当在完善我国生态补偿顶层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即通过《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或《生态补偿法》的制定,明确将区域生态补偿或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作为我国生态补偿的类型之一。同时,由于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跨界污染主要集中在跨界水污染和跨界大气污染两个方面,因而当务之急即是在跨界水污染、跨界大气污染及其治理领域中适用生态补偿。为此,应当在相关的单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立法中进一步对跨界水污染治理、跨界大气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作出细化规定,从而借助于国家立法将我国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拓宽至跨界污染治理的关键领域。这能够通过国家立法的引领作用,使地方政府在跨界污染治理中生态补偿的实施上获得必要的依据,以推进生态补偿在跨界污染治理中的实践领域。
第三,合理构建生态补偿的标准。生态补偿的标准是指补偿时据以参照的条件。[7]对于跨界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而言,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生态补偿的标准设定问题:一是为保护生态环境或治理环境污染所发生的直接投入;二是为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预期利益,此即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三是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它不仅包括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各种可折算成货币形式的其他损失,而且还包括由此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四是保护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生态价值,即某一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对于区域整体生态环境所产生的价值。在这些补偿项目中,部分是量化的货币指标,而部分则是较为抽象的价值范畴。因此,对于前者,应当严格依照实际的资金支出进行补偿;而对于后者,尽管难以简单地将其换算成为精确的货币数值,但也可以借助于相关的调查与评估,得出一个大致的补偿金额。而且,在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对此进行补偿时,可适当提高补偿的标准,以对各地区保护环境的行为予以鼓励;而在通过横向转移支付中,则可由各地方政府在评估金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补偿标准作出更为细致的约定。
第四,充实和丰富生态补偿的方式。生态补偿应建立国家、地方、区域、行业多层次的补偿系统,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8]首先,要提高各地方政府对于生态补偿的认识,促进它们在生态补偿方面的协商,从而加强横向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中的运用。其次,可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从而通过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向社会发行生态补偿债券或彩票、实施BOT融资方式[9]等,丰富筹措生态补偿资金的手段,以减轻各级政府财政在生态补偿方面的压力。最后,应积极推动生态补偿由补偿金支付的单一化方式向多元化方式发展,如可通过由各地方政府共建环境污染治理项目、由受益地区向生态保护地区公民提供就业机会等方式来实现生态补偿。
[1]何聪.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3年 新安江清了、净了、美了[EB/OL]. http://www.ah.xinhuanet.com/2014-12/12/c_1113622713.htm,2016-10-14.
[2]汪漪.河南千万立方污水污染安徽涡河[EB/OL].http://news.wehefei.com/html/201304/01195035632.html,2016-10-14.
[3]欧阳志云,郑华,岳平. 建立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与措施 [J]. 生态学报,2013,(3):687.
[4]吕明合.保住“一江清水”,换来贫穷落后?[EB/OL].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38,2016-10-14.
[5]孙浩康. 中国区域政策法制化研究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6]朱最新. 珠三角一体化政策之法律化研究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9-10.
[7]曹明德. 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再思考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34.
[8]李静云,王世进. 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J]. 河北法学,2007,(6):112.
[9]曹明德. 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简论 [J]. 政法论坛,2005,(1):137.
责任编辑:韩 静
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Its System Improvement in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Huang Zhe
(Center of Rule of Law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The issue of public interest generate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in propelling the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would b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fair shouldering, profit & loss balancing, legal compensation and protocol compensation“.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the fast development i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Nevertheless, the arising problems cannot be neglected. For instance,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limited and monotonic, while still staying in the status of discussion and miss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refore, the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top by law-making. Moreover,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roadening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nstruct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nriching the approache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governa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nterests relationship;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2016-10-08< class="content">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区域协调发展中府际合作的软法治理研究”(16AFX0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14BFX03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区域协调发展中府际合作的软法治理研究”(16AFX0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行政法问题研究”(14BFX036)< class="content">作者简介:黄喆(1986-),男,广东湛江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从事行政法学、区域法治、地方立法研究。
黄喆(1986-),男,广东湛江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从事行政法学、区域法治、地方立法研究。
D912.6
A
1009-3745(2016)06-0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