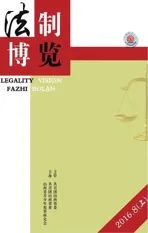老年人精神赡养现状探析*
2016-02-02李树堂何雅诗许仁和
李树堂 何雅诗 许仁和 方 正
江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老年人精神赡养现状探析*
李树堂何雅诗许仁和方正
江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56
摘要: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的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做了明文规定,现实中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满足,但随着社会发展、老龄化进程加快,家庭机构转换,突现老年人对精神赡养的强烈需求,本文基于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现状加于探析,完善法律,协调其他部门法,以保障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利。
关键词:老年人;精神赡养;法律完善
据统计显示,2014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高出2013年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①且从武汉市老龄办获悉,截至2014年底,全市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达156.01万,占总人口的18.86%,远远超过了10%的国际标准,武汉市2014年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比2013年增加10.39万人,老龄化程度与2013年相比增长1.16个百分点,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年增总量突破10万人。②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人问题尤为重要,已城镇老年人为蓝本,在物质条件满足的前提下,老年人赡养问题引起广泛关注,随着新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中关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和实施情况更是成为当前社会热门话题。
一、老年人精神赡养之现状分析
“敬老”、“尊老”、“孝”自古以来乃中国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精髓,其维持着中国家庭关系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当代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程中,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情况在家庭、社区以及福利院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表现。本文通过武汉粮道街社区周围的家庭、社区、福利院走访、调查、采访,了解和分析与之相关的老年人精神赡养现状。
(一)家庭方面
家庭是作为养老最主要的主体,也是与老年人最直接亲密的接触主体,实践中,子女由于工作、生活、婚姻等原因远离父母,或者重新组建新家庭,或者搬离出去,远拒父母,余下父母孤寡老人独守原始家庭,而家庭子女一般只在经济层面给予父母帮助,对于家庭出游、节假日欢聚、与老人促膝长谈、在外工作电话慰问等情况可以让老人充分感受到精神的享受与愉悦的活动,家庭无法充分保证,更有甚者连老年人基本的生活照料费都未给,未尽到赡养义务,此类现象,现实中老年人将自己子女告上法院的不在少数。有关文献足以表明,2006年至2011年司法行政机关对全国老年人的法律援助进行数据统计,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从2006年的60198人到2011年的102206。[1]由此,孤独感与老年人常伴,无法做到在老年人因病或者年迈时需要全面的身体养老或心灵安慰。
简而言之,家庭层面可以发现子女虽然在老人精神赡养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物资主要帮助者、日常生活的主要伺候者、情感的主要倾听者,但是明显不够的,存在一定的缺陷,家庭过度偏向物质层次、不够专业化、养老风险大等情况。
(二)社区方面
以社区组织和社区服务者为主体,充分利用及开发社区资源,满足老年人其生活经济需求、基本照料和精神慰藉,以及老年人自发组织,还有少数的商业性老年活动。社区进行网格式划分,每个网格在范围内都设由有一个网格员,并在社区各个网格内张贴网格公示牌,把各个负责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都详细告知。每个网格都实行“三长三员”制,即“党小组长、中心户长、门栋长”和“民情信息员、文明宣传员、治安巡逻员”,并配有社区医生、社区律师等。各个社区居委会通过联系各个负责人,定期开展会议的方式整体了解社区老人的需求和近期集中的问题。如楼栋长制度,楼栋长对自己这一栋居住的老年人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楼栋长会定期联系居委会,从而关注老年人生活需求,并特别关注高龄老人的身体状况。社区都设立有老年人活动室,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和聊天的地方,社区服务人员能在通过和老人们的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除此之外,社区居委会均表示会定期对高龄老人进行慰问,关注特困老人、空巢老人,并会经常和医院联合为老年人举行义诊。
社区养老更多的只是起辅助性作用,相对于有家庭子女的老人,家庭才是主要的精神赡养主体,同时因受传统观念制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年人并不会与社区组织及相关人士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且社区内缺乏照顾老人的专业人员,志愿者队伍不够壮大等都是面临的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社区内服务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并不高,很多人员不具备养老服务护理员的专业资质和执业资格,大多只是接受过短期上岗培训。服务内容仅局限于帮助老年人做家务、简单的照料等,至于老年人更加渴望的精神慰藉、情感支持方面,则基本上处于被忽略的状况。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中的志愿者队伍普遍缺乏,社区公众的支持与参与不足,志愿服务的开展并不固定。故非正规化的社区养老是远远达不到老年人的需求,特别是精神层次。
(三)福利院方面
以工作人员和服务者为主对老年人进行照料,当老年人交由福利院代养后,子女的参与度就降低,且福利院对于改善精神赡养困境的举措明显有限,通过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走访,福利院内600多位老人相对应的却仅有5名社工,典型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福利院内虽有一些丰富老人娱乐生活的定期性活动,但这也仅限于福利院内30%的老人,福利院内有70%的老人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几乎只是卧在床上,而且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们,对于福利院组织的活动的参与度也并不高。当然在福利院占少数但是不容忽视的“三无”老人,这类老人本就由于没有子女等原因而得以受到福利院的救济养老,所以对于这类老人来说,他们对于子女的精神赡养专属亲情慰藉的可能性变无。显然对此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根本无法得到更好的实现以及保障。
家庭、社区以及福利院三方面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也存在缺陷,对于老年人精神赡养应坚持家庭为主,辅之以社区、福利院,实践中没有规则、法律可以让三方面依照而行,特别是社区和福利院,基本按照内部的规章制度。
二、老年人精神赡养之法律问题
2013年新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的“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等相关法条,都明确老年人应当享有精神赡养的权利,将其上升至法律层面,说明这是一种制度,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在这一个法律调整不明确的精神赡养区域,很难要求权利人保障其权利,也很难要求义务人履行其应尽义务,老年人精神赡养存在诸多法律问题。
(一)主体不确定
法条中规定家庭成员作为赡养人,家庭成员是否应该包括除了子女以外的外孙子和孙子女,即按照杨立新认为,家庭成员并非严格的亲属法概念,家庭成员就是以婚姻、血缘关系和共同经济为纽带而组成的亲属团体中的成员,且其将负有探望义务的主体界定为晚辈卑亲属。[2]那么义务主体应界定为晚辈卑亲属,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将其化为赡养主体。同时在条文中出现的“赡养人”以及“家庭成员”两者之间如何区分,并无明确性。
(二)内容不具体
完善的法律条文应加以明确法律责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关于精神赡养主体如果不履行赡养义务,其惩罚会如何,并没有明确规定,就使得法律缺少必要的威慑力,当然有学者会提出用冰冷的法律来约束、强制温暖的亲情,是有悖道德层面的要求,此主张是由于法律和道德相交叉而引起的。惩罚性可否考虑“声誉罚”,“声誉罚”被视为信用社会和网络经济的封喉利剑。在现代经济法上,逐渐衍生出一种“专业不名誉”的责任形式,如借贷信用黑名单、信誉评估降级、不纳税信息公告以及责令公开解释或道歉、发出劝告令、申诫令,都是这种“信用减等”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信誉是交易者的通行证。因此,信誉减等无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具杀伤力的处罚形式。[3]通过信用等级的法律责任机制,影响赡养主体的生活,最终达到惩罚性效果。当然对于条文的用词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经常”“探望”“问候”等具体是多长时间一次,是否应结合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精神需求强度、与赡养主体的距离、以及节假日等因素综合考虑。
(三)救济方式不明确
当老人诉讼子女要求子女每月给予赡养费、每月至少来看望自己多长时间且时间不得少于多少时,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进行调解,且诉讼请求不纳入调解书中,主要基于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强制性和可执行性,如果将其写入文书之中,如果赡养人不执行,然而法律对此却是空白的,就缺乏操作性,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对此也不可能硬性要求,否则司法机关将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关于精神赡养部分中的救济方式有欠缺,需将其空白填补,才能真正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精神权益。
三、老年人精神赡养之法律完善
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完善迫在眉睫,法律的实施,应取自于民并馈之于民,结合当代国情,依据国家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从本辖区的实际条件及特点考虑,制定并适用于辖区内的具体实施细则。当然国家层面的立法在老年人精神权益保障的范围内缺乏一定规定,会形成地方行为缺少一定的鼓励和形成制约,由此,地方政府制定出的具体的立法文件,也难与国家立法层面保持相应的步调,法律的实施落实需要具体明确,健全立法,完善法规,是当前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大势所趋,是刻不容缓的现状。
(一)扩大赡养主体范围
由于精神赡养义务缘由存在着多样性,决定赡养人的主体范围应扩大化,应坚持杨立新教授的观点,将晚辈卑亲属纳入赡养范围内,即不应局限于婚姻家庭关系之中的子女,应将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遗赠扶养协议之中的扶养人、同时对养老院或福利院机构的相关所有人或管理人等也应包括。可将赡养人主体划分为两类自然人和社会机构。当然自然人作为赡养人的主体资格条件,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有规定,如《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对此,可适当参照予以施行,社会机构作为主体也可以参照借鉴国家、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养老机构的规定和管理设置的法规、政策和规定。[4]
(二)明确及具化履行方式、法律责任
设置老年人精神权益最低保障底线要求,用量化的方法逐渐达到质化的要求,明确具体规定子女探视父母的时间次数,特别法定节假日,进而最大限度化地保障精神赡养的质量,对于发生赡养诉讼类的案件,给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情况下,合理运用民法刑法等法律中侵权赔偿、赔礼道歉、精神损失费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训诫、罚款、拘留、社区矫正等手段方式方法加大其法律责任,增强其法律处罚力度强度。同时结合地方特色,当地政府比较了解民生情况,应监督落实情况,专门建立相关的负责部门对接,发生纠纷或者其他情况时,及时与相关部门协商处理解决。
(三)协调部门法,扩充内容
老年人精神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制,主要以《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为主,虽然在《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保险法》、《刑法》等中都略有涉及,但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的法律系统,且大多是宣言式、无标准的规定,关乎独立完善的保障老年人精神权益方面的立法仍就缺失,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靠道德、情理去约束,然道德、情理本身无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所以当老年人的精神权益遭受侵犯时,就无法做到有法可依,保障其权利。就其精神内容而言,应该以作为形式的给予老年人精神必须的生活保障、必要的精神慰藉和不作为形式上以不肢体伤害、谩骂、殴打、挖讽等行为给予老人精神上痛苦、使其遭受精神虐待,当然更不得限制其自由的权利,如对其结交、再婚、参与文娱等追求精神享受的权利。
四、结语
老龄化速度加剧,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城镇老年人物质需求逐渐满足的条件下,老年人对精神需求越发强烈,精神赡养强调以家庭为主、社区、机构为辅,目前,政府虽采取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但也无法满足其需求,其中关于精神方面更是少之又少,为了解决当前问题,同时也为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我们需要在法律层面,健全法律,完善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在政府层面建立健全养老制度,保险制度,两者相互贯彻,确保落到实处,继而建立符合实际的精神养老服务体系法律。如此措施,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才能有效缓解,和谐社会才能更好实现。
[注释]
①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37/69715.html(全国老龄办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②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10/72549.html(全国老龄办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参考文献]
[1]张娟.我国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研究[J].科技视界,2016(09).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李志刚.调制受体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J].法学,2007(6).
[4]李晓艳.论精神赡养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律,2009.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2-0038-03
作者简介:李树堂(1994-),男,壮族,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
*江汉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编号:20151107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