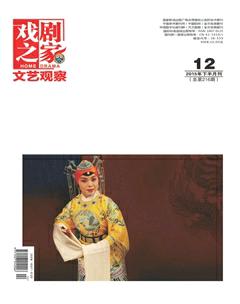试论元散曲中的民歌化迹象
2016-01-12饶莹
饶莹
【摘 要】民歌一系自古有之,至明代则“涌上地面”几成大观之势。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而晚明却人欲“反扑”天理,独树一帜,形成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学界向来将此间理学以“宋明”并称,元代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而被隐没。然元有“一代之文学”——散曲。作为过渡的一代,其社会思想无疑会对文人创作产生影响——将“民歌精神”渗入散曲。本文试以晚明情形为潜在参考,旨在力图对元散曲与民歌一体之关系作一点梳理认知。
【关键词】散曲;俚俗;民歌化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021-02
任半塘先生《散曲概论·派别》中有云:
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谓南词,固绝不足与元人北曲对峙,即冯、施之业,亦承元人余绪,未足以云分庭抗礼也。若明人独创之艺,为前人所无者,只此小曲耳。[1](p110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惟散曲继承元代的余绪,犹能振作精神,颇有成就”这一论断与任先生“承元人余绪”之语意味相似。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明代“文人散曲中时而出现‘小曲,已是普遍现象”且“文人作小曲已成某种风气”。周玉波师《明代民歌研究》在讨论晚明韵文民歌化问题之时,亦认为“散曲是一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既是“风气渐盛”,自然易形成一种“倾向”。可以想见,明代民歌俚曲对当时文人散曲的渗透,继而有“民歌化”这一趋势。
关于元代文人诗歌与民间小曲的“合流”现象,李昌集《散曲史》这样说道:
元散曲,在文人诗歌系统中,可谓口语化程度最高,其“俚语化”一流(尤其是吟唱风情之曲),直与小曲同类。其中潜映的事实是“小曲”在古代一直兴盛不衰,并对文人诗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2](p406)
遗憾的是,由于元代“‘小曲没有系统而丰富的资料存世”,无法得知其详,故笔者论题只说“迹象”。而从李昌集所言“元代若干无名氏的散曲——至少其中有相当部分完全可以认作是元代的‘小曲”可知,民歌在元散曲中确实留下了“印记”。这是本文进行论述的前提,下文对“民歌化迹象”的产生作大概的思路整理。
任先生《散曲概论》语:
只就散曲以观,上而时会盛衰、政事兴废,下而里巷琐故、帏闼祕闻,其间形形式式,或议或叙,举无不可与此体中发挥之者。冠冕则极其冠冕,淫鄙则极其淫鄙,而都不失其为当行也。[1](p1077)
诚如周师《明代民歌研究》中所说,“曲与民歌,是大有渊源的”,散曲与民歌更是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内里的共通,在元代特定的文学背景中,使二者的“结合”犹如“金风玉露一相逢”,衍生出散曲这一文学史上的“风流韵事”。当然,元代散曲成“一代之文学”乃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但若无民歌俗曲这一“暗流”的“刺激”,散曲的体制终究如何,谁也无法想象。
吴梅先生《南北戏曲概论》云:
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同时诸调词行,即变为曲之始。①
李昌集认为“这是一个立足于文学本体的敏锐之见,是对散曲文学发源的正确论断”。然散曲并非在元代突然出现,而“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是散曲一体进入文坛的决定性因素”。关于散曲的形成,李昌集道:
从散曲本身形式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散曲独特语言形态的形成,乃是民间歌手和文人阶层共同创造的结果,是诗歌的民间形式与文人形式的复合。曲体的散文化语态特征,根源在其母体——民间歌辞。[2](p216)
如果说“文人与民间曲唱的结合是散曲输入文坛的主要途径”的话,那么秦楼楚馆就是二者间最重要的“中转站”。古代文人的周边总少不了歌伎的身影,不独元代如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或明或暗地让古典文学多了一重韵味。没有那些勾栏瓦舍,里巷俗曲向文人层的扩散会艰难得多。然二者能够结合的深层原因,则离不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换言之,主要是元代文人地位的改变。
朱经《青楼集序》曰:
我皇元初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3](p20)
朝代更替,异族入主。汉家王朝的覆没于文人而言,其耻辱之大几近于“‘祖坟的被掘”。学界皆云元代无科举,或无正常科举制——“时举时停”。这直接导致文人地位的失落。当此之时,他们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从文人到平民,地位变了,心态也就无可避免要变。所谓的“断肠人在天涯”,与其说是游子的慨叹,不如说是有元一代文人的心声。他们失落,同时又不甘心。昔日文人的王国已成“彼岸世界”,他们被逼入了世俗的“此岸”。然而在精神上,他们对传统文人价值的追求和向往却从未停止过。“虽‘俗而雅,身在世俗,‘心则避之”,世俗生活从未完全真正融入他们的世界,甚至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排斥的。“兼济天下”,如今他们已是身在天下。挣扎呐喊也好,浅吟低唱也罢。他们的“顾影自怜”中已难以阻挡地带有世俗生活的意味,即“以世俗生活、世俗情趣为表现对象”。
余英时所著《中国文化史通释》提及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一段话: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4](p283)
苏轼评论晋人之病,说他们“意以谓心,迹不相关”。所谓心迹不相关,也就是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口谈虚玄而入世甚深”:
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婴世务结合起来,口谈虚玄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5](p196)
一定程度上,东晋士人与元代文人有着同样的境遇——政治生活中的被“边缘化”。宋明两代理学发达,明代更是很好地继承甚至超越了宋代。而元代近百年的统治由何种思想维系?这种思想对宋明两代理学之承继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学界至今未有确切说法。文学即是人学。王骥德《曲律》中“人情原不相远”一语,是对当时南北民歌融合很好的诠释。“散曲民歌化”进程受文学思潮、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对元明两代文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人情使然。从文人角度出发,亦是自我的一种需要——人情所属。即如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所指:
寻个好生涯,是士人世俗化的一种趋势。首先是要生活,而且是要有好的生活。那些游离于仕途边缘的士人尤其如此……同时,他们又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人生道路,以入仕为正途。他们是徘徊于士人的传统人生道路与世俗人生之间的一个群落。[6](p162)
同样是进入世俗世界,晚明文人似乎没有元人那么多的被迫和无奈。除却科举制度,亦或与两朝不同社会风气及其他因素有关。由宋至明,程朱理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许是晚明革新思潮声势之浩大,触目所及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将“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当成其时思想之主潮。但身处世俗生活中的晚明士人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其“浸润”,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散曲民歌化这一“倾向”。民歌俚曲如同一股暗潜在文学中的清流。当时机合适,这渠“活水”纵然无法如浪花般翻涌,其激起的涟漪也定会打破平静,即便最后仍要终归平静。
古代文人从来都是“壶中岁月,梦里功名”,元明之人犹然。无论是文学自身的规律,还是文体发展的需要,至少对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而言,民歌都只能是“配角”。即便如袁宏道,晚年亦有此语:
不绝欲亦不纵欲,不去利亦不贪利,不逃名亦不贪名。人情内做出天理来,此理近道学腐套,然实是我辈安身立命处也。[7](p976)
就像民歌,在结束了“刺激”这一使命后,它“仍旧回到自己的位置”安身立命。诚然元曲经历的“刺激”无法比拟晚明的“气概”,但民歌在散曲中留下的痕迹是抹不去的。
注释:
①转引自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然并未发现吴梅先生曾著有此书。今见王卫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曲家通论·家数》中有此一段:“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诗词,酒边灯下,四字【沁园春】,七字【瑞鹧鸪】,粗豪横决,动以稼轩、龙州自况。”至于李先生所谓“同时诸调词行,即变为曲之始”由何而来,尚有待查证。
参考文献:
[1]任中敏.散曲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夏庭芝.青楼集笺注[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7]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饶 莹(1990-),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民歌与戏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