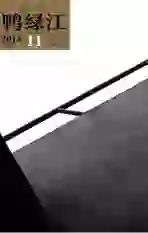麦城:戏谑的诡异和悲凉
2015-11-06陈国峰
陈国峰,1962年生于辽宁阜新。国家一级编剧,北京大学国内访问学者,国际戏剧评论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辽宁省文联委员,辽宁省文化厅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戏剧家协会理事。现在辽宁省艺术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戏剧和影视剧创作。有京剧、评剧、话剧等多部作品,获得全国省、市优秀作品奖。有论文获全国及省级优秀作品奖。
2009年深秋,诗人麦城游历西安。
在中国,有几座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行政区划的概念,她们所独具的厚重历史,使她们就像饱经沧桑的贵妇人,处子的清丽和华贵的婚礼、乖张的婚变以及颠沛流离,漫长曲折的故事使她们的生命成为沁色的美玉,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历史,从来不是时间的一个指称,历史的深度取决于时代的丰富性,以及后人对于她的体认水平——西安,这座号称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她的漫长历史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西安,是一座历史的城市,文化的城市,政治的城市,诗歌的城市。
秦汉以降,迨至盛唐,西安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城市。举凡汉唐时代名垂青史的诗人们,或生于西安,或死于西安,或流连在西安,总之几乎无不和西安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在这样一个到处荡漾唐诗波光、宋词薰风的城市里,现代诗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尴尬——还有谁敢于在那里卖弄汉语的优美华丽或者清新质朴?
麦城显然很明白西安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远高于那古老的城墙。他以自己一贯的狡黠和诡异,以自己独特的戏谑风格,在那古老的城墙下面,挖了一个现代性的盗洞——
在西安
——讣告:饿
陕西农业的胃里
没一粒粮食
能喂养我在西安的身影
朱雀大街上
哪一根汉代柱子
来拴我的旅程
沈奇、昌平和魏杰
一早赶赴咸阳
接待他们的
是秦朝末年最后一种观点
秦始皇
这个远近闻名的小老头
躺在《史记》里
最大的一张床上
依旧做着他的
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
后来,沈奇
在这个小老头的梦的下沿
拿洛阳铲留言
你真牛B
几千年下来
没人敢从你的梦里
盗别的梦
诗的副题是“讣告:饿”,这是别有意趣的副题。乍看似乎很难理解:谁发的讣告?给谁发的讣告?死者是谁?何故而死?麦城给了一个清晰具体的答案,饿。那么,是麦城给饿死的人发的讣告吗?
当然不是!如果这么简单,那么诡异也就不是麦城诗歌的代名词了。诗人尽管一开头就说到了“饥饿”,但饥饿仅仅是麦城惯用的借喻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正是麦城诗歌的一贯伎俩。
讣告是宣布死亡的公告,而且向来只属于有地位者的死亡,即无论是在封建等级制社会里,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民俗性遗存,普通百姓的死亡是不能发布讣告的。换句话说,“讣告”这一形式,让死亡成为一种重大的体面的事件,它的潜台词和权贵相关。然而在麦城这里,讣告所指涉的主体角色却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诡异的是,“饿”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现象状态。读罢全诗,我们发现讣告所指涉的主体对象非但没有因为“死亡”而进入一种沉寂静穆的状态,它反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活跃性。讣告宣布的饿,这种反常规的词语组合,使彼此逆向激荡,醒目地昭示了一种重大的、然而也格外滑稽的意义:讣告宣布的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活跃的生理情状,它使饥饿成为一种尖锐的深刻的超越死亡而顽固存在的活体性相。
讣告本应宣告死亡,但这个讣告宣布的却是强烈的生命感觉。
饿,于是超越了死亡,也超越了普通生理范畴,而成为一种诡异的意义指涉。
饿,对应的是饥肠辘辘的感觉,它唤起的总是非常具体真切的生理感受,而且从来都同时伴生相应的心理欲望,即渴望进食,亦即渴望从外界获得能量的补充——如果麦城的“饿”不是普通的饿,那么他究竟渴望补充什么呢?特别是在西安,他渴望补充什么呢?
“陕西农业的胃里 / 没一粒粮食 / 能喂养我在西安的身影”。
虽然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陕西的昔日荣华早已随着工业化的来临而黯然老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她的主体产业就是落后的同义语。陕西当然有相当规模和相当先进的现代工业,但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三线建设的政策而造就的。和漫长的农耕文明相比,陕西的工业化形象显然还很稚嫩,还不足以作为陕西的地域特色代表。特别是产业分置的不平衡,凸显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特征的强悍性。除了西安,陕西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称之为“农业形象”。
那么,陕西农业的胃里有没有足够的粮食,跟我(诗人)有什么关系呢?
麦城的饥饿,陕西的粮食无法喂养他,其实他的饥饿,根本就和食物无关。
因为陕西的胃,是农业的胃,而不是现代工业或现代商业的胃,所以无法喂养“我”。
这个“我”,表面是诗人的自称,其实代表一个更大的概念,即一个更为广谱的身份,因为别人的胃口里有什么都不能喂养你,只有你自己胃里的食物才对你的饥饿有价值。因此,当麦城说“陕西农业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能喂养我在西安的身影”时,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幻化成了“陕西”,他想说的是一种矛盾,即西安的商业性和现代性,跟古老的农业陕西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反差。
当“我”在西安时,我不仅是身份指涉,而且还是一个时间指涉:我在的西安,是一个现代西安。
现代的西安,是一个商业性的都市,是一个西化的繁华都市,她和陕西的农业形象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陕西的农业形象,即陕西所能提供的文化给养,和诗人的主体需求存在一种错位和疏离。
那么,为什么“无法喂养”的不是“我”,而是“我在西安的身影”呢?
这并非只是一种俏皮的说法,“身影”的使用,再次展示了麦城语言风格的独特性,看似随意而俏皮的词语使用,其实是一种刻意的强调:没有“我”的存在,当然就没有我的“身影”,但身影却又不是我,一如我们观看镜像,镜像和身影一样,是一种禅境的魅惑,它和主体既是合一的,又是分离的。如果把“我”确定为一种实在的主体,那么镜像或身影则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一种扩展性的存在。麦城用“身影”一词,再次强调他的这首诗,跟实际的生理饥饿并没有关系,他要在陕西或西安品味的,是一种文化给养。
所以,他进一步反问和自诘:朱雀大街上 / 哪一根汉代柱子 / 来拴我的旅程?
朱雀大街是西安最著名的大街。但是,不借助历史性的解读,朱雀大街的丰富意义就会大大流失。朱雀大街是古都西安(长安)的南大街,亦即皇城南面的大街,所谓南朱雀、北玄武者,它的名称关涉中国的堪舆风水文化,名称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古老的巫术观念,是以上佳的风水来保佑国泰民安的祈福思想。在西安(长安)的光荣历史里,朱雀大街曾是一种令人惊艳的象征,它宽达百步,是历史上全世界最为宽大的街道,四海的朝贡者都将经由这条大街而进入皇城,它是帝国的象征,是无上皇权的象征,是国力鼎盛的象征。
汉唐时代,是长安的全盛时代,也是中国的全盛时代。
现代的西安,是著名的世界性旅游城市,古迹遗存(包括现代人的复古制作)是她的鲜明标志。但是,对麦城来说,西安还有“汉代柱子”吗?那曾经的繁华与强盛,那曾经令世界敬仰的文明,是否已经灰飞烟灭?民族记忆中的历史,是否早已成了一种光荣的传说?现代的西安,不再是古老的长安了,而长安的衰落,绝不仅仅是时间的涤荡,她的光荣与衰败,内蕴着格外值得反思的文化原因——封建王权的专制性,体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吊诡:专制越强悍,行政越有效;行政越有效,则衰败越迅疾,代价越惨重。
中华帝国的光荣历史,让麦城感慨,所以他想到了“汉代柱子”。
中华帝国的悲惨历史,让麦城疑惑,所以他问“哪一根汉代柱子 / 来拴我的旅程”?
这一问,突出了诗人的现代性立场——和历史上无数的复古者不同,更和当下的复古热潮相反,农耕文明的陕西(代表古老中国)不是他的文化皈依,历史上的光荣反而是一种对比性的诘问:如果我们的文化和制度没有根本缺陷,那全盛的伟大时代何以而竟终结?
麦城用下面的诗句,以戏谑的风格,给出了惊心动魄的回答——
沈奇、昌平和魏杰
一早赶赴咸阳
接待他们的
是秦朝末年最后一种观点
沈奇是西安的诗人和评论家,昌平则是一位小说家,他们是麦城的好友。麦城直接把他们写进诗里,是他近年来写作的一个特点,这似乎不太符合新诗的传统,因为这些名字,对不熟悉他们的普通读者来说,显然有些突兀,是一些陌生的符号。其实这并不新鲜,汉唐的诗人们就这样做过。“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伦就是当时大多数读者不熟悉的名字。不过,这里其实还是有意义上的一些区别。李白的这首诗,是直接赠给汪伦的,而且李白的多数诗作,写作的当时并非公共印刷物,自我性私密性是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而现代诗歌的创作,基本上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对象定位,因此,麦城这样写并非袭用传统,他把朋友们的名字直接写进诗中,等于在表达一种权力,即他乐于彰显他的友谊。
这样做,可能隐藏着特定的私密性指涉,也可能只是为了凸显作品的戏谑娱乐特征。
对这首诗而言,重要的不是麦城把谁写进了作品里,而是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接待他们的/是秦朝末年最后一种观点。
我在以前写的评论中说过,把抽象概念拟人化、情节化、戏剧化,或者把具象内容抽象化,正是麦城诗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而这也正是一种诗歌思维,即以反常的语言建构独特的意境。本来抽象的“观点”,现在却可以接待人了,“观点”立刻获得了拟人化的活力。
但接待那几个人的,是什么“观点”呢?
秦朝末年的最后一种观点。
这是什么意思?
咸阳既是诸侯秦国的封藩都城,也是秦帝国的发祥地,更是大秦帝国的首都,现在则是西安的国际机场所在地。那几个人为什么一早赶赴咸阳?有可能去咸阳国际机场接麦城的航班,或者去那里搭乘航班,但更可能是去咸阳“朝拜”秦始皇陵墓。是什么力量和诱惑驱动着他们?他们又在咸阳遇到了什么?——秦朝末年的最后一种观点!
秦朝末年是动荡的岁月,秦帝国的专制暴政走到了尽头,暴乱和起义,即推翻暴秦,打出一片新天地,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成为那个时代最为流行最为重要的“观点”。
看破了这个切口,沈奇和昌平的人名立刻丧失了具体指涉意义,而成为一种明确的“时间”象征,今天的人被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观点接待,历史和现实瞬间奇妙对接出火花,让我们领悟到麦城真正的隐喻——传统文化是一种超稳定的存在,而新秩序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权力等级的重新分化与配置,历史有时是一种同质循环,而不是一种结构性的革命与更新。
任何王朝末年的最后一种观点,肯定都是革命的观点。
问题是,接待21世纪的沈奇昌平们的观点,却还是秦朝末年的观点!
因此,这种革命,实质上已经不是革命了,而是一种低级重复,漫长的历史和现实的穿越,愈发凸显成一种悲凉的滑稽!
为了让读者更确切地理解自己的隐喻,诗人继续写道:
秦始皇
这个远近闻名的小老头
躺在《史记》里
最大的一张床上
依旧做着他的
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
秦始皇的传记,在《史记》的“帝王本纪”中。在封建官本位的社会里,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史书中也尊享着最高等级的待遇,所以麦城说秦始皇躺在《史记》“最大的一张床上”。秦始皇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创始人,他把诸侯列国的分封制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长久延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秦至二世而亡,但秦始皇所创建的国家政体模式,却被其后的所有王朝承袭沿用。秦始皇当年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而事实上,秦帝国也的确是当年全世界幅员最辽阔的帝国,所以麦城说秦始皇做的是“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
但是且慢——秦始皇不是死了吗?他不是已经进入《史记》的帝王本纪里、成为一个逝去的人物吗?他怎么还能“躺在《史记》里”,“依旧做着他的 / 中国最宽阔无比的一个梦”呢?
这正是麦城的诡异和狡黠,也正是我喜欢他的深刻处。
作为活体的帝王,秦始皇确实早死了。然而,作为秦帝国的创建者,他的大一统思想、王权至上观念、专制主义行政风格却从来未曾死去,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继续做着这样的迷梦!
就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而言,秦始皇是一个鲜明的标志,是一个分水岭。他不但终结了上古的诸侯分封制度,而且终结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伦理,开创了以暴力确立统治权、家传天下的新时代。
当民主政治让位于强权政治时,它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极端化——大多数人的梦想和自由会受到最大限度的压制,而少数人的梦想和自由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刺激。尧舜时代,天子真是人民的公仆,是“以一人而奉天下”;秦始皇之后,人民是天子的奴仆,是“以天下而奉一人”。
长久的封建专制会造成什么恶果呢?
那就是原本英雄迭出、意气风发、活力四射的伟大民族,会在强权的严密压制下,逐渐变成一个唯长官马首是瞻、谄媚风行、道德虚伪、小人得志的卑劣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列强给中国所造成的亡国灭种的惨重悲剧,使国民普遍愚昧的专制制度,恰恰是最重要的内因。所以,麦城写道:
后来,沈奇
在这个小老头的梦的下沿
拿洛阳铲留言
你真牛B
几千年下来
没人敢从你的梦里
盗别的梦
洛阳铲是盗墓工具。说沈奇用洛阳铲,是麦城惯用的戏谑风格,而不是真说沈奇参与过盗墓。一如我前面所说的,这里的具体人名已经不再是通常的含义了,它指的是一种“时间”代码。当年项羽和刘邦看见秦始皇出巡的辉煌规模,刘邦艳羡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则立刻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两个推翻暴秦的最重要人物显然具有惊世骇俗的英雄豪情。但是到了今天,到了“沈奇”们(即我们)的时代,我们只能躲在秦始皇的梦的下沿,用洛阳铲来干盗墓的勾当了。伟大的英雄情怀已经蜕变为卑贱的蝇营狗苟,意气风发的英雄主义已经被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取而代之!
以是,“几千年下来 / 没人敢从你的梦里 / 盗别的梦”。
秦始皇所代表的封建极权专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核!
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与时代迭荡,其实都是在重复秦始皇的那个梦而已!
麦城的这首诗,是对历史的一次戏谑。这不是娱乐的戏谑,而是悲凉的戏谑、辛酸的戏谑、沉重的戏谑!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