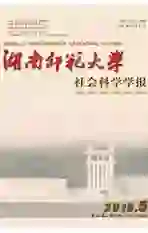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
2015-09-25戴佳曾繁旭黄硕
戴佳++曾繁旭++黄硕
摘 要:随着环境问题在近年来不断涌现,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意义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一门危机学科,环境传播承担着为公众提供可供决策的环境知识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涉及了多方面的伦理责任问题,包括科学、传播与健全的公共政策间的关系、专家与本地公众意见的协调、利益群体作为消息源的利弊、环境传播中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偏向以及媒体作为报道者和环保倡导者角色的矛盾等。结合相关文献与案例探讨以上问题,力求为环境传播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提供理论视角。
关键词:环境传播;伦理;媒体;技术专家;社会阶层
作者简介: 戴 佳,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北京 100084)
曾繁旭,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4)
黄 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环境问题的涌现。环境与生态污染在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构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风险。环境风险及其所引发的恐慌与社会抗争在全国各地频密出现,例如在全国多地出现的因抵制PX(俗称“对二甲苯”的化工原料)生产项目而形成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什邡、启东等地环境抗争中出现的暴力事件,引发了社会动乱。
由于围绕环境议题形成的传播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公共舆论、政策制定、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安定,研究如何促成良性的环境传播,促成议题各方对于风险的正确评估、理性协商,形成政策成果并有效消弭对抗行为,不但有利于对环境问题舆论的因势利导,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反之,环境传播的扭曲和失衡导致信息失真、风险放大,甚至引发民众谣言与抗争,为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例如,在环境危机发生的三个阶段,即对风险的了解(前危机阶段)、风险的呈现和公共关注(危机阶段)和习得、分享经验教训(后危机阶段),都离不开传播的参与{1}。因此,作为对环境问题进行解释并构建公众对环境议题认知的环境传播,其学科定位与社会责任理当引起重视。
一、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及其困境
环境传播是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以及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和建构的手段{2}。环境传播的实用功能在于“教育、警示、说服、调动和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而建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形成对自然和环境问题的观念感知{3}。
环境传播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之时,正值污染、生态灾难、技术风险等环境危机开始涌现。危机既包括由人类造成的对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威胁,也包括社会机构未能成功地应对与解决危机带来的压力,环境传播因此被视为“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这一学科定位不仅在于对环境危机和问题的理论建构和解读,更包含致力于改善环境危机和加强环保意识的伦理责任。Cox概括了环境传播的四个规范性原则,这些原则集中体现了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4}:(1)环境传播旨在帮助社会提高对有关人类社会和自然生物系统福祉的环境信号的正确反应能力。(2)在社会层面上,环境信息如政府信息、科学咨询系统和决策过程等的呈现,应是公开透明且易于被公众理解的。相应地,受到环境质量问题影响的群体也应享有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从而参与到关乎他们自身及其社群健康和生活状况的决策中去。(3)个人和社会都享有条件和能力对自然界进行学习、与之互动并分享其经验,同时基于这些经验与他人进行交流。这种经验本质上是积极健康的,应当受到鼓励和培养。(4)一些政策是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不利的或不可持续性的,当它们妨害了环境的社会表象/符号表征、知识主张或其他传播活动时,学者、教师和实践者有责任在适当的平台中就此进行教育、质询和批判性评价。相应地,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定义和推广前面提到的第一项规范性原则。
Cox这段关于环境传播伦理责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与伦理有关的环境传播的目标、过程、主体能动性以及批判能力的框架。具体来说,环境传播所要解决的不仅是改善环境,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提供福祉,同时也要允许针对环境事务的信息呈现与公共表达。这种信息呈现与公共表达不仅要积极、相关、透明、易于理解,而且要具有针对政治压力、怀有偏见的知识主张等妨碍性因素进行批判质疑的能力。 1996年,在美国演讲传播协会(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的前身)成立环境传播委员会这一环境传播的旗舰组织时,学者们就曾呼吁,环境传播应当作为“一个可识别的学科资源,为公共政策决策者、社会群体、商业交易、教育者和市民群体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知识”{5}。
然而,作为一门危机学科,环境传播伦理责任的实现也面临诸多困境。“环境”概念同时涵盖物质和社会/符号过程,而社会/符号表征往往会通过环境传播去塑造导向、引导公众兴趣,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方面,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本为环境表达提供渠道和可能,另一方面也在表达的过程中“对某些观点或群体加以限制,从而对环境的再现产生了阻碍”{6}。这种阻碍的具体表现,就是与环境议题相关的异常激烈的舆论争夺。在环境议题的表达中,既有媒体机构的报道与建构,公益组织的倡导,也有政府与企业的风险沟通,与此相应还有民众的诉求表达、谣言制造,以及集体反抗。
除了相关利益方的舆论争夺这种外部压力,当事者与公众主观意愿倾向也是伦理困境的来源。Senecah指出,尽管现实环境恶化的威胁十分紧迫,但危机的关键却在于人们对于政府行为愈发不信任、对公共生活各个层面的态度愈发激进{7},如近年来接连在多个城市发生的反对PX项目事件中,都体现出公众对政府信任的缺失,从而形成了群体性事件{8}。这种愤世嫉俗感和对改变现实的无力感使得一部分人不再热衷公民参与,或更多地采取斗争框架来看待环境事务{9}。
为了应对这种外部压力和主观意愿上的双重危机,保证对环境议题再现的客观公正,同时改善人们对待环境事务公共参与的态度,我们需要探讨环境传播伦理困境的症结所在,并寻找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科学、传播与健全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而二者有效运转的前提是健全的公共政策。制定关于环境议题的公共政策,有赖于环境传播对风险的适当的再现、诠释、评估,以及透明与公平的沟通带来的公共参与。而科学传播及健全的公共政策之间的建设性联系,在于环境传播是否能为关心风险的受众提供适当的信息{10},实现协调和沟通责任。
环境传播需要将对于环境现象的专业、科学的认知与研究结果以合理的方式传达给公众。由于环境议题与风险经常涉及具有较高专业技术门槛的知识,且具有不确定性,专业人士对技术本身及其危害的解释对公众理解至关重要。研究表明,专家的观点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和传播,就无益于民众理解真相{11}。
然而,媒体对环境问题的报道高度依赖专家信源,因此媒体态度常常倾向于与专家一致,较少呈现专家之间、专家与公众之间的观点争锋,由此产生了重视专业知识及专业权威的风险沟通的“科技范式”{12}。虽然它在告知、宣传科技造成的风险方面可能具有较高权威与效率,但过度倚赖专家、排斥公众参与讨论与决策,易导致对公众能力、意见与利益的轻视{13}。此外,公众的风险认知受到文化、政治等社会环境的影响,混合着多元价值、信仰、情感和政策偏向,只有通过充分的沟通、公众参与及风险协同管理,才能降低环境议题的争议性,建构公平公正的环境政策{14}。同样,Cox也指出,为形成民主环境下的合理环境诉求,需要检验媒介话语对自然世界的符号化展现,寻求不同观点之间潜在的一致之处,以维系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质量、促进它们在环境事件中的共同合作,并将其融入环保政策的制定中{15}。
因此,学者们呼吁,以专门知识垄断的消除与决策结构的开放为特征的风险沟通“民主模式”才是健全的公共政策产生的必由之路{16}。风险传播的“民主模式”在于建立一个建设性的专家——公众风险沟通模式,在传播专业知识、保证专业权威的前提下,纳入公众意见并实现“兼容性的参与”,以加强公正性与完善决策{17}。
三、技术专家和本地公众的意见协调
技术手段、利益和政治立场等决定了不同群体在环境问题的风险感知与应对中存在竞争和冲突{18}。因此,环境传播在协调专家与公众关系时的社会责任包括沟通和平衡两个层面:一方面,环境传播应在风险认知中将专家框架下的意见转述给具有认知差异的公众;另一方面,环境传播应在风险评估中平衡不同立场的专家与公众意见,使各方的诉求和技术观点都平等呈现。
由于环境问题通常有着较高的科学技术门槛,因此权威机构以及专业人士对技术本身及其危害的解释对公众理解至关重要。媒体作为公共话语平台,是不同话语主体争夺“结构性影响力”{19}的竞技场,而对于专家及其话语的选择,媒体引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涉及环境议题的讨论中,技术专家通常会通过媒介构建不同版本的“风险故事”{20},并展开意见争夺。一些对中国环境传播事件的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有时会过分偏向使用官方立场的专家作为信源,而较少采用其他独立研究或与官方意见相异的专家意见{21}。在政府压力下,官方专家的声音更容易得到彰显。例如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事件中,官方立场的“主烧派”专家的意见就更多地受到关注,而反对立场的“反烧派”专家则处于劣势{22}。
技术专家意见在环境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了媒体对本地公众、尤其是直接面对环境恶化的公众的意见的忽略。发端于1980年代的“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认为公众因科学知识的缺乏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持怀疑态度。因此,科学技术专家需要普及科学知识、帮助公众克服 “知识赤字”{23}。在这种认识模式的支配下,公众意见被视为缺乏科学基础的外行意见,无法引起媒介的重视。其结果是,公众意见表达在媒介中的缺位往往损害公众的利益{24}。
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经对“缺陷模式”进行了质疑。由科学技术专家提供更多的信息,并不一定能成功地化解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怀疑态度{25}。因为任何决策过程不仅依赖科学的“事实”,而且依赖于个人经验、当地文化习俗等外部因素。例如,无论专家如何言之凿凿地论证垃圾焚烧无害于人类健康,公众也会依据生活经验开展邻避运动,抵制居住地附近的垃圾焚烧工程。有学者甚至指出,技术风险和危机往往酿成政治事件,其中事实与政治和价值取向交杂呈现,牵涉了多方博弈而并非只关乎科学评估{26}。
同时,专家与民众认知风险框架的不同、背景知识及表达方式的差异也有可能使专业意见无法适当地传达给公众。其结果或者造成民众认知中的风险大于实际风险,形成恐慌{27},或者导致各不相同的公众解读和认知{28},失去其预期的解释效果,无法打消公众对风险的顾虑。在公众和政府观点冲突的环境抗争事件中,对于官方立场专家意见的过分偏向也会引发公众对媒体和专家本身的不信任,以及对政府的愈发不满{29}。此外,公众也并非被动的信息和科学知识的接收者。在媒介全面渗透生活的时代,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降低知识赤字,并自行评估大众媒体和政府公布的信息的真实性。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鼓励公共参与决策的参与模式,已经取代了强调专家在传播中的核心地位的“缺陷模式”{30},而公众意见对于风险评估的重要价值也应得到重视。一方面,本地知识和信息对于风险分析和传播有着重要意义{31},因为来自本地利益相关群体的知识可以在技术专家观点之外提供必要经验{32}。
另一方面,公众中存在的多元利益群体,彼此之间知识、立场、资源与影响力迥异,不应被简单地归纳为单一的“公众”{33}。在这一背景下,主要重视专家观点的风险评估会不可避免地形成用单一利益代表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局面{34},从而造成个人或群体利益的牺牲和不满。
因此,环境传播所要担负的另一责任就是平衡公共空间中的专家观点和当地公众意见,同时促进不同群体平等的诉求表达。例如,在报道环境争议时,媒体应不仅传递来自专家或权威的话语,同时也要纳入本地公众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居民、环保团体等)的意见。由此促进的多元、平衡报道可以提高风险评估的兼容性、公正性和合法性,从而在技术层面达成更为适当的决策{35},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36}。
四、利益团体作为消息源的利弊
环境事件中涉及的利益相关团体,出于表达诉求的愿望或需要,会主动向媒介提供信息并与媒介保持互动。利益团体作为消息源,固然可以为媒介提供一手的事件信息,但同时也存在议程设置或影响公正客观报道的可能。因此,如何在充分利用利益团体作为消息源的同时,警惕与规避利益团体的引导与利用,是环境传播面对的另一个伦理难题。
环保组织是环境事件中的重要利益团体。环保组织对于媒介的信息补贴,是其进行议题倡导进而对公共讨论与决策施加影响的重要途径{37}。信息补贴的概念最早由传播学者Gandy提出,用来描述新闻生产过程中消息源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资源置换关系:即记者要以低成本制作新闻,而消息源要以低成本扩散自己的信息。具体做法包括消息源运用各种公关措施,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38}。曾繁旭针对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家园志愿者”的研究指出,“绿色家园志愿者”通过定期组织由几十名记者参加的“环境记者沙龙”,发动多家媒体参加国家环保局的论证会,使怒江议题广泛传播。之后随着一些媒体开始主动采访,“绿色家园志愿者”积极配合,提供信息,通过精英媒体的报道形成媒体共鸣;同时通过与国际媒体的互动将议题传播至海外,成功实现了民意塑造{39}。此外,环保组织有时也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信息来影响舆论。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就通过在网站发表博客文章揭露转基因食物“黄金大米”在中国湖南某小学进行涉嫌违规的实验,之后文章被媒体大量转载,受到公众关注{40}。
利益团体作为消息源对于环境传播伦理的挑战,主要在于利益团体对信息的操控可能影响媒体的客观报道。首先,相较于媒体资源丰富、有充足的人力和资金与媒体进行互动的团体,资源欠缺的团体通常因为对媒体不具吸引力而被边缘化{41}。因此,一些利益团体的诉求得到彰显,而另一些相对弱势团体的声音却受到抑制。其次,深谙新闻操作规律的利益团体,可能为增加曝光效果,主动选择呈现媒体感兴趣的话题,运用耸人听闻的景观和夸张煽情的表达方式来获取媒介关注{42}。结果导致话题过于集中或偏激的现象,不利于公众对客观事实的理解与理性的公共协商。此外,尽管来自环保利益团体的新闻往往能给媒体带来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且环保议题相对受到较少限制{43},但有时一些敏感话题也会使利益团体诉求与官方对媒体的“喉舌”要求或官方话语发生冲突{44}。媒体为规避官方压力保障安全的新闻生产,可能选择对一些利益集团的敏感诉求保持静默,甚至站在官方立场对其进行批评挞伐。因此是否屏蔽正当而敏感的利益集团信息源,同样考验着媒体的专业伦理和社会责任。
相比于非政府团体,政府机构作为信源在吸引媒体和影响公众上有着更多天然优势,其行动和决策本身就常常成为媒体关注追逐的对象{45}。然而由于环境事件通常对地方政绩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往往封锁或不及时公布信息,如在2009年湖南等地的血铅事件、2011年渤海溢油事件以及2014年兰州水污染等事件当中,政府信息披露都不及时充分,促生了大量自下而上的控诉与抗议行为{46}。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环境表达的平台和环保运动动员的工具{47}。例如在厦门PX事件、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事件中,民众主动接近媒体,制造舆论并影响到政府最终的决策{48}。但与此同时,借助网络谣言等非正常手段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的案例也层出不穷,如2012年什邡钼铜事件、宁波反PX事件中的谣言,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不利于正常传播秩序的维持{49}。
五、中产阶级和底层社会在环境传播中的不对等地位
除了平衡专家观点和公众诉求,对作为信息源的利益集团进行甄别,环境传播也需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话语权的平衡。近年来在环境事件中进入公众视野的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体,在话语权与媒介素养上都呈现巨大差异,突显了媒体在环境传播中的另一重伦理困境。
中产阶级通过丰富的资源与媒体进行互动并成为信息源,乃至通过媒体设定报道框架{50}。而底层群体由于与媒体缺乏共同利益纽带,在媒体中的能见度较低。他们往往被媒体当做可任意剪裁的新闻素材为新闻主题服务,如一些官方媒体塑造农民感激涕零的形象建构政府政策的合法性,而另一些媒体曾通过展示底层民众利益受损的悲惨境遇来博取同情性理解{51}。同样是反对垃圾焚烧抗争,在广东番禺由于参与者多为中产阶级,文化素质和媒介素养较高,因此成功地利用媒体表达了诉求;而在广东永兴村的农民反烧事件中,村民们则很难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出声音,掌握传播主动权{52}。
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新媒体素养差异,更加剧了话语权不平等的问题。相对于中产阶级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平台吸引公众关注,甚至将环境抗争运动延伸至虚拟空间,很多底层群体几乎不了解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使用,在这一空间中的表达接近空白。
不同社会阶层在媒体资源的可接近性与媒介素养上的差异,导致了各阶层通过媒介进行利益表达时呈现大相径庭的能见度。媒体如何恪守专业准则在传播过程中平衡展现各个群体,保证不同群体——尤其是底层和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将最终决定环境抗争的走向与结果。同时,底层社会的新媒体素养也亟待通过行政与教育手段得到提升,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环境运动中的平等公民赋权。
六、媒体作为新闻报道者和环保倡导者的双重角色
相较于政府机构环境事件中的抗争诉求主体往往拥有较少的动员资源和话语权力,也缺乏通畅的诉求渠道,因而更多地寄望于媒体,将媒体作为赖以发声的外部资源和争取政治机会的途径{53},力图通过媒介来进行抗争行为的组织动员。媒体因此在环境传播中扮演议题的报道者和倡导者的双重角色,并可能面临这两种角色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要求媒体对事件保持冷静中立的观察与记录态度,不应直接介入环保行动中倡导公共议题{54}。另一方面新闻记者群体如果基于自身理想或利益,在环境诉求上与抗争者产生共鸣,也可能通过报道框架的使用为抗争行动推波助澜。
事实上,近年来在很多环境议题中,媒体表现活跃,它们不仅一直是各类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支持者和同盟{55},同时也在公民自发组织的环保活动中充当了议题发起人和推动者。例如一些传统媒体明确声援市民的环保活动,甚至直接参与活动为行动者们出谋划策等,成为了组织行动的“风向标”{56}。媒体积极进行环境倡导的现象,或许可以理解为媒体自身“追溯社会权力”和维护“专业性”的职业需要{57}。例如,通过将民众的批评和质疑传递给官方以寻求回应{58},媒体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抗衡官方主导的议题,而且能够充当被批评的政府与激进的公众之间的调停人{59},促进公共空间话语的多样性和积极有效的沟通。
七、结 语
本文从环境传播学者Cox 关于环境传播的四个规范性原则出发,探讨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并就目前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作出反思。讨论的核心在于环境传播在实现环境议题的信息呈现与公共表达过程中,如何发展针对政治压力、怀有偏见的知识主张等妨碍性因素进行批判质疑与修正的能力。
整体而言,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在于实现对环境信息的公正理解与沟通,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公开意见交换,合理地呈现自然与人类世界中存在的危害及应对策略。环境传播关注的是传播的合法性过程,如呈现“环境正义的故事”、“暴露问题并解决问题”{60},在决策讨论中呈现公众对于真相的不同认识框架{61},并“形成适当的个人行动和/或政策成果的更为公共性的辩论和讨论”{62}。它并不奢求达成一个确定的结果,如达成共识、劝服或一项政策的制定。这种特性因而要求环境传播者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防止受到局部利益、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
随着网络技术和新媒体应用的发展,环境传播的伦理责任也需要应对更多新的挑战。一方面,新媒体使底层赋权成为可能{63},促进了公共讨论的多元化,进一步打破了官方垄断话语权、民众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局面;但另一方面,网络意见领袖的动员效应{64}和议程设置功能也催生了老问题在新平台中的出现:即信息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被技术专家、利益集团、中产阶级以及热衷于倡导的新闻记者把控,而普通公众、弱势群体或底层民众的环保诉求被进一步弱化与边缘化。新媒体环境也促生了谣言{65}、群体极化效应{66}(桑斯坦,2010)、回音壁效应{67}以及怨恨、戏谑等问题{68},可能加剧环境传播的伦理困境。正因如此,增强道德自觉,深入反思媒介对于环境报道的伦理缺失并调整传播方式,环境传播才能改善环境,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良性发展提供福祉。
注 释:
①⑩{26}{28}Heath R L,PalencharM J,Proutheau S,Hocke T M:“Nature,crisis,risk,science,and society:What is our ethical 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1,No.1,2007.
②③Cox R:“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2nd edition)”,London:Sage,2010,pp.20-21,pp.20-21.
④⑥{15}Cox R:“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No.1,2007.
⑤⑦⑨Senecah Susan L:“Impetus,mission,and future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division:are we still on track? Were we ever?”,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1,No.1,2007.
⑧龙小农、舒凌云:《自媒体时代舆论聚变的非理性与信息公开滞后性的互构——以 “PX 项目魔咒” 的建构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郑旭涛:《预防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以什邡,启东,宁波事件为例》,《东南学术》2013年第3期。
{11}Campbell K K:“The rhetorical act (2nd ed.)”,Belmont,CA:Wadsworth,1996,pp.3;Heath R L,Palenchar M J,Proutheau S, Hocke T M:“Nature,crisis,risk,science,and society:What is our ethical 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1,No.1,2007.
{12}{16}郭小平:《风险传播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国传媒报告》2006年第3期。
{13}Katz S B, Miller C R:“The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siting controversy in North Carolina:Toward a rhetorical model of risk communication”,C G Herndl,S C Brown (Eds.):Green culture:Environmental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1996,pp.111-139;Sturgis P,Allum N:“Science in society:re-evaluating the deficit model of public attitude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ol.13,No.1,2004;Wynne B:“Knowledges in context”,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Vol.16,No.1,1991.
{14}Waddell C:“Saving the Great Lakes: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Green culture:“Environmental rhetoric in contemporary America”,1996,pp.141-165.
{17}Fischer F:“Citizens,experts,and the environment:The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p.352;Flyvbjerg B,Bruzelius N,Rothengatter W:“Megaprojects and risk:An anatomy of amb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8}Schütz H,Wiedemann P M:“How to deal with dissent among experts. Risk evaluation of EMF in a scientific dialogue”,Journal of Risk Research,Vol.8,No.6,2005.
{19}Lukes S:“Power:A radical view”,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00.
{20}Wildemann T M: “Communicating risks of foodborne diseases”,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e,Vol.1,No.1,2006.
{21}尹瑛:《冲突性环境议题中民意表达的困境与策略: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 事件的个案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1期;仇玲:《环境危机议题的媒体建构与信息来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
{22}{29}尹瑛:《冲突性环境议题中民意表达的困境与策略:对 “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 事件的个案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0年第1期。
{23}Dickson D:“The Case for a ‘deficit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Vol.27,2005.
{24}{31}{32}{33}{34}{35}{36}Kinsella W J:“Reconceptualizing 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No.30,2007.
{25}Kearnes M,Macnaghten P,Wilsdon J:“Governing at the nanoscale”,http://www.demos.co.uk/publications/governingatthenano scale,2006.
{27}Hocke T M:“Social amplication of risk”,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States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Dallas,TX,2006.
{30}Boykoff M T:“Creating a Climate for Change: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Change”,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9,No.2,2009.
{37}{38}{44}曾繁旭、黄广生:《地方媒介体系:一种都市抗战的政治资源》,《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4期。
{39}{41}{42}曾繁旭:《形成中的媒体市民社会:民间声音如何影响政策议程》,《新闻学研究》2009年总第100期。
{40}沈秋坦:《科技危机传播中政府、公众与媒体关系的探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7页。
{43}{55}Yang,G:“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Vol.181,2005.
{45}汪莹莹:《珠三角地区环境传播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59页。
{46}许加彪:《风险社会下中国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新型媒介生态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34期(11);朱谦:《突发海洋溢油事件政府信息发布制度之检讨——以蓬莱 19-3 油田溢油事件为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47}{49}郭小平:《中国网络环境传播与环保运动》,《绿叶》2013年第10期。
{48}范松楠:《环境传播中公民新闻的类型与功能》,《青年记者》2013年第14期。
{50}{51}{52}{64}曾繁旭、黄广生、李艳红:《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东南学术》2012年第2期。
{53}Brockett C D:“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central America”,Comparative politics,Vol.23,1991.
{54}{56}{58}黄煜、曾繁旭:《从以邻为壑到政策倡导:媒体与社会抗争的互激模式》,《新闻学研究》2011年总第109期。
{57}聂静虹、王博:《多元框架整合:传统媒体都市集体行动报道方式探究——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新闻大学》2013年第5期。
{59}曾繁旭:《传统媒体作为调停人:框架整合与政策回应》,《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60}Valenti J:“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Vol.13,No.4,1998.
{61}{62}Valenti J,Wilkins L:“An ethical risk communication protocol for science and mass communication”,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ol.4,1995.
{63}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5页。
{65}戴佳、 曾繁旭、黄硕:《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PX 事件的启示》,《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66}[美]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67}Gilbert E,Bergstrom T,Karahalios K:“Blogs are Echo Chambers:Blogs are Echo Chambers”,//HICSS '09. 42n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JAN. 5-8,Big island,2009.
{68}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研究》2009年第9期。
Ethical Dilemma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DAI Jia,ZENG Fan-xu,HUANG Shuo
Abstract: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nstantly emerge 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 to. As a crisis discipline,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s the mission to provid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based on which the public can make justifie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To achieve this goal involves addressing the ethical problem in many aspects,inclu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communication and sound public policy;coordination among expertsand local publicsopinion;the pros and cons of interest groups as news sources;the bias towards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medias dual roles as both reporters and advocators. Connec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ase examples,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solution of the ethical dilemmas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ethics;media;expert;social class
(责任编校:文 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