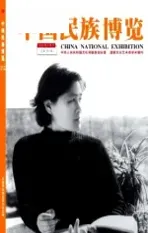吐蕃西夏文化交流与西夏藏传风格唐卡
2015-08-15谢继胜
文/谢继胜
藏语称西夏为mi-nyag,这一称呼既指西夏建国以前的党项人,也指西夏建国以后的西夏人。【1】《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记西夏陵为“木纳西夏祖坟”,“木纳”即“木雅”minyag。【2】论及西夏与吐蕃的历史文化联系,从公元7世纪初党项羌与吐蕃王朝发生联系开始,到13世纪初西夏亡国时为止,长达600多年,其间你来我往,水乳交融,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少见的现象之一。【3】唐时,吐蕃和党项部落之间的战争使得大批的党项人归属于吐蕃王朝治下,两族杂居者为数众多;雅隆王朝解体以后,东迁河陇、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与内徙的党项人部落杂居共处;西夏建国以后,上述地方有很大一部分吐蕃人被收归治下,成了西夏的“编户齐民”。吐蕃与党项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军事争夺与两族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构成了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民族上的杂居与融和,文化上极为密切的相互交流。【4】
一、吐蕃佛教对党项人的影响
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由于地域和族群的关系,吐蕃人和党项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有诸多的共同之处,宋人称“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5】传为阿底峡所掘伏藏《柱间史》记载,松赞干布的第三位妃子是木雅女茹雍东萨尺尊,她主持修建了查拉贡布神殿(即岩神大黑天神殿),此妃还在女妖魔窟旁的一岩石壁上勒石作大日如来像。另在宫殿的西北面,为阻断厉鬼出没之地而起造白塔,举行佑僧仪式,【6】并主持修建了米茫才神殿(migmang-tsal-gyilha-khang)。【7】松赞干布命人在弥药热甫岗地方建造了佛寺并以弥药人为监工在康区建造隆唐准玛寺。【8】在吐蕃地方也有很多来自党项的僧人和学问僧。【9】据《木雅五学者传》记,热德玛桑格大师等五位学者,早期都无一例外的去过吐蕃地区,在桑普寺求经学法,还到过夏鲁、萨迦、那唐及觉木隆等地寺院,学有所成。【10】宋人周辉撰《清波杂志》云:“蕃方唯(西夏)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11】可见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早在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西夏佛教实际上受到了西藏前宏期佛教的影响。与此同时,党项人的佛教上师对吐蕃佛教尤其是吐蕃后宏期佛教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为11世纪藏传佛教支派进入西夏佛教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吐蕃王朝在卫藏的统治变的衰弱,朗达玛赞普灭佛之时,与吐蕃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党项人乘机填补了这一空白,取代吐蕃成为吐蕃东北部这一广大区域的佛教文化中心,《西藏王统记》描述这种局面时将卫藏形容为黑暗之域并记载说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连佛法的名字都无人敢及。【12】卫藏的僧俗为避灭法战乱,取道各路逃离卫藏,来到与党项人杂居的多康学法和从事宗教活动,以致于多康成为10至11世纪佛教传播的中心,下路弘法的起点。东律初祖拉钦·贡巴饶赛(952-1035)就是宗喀德康(今青海循化黄河以北)地方人,【13】据说大师曾从弥药上师学法。【14】拉钦驻锡丹迪寺时,朗达玛大妃那囊氏之子永丹六世孙益西坚赞,派卫藏十人赴丹迪学法,其中有前藏赴多康的鲁梅(另一种说法是鲁梅是贡巴饶赛的弟子粗·喜饶乔 [mtshur shes rab mchog]的弟子)。【15】鲁梅等受戒弟子陆续返回卫藏的时间是在公元975年以后,在卫藏各地广收门徒,其弟子有“四柱八梁三十二椽”之说,并在卫藏建立了很多的寺庙,剃度了很多的僧人并形成了各自的传承,他们所属的寺庙正是公元11世纪前后在西藏艺术史上有重要意义的那一批卫藏早期寺院,其建寺的时间正好是鲁梅等人返回卫藏的时间。作为西夏佛寺主体,建于都城兴庆附近的寺院,其建寺时间也都在这一时期。【16】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设想,正是以鲁梅为首的一大批赴多康学法的僧人将多康党项等地包括佛教艺术在内的佛教文化传入卫藏,因为卫藏的佛教传承完全中断了近一百年,所有的寺庙,佛像等等几乎被彻底的毁坏,没有多康边地保留的佛教文化传承,卫藏佛教不可能如此迅速的复兴。然而,多康党项等地保留的吐蕃佛教艺术遗存应该是前弘期末由东印度传入西藏的波罗风格,在党项故地的近一个世纪,艺术风格融进了某些当地的艺术成份,而这些当地的艺术成份本身就是多元风格的组合体,其中包括传自西域的中亚风格和经由中亚传入西夏的东印度波罗风格。所以,11世纪西藏艺术中出现的中亚特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夏艺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虽然,我们并不能将藏文史书中提及的多康地区完全与党项人生活的地区等同起来,将10世纪前后的多康地方化的吐蕃时期遗留佛教看作是西夏立国以后的西夏佛教,但是,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兴盛。我们今天在西夏人活动过的地区都可以发现西夏地方化的藏传佛教遗存,这些遗存连接成若干条西夏艺术向外传播的通道,将西夏与西藏联系在一起【17】。我们可以认为出现在11世纪前后卫藏寺院中的壁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西夏艺术”的逆向影响,扎唐寺的壁画某些风格成分就是如此。然而,必须加以确认的是,以上谈到的“西夏艺术”仅仅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因为我们设想的西夏艺术对藏传艺术的影响,发生在藏传佛教前宏期的初年,此时西夏还没有建国,生活在这一广大区域的党项人的艺术创作,根本无法称之为一种艺术流派,更谈不上对其他域外艺术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只是7世纪以来中原艺术对吐蕃艺术影响的继续。
二、西夏建国以后藏传佛教的宏传
西夏王朝的建立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从唐时党项人在吐蕃势力挤压下的多次辗转迁徙,五代时期与诸藩镇政权的周旋直到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可以说是从列强夹缝中成长起来的。西夏的人民经历了太多的颠沛流离和无尽的战乱,他们希望有一种宗教能够及时的解除心灵的苦难,舒缓精神的压力。西夏社会的这种特征导致了西夏佛教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极强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包容性。这种佛教并不重视其遵循何种流派,奉行何种教义,而是强调通过直观的可以操作的宗教仪式让信徒取得精神安慰感,西夏大规模的译经与刻经活动,究其本质,并非要建立自己的佛教体系,而是西夏王室这种情绪的宣泄。所以,西夏佛教同时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兼收并蓄的融合在一起,极为侧重藏汉佛教中有关实践的内容并因此看重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噶玛噶举派的教法具有明显的实践色彩,正好迎合了西夏佛教重仪轨、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使其得以在西夏朝野得以迅速的传播。
西夏建国后,早期曾与河湟吐蕃首领唃厮罗产生矛盾,两者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西夏腹背受敌,形成被吐蕃、北宋夹击的形势。秉常时期,皇太后梁氏为联络吐蕃以自己的女儿向吐蕃首领董毡之子蔺圃比请婚。乾顺时期,西夏国相梁乙埋又向吐蕃首领阿里骨为自己的儿子请婚,后来吐蕃首领拢拶又与西夏宗室结为婚姻,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交往比早期明显增多。【18】可以说整个12世纪,西夏没有和吐蕃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一直和平相处,近一百年的和平时期为西夏和吐蕃的文化交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19】而河湟吐蕃时期遗留佛教的兴盛则为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夏建国前后,正是唃厮罗政权统治的河湟一带佛教盛行的时期,现存西宁北山的土楼山石窟壁画,就是河湟吐蕃时期藏传艺术的留存,西窟可见大日如来圆形构图坛城。【20】宋绍圣中(1094-1097),武举人李远官镇洮,奉檄军前记其经历见闻,撰《青唐录》,文内有云:“(青唐)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哥,水西平原,建佛寺广五六里,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阿离骨敛民作是像,民始贰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之丽法无不免者。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王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21】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青唐城佛教的鼎盛,佛寺几乎占据了城市建筑的一半,并且能够塑造高达13级浮屠的鎏金大佛像,其造像技艺之高超可以想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熙宁五年十月(1072年),宋军收复镇洮军(熙河)接收归附吐蕃各部后在当地建寺,以“大威德禅院为额”,这里的“大威德”疑为密教神灵,【22】因为“大威德”一词专指rdo-rje vjigs-byed,梵文Vajrabhairava,况且这是安抚吐蕃部落所建寺院,若是,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藏传密教造像在这一地区流行在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
《青唐录》撰写的时间正是在西夏建国的初年,青唐吐蕃部落保留的吐蕃前弘期的艺术(11世纪初年西藏本土后弘期艺术风格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何不传播到与之杂居的西夏人那里?所以,我们在讨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时,应该充分考虑河湟吐蕃对西夏的影响。如上所述,藏文文献记载吐蕃佛教在西夏建国以前很长时间就已经传入迁徙至内地西北的党项人中间,我们以为其年代最晚应该早于大师贡巴饶赛(952-1035),因为大师曾向西夏上师学法。至西夏建国初期,藏传佛教似乎已经盛传开来,乾顺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的西夏文部分末尾列举了修塔的有关人员,其中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西夏文的“羌”字音“勃”,正与吐蕃的“蕃”字同音,此字应是吐蕃的称谓,可知当时凉州已有管理蕃汉事物的僧官。【23】事实上,西夏与吐蕃的关系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密切,远在1036年西夏攻陷瓜沙之际,张掖河流域的人们已经普遍使用藏语,《宋史·夏国传》记:(德明之子)元昊“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在他新制西夏文字以前,所谓“蕃字”就是指的藏文,因此元昊早年就已和藏传佛教发生关系,应该是可以肯定的。【24】如1045年,西夏派僧人吉外吉、法正等到宋朝,感谢宋朝第二次赐经事。这里的“吉外吉”,应为藏文chos-rje的译音,意为法王,是藏传佛教高僧的一种称号,萨迦派即以chos-rje称萨迦班智达。【25】又如,1093年西夏建感应塔及寺院,完工后立碑志庆,碑文末尾的名单中有“庆寺都大勾当铭赛正嚷挨黎臣梁行者 庆寺都大勾当卧则罗正兼顶直罗外母罗正律晶赐绯僧”之句。“都大勾当”在黑水桥碑藏文中作spyi-vi-zhalsnga-ba,可能相当于后期藏传寺院中管理行政事物的机构spyi-ba;“卧则罗正”可能就是藏传寺院的领经师dbumdzad-slob-dpon。【26】1098年(永安元年)《敕赐宝觉寺碑记》提到在甘州建卧佛寺的西夏国师嵬名思能早年曾随燕丹国师学习佛理。这里的“燕丹”,当即藏语的yon-tan,可能这位国师来自西藏,也可能西夏国师以藏语作为国师称号。【27】此外,西夏境内有很多的吐蕃人,他们主要使用藏语,这是藏传风格佛教艺术在西夏广为流传的因素之一,在吐蕃撤出河西敦煌和于阗一线后,藏语文直到公元10世纪仍被作为官方语言而普遍使用着,【28】以至于藏人出家也要层层考试才能度为僧人;【29】西夏人在吐蕃人聚居的河西立碑时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如乾祐七年(1176年)于甘州城西张掖河桥畔之《黑水建桥敕碑》表明,可见此地使用藏文已经不短的时间了。【30】今存敦煌写本《嵬名王传》,则是西夏民间用藏文字母代替西夏文拼音写成。【31】
此外,藏语文在西夏境内,还是诵读佛经的必备文字之一,如乾祐二十年(1189年)的大法会“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将藏语经文(西番)放在首位,可见藏语在西夏佛教活动中的地位。克恰诺夫(E.I.Kychanov)认为,西夏国内佛教徒学习藏语文是强制性的。他还以法典为例,说明藏语的重要性。据统计,要求用藏语诵读的佛经有:《文殊室利名经》、《毗奈耶决定伏波离所问经》、《大方光佛华严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切恶道消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无垢净光明摩诃陀罗尼经》和《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等。【32】综上所述,西夏建国以后藏传佛教的流行实际上是党项人的佛教与吐蕃前宏期和后宏期交替时期佛教关系的继续。因此,我们在分析包括黑水城在内的西夏藏式风格作品时,并不能将这些作品的出现年代严格限定在噶玛噶举和萨迦派僧人和西夏朝廷发生联系之后,而应该考虑党项人和吐蕃的关系,西夏早期、中期和河湟吐蕃佛教的关系。假如没有两者之间地域、民族与宗教之间绵长深厚的历史联系,很难设想10世纪前后后宏期在吐蕃复兴,11世纪后弘期初年复由阿里等地进入卫藏的修行上乐金刚金刚亥母本尊坛城的密法几乎同时能够在西夏的广大区域流行。
西藏艺术史家在讨论由西藏使夏的僧人上师时,一致将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的弟子藏巴顿库瓦入藏作为藏传佛教绘画进入西夏之始,并以此作为西夏藏传风格绘画断代的依据,【33】从而将出现修习上乐金刚根本续双身像的西夏绘画断代在1189年藏巴顿库瓦使赴西夏之后,这种断代无疑是错误的,还会产生一些断代上的矛盾。例如,出自贺兰县宏佛塔——一种唐宋以来流行的密檐式砖塔而不是喇嘛塔——的上乐金刚像,其建塔的年代有可能早至元昊时期,此塔没有重新装藏的迹象,我们很难将他们断代在藏巴顿库瓦入夏之后,即1189年以后。所以,与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历史进程相对应,西夏故地佛塔所出藏传绘画作品表明,早在元昊时代这些作品已经存在,【34】至少在仁宗(1139-1193)初期,藏传绘画已经盛传开来。确凿的文献表明,在噶举派僧人到来之前,当时有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和西藏的僧人久居西夏从事译经事业。例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刊汉藏合璧的偈子《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v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yon tan rin po che bsdud pa tshig su bcad pa),这份偈子原是仁宗朝从梵文原本译为西夏文、汉文和藏文的,明刊本保留了一篇明代的序言和一篇原有的西夏题记(仅用汉文),其中提到6个人名,其中有梵文译者遏啊难捺吃哩底,上师拶也阿难捺,主校波罗显胜。据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考证,遏啊难捺吃哩底梵文为nadakirti ;还原为藏文kun-dgavgrags,断定他是一位吐蕃僧人。拶也阿难捺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藏文和西夏文的佛经跋页中,据考他是来自克什米尔的上师。作为译经职位最高的上师,按照西夏僧官制度,应为藏人,所以史金波先生认为波罗显胜是西藏僧人。这些僧人的活动年代大多都在仁宗初年。【35】其时,噶玛噶举和西夏的联系还没有见诸记载。
此外,我们从西夏大藏经所刊刻的木刻画也可以印证如上记载。西夏文佛经译自汉文的经典一般时代较早,所译藏文经典的时代多在后期。现在黑水城出土或者其他博物馆所藏的带有西藏绘画风格的版画常常被认为是出自西夏文译自藏文的经典,联系到西夏和西藏当时的教派联系的历史事实,常常将这些作品的断代定得较晚,而事实并非如此:带有藏式风格的绘画不仅出现在西夏文佛经中,而且也出现在汉文佛经中。我们检出西夏雕印的汉文带有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最早的作品出自正德十五年(1141)《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经首版画佛像;【36】其后有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宗仁孝皇帝(1139-1193)印施汉文《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37】其中的木刻版插图带有典型的卫藏波罗风格,般若佛母的背光式样与扎唐寺壁画大背光及柏兹克里特石窟同期的背光式样相同,更为突出的是环绕主尊的菩萨的头饰与扎唐寺以及后来的夏鲁寺、敦煌465窟等的菩萨头饰完全一致,画面众菩萨以七分面朝向主尊的构图方式与扎唐寺以及465窟窟顶壁画大致相同。【38】这件作品的存在本身说明在1189年噶玛噶举僧人使夏以前的1167年就有了藏传绘画的雕版印画,其传入西夏的年代应该更早,现藏印度博物馆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刻经版画残片与此经应该是同时代的作品。【39】又如西夏乾祐二十年,仁宗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其时作大法会凡十昼夜,敬请与会的众国师据说都是西藏高僧。在这部汉藏风格合璧的经前插图中,西藏风格被置于右侧卷首最为尊贵的地位。作品中主尊的身相,佛龛宫殿的样式,两侧的立兽以及上面提到的菩萨三角形头饰都与同时期的唐卡作品相同,但是构图方式更象扎唐寺壁画,实际上反映的是汉地中亚的风格。上述木刻作品与1229年至1322年刊刻的《碛砂藏》版中的带有西藏风格的插图在人物造像和母题细节上截然不同,例如,后者作为主尊的佛像已经没有了黑水城版画中与唐卡造像完全相同的粗短脖颈,菩萨三角形头饰倾向于圆形等等,此外,刀法趋于细腻,线条更加细密、流畅和圆润。这些图像都出现在1302年杭州刻印的元《碛砂藏》中,说明当时汉地所绘有关藏式风格的作品造像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40】以上的木刻版画都有比较明确的纪年,这就为西夏黑水城唐卡和西夏故地佛塔出土的西夏藏传绘画提供了一个相对的时间坐标。
三、西夏文献中的国师与密法
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经卷残片证明,早在藏巴顿库瓦之前,西夏已有藏人国师传授上乐金刚法。汉文经卷名为《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和《是钉撅咒》。
前一份经文录文为:
……空本续……国师 知金刚传
[沙]门提点 海照译
……解脱;众相不变最上身。□□□□共观主;不二尊处恭敬礼。□□□心纂略义;此之三种实幽玄。□□上师【41】真要门;文义分明我宣说。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之义者因道果三也,其中因者……相,风脉明点之□□之道者……四主及能解脱增究……[谓]依此而修……。
残卷上“国师 知金刚传,[沙]门提点海照译”中的“国师知金刚”显然是吐蕃僧人,此汉文本系由藏文翻译,但国师知金刚何许人也?史金波先生《西夏佛教史略》收录13位国师,其中也没有知金刚的踪影。【42】他决不是噶玛噶举弟子格西藏波瓦或藏巴顿库瓦,因为没有名义上的对应。“格西藏波瓦”,藏文作dge bshes gtsang po ba,意为“后藏善知识”;“藏巴顿库瓦”藏文作gtsang-pa-dung-khur-ba,意为“后藏持螺者”;知金刚还原为藏文为“多吉庆饶”rdo-rje mkhyen-rab,“益西多吉”ye-shes rdo-rje或“喜饶多吉”shes-rab rdo-rje,可见它们之间没有联系。此外,国师称号始于西夏早期,使夏的噶举派僧人是否做了国师尚待考证,因为藏文文献只是说他们做了上师,写作bla-ma,如果是国师,《红史》、《贤者喜宴》等噶举派僧人撰藏文文献就可能直接写作藏文的gu-shri,因为当时这个音译词已经在使用。
拜寺沟后一份经卷残叶《是钉撅咒》,定名实际上指的是左侧半叶,右侧半叶我们以为是译自藏文《上乐根本续》的一部分。经文记载的是上乐金刚坛城语轮和意轮的神灵安排,有些神名可以还原为藏文和梵文。
梵文经典所列语轮与意轮神灵如下:
环绕中央莲花的内圈神灵共有8对(或9对)代表“意”(citta)位于天界,其中女神的名字是暴怒女(Pracandā/ra-tu-gtum-mo),以托贝杜保(“颅骨小块”Khandakapāla/ thod-pavidum-bu)象征长久神变的基础;怒眼女(Pracandaksī/ gtum-pavi-mig-canma),以大骷髅(Mahākañkāla/keng-rus-chen-po)象征对神变力的证悟;具光女(Prabhāvatī/ vodldan-ma),以骷髅(Kañkāla/ kengrus)也象征对神变力的证悟;大鼻女(Mahānāsā/ sna-chen-ma),以暴露獠牙(Vikatadamstrin/ mche-barnam-par-gtsigs-pa)象征思想神变力的基础;勇士智慧女(Vīramatī/dpav-bovi-blo-gros-ma),以无量光佛(Amitābha/ vod-dpag-med)象征勇力;楞伽自在女(Lanke varī/lang-kavi-dbang-phyug-ma),以金刚光(Vajraprabha/ rdo-rje-vod)象征意识力。
方塔所出《是钉撅咒》所录意轮神灵如下:“及最掇母;北方上拶兰坦罗处大骷骨及掇眼母;西方上乌眼处骷骨及具光母;南方上阿乌坦处咬□及大鼻母;火隅上俄坦瓦哩处酒□及勇……;□上罗弥说罗处无量光及人□母;风隅上……处金刚光及兰机自在母;自在隅上马棘瓦数金刚身及树影母。此数是意轮也。”
这里的对应是明显的,最掇母就是暴怒女;托贝杜保为大骷骨;怒眼女为掇眼母;大鼻女等同于大鼻母;金刚光、兰机自在母(楞伽自在女)皆相同。
梵文经典的语轮神灵为:环绕中央莲花的中圈神灵在一些唐卡是两边排坛城神灵上部的8位(或9 位)黄色双修神灵(yab-yum),代表“语”(vāk),位于地上,其中女神的名字是护地女(Irāvatī/ sa-bsrungsma)以新芽(Añkuraka/ myu-guc a n)象征洞察力;大威德金刚女(Mahābhairavā/ vjigs-byedchen-mo)以金刚辫(Vajrajatila/rdo-rje-ral-pa-can)象征皈依;风身女(Vāyuvegā/ rlung-gi-zugscan-ma)以大勇力(Mahāvīra/dpav-bo-chen-po)象征勇力;饮酒女(Surabhaksī/ chang-vthungma)以金刚持轰(Vajrahūmkara/rdo-rje-hum-mdzad)象征意识力;除疥天女(yām ā devī/ l h amo-sngo-bsangs-ma)以善金刚(Subhadra/ rdo-rje-bzang-po)象征三摩地;普贤(Subhadrā/ shing-tubzang-po)以金刚光(Vajrabhadra/rdo-rje-vod)象征洞察力;马耳女(Hayakarnī/ rta-rna-ma),以大威德(Mahābhairava/ vjigs-byedchen-po)象征顿悟三摩地;鸟面女(Khagānanā/ bya-gdong-ma)以目无善(广目天王Vīrūpāksa/ migmi-bzang)象征顿悟要旨。
方塔所出《是钉撅咒》所录语轮神灵如下:“次语轮者红色,八辐红莲蔓绕于东辐;上葛麻录巴处具茅及护地母;北方上说坦处具发金刚及大怖母(下缺)……。”
这里护地女,金刚辫,大怖母(大威德金刚女)都严格对应。
从以上《上乐根本续》与《是钉撅咒》的对比,我们可以确认方塔残片为【43】《上乐根本续》 的内容。
与此印证的是,拜寺沟方塔的建寺年代。据孙昌盛先生拼对完整的方塔塔心木建塔题记云:【44】“白高大国大安二□(年),寅卯岁五月,□□大□□□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画佛像,至四月一日起立塔心柱……。”“白高大国”为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惠宗秉常年号。由题记我们可以确认,拜寺沟方塔建于西夏大安二年四月一日,即公元1075年!这样,我们就不能排除塔中所出有关上乐金刚等藏传佛教的仪轨文献断代在1075年之前的可能性。【45】有些经文很可能是直接从梵文译为汉文,因为塔中所出捺印金刚座触地印释迦牟尼佛和佛顶尊胜佛母周围字母都是梵文而非藏文,但两位主尊的背龛样式完全是早期印度波罗样式,与西藏早期绘画样式相同。这些捺印佛像甚至有可能是公元9世纪流向黑水城的敦煌作品,黑水城也发现了10幅单张的捺印佛画,据考是敦煌时期的作品。【46】此外,方塔题记中特意提到“缠腰塑画佛像”,说明此塔原来有塑像和壁画。
《上乐根本续》所传上乐仪轨在西夏传播的时间,目前仍然需要加以考证。因为此塔文物尚有乾祐十一年(1180)仁宗仁孝皇帝的发愿文,但方塔建塔的确凿年代是在大安二年,我们并不能排除某些经文是建塔时作为塔藏放置在塔内的可能性。然而,有关上乐根本续和大手印法的梵文经典,由仁钦桑布(958-1055)等译师译为藏文的时间也大多是在11世纪初年,难道这些经典在译为藏文以后随即被译成了西夏文;抑或西夏文的这些经典是直接译自梵文?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有关上乐根本续等等的西夏文、汉文文献与上乐金刚坛城、大手印等修习法肯定不是噶玛噶举派僧人藏巴顿库瓦1189年进入西夏王廷以后才在西夏传播开来,而是在噶玛噶举僧人入夏以前就已经盛传。方塔《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卷残片记传授此法者为国师知金刚,标明“国师”,说明他是在西夏的吐蕃僧人。从知金刚的名称我们看不出他与藏巴顿库瓦等人的关系,知金刚的名字也不见于上面提到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出现的上师名单。
陈庆英教授近年发表论文,分析了近年重刊的汉文《大乘要道密集》的相关题跋,对探索“知金刚”的身份乃至确认西夏早期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7】这些散佚皇家、传自西夏的译本,经首或经末遗有原篇原有的传法者、汇集者、翻译者的名字,其间注明的师承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藏传佛教噶举派和萨迦派在西夏早期的传播。陈庆英先生指出了不见著录的“大乘玄密国师”和“大乘玄密帝师”;我们上文检出的“知金刚”也找到了来历,在《密集》所辑83个卷子的经首,“知金刚”共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陈健民上师编《萨家道果新编》第13卷“师承等处奉集仪轨”(页162-164),其所赞的师承关系为:金刚亥母——萨干哩巴——得哩干——大师金刚手——大师巴波无生【48】——大师末则啰孤噜【49】——大师辣麻胆——大师智金刚。
第二次出现在第68卷“新译大手印金璎珞要门”(页411-418)本篇开头处记:其师承者,萨斡哩巴传与铭得哩斡师,此师传与巴彼无生师,此师传与末则啰孤噜师,此师传与玄密帝师,此师传与智金刚师,此师传与玄照国师。
篇末又记:“路赞讹辣麻光萨译西番。”
《大乘要道密集》第66卷“大手印伽陀支要门”(页406-409)的师承记载为我们了解知金刚的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本篇开头处记载:
然此要门师承次第者,真实究竟明满传与菩提勇识大宝意解脱师,此师传与萨啰喝师,此师传与萨啰巴师,此师传与哑斡诺帝,此师传与辣麻马巴,此师传与铭移辣啰悉巴,此师传与辣麻辣征,此师传与玄密帝师,此师传与大宝上师,此师传与玄照国师。【50】
后面的引文除了印度上师“萨啰喝师”(sa-ra-ha-pa)等人之外,出现了此法的西藏传承。所谓“辣麻马巴”即bla-ma mar-pa,“铭移辣啰悉巴”即米拉热巴上师mi-la-ras-pa,“辣麻辣征”即为日琼巴bla-ma ras-chungpa,“辣征”读音为ras-chung[-pa]。“辣麻辣征”之后即进入西夏传承:日琼巴传法与玄密帝师,玄密帝师传法与大宝上师(即藏文rin-chen),此师传法与玄照国师。
以此次第对照出现“智金刚”的记载,发现以上两条记载的师承缺乏若干环节。补充排列如下:玛尔巴/辣麻马巴——米拉热巴/铭移辣啰悉巴——日琼巴/辣麻辣征——玄密帝师——知金刚国师/大宝上师——玄密国师。
从上述记载分析,日琼巴生卒年为1084-1161年,日琼巴的弟子中已经有人在西夏作了帝师。弟子玄密帝师的活动年代当在大师自印度返回之后,假如是在他40岁以后,就是1130-1161年。依此可以判定西夏人是在1130年前后就和早期噶举派发生了联系,而不是在1189年噶玛噶举的僧人入夏以后。陈庆英先生判断乾祐二十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出现的“大乘玄密国师”,就是这里的玄密帝师。上文记载智金刚是玄密帝师的弟子,假如其活动年代比日琼巴传法与玄密帝师晚20年计,当在1160-1200年间。
从拜寺口方塔所出文物年代综合考虑,知金刚最晚活动于仁宗仁孝中晚期,因为塔中出土的汉文佛经《初轮功德十二偈》,其中有“身语意之三密”、“大密咒”、“明咒”、“种子”、和“相续”等字,表明此经译自藏文,经文为雕版印刷,楷体,字体清新而浑厚。【51】假如考虑到日琼巴弟子在西夏传法的事实,推算此类经典从译为夏汉文到雕版印制的时间,上乐根本续相关经文与仪轨传入西夏的时间确定在仁宗仁孝时期是没有疑问的。西夏后期,上乐金刚坛城和大手印法的修习已经滥觞,成了一种社会风俗。黑水城出土汉文《密教念诵集》有云“奉此美女大宝故,无明点暗得蠲除;胜惠悟人法界理,双证方便及智慧。”【52】《黑鞑事略》云:“徐揖尝见王霆云,某向随成吉思汗攻西夏,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侍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成吉思汗既灭夏,先裔国师,国师比丘僧也。”【53】这些记载表明西夏藏传佛教的修习由来已久。我们以为,西夏僧人娶妻之风,并非来自噶举派,西夏后期所传噶玛噶举并不提倡僧人娶妻生子,西夏此俗实际上来源于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在前弘期传入党项佛教的证据之一。
四、西夏藏传绘画的起源及其意义
研究西藏艺术的学者在论及西夏藏传风格的绘画,尤其是研究西夏唐卡时,都将其出现的时间归之于乾祐二十年西夏王室与噶玛噶举发生联系之后。通过如上描述,我们可以确认藏传佛教造像系统传入西夏的时间比噶玛噶举僧人进藏的时间要早得多。西夏佛教中涉及无上瑜伽密的内容与吐蕃佛教前宏期的旧派大圆满法不无关系。对于《上乐根本续》所传上乐仪轨在西夏传播的时间,目前仍然需要加以考证。因为宁夏拜寺口方塔出土了译自藏文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西夏文佛经共九卷;汉文《上乐根本续》中坛城仪轨经文片段,如《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藏》,经文中出现了“身语意三密”、“金刚亥母”、“阴阳二身”和“愿证大乐”等等,虽然此塔文物有乾祐十一年仁宗仁孝皇帝的发愿文,但方塔建塔的确凿年代毕竟是在大安二年(1075),某些经文可能是建塔时的塔藏。在另一方面,仁钦桑布等译师将有关上乐根本续和大手印法的梵文经典译为藏文的时间也大多是在11世纪初年。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有关上乐根本续等等的西夏文、汉文文献与上乐金刚坛城、大手印等修习法肯定不是噶玛噶举派僧人藏巴顿库瓦1189年进入西夏王廷以后才在西夏传播开来的,而是在噶玛噶举僧人入夏以前就已经盛传。如前所述,上乐根本续相关经文与仪轨传入西夏的时间应在仁宗仁孝在位早期。因为到了西夏后期,上乐金刚坛城和大手印法的修习已经滥觞,成了一种社会风俗。
虽然西夏艺术从其党项羌时期就受到了吐蕃前宏期艺术的影响,但西夏唐卡大规模的出现仍然与早期噶举派的上乐金刚坛城仪轨以及大手印法在西夏传播开来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推断西藏唐卡进入西夏的时间可能很早,但西夏人将这种艺术形式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绘画样式并能够熟练应用,则是在12世纪初叶以后。
我们之所以将西藏绘画影响党项羌和西夏的时间确定为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主要考虑到内徙之前的党项人的某些部落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吐蕃部落,早期党项部落和吐蕃人之间的地域血缘联系与党项内迁以后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质的不同。吐蕃佛教对党项的影响真正开始于吐蕃本土灭法、卫藏各派僧人进入安多以后,其间流行的是吐蕃时期佛教和早期宁玛派。在藏传佛教后弘期西夏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由于西夏统治者吸纳藏传佛教作为国家宗教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的很多教法开始在西夏传播,因而,卫藏绘画图像及其绘画风格随着一些藏传佛教支派,如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的传入西夏而在西夏再度流行开来。至公元12世纪中叶,以卫藏风格绘画作为粉本而发展起来西夏藏传绘画已经形成。
藏传绘画在西夏的传播是西藏艺术真正意义上的东传,其最初传播的时间正好跨越了藏传佛教前宏期和后宏期,填补了西藏艺术这一阶段缺乏作品例证的不足。藏传风格的这次传播在藏传绘画史乃至整个中国美术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西夏人凭借他们对藏传艺术的高度虔诚将藏传美术与汉地中原艺术水乳交融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架起西藏艺术进入中原的桥梁,拉开了元代汉藏艺术空前规模交流的序幕。
西夏藏传绘画描绘的藏传佛教图像的题材和内容拓展了藏传绘画的领域,为我们勾勒藏传佛教图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我们得以了解在15-16世纪藏传佛教图像体系形成之前一些藏传佛教神灵的当时的面貌。
西夏藏传绘画风格将汉藏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有机地融和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是西夏绘画作为一种不同于宋、辽、金绘画的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我们很难将西夏早期绘画和五代晚期的汉地风格绘画区别开来,以至于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人们并不认为存在一种西夏自己的绘画风格;西夏绘画风格形成于西夏后期,由于西夏居地位于河西走廊,它的艺术是以汉地河陇绘画风格为主体、融合多种艺术风格成分的结果,除了藏传绘画风格外,尚有回鹘风格和其他中亚风格成分。所以,分析西夏藏传绘画有助于我们探索西夏绘画风格形成的轨迹;有助于我们认识,藏传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了如何的演变。西夏人对藏传佛教和藏传绘画的认识和态度强烈地影响了蒙古人,元代藏传绘画在内地的广泛传播直接继承了西夏与吐蕃及西藏绘画风格的联系,在元代藏传绘画作品中可以找到很多西夏绘画的风格成分。元明以后汉藏艺术的大范围交流,虽然主要是政治因素,但西夏艺术的作用不可低估。
西夏藏传绘画在整个藏传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其丰富的作品遗存充实了藏传绘画早期作品的例证,为早期藏传绘画的研究提供了资料;西夏藏传图像种类的多样化填补了早期藏传佛教图像的缺乏,在藏传绘画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是西藏绘画风格最成功的对外传播形式之一。
文章注释:
【1】《宋史》称西夏为“夏国”,《辽史》、《金史》和《元史》称“西夏”,《长春真人西游记》称“河西”,《蒙古秘史》称“唐兀”,马可波罗《游记》称Tangut“唐古忒”,西文对西夏的称呼即出于此处。西夏人自称“大夏”、“大白上国”、“白上大夏国”,1038年建国(宋仁宗景祐五年),传十位皇帝: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安全——遵项——德旺——(目见),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时190年。
【2】清·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卷首,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
【3】党项羌与吐蕃正式发生联系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遣使入朝,唐太宗遣冯德遐为使下书临抚。松赞干布又听说突厥、吐谷浑“皆得尚公主”,乃遣使送币向唐朝求婚,太宗没有答应,“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这是见于汉文史籍的党项与吐蕃的最初接触。
【4】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114-131页。
【5】《宋史》卷六十四“宋琪传”。
【6】Bkav-chems-ka-khol-ma,pp.231-232:devi phyi ma ru yong stong bzav khri btshun-yin/ des brag lha mgon povi lha khang gi rmang gting ngo/ 此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藏文版仅记载木雅妃建造了神殿,没有提到勒石造像之事,此书卢亚军汉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上文字不知据何种本子而来,。
【7】黄灏《〈贤者喜筵〉译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但《柱间史》记米茫才神殿为来自李域的妃子李姜通萨尺尊所建:devi phyi ma ni li lcam mthon bzav khri btshun yin/ des lha sa mig mangs tshil gyi lha khang gi rmang bding ngo.
【8】此事见藏文史书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筵》,黄灏译注本,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 第2期。另见黄灏《藏文史书中的弥药(西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9】这些僧人名前往往冠有“木雅巴”(mi-nyag-pa)、“木雅”(mi-nya)或“咱米”(rtsa-mi)的名称,如《贤者喜筵》所记生于下多康弥药地区的高僧咱米桑杰扎巴(rtsa-mi sangs-rgyas grags-pa)是一位著名的西夏译师,也是蔡巴噶举派创始人贡唐相喇嘛依止的上师之一,在贡唐相喇嘛的传记中对这位上师有记载:生于多康木雅咱米地方,曾任印度金刚座寺(印度比哈尔的超岩寺)的堪布20年之久。其事迹还见于《青史》(郭和卿译本第44-67页,罗列赫译本第49页),很多西夏唐卡中的上师像很可能正是描绘他。另外,据《巴协》、《青史》记载,赤松德赞为弘扬佛法派遣巴塞囊和桑喜前往汉地迎请高僧,同时也请来了“木雅和尚”,他们成了赞普的上师,教授大乘密教理论。此后并形成木雅上师传承(郭和卿译《青史》,第517-518页)。Elliot Spering,“Rtsa-mi Lotsa-ba Sangs-rgyas Grags-pa and the Tangut Background to Early Mongol-Tibetan Relations”,in 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vol.2,ed.by Per Kvaerne,Oslo,1994,pp.801-824.
【10】高景茂译《木雅五贤者传》,转引自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114-131页。
【11】周辉《清波杂志》卷十“唃厮啰”:“康定二年,刘涣奉使入西羌,招纳唃厮啰族部。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涣乃落发僧衣以行。”。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乌王考》,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第684页。
【12】“彼时,佛法弘扬于多康之地,而藏地却无佛法,成为黑暗之域。”(de ltar khams na sangs rgyas kyi bstan pa dar bzhing/ bod na chos med par mun pavi smag rum du gyur na)卫藏这种没有佛法的黑暗年代,大约一百年左右:“藏王朗达玛阴铁鸡年(辛酉年,即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灭法,阴铁鸡年(辛酉年,唐昭宗光化四年,公元901年)佛教余烬复燃。或云历时六小甲子,然实际上是八小甲子。在此98年中,就是佛教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de ltar rgyal po glang dar mas lcags mo bya la chos snubs/ lcags mo bya la bstan pavi me ro langs nas/ lo skor dguvi bar du dbus gtsang na chos med do zer kyang/ nges pa can du lo skor brgyad/ lo dgu bcu go brgyad kyi bar chos kyi ming tsam yang med do/ )见《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藏文本,第240、242页。
【13】如《安多政教史》所记:“圣教在多麦地区的弘传,虽然没有前弘期与后弘期之分,但毫无疑问在前弘期时,许多智者、成就大师、法王和大臣们以公开或不公开的方式为众生作过弘法传承,这是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当朗达玛毁灭西藏地区圣教之后,在吉祥曲沃日山(chu-bo-ri)的禅院中修行的约尔堆(gyorstod)的玛班·释迦牟尼(dmar pan shvakya mu ni)、哲穹多(drad-chung-mdo)的约格迥(g-yo-dge-vbyung)、嘉热巴(rgya-rab-pa)的藏热赛(gtsang-rabgsal)三人用骡驮上律部经论,逃往上部阿里,又从那里转往葛逻禄(gar log),由此取道霍尔地区,经多麦南部白日(be-ri)的察措湖(tshva-mtsho),来到黄河峡谷的金刚岩洞、安穹南宗窟(an-chung-gan-gnam-rdzong)、丹斗寺等处修行。有一天,被黄河边的一位牧童发现了,他于晚上在人群中议论此事,宗喀地区的一位叫做穆苏萨巴尔(dmu-zu-gsal-vbar)的年轻人听见后,产生信仰,请求剃度。于是,藏任亲教师,约和玛二人任规范师,度其出家,授比丘具足戒,命名为格瓦饶萨(dge-ba-rab-gsal)。后来由于学问渊博,洞晓义理,被人们尊称为贡巴饶赛(dgongs-pa-rab-gsal)。”(吴均等汉译本,第22页)然而,更多的文献将贡巴饶赛看作是前藏彭域地方人,后移居青海化隆丹迪寺。《藏汉大辞典》介绍贡巴饶赛事迹云:“贡巴饶赛大喇嘛……生于拉萨东北之彭域,移居青海境化隆县丹迪地方。”今青海互助所存白马寺,即是大师圆寂后其弟子修建。
【14】“(贡巴饶赛)从上述亲教师和规范师即北方木雅噶的郭戎森格扎处学习律经”(吴均等汉译本《安多政教史》,第23页),这里的“木雅噶”藏文作mi nyag gha.
【15】“当恶王(朗达玛)灭法后约八十余年,桑耶小王擦那益西坚赞为施主,送弟子赴多康求戒,其首次求得戒律者,则名为卫藏七人”(rgyal po sdig can gyis chos bsnubs nas lo brgyad cu lon pa na bsam yas kyi mngav bdag/ tsha na ye shes rgyal mtshan des bdag rkyen mdzad nas khams su sdom pa len pavi thog mar/ dbus gtsang gi mi bdun du grags pa ni/ klu mes……《西藏王统记》,第242页)。又如《巴协》所记:“彼时,在多麦康区的师徒传承并没有中断的消息就传开了。吐蕃地方有信仰而且想行佛法的人便都到康区去寻求戒律。后来,有卫藏的鲁梅等12人也到康地学法。学成返回卫藏时,连同途中遇到一起回去的一人,共13人”(dus de tsa na mdo smad kyi khams na mkhan slob kyi bkav rgyud ma chad par vdug par grags/ bod dad pa can chos bya bar vdod pa kun sdom khams su len par vgro/ phyis [dbus gtsang]klu mes la sogs pa mi bcu gnyis lam nas …log pa gcig dang bcu gsum vod/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本,汉文第72页,藏文第203页)。
【16】有纪年可考的寺院如位于兴庆府东的高台寺(1047年)与承天寺(1055年)。
【17】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一书对西夏境内的寺院逐一进行了分析,将其概括为兴庆府-贺兰山中心;甘州-凉州中心;敦煌-安西中心即黑水城中心(第122-125页)。这几个中心现在都发现了藏传佛教遗迹,如东部的宏佛塔、拜寺口双塔以及出土的唐卡及木雕上乐金刚像等,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及附近的喇嘛塔内发现的两幅唐卡,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百眼窑石窟(蒙语阿尔寨石窟〕的壁画(王大方等《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西部的安西榆林窟西夏晚期藏密洞窑形式及壁画(张伯元《东千佛洞调查简记》,《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安西千佛洞第5壁窑门北侧壁画中的藏式佛像以及五个庙石窟的藏传密迹等(张宝玺《五个庙石窟壁画内容》,《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
【1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51页。
【19】参看杜建录著《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6-151页。
【20】该窟东窟壁画有宋宣和三年(1121年)游人题记,可见这些壁画是1121年以前的作品。参看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故道上的石窟》,刊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第150-151页。
【21】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第276页:(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店堂旁边就供有“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广仁禅院碑》描述河湟吐蕃云:“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乌决]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张维《陇右金石录》,转引祝启源第278页。
【2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甲申记事。
【23】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52页。
【24】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第23页。
【25】语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转引自史金波《西夏佛教的流传》,1986年第1期;参看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1993年第五辑,第46-47页。《西夏书事》亦有记载:“(元昊)遣蕃僧吉外吉法正等报谢景佑中所赐经”,事在宋庆历五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其时宋与西夏已成和议,此年元昊即先后遣使贺宋正旦及宋帝生辰,宋亦颁历于西夏。
【26】罗福颐《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文物》,1981年第4-5期,收入《西夏史论文集》,第452-458页。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1993年第五辑,第46-47页。
【27】史金波《西夏佛教的流传》,1986年第1期;参看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藏学研究论丛》1993年第五辑,第47页。
【28】乌瑞《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使用藏语的情况》,参看巴黎《亚洲杂志》1981年,第81-91页。
【29】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云:“番、汉、羌(指藏人)行童中有能晓颂经全部,则量其业行,中书大人,承旨当遣一二□(人),令如下诵经颂十一种,使依法颂之,量其行业,能颂之无障碍,则可奏为出家僧人。”参看史金波《西夏的佛教制度》载李范文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313页。
【30】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第51-63页。
【31】参看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
【32】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第114-131页。
【33】有关噶玛噶举派和西夏朝廷关系的记载,最早的是蔡巴·贡噶多吉所撰《红史》,但广为学界所知的却是噶玛噶举派僧人巴卧·祖拉陈瓦(1504-1566)撰《贤者喜筵》。书中在叙述西夏王统时记载:西夏王泰呼非常崇敬一世噶玛巴都松庆巴,曾派遣使臣入藏延请都松庆巴到西夏传法,都松庆巴未能前来,便派遣弟子格西藏索瓦来到西夏。藏索瓦被西夏王尊为上师,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佛经,极受宠信。后来都松庆巴在他所建楚布寺修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璎珞及经幢、华盖等各种饰物。都松庆巴圆寂后,在其焚尸处建造吉祥聚米塔,藏索瓦用西夏的贡物,以金铜包饰此塔。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几乎国内外涉及西藏与西夏文化关系时都要引用,并作为断代的依据。我们将这段原文引述如下并加以翻译:“对此,泰呼王说:“法王都松庆巴到了楚布寺驻锡于此,我邀请他前来,但未能成行,但您(都松庆巴)的使者,新收的一个弟子可作应供。”于是格西藏波瓦去了西夏,做了西夏王的上师。后来,西夏王又献楚布寺白登哲蚌白塔的金铜包裹和华盖等物。”(vdi la rgyal po thvi hus chos kyi rje dus gsum mkhyen pa mtshar [mtshur]phur phebs te bzhugs pa la spyan vdren btang bas ma byon/ vo na khyed rang gi sku tshab gsar pavi slob ma zhig mchos gnas su gtong bar zhus pas dge bshes gtsang po ba btang ste rgyal pos bla mar bskur/ phyis mtshur phuvi dpal ldan vbras spungs kyi mchos rten la gser zangs kyi na za dang bla res sogs bskur ba yin/)同样的记载也见于《贤者喜筵》中都松庆巴的传记部分,书中讲到,都松庆巴为藏索瓦讲法时预言,藏索瓦将成为西夏王的上师。这里所记载的西夏“泰呼王”为第五世,按西夏帝王顺序应为仁孝。仁孝在位时间为1140-1193年,与都松庆巴在世时间大体相当。“仁孝”二字的西夏文读音为“尼芍、勿”与藏文“泰呼”(the-hu)音近。可见遣使入藏迎请上师,后又贡献饰物助修佛塔等活动当在仁孝时期。后代藏文文献,对甘青多麦地区宗教史实记载尤详的《安多政教史》中也叙述了这段史实。《贤者喜筵》还记载了蔡巴噶举派喇嘛相的弟子藏巴敦库瓦等师徒七人先到蒙古地方,后转道西夏,在西夏担任翻译,讲授三宝密咒。这位上师在成吉思汗毁灭西夏并破坏西夏寺院时,曾劝说成吉思汗修复佛寺,据说这是最早见到蒙古人的藏人。这位喇嘛相还指点雅隆地方人查巴僧格到西夏地方修习,作了西夏王的上师,在西夏的果热衮木切及帕底地方弘扬佛法。东嘎仁波且编注《红史》对藏巴敦库瓦所作注释云:“藏巴敦库瓦(gtsang-pa-dung-khur-ba),又名藏巴敦库瓦旺秋扎西,他是贡唐喇嘛相(1123-1194)的弟子,最初受西夏的邀请,为西夏王的上师,并在西夏弘扬了蔡巴噶举的教法……生卒年不详。”然而,成书时间远远早于《贤者喜筵》,由噶举派支系蔡巴噶举僧人蔡巴司徒·贡噶多吉所撰《红史》(成书于1363年)在其叙述西夏王统与都松庆巴传记时却没有提到西夏王邀请都松庆巴赴西夏之事,只是在叙述蔡巴噶举教派史时记载,藏巴敦库瓦为贡唐喇嘛相的再传弟子,其所从上师为涅麦仁波且。这位藏巴敦库瓦与上面提到的格西藏索瓦和格西藏波,都是一世噶玛巴都松庆巴和蔡巴噶举派上师喇嘛相分别派往西夏的弟子。我们认为格西藏索瓦、格西藏波同为一人,《贤者喜筵》在叙述西夏王统时将这位使者写成“藏波瓦”,但在叙述都松庆巴传记时又写成“藏索瓦”;《红史》称藏巴敦库瓦等为“众格西弟子”。值得注意的是,喇嘛相出家时依止的根本上师咱米译师就是来自弥药,所以他派弟子赴西夏传法亦顺理成章。喇嘛相生卒年为1123-1194,都松庆巴生卒年1110-1193,所以,《红史》中记载的藏巴敦库瓦,其生卒年极可能与喇嘛相的生卒年相当,考虑到藏巴敦库瓦是再传弟子并曾劝说成吉思汗不要毁坏佛寺,其生活年代当在1150至1227年之间。此外,《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第三祖扎巴坚赞有一名弟子叫国师觉本者,前往米涅(西夏),作了米涅王之应供喇嘛。扎巴坚赞的生卒年为1147至1216年,他的弟子的活动年代应与藏巴敦库瓦的活动年代大致相同。可见同时前往西夏的并非只有噶玛噶举派的僧人。因而,西夏存留的藏传绘画并不能只用噶玛噶举在西夏宏法的史实加以解释。
【34】据黄灏先生所说,建于1098年的张掖大佛寺,大佛颈部刻有藏文aom的六字真言之第一字。《马可波罗行记》则说大佛寺内杂有有喇嘛像。甘肃炳灵寺石窟(1098)也发现有藏文和西夏文同时出现的咒语(参看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57页)。
【35】参看如下论文:罗昭《藏汉合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录》,《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范德康撰,陈小强、乔天碧译《拶也阿难捺:12世纪唐古忒的克什米尔国师》,《国外藏学译文集》第14集,第341-351页;邓如萍著,聂鸿音、彭玉兰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我们以为“波罗显胜”的“显胜”是藏语的rgyal-mtshan。
【36】此卷编号TK-164,经首有3幅版画。经首有口传此经者的署名:“天竺大般弥怛五明显密国师在家功德司正嚷乃将沙门拶也阿难捺 传”,这是藏汉合壁“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的国师又一次见诸文献,这位僧人活动于仁宗初年的判定是正确的。其中“天竺大般弥怛”中的“天竺”是概指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人,不一定确指印度。“大般弥怛”无疑来自梵文的“班智达”(Pandita)。此经书影参看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附录页15;整个经最后的残片上有仁宗的年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去邪淳睦懿恭皇帝”。刻印日期阙佚,但后序发愿文中说刻此番汉经的目的是纪念去世的父亲崇宗皇帝(1087-1138),孟列夫认为大概不早于崇宗去世3周年,不晚于曹皇后去世后3周年,1167年的TK-128说曹皇后已去世3周年。崇宗的称号是1141年从金得到的,这个日期是最可能的刻印日期。
【37】此经插图见于编号TK-128的卷子。后序发愿文中有刻印日期:“天盛十九年岁次丁亥五月初九日”。
【38】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997,第1卷卷首插图。
【39】参看 Heather Karmay,Early Sino-Tibetan Art,Warminster,1975,p.36,pls.16-22.
【40】Heather Karmay,Early Sino-Tibetan Art,p.36,pls.26-30.
【41】此处的“□□上师”或许是后面“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大宝上师”即藏文的rin-chen。
【4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143-147页。
【43】这幅文献梵文本收在Kazi Dawa-samdup,ed.,Shrīchakrasambhāra Tantra:A Buddhist Tantra,Calcutta:Thacker,Spink and Co.,1919;reprint,New Delhi:Aditya Prakashan,1987.Shinīchi Tsuda,The Samvarodaya-Tantra:Selected Chapters,Tokyo,The Hokuseido Press,1974。这份藏文文献的英语译文见Susan L.Huntington&John C.Huntington,The Art of Pâla India (8th-12th centuries) and Its International Legacy:Leaves From the Bodhi Tree,Seattle and London,1990,pp.535-540.Appendix II:“The Iconography of Cakrasamvara and the Deities of His Mandala”.
【44】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夏佛塔》,1995年,第53页。孙昌盛《拜寺口方塔始建年代考》,刊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9-365页。
【45】因为方塔同时发现了乾祐十一年仁宗仁孝皇帝的发愿文,由于方塔1990年被炸毁,我们不能判定现在收集到的经文是1075年修建方塔时作为塔藏放置,还是方塔寺院的收藏。
【46】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0-21页;第229-234页。
【47】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9页。
【48】这里的巴波无生师,我们检出藏文为bal-po skyes-med,参看《红史》藏文本,第80页。关于这里涉及的藏文名称,我们将另文研究。
【49】“孤噜”似为guru,即“上师”,藏文文献经常以此替代bla-ma。
【50】聂鸿音先生认为西夏人翻译藏文为西夏文遵循如下规律:意译与音译合壁或全部意译的规律,这里出现的“大宝”为意译,“辣麻”为音译,“巴波无生”(bol-po-skyes-med)则是音义合壁。
【51】《西夏佛塔》图版一O;第46-49页。
【52】《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卷,第224页。
【53】清·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清初陕西边群山中“僧人皆有家小”,认为此乃西夏所属甘、凉一带“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