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永远做一个乡土作家——鲍十访谈录
2015-07-18访问者作家在江西省文联工作
访问者:杨 玄(作家,在江西省文联工作)
受访者:鲍 十
杨玄(以下简称杨):老同学,你好!首先我想请你谈谈你这个笔名的来历。记得当年在鲁迅文学院第三期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有幸与你同桌,看到你桌上的名牌写着“鲍玉学”三字,对这个名字我感到很陌生,就没敢多问,上了几天课后才发现你是大名鼎鼎的“鲍十”。这个笔名取得很妙,既简洁又好记,签名售书也比较方便,笔划少嘛。(笑)请问你是怎样取的?
鲍十(以下简称鲍):呵呵,兄弟还记着当年的事啊!这事说来并不复杂,甚至非常简单。我的原名中不是有个“玉”吗?如果把“玉”字的上下两横,包括那个“点”,全部去掉,剩下的就是一个“十”字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点点其他的意思。你可以把其他笔划都想象成羁绊,想象成啰嗦。那么,去掉那些笔划,就是去掉了羁绊,同时也去掉了啰嗦。对吧?
杨:我明白了,这是做减法。并且我的理解是写作也应如此,对吗?不过一个人的阅历肯定是做“加法”,你这个人一眼看去就给人以阅历比较丰富的印象。
鲍:其实也谈不上多么丰富,应该跟很多人差不多吧。我是在农村出生长大的,十九岁考学才离开家乡。我老家是黑龙江省肇东市的一个村子。十九岁之前,我在老家读了小学和中学,中学毕业后又当了几年农民(是真正的农民哦)。然后国家恢复高考,因为数学成绩差,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招生,因不考数学,好歹才考上了。先读了两年中专,又读了三年专科,毕业后留在学校当了老师,期间结了婚,生了儿子,也一直在学习写小说。八年后调入《小说林》编辑部,算是进入了文学圈。后来我又在哈尔滨文学创作所做了三年专业作家。到二○○三年,先以作家的身份调到了广州市的文学创作研究所,两年后调进了《广州文艺》杂志社,直到今天。
杨:这样看来,你的前二十多年的生活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鲍:是的。回想起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在老家的那段时光。那儿有我太多的记忆了。那些对贫穷的记忆,对当年饥饿的记忆,对找不到出路时的茫然和无助的记忆,对歧视的记忆,对劳动的记忆,对亲情的记忆,对亲戚的记忆,对少年伙伴的记忆,总之,对一切丑陋和美好的记忆。这些记忆太深刻了。很多人说过,从童年到青年,正是一个人心灵发育的关键时期。当时年龄小,对很多事情都懵懵懂懂,但在长大以后,会不断地反思。

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

葵花开放的声音-鲍十小说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拜庄,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
杨:有人说作家就是以各种方式不断地重写童年记忆,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在你这里也再一次得到了印证。那么你是怎样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的呢?
鲍:那我首先要说说我读书的情况。因为读书是写作的前因,有了前因才有后果。对吧?
杨:确实如此,这也是每一个写作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你最初读的是些什么书?
鲍:大概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就开始读“闲书”了。我读的第一本书是《烈火金刚》,写抗日战争的。接着读了《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和《红旗谱》。印象最深的是读了一本《铜墙铁壁》(柳青写的),那是一本繁体字的书,竖排版,一句话里有一半的字不认识,我就一边猜一边往下读。有趣的是,这本书读完,繁体字也就基本认识了。现在回想,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之后又读过《林则徐全传》《水浒传》《岳飞传》《醒世恒言》等。还读了《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红日》《保卫延安》《苦菜花》《艳阳天》。后来还读了你父亲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剑》(笑),以及黑龙江作家林予写的《雁飞塞北》《咆哮的松花江》等。还读过一本苏联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和一本描写一个俄罗斯流浪少年的小说(书名忘记了)。还读了一些武侠和绿林小说,《三侠五义》《大八义》《响马传》等。另外还有好多,如果都写下来,会是很长的一串。
杨: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要读到这么多的书,恐怕得费一番工夫吧?
鲍:确实,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在我们那种远离文化的地方,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多喜欢读书的人。这些书都散落在乡间,大家传来传去地看。只要听说哪个村子有一本什么书,就会走几里路过去借来。由于看的人太多,很多书都残残破破的。
无疑就是这些书,开启了我最初的文学想象,也诱发了我的文学梦想。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名叫郝克楠。郝老师的家跟我家归同一个公社(现在叫乡)管辖。他后来出去当兵,在部队搞通讯报道,好像是师部(或者是军部)的通讯报道员,有一年转业了,派到我读书的中学当老师。据说因为他当时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但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郝老师的爱人也是我们的老师,教数学。郝老师教我们语文课,还是我们班的班主任。郝老师上课不像别的老师,感觉特别随便,有时候讲着讲着,就讲起了他在部队写文章的事,讲他怎样跟着部队采访,讲帮助房东大娘扫院子。有一次,他还拿来了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他写的影评,评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给我们读了。有一次,他布置了一篇作文,在讲评的时候,他不仅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了,还进行了隆重的表扬。这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那之后的某一天,他还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单独给我布置任务,叫我每周写两篇作文交他批改。我真的这么做了。每次把作文交给他,他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面对面地跟我讲,这篇作文怎么样,哪儿好哪儿不好。我要说,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大到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现在郝老师已经不在了,我后来听说,他因为心情一直不好,竟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最后患了肝癌,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非常伤心。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逻辑: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就考不上省艺校,可能也就不会有我后来的写作。
但说到写作,还是在我上了“艺校”之后。在“艺校”期间,我读到了更多的书。诸如《契诃夫短篇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海明威短篇小说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索尔仁尼琴、艾特玛托夫、沈从文、萧红、汪曾祺、废名、柔石、叶紫、施蛰存、巴金的小说,以及奥尼尔、易卜生、迪伦马特的剧本等。这样读着读着,便萌生了写作的愿望。我想很多写作的人都是这样开始的吧?
杨:我注意到,很多评论者习惯以调入广州为标志,来划分您的创作时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调入广州对你的创作确实起了较大的影响吗?
鲍:应该说,这种划分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不过就我的写作情况来说,在这前后,也确实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但不是很大。最突出的一点,可能是我对文学的理解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当然这与年龄的增长也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肯定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可能会相对深入一些,一岁年龄一岁人嘛!我早期的作品,也就是广州之前的作品,似乎要相对单纯一点儿、诗意一点儿,但在主题的开掘上,还是相对简单的,也可说是浅显的,总之就是在我们都知道的很狭窄的范围里转圈圈(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出息的)。这几年,也就是来到广州之后,我的作品可能变得驳杂了一点儿,也粗砺了一点儿,也尖锐了一点儿。但仅仅是一点儿而已。二○一二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冼阿芳的事》。浙江作家钟求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评价这篇小说时说:“在《冼阿芳的事》中,鲍十推开叙事技术,平白耐心地讲述了一个城郊女人的劳碌一生。生活的逼迫和身心的辛苦在这个女人身上一一呈现出来。显然,鲍十想在现代都市中找出被奢华掩盖着的真实东西。”这正是我想做的。我意识到,小说,可能永远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是赞美诗,不是娱乐工具,不是宣传品。好的小说,应该而且必须是直面生活本质的,直面人的精神世界。有读者说,我现在的写作中有“去小说化”的倾向。我个人的感觉,现在很多的小说可能太“小说”了,这样反倒丧失了小说的本质。由于我本人也做编辑的缘故,会看到大量的小说来稿,时间久了,便发现了太多相似的东西,故事、情节、人物、主题,包括叙述方式,都多有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浮在生活的面上,缺少独立思考,也缺少独特的细节,顾自在那儿编来编去。有人说中国文学“伪”风很盛,这种伪,恐怕一时难以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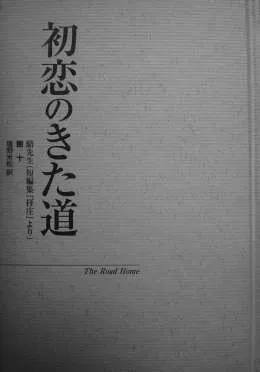
初恋之路,日文版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2000年

道路母亲·樱桃,日文版日本东方出版社2008年

痴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

我的父亲母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好运之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我的父亲母亲作家出版社2007年
不好意思,话说远了。
杨:(笑)把话说远点正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们干脆再说远点——你的作品对外翻译出版似乎主要是在日本,为何日本文坛对您的作品特别感兴趣呢?这里面有什么机缘?
鲍:最近几年,我有几篇小说被译成了日文,出了两本单行本的书,还有几篇单篇的,发表在杂志上。第一本书是《纪念》,译者叫盐野米松,我后来知道,他也是位作家。翻译时,他给作品改了个名字,叫《初恋之路》。他们翻译《纪念》,显然跟那个电影有关,这是借了那个电影的光。出版那本书的出版社叫“讲谈社”,据说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第二本书叫《道路母亲·樱桃》,译者叫三好理英子,但具体情况不清楚。这本书也与电影有关系,那部电影叫《樱桃》,苗圃主演的,是中日合拍片,曾经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后来还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再就是几篇单篇的作品了,都发表在日本一本刊物上。这几篇作品都是一个人翻译的。译者名叫関口美幸,是一位大学教授,好像在中国留过学。她是通过中国语言大学的一位教授联系的我。值得一提的是,译者还把我的一篇小说改编成了话剧。那篇小说叫《葵花开放的声音》,写的是一个养老院里发生的故事,其中写到了一位独身的老教师。小说里留有大量的空白,她在改编时填补了那些空白。我看了她寄给我的演出的光碟,感觉还是颇有匠心的。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杨:关于你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想必你已经被访问过无数次了。但你很谦虚低调,我在鲁院时就意识到你不大愿意提到这部令你成名的电影以及小说原作。但在访谈中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这件事,因为读者想必会对这方面的情况感兴趣的。
鲍: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谈吗?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谈的。不过,既然你问到了,我倒是想谈一点儿其他的事情。第一,现在张艺谋饱受诟病。他的私生活,他的作品,几乎都处在风口浪尖上,不断地被人指责。对他的私生活,我不想说什么。但在其他方面,情况可能要相对复杂一些。我个人觉得,那些对他的指责,大多是裁判式的,可能缺少了一些理性的分析。有人说这当中可能掺杂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些非艺术的因素。我有一个感觉:好像他这些年怎么做都不对,做什么都是错的。就拿《归来》来说吧,一个那么敏感的题材,非常难以把握,很多人可能连碰都不敢碰,而且感动了那么多的人,却还有人说是烂片,这就明显过分了,起码是缺少了一种“设身处地”的态度。第二,张艺谋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这应该是大家所公认的吧。统观张艺谋目前所有的作品,可能谁也无法否认他取得的艺术成就。这一点,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第三,我所接触到的张艺谋,其实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说话做事都很实在,跟人接触也没有虚头巴脑那一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任何大话和狂话,从来不讲是非,谈论具体的事情时坦诚而审慎。日常生活也十分简单,大概出于健康的考虑吧,吃东西很节制。在我们合作期间,没见他喝过酒,也没吸过烟。做事情却特别地认真,认真到了痴狂的程度,谈剧本的时候,会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不满意绝不放过。总之我觉得,看一个人一定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不要过于片面,也不要求全责备。
杨:好的,我多少还是在这个话题上挖出了一点东西,也算可以交差了。(笑)那么,顺着这个话题说开去,大多数“触电”的作家都很难从影视回归小说,这是困扰小说家的一个普遍问题。而您的小说创作似乎并没有受到影视创作的负面影响,请问您有什么“免疫”的秘诀?
鲍: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太好说,我看我只能讲一些具体的情况,这样也许可以侧面回答这个问题。在《我的父亲母亲》之前,我一直在写小说,也发表了一些,可都没有什么反响。所以《我的父亲母亲》出来后,我心里还是高兴的,毕竟有人赏识了我的作品嘛!但是有一点,我写那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想过改编电影的事情(之后的写作也没有这样想过)。而且,我始终认为,那只是一个偶发事件(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还算是清醒的)。不过在那之后,也确实有很多影视公司来找我写电影和电视剧,我多数都没接。这些年,我只接了一个旅日华侨导演张加贝的两个电影,一个叫《樱桃》,已经公映了,另一个是跟一个日本人合写的,拍完了但还没有上映。后来有人要把《樱桃》改编成电视剧,找我写剧本,我没有接,推荐了我在艺校的一位师兄做编剧。电视剧几年前就播出了,据说反响还不错。我没能在影视剧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主要还是我的主观原因。一个是我知道写影视剧本太麻烦了,要没完没了地改,非常没意思。另外就是我实在放不下小说,是从骨子里放不下。这个我一说你就理解了。除此还有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我写电影都是被动的,都是对方找的我,我还从没主动去找过对方。在写电影这件事上,我的想法一直是明确的,就是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票友,偶尔尝试一下(另外可以多得一些稿酬,呵呵)。好在电影篇幅不大,很容易脱身。

樱桃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

扮演者手记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
杨: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文学,回到小说。《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可以说是你创作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已历时十五年,并且还在不断创作新作品,这次《星火》发表的《刘贵》就是这个系列里最新的一篇。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讨论这套系列小说似乎是很困难的,不过我还是想请你系统地介绍一下这套作品的缘起、创作过程和想法。
鲍:好的。说实话,我个人确实很看重这组作品,写作的时候也很用心。但从整体上看,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有些篇目还过得去,有些则不是很好。这不好,包括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一些局限。因为这些作品是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一边写一边零散地发表,时间跨度较大。早期的一些想法,还不是很深入。我在前边说过,我们的一些想法,肯定是逐渐成熟起来的,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不断地思考。这组作品最早写于一九九九年,当时《我的父亲母亲》刚刚上映没多久,那边的杂事一处理完,我就去了呼兰县(现在是哈尔滨市呼兰区),请一位朋友帮忙,联系了一个乡政府,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没事儿就四处闲逛,找人聊天。后来我返回了哈尔滨,开始写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作品。我最初的想法,是想通过这样一些系列作品,以具象的、散点透视的方式,来反映东北乡村的社会风貌,包括民风民俗、人情世故,以及历史沿革、文化现象、政治风云等等,让那些即使没有来过东北的人,也能通过这些作品,对东北的乡村社会有个大体的了解。与此同时,我还查阅了一些史料,包括县志和一些民间轶事等,其中的一些故事,就是这么来的。有些故事也来自我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和印象。我自信这一定是有价值的,也许还会有文学之外的价值。
这些作品在刊物上发表时,标题是《东北平原写生集》,一般两篇一组,结集出版时才改成了《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在这些作品里,我着重强调了“写生”这个概念,而强调“写生”,其实是为了强调作品的写实感。但写实感并不等于写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要说的是,我写的那些故事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即便有原型,我也做了相应的处理。确切一点儿说,那些故事更可能是半真半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或者是似非而是的。这样效果或许更好,会给作品留下更大的空间。评论家徐肖楠教授曾经为我这些作品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理论刊物《南方文坛》上。针对这些作品,他提出了几个概念。第一个,他说我这些小说写了一些中国角落里的事情,我觉得“角落”是一个很有内涵的提法。第二个,他说我这些小说有通过对民间记忆的重述来反抗遗忘的意义,他认为,按照人类的本性,人们的遗忘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性的遗忘,一种是主动性的遗忘,而主动性的遗忘多半是带有选择性的。第三个,他对我这个系列小说有一个定义,将其称为“传说化小说”。读过这些小说,你可能真的会产生传说的感觉,那是历史的传说,也是现实的传说。而我所做的,则是把传说写成了现实,把现实写成了传说。
杨:你给人的整体印象无疑是一个乡土文学作家,但我注意到您也有一个描写城市的小说系列:广州风情系列。一位习惯于乡土写作的作家掉转笔触来写城市,定然别有一番风味。
鲍:你说的没错,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个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我确实痴迷于乡土文学的写作。原因很简单,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对乡村的事物有深刻的记忆,也有深厚的感情。以后,我还会继续写作乡土题材的作品。拿《东北平原写生集》来说吧,其实还没写完,我还会接着写一些。去年夏天在杭州跟钟求是见面,我们还聊起了这件事,他也认为应该接着写。作为一个作家,一辈子做成这一件事,也算不错了。我很愿意永远做一个乡土作家。
当然,我以前也并不是只写乡土小说,也写了一些城市小知识分子,就是类似我这种身份的人。我写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情感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所产生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挣扎、堕落、逃避,等等。这也是我本人曾经经历和面对过的问题。我还是秉承了我一贯的创作理念,写我熟悉的生活,写我能写的作品,写我想写的作品。
有关以广州为背景的小说,我也写过几篇。我觉得你这个“广州风情系列”的说法非常好,可说给我指出了一个方向。所以说作家之间偶尔还是要交流,交流一定有碰撞,也一定有启发。我在广州十一年了,我希望把根扎得再深些,我内心不想做一个浮光掠影的过客。有关广州的小说我也会继续写,但是不会特别刻意,也不会急躁(没什么可急躁的),我会去慢慢碰,有感觉的时候就写一篇,这可能还要靠运气。不过,有一点我是自信的,我一定会找到我自己的角度,跟别人的不一样。
杨:相较于某些当红小说家的自我膨胀,你更多的是一个低调、隐忍的写作者,总是埋头写作,很少自我表白,更不会“指点江山”。但你其实拥有一个较为成型的文学思想体系,我打算“迫使”你作一个文学理念上的自我表白,您看如何?
鲍:好的,那我就试着“表白”一下。但要说我拥有了一个“较为成型的文学思想体系”,那是说大了。你说我没有自我膨胀,那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膨胀的资本。老实说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作品写得不够好,觉得最好的作品还没写出来,总觉得下一篇作品可能会好一点儿,觉得偶尔有一篇作品获得一点儿好评是偶然现象。况且,即便你自己四处去说自己的好,或者请几个朋友帮你说好,包括开几个研讨会,吹捧一番,实际都是不算数的。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毕竟是学过文学史的人嘛。说起文学理念,我只能讲一些我对文学的感悟。我觉得,作家首先要有良知,最好不写违心的作品,不是为了利益和好处去写作。其次,作家还是要有一点儿责任感,这个责任,是大责任,是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是对正义的责任。第三,作家要保持独立思考,不受其他人或其他想法的干扰。第四,作家要有信念,包括政治信念。没有以上几点,不论你写了多少作品,最后一定是不成的,文学,绝不是个技术活。
最后,衷心感谢贵刊刊载我的作品,感谢你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