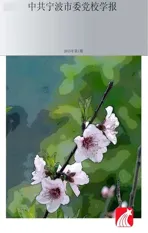展露解释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境域:重申对象性的活动原则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释义
2015-01-30张文喜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展露解释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境域:重申对象性的活动原则
——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释义
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直引发不少的热议。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是在《手稿》中表现出他的哲学独创性的,在那里,他背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规定,并且反对它们想象中的存在论—知识论的王国,直接为对象性的活动的存在意义获得释义学处境和方法论特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论;对象性的活动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方法一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这部书是有名的难读,难度甚至还要超过《资本论》。用阿尔都塞的话说:“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青年马克思实际上“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然后是费尔巴哈派”。因此,“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当然,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难读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根据这种观点,《手稿》也难读。像国内著名的康德、黑格尔专家研究一辈子康德、黑格尔,他们大多也只能“掠影”、“解读”或“释义”一下,很难将一个完整的康德、黑格尔从一个人脑子中完全传送给另一个人。但是,像阿尔都塞这样一个执迷于“认识论断裂”的批评家,这个关于马克思的评论显然不怎么可靠:为了玩味《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确实不需要成为黑格尔派成员,或者说,但另一个事实同样成立,即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克思确实不需要成为人道主义者。
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手稿》的读法,想必有跟别的经典著作有所不同的读法,而关于这些读法,版本也是五花八门。举其要者,大概有这么几种读法。
一是,要一句一句理解、解释一遍,马克思这本书究竟有什么样专门属于它的财富,一句一句给弄弄清楚,用邓晓芒的说法,就是“句读”。到目前为止,对《手稿》进行句读的作品,我还未曾见过。这种读法的好处在于,不会漏掉你不懂的地方,一字一句读,只要有时间,总是能够搞懂这150多页中文书的,但是我自己感觉这种一字一句的“句读”沉闷无趣,似乎没有什么目标。既不关心精神内涵,也不思虑启迪心智,只是每读一句话与精神错乱地每三秒钟嗅一下鞋油相类似,或者乐于拘泥于细节。不支持这种读法的一个坚强理由是,你很难知道马克思在写《手稿》时的“初始经验”是什么,因此也很难知道你是否在自己的脑子中正确地重新建构了它。你所拥有的是大量读者对此著作的“读法或体验”,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面临这样的危险: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个《手稿》。现今的解释学承认,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像马克思那样哲学家的“初始经验”,因此“初始经验”不过就是不同读者对它的阅读的经验总和。
二是,挑出一些难点、重点,做一些句读的功夫,相对地采取大而化之的方式,因而在时间的运筹中,可以加入一些我们的思考,我们把此种读书法看作是一种集体创作,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容易分散马克思究竟是如何考虑他的主题的——比如说,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非常有力的,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虽然反对那种搞一个框架,并在同一个框架里,不断地去装别的东西,这个框架还是这个框架,它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他的《精神现象学》用得正是上帝创造世界这样一种基督教的框架,去篡改黑格尔自己写《精神现象学》的初衷。也就是说,对黑格尔来说,我们看到的绿色的树、红色的花,阳光、空气,一个运动操场有多少米,一个高个子有多少高等等,所有这些规定的东西都是逻各斯自己一步步发展演变出来的,黑格尔最开始并没有用一个逻各斯的框架去把这些东西装进去,但黑格尔为什么基本上不提这是他自己的看法。在《精神现象学》中为什么很少提人的名字,无论是国家、人名还是事件?黑格尔夸夸其谈要把理性绝对化,又以最堂皇的理由解释他的逻辑学碰巧跟上帝神交——这样的借口只有他自己才会相信。马克思揭示出,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结构只是在他的主观精神里,黑格尔就是从主观精神建立起客观精神、客观理性的。马克思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表面上的诞生地是《逻辑学》,即神学。马克思其实已经说得很客气了。如果黑格尔——你就是从你自己、你的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的历史进程出发,你搞出一套体系,你却说它是世界的结构,这跟占星术无疑差不多,而你又要让所有人都相信,那么你凭什么要求人家相信?《逻辑学》中有一种怪异的自我陶醉,在它看来,对我们自己(自我)的所有说明都间接地说明了世界。这是一个错误。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黑格尔究竟有多相信自己小心翼翼培育出的谬论,或者甚至无法理解这儿所说的“相信”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方面,他说无中生有,从虚无中产生出存在,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最开始有一个存在,你也可以说每一次穿越中关村大街对你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每一次穿越没有被车撞,是上帝存在;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是逻辑学里面的存在范畴、存在概念,有、是,这样一个概念,就像传说中的小妖精,它虽然还什么都不是,却会不停地变化,一步步地搞出花样翻新的事物来。所以,马克思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暗中包含着唯心主义所发挥了的人的能动性的主体性。黑格尔的例子表明,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对世界的关注,实际上却是对关于世界的意识的关注,是对主体的关注;至于,黑格尔是否真的相信上帝,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信仰是否在他的理论体系里实现了某些事。所以,马克思读《精神现象学》就是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要求主观精神和客观基础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为我们解读他的《手稿》提供了范例。
三是,介绍国内外学者讲人生、讲百家讲坛式的方式。这种方式认为,思想是一种“心境指示”,也许在此种观点中,人们可以心满意足地避免原因、本质、本体、属性、偶然等等这些形而上学的范畴。也许对中国学者而言,重要的是话语的力量或“姿态”,是像《手稿》中明确的要旨,而不是其光秃秃的逻辑结构。但是,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你今天读到《手稿》,但是别人说,有一本书比方说《存在与时间》你还没有读过,所以你的观点还成立不起来,但是我究竟读了哪些书才算成立了呢?这都是偶然的情况,你的经验只不过是某些书的经验,就好像你估计自己会胃疼的时候就真的胃疼了。如果要尽可能避免这种偶然性,就要依靠逻辑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任何理论都是僵化固执的敌人。要坚持你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是训导出来的思考。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从普通常识的立场看,我们在读《手稿》的时候,每一句话你都要凭着更好地鉴赏复杂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每一句话你都几乎不能当有一个固定的意义,你不要把它教条化了。其实,就话语来说,马克思的话你也不能死磕,你死磕了,那你可能就跑偏了。否则,除了简单重复之外,你就很难知道如何描述话语背后的心灵活动。很显然,《手稿》这儿的说法是由张力和极性组成的。换句话说,如果引用马克思的说法,认为纸面上的词句的发言权是有限的,那么这能够将我们隔离在意识形态最邪恶的可能性之外。
四是,一个成功的解读就在于产生一个成功的交流行为——比如说,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要理解上帝就是逻辑,至于黑格尔凭什么能够站在上帝的立场、神的立场来宣称“绝对理性”,就在于他讲的“理性”是“无人身的”(马克思语)。上个星期五,上帝没有迫使我打扮成一个教师的样子,也没有迫使我叫自己张文喜;但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知道,我会,我也能在脑海里很好地搭建起他的宇宙构架,同时,有上星期五张文喜的一些事情。在今天,它就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形式出现的文化理论中,仍然流行着这种使身体客观化的谈论,仿佛这不是“我”自己的身体。不过,人类的身体确实还是一个物质客体,它是我们实现所有历史创造的前提要素。身体使我容易受到剥削或歧视,同时它也是所有增进人类关系互动的可能性的基础。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问题在于,黑格尔由于某种异化感将所有的客观化等同起来。像这些问题都需要塞进解读《手稿》当中来讨论。有人认为,课堂讨论的环节,这么多学生讲得总有比老师讲得有见地的地方。可是即使如此,很多人还是会认为,老师是一个心灵上的集权主义者,有时也是一个垃圾处理员。课堂讨论尽管有意思,但通过课堂讨论获得真理同样也仅仅是一种保证。你不要当真,你不要以为“我”说的就是真理了,就像你认为你说的就是真理了。我保证我说的是对的,但这还是仅仅是保证,我们还得走着瞧。尽管我和你都在阅读《手稿》,但是我们的阅读目标也都是在于“对话”,从中受益。
五是,说从作家本人的哲学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方式。因而需要在解读中加入许多材料。如此等等。我们觉得,经典著作究竟要怎么样读的问题常常被提及,但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满意的解决。我们不妨承认,对于解读《手稿》的基本需要,提及的这种那种读法都行之有效,因为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了人类对精神财富可能占有的方式,以及无论这种那种读法是多么有所欠缺,它们都可能各得其所。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二、依对象性活动原则解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结构
大体说来,《手稿》的论述比较繁复,加之它本身并没有最后完成,对一个不是精通经济学哲学的人来说,要把其中主要论点提纲挈领地叙述出来,未免有些困难。但是《手稿》的内容还是非常明确和集中的。它的主线是贯彻“对象性活动”的原则,而这种贯彻如同百川归海那样,指向存在论问题的优先地位。无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心服口服地承认《手稿》它是一部开启存在论新的境域的作品。此外,我们应该对《手稿》几部分内容有很好的理解。我把我在上述讲述中所要指出的总问题概括为:劳动问题。大体上讲,马克思尝试从两个角度展示异化劳动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历史道路。指明,劳动究竟为什么是人在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的自我异化。我们可以很适宜地分出三个分问题,这三个分问题决定了《手稿》的根本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的本质的哲学规定,异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再没有像异化劳动存在的共产主义学说。这一点是明摆的。
第一,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问题的时代”之中问题感很强的著作。每一个翻阅它的每一页文字中,读者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资本主宰的社会从根上就有毛病。可以很确定地说,这里,只有当你问“哪一条根?”时,你才开始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立场。大家知道,在写作《手稿》之前,马克思打算写一部法哲学著作。原本像康德的《法学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那样搞出一部他自己的“法的形而上学”著作。他自己的设想是,在法哲学的第一部分的“法的形而上学”中,搞出一套类似于费希特那样脱离法的实际的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等等,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也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它的起源在柏拉图主义,它最充分的表达则是在现代技术的本质中。在现实面前,马克思深刻感到不能沦落到与费希特为伍的地步,他隐隐感到没有深入经济学领域,他根本不可能把青年时期的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贯彻到法哲学研究当中,他所做的至多是在模仿脱离实际的费希特的那一套而已。
显然,说这些话的并不是我们,而是马克思自己。在他几个月之前动笔,之后又放弃写作法哲学巨著。他会告诉我们,作为费希特《知识学》的“自我”唤醒如法国革命般的实现变革的行动是无稽之谈,因为变革从未发生过。目前马克思自己的任务是打败先验主义。他认为,一个天赋过人的作家,不应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以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马克思在思想魅力方面之所以更加迷人,是因为现实感的影响势必会扩大。1843年12月,海因里希·海涅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他被马克思迷住了,他也像1841年时的莫泽斯·赫斯那样成为马克思的“粉丝”。赫斯这样说:“马克思博士,我的偶像就叫这个名字,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男子……他将最尖刻的幽默与最深刻哲学的严肃联系在一起;”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这些头脑加在一块,这就是马克思。弗·科本在1841年给23岁马克思的信中,更把马克思描述为“思想的仓库和制造厂”或“思想的牛首。”这些赞扬都表明马克思不仅仅博览群书,每年读的书若一页一页铺开,我估计能够铺几里地。而且,马克思是对当时欧洲人的精神危机特别有感觉的人。
对一般人来说,年轻的马克思只不过抓住康德、费希特哲学这个或那个的软肋,揭露它,把它拖拽到理性的光天化日之下,送到哲学史的审判庭,一切就万事大吉了,这毕竟就是一般人理解。这也是错觉。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新问题,它不是在西方形而上学内部提出,而是针对这个形而上学本身。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幻想过仅靠割掉小脓包就能根治西方精神毛病。而且,正如马克思本人的行动所表明,他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写满三百印张的法哲学巨著“处决”了。后来,为了寻找思想的出路,马克思又把自己投身到文学艺术之中,马克思也创作了不少作品,但同样当他发现作家的文学人格同其个人性格非常矛盾时,他就果断地烧掉了自己的诗歌和小说文稿。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烦恼,以及搞法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困难,都促使马克思回心转意“渴望专攻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也许可以说,从1841年3月完成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到1844年春夏完成的《手稿》,马克思的思想似乎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从许多方面看,《手稿》回归到了最初的风格和哲学理想。但是,这已经完全不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那一套了。任何人只要认真阅读过《手稿》都会有这种感觉。
第二,就“存在论”一词所蕴含的一般意义来看,马克思也并不是传统西方存在论的拥趸。不过,他的立场却需要好好界定一番。不管马克思会被认为是哪一类哲学家,他都不能算是为了拯救什么“绝对知识”而写作的人。他不是心里似乎已经知道“存在是什么”,又头头是道热衷于讨论“某某东西是否存在?”“我们如何证明它们的客观存在?”的痴人,更不会简单地认为如果对一些哲学内部的规章制度加以改进和纠正,再废除一些“是否有身体存在”之类的反常问题,哲学世界就会变得完美无缺的真理福地。
在这里,有必要把他跟德国古典哲学家做一点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对我们今天学习《手稿》来说很重要,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相通。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来说,按照马克思,这些人里面,算黑格尔哲学最集大成。就是认为“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并且把自己的哲学描述成这种哲学。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所做的事情。”随着黑格尔的出现,哲学的传统也就因此走到头了。就像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最明确地宣布的那样,在哲学讨论的,正是一种哲学的终结。黑格尔说:“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而因为每个参加豪饮者离开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原来真理就是酗酒后的踉踉跄跄,在真理的酒席上,大家都酩酊大醉,都互相渗透,不分彼此,不论什么身份,也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医生、保险公司推销员、公务员、歌剧男高音,大家既然来了,就得一醉方休,大家融化在一种一团和气的气氛中。一旦每一个人一离开酒席,真理就没有了。大家都参与的时候才是真理,这个整体就是最后的真理。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在大家清醒的时候,就要分出彼此,谁是主宾,谁是陪同。所以,当时德国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闲适的社交聚会,在柏林,俱乐部、协会、聚餐和小型舞会,突然冒了出来。黑格尔也时不时参与这类活动。但是,聚会本身牵涉到主体相互之间确认,他们想确认自己站在坚实的地面上。这种大家不分彼此的酩酊大醉,能在黑格尔的课堂上很好地显现,所以,各色人等,都蜂拥而至,聆听黑格尔的讲演。尽管大家不一定听懂黑格尔的思想,但黑格尔给人一种能够领会一切的感觉,而且也许他真的起到了改变舆论的作用。不过,现有与应有的矛盾,让马克思看透现有哲学的形式下那些不可能得到改变的现实,这是黑格尔望尘莫及的。
1840年代的马克思做的最根本性的大事便是从黑格尔那里解放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存在论原理就得改写为:存在决定意识。但什么是这个——存在?我们知道,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条路线是按照对“人”的“精神世界”、“理性世界”的理解一路走来的。其突出的特点是,自我意识地表达存在。具体地说,“人”已经将自己的“自然”方面“搁置”起来了。这是一个理解意识决定存在这一原理的前提。当人将自己的“自然”方面暂时“搁置”起来再来看“精神世界”,或作为“理性”的“人”,它的“世界”和“能动性”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重要性的问题不再是吃喝住穿这些物质生活问题,毋宁说这些方面不重要,才可以理解人将自己的“自然”方面搁置起来,才可以理解历史和自然之生命过程的能动性,只有人们以自我的方式思考真理整体才能领会,才可以理解人之为了理想而“杀身成仁”的问题。
但问题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丝毫不具有革命性。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希望推翻现有秩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相信如果推翻现有秩序的话,社会将发生重大转变。实际上,他们的哲学目标根本不是社会,而是所谓“人性”。很难在他们的书里找出哪一段来清楚表明,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是错误的。例如,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说法,不过是说人在他的环境中很少找到直接对他有用的原料。他唯一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以这样的基础形成的经济体系,就像星球体系形成一样,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政治经济学,黑格尔把它叫做“国家经济学”,这种叫法就已经告诉我们,黑格尔不可能对私有财产制度发表攻击性言论。黑格尔还说:“文化的开端”,就是“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来,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来说:存在并非其他,根本就是自由之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有一些共同点。最突出的一点是,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也把劳动和资本的结合看成人间天堂。黑格尔比国民经济学家更加深刻。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给资本主义世界原理涂抹上了几丝圣辉,几丝能够足以赢得国民经济学家满腔同情的圣辉。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加强调劳动的积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懂得黑格尔哲学才能理解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和出发点。原因也是因为,黑格尔哲学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示哲学方面的支持。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为你自己在读黑格尔著作时得出与马克思相近的这个结论,而且你确实可以从黑格尔哲学的全部作品中得出他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确有些替资本主义世界说话的意味。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作此结论。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有立场的话,这立场则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因为它的道德训诫就是,劳动是有积极意义的,工人应该劳动,而不是说工人应该反叛资本家。读者能从马克思《手稿》中吸取的黑格尔的社会批评也就是这些了。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看,《手稿》中不断出现的是“忌妒心”、“贪财欲”、“工业的太监”、“诱骗”、“堕落”、“腐化”这样一些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词汇,这些词汇像一根丝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可以看见,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天拿着金钱送人的“有钱的好人”是不敢想像的。从亚当·斯密开始,对乐善好施的现象就排除在经济领域而转移到伦理领域。而马克思则不会认为个人的仁慈能够成为包治社会病的良药。这个变化意义重大。它是触及到存在论的真正的问题。因此,什么是这个——存在?在马克思那里,这个——存在,决不是搁置自然“精神—自由”的问题,这个——存在,是与自然进行物质代谢的人,这是劳动着的并通过劳动而社会化的人,人在劳动中表明他的本质力量,创造自身和社会。
第三,“对象性的活动”提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根基。在《手稿》有“对象性的活动”这一提法。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基本存在论概念使用如下这样一些词汇:“人”、“对象性”、“感性活动”、“感性意识”、“异化”、“劳动”、“实践”、“自然”、“历史”、“社会”。这些概念只是《手稿》的一部分词汇而已。它们会把人们直接送入德国古典哲学的境界当中。没有这些旧词汇,传统这部机器就转不动。比如,费尔巴哈常常用“感性”概念。它是与“理性”相对立的。也就是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互对立。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感性直接提示着实在性。也就是说,实在性就是感性。费尔巴哈的第一原则就是“感性”原则。譬如,他称呼身体的感官为“绝对的器官”,“人与人——‘我’和‘你’的统一是上帝。”
所以,要对马克思的“对象性的活动”这一提法作出说明常常是同德国古典哲学联系起来,其要旨在于质疑作为自我意识的活动和主体的起源。在这么一种关联中,在马克思之前,所谓“活动”充其量只是理性的目的论的一个主题,一个哲学和内在性问题的主题。黑格尔说,自笛卡尔开始,“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按照这个内在性原则,思维,独立的思维,最内在的东西,最纯粹的内在顶峰,就是现在自觉地提出的这种内在性。”或者说在传统哲学中,首先要确立一个主体,它是一个对象性的、固定的基础。然后,这个固定的主体现在变成进行认知的自我本身,是各种宾词或范畴的联结活动。而在马克思那里,人们再也无法从此种“活动”中取得什么?而之所以无法,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家给出了结论,但是尚未澄清前提。他们的结论是,“一切都处在运动中,活动着。”费希特会说:“我们想到这点,但更多的是:我们在自身的活力中感觉这点。世界以一种行动开始,要是我们说出自我,一种行动也开始。”“我创造作为我的自我。因而我是”。不过,这种创造是如何进行的?我们简单用黑格尔的两句话来讲: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的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句话。只不过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一切符合道理的事情都会成为现实的;另一方面,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从道理上去理解它,它的存在,是有一定理由的,并不仅仅是为现存事物“辩护”的意思。
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尔滕施泰因以这样的话对黑格尔表示祝贺:“您赋予……哲学……对于现实的惟一正确的立场,您肯定会成功,保护您的听众不受有害的自负的损伤,这种自负鄙弃未被认知的现存事物,尤其在涉及国家方面,它喜欢以任意提出内容空虚的理念来卖弄自己。”这样的主体是一个现实的创立活动的概念。它成了最重要的哲学主题。
事情会愈来愈清楚,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来说,谁要想成为一个哲学家,谁就要了解构成知识的科学体系。近代以来,哲学特别着重探讨自我意识的精神是什么,作为认知它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也就是关于它自己的存在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以降,存在是什么?一直到近代,哲学主要探讨是存在论,存在论是一种知识。自我意识的精神特别继承了这样一个存在论的话题。弗·施莱格尔甚至把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法国大革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相提并论,称之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三大成就。
我们一定知道马克思在哲学中所做的革新,以及对传统哲学知识论所持的批判态度。马克思无疑不会在知识论或自我意识或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概念的意义上建立和发展他自己的对象性活动的哲学学说;与现实的创立活动相比,康德的“纯粹活动”、费希特的“活动本身”、谢林的“无限活动”和黑格尔的“自我活动”在哲学事业上添加的不仅仅是一种危险,而且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马克思认为,这些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情况也的确是这样的。举例来说,在耶拿有一个关于费希特“有活力的自我”的传说:费希特如何在学校的课堂上要求学生,目视对面的墙壁,同学们,请思考墙壁,费希特说,然后请思考自身,作为与墙壁相异者。“人们嘲笑地为那些有抱负的大学生感到惋惜,什么也发觉不了,因为他们想不起本己之我。但是,费希特想以他的墙壁例子,让通常的意识从它那自我的僵化和自我的物化中得到解脱,因为,他习惯于这么说,人更容易受到诱导,自视为月亮上的一块熔岩,而非一个活生生的自我。”费希特认为,不对!主体,那个活动的进行辨识的自我,是建立基础的事物。不存在任何超越这个自我之绝对论的事物,但一切都要进入这个绝对论。席勒和歌德针对费希特开起玩笑。费希特和大学生组织发生了一次争执,大学生半夜砸他的窗户,歌德给他的大臣同事写道:“您见到了这个绝对的自我身处巨大的窘境,东西当然从那些被人设定的非我那里,极不礼貌地穿越了玻璃。”在后来歌德给霍芬的一封信里称费希特是“康德之后本世纪最伟大的思辨性哲人:世界对他仅仅是个球。自我将它扔出,又在反思时将它重新接住。”
另外,说到对象性原则应当提到一个人,这就是费尔巴哈。1839年时的费尔巴哈在其《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写道,人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必须也在哲学中肯定为思维的基础。过了两年,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主张,上帝观念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形态,因而作为人关于自己的真实的自我的表象投射在虚构的天国的结果。这些说法依然很有说服力。但是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这个观念有过度依赖,这纯粹是学院化或公式化了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想像。恰恰相反,马克思只有无情地讥讽费尔巴哈用感性的整体来克服黑格尔的纯粹思维,才能真正创立“对象性活动”原则。不管怎么说,马克思都是以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发言人的身份来提出这一原则的。
三、结语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仅跟我们这个时代相通,而且像黑格尔这样的偶像级哲学家,很好地扮演了时代的儿子的角色。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表现为满足于巩固历来的定在和表象,我们不知疲倦地倡导已经被定住了的那样一些存在方式比方说尊重科学、尊重传统道德观念,这是属于去“接受”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更注重去创新、去“给予”,去给科学知识立下法规。所以这本书也被一个概念所支配,即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某些原始的虚无中撕裂出一个伤口。本来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东西,因此要创造就必然要损害那种纯粹。马克思《手稿》对“对象性活动”原则的拥护,或者其对“创造”或“给予”的专心追求,也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精神。如果我们摒弃“对象性活动”之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概念性质,那么,《手稿》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对应。
[注释]
责任编辑:朱明
B0-0
A
1008-4479(2015)01-0010-07
2014-09-28
张文喜(1961-),浙江东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