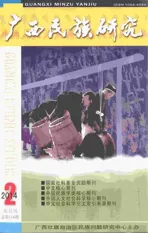岭南民族歌圩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审美智慧*
2014-12-12何飞雁
何飞雁
生态审美观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由中国学者首次提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审美观”,是“指建立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1]163在彰显生态文明的全球化时代,生态审美的民族性问题和少数民族生态审美文化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仪平策先生指出:“作为一个积淀着深刻的人文性、精神性、体验性内涵的概念,生态美学总是跟特定具体的时代、地域、民族、文化中的人相联系,总是一个具体的、此在的概念。不同时代、地域、民族、文化中的人,其生态审美趣味和美学理想必定是缤纷多样、互有差异的。”[2]黄秉生等学者认为:“相对于工具理性特别发达的世界主流文化而言,少数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在她们的文化中蕴含着更多的生态智慧。”[3]1因此,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不仅针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更应当关注生态美学研究的民族性,即不同地域民族与自然以及民族内部的生态审美关系特征”。[4]这也是建构本土化的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态审美的民族性“是在生态审美的普遍价值框架之下所呈现出的不同民族生境、民族文化的审美特性,包括将特定区域的自然景观、风俗、风物、风情纳入生态主义的视域中,从世界性的整体意识出发,呈现一种特殊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之美和生态整体观照。”[5]歌圩是岭南壮、侗、苗、瑶等民族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的以青年男女倚歌择偶为中心的节日性聚会唱歌活动形式,由于它“以相互酬唱为主体,每场聚集人众不下千人,唱和竟日,犹如唱歌的集市,后来人们把它统称为歌圩。”[6]2这一极富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传统习俗是关乎民族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谐的重要文化事项,其中包含着重要的生态审美智慧。
一、山椒水湄中的歌唱活动:人与自然的相依相生
歌圩是岭南壮、侗、苗、瑶等民族人们在春秋季节于“山椒水湄”之中举行的节日性聚会唱歌活动形式。明代邝露的《赤雅》中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竟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民国《上思县志》也载:“每年春间,值各乡村歌圩期,青年男女,结队联群,趋之若鹜,或聚合于山岗旷野,或麕集于村边,彼此唱山歌为乐,其歌类多男女相谑之词。”[7]242这里道出了歌圩举行的时间一般是春秋季节,如“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中秋节”等,其中尤以春天为盛,歌圩依托的自然生境则是村边旷野或山椒水湄之中,即岭南民族所说的“峒”(山间开阔田野)和“那”(水田),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和谐之美。
我们还可以从歌圩的称谓中看出其与岭南民族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在壮语中,歌圩常见的称谓是“陇峒”,其中“陇”指“四周环山之地”[6]26,“峒”原是“壮族对山间开阔田野的称谓”[6]18, “陇峒”意为“下到田峒对歌”。另外,广西崇左、宁明一带叫“窝坡”,意即“出到坡地上去相会”,或“歌坡”,意即“坡场上会歌”,德保一带叫“航端”,意即“峒场圩市”。由此可以看出,山之坡、水之湄 (岭南民族所说的“峒”和“那”)是歌圩所依托的自然生态环境,它们与歌圩及歌圩活动的主体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亲缘性关系,并且对歌圩民歌的文化特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季节变换等为主题的民歌种类,即所谓的季节歌、花果歌、草木歌等。这类民歌往往以一问一答的盘歌形式出现,内容涉及一年四季中自然界的各种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如下面的这一组盘歌:
男:什么结果抱娘颈哎,什么结果一条心哎,什么结果抱梳子哎,什么结果披鱼鳞哎?
女:木瓜结果抱娘颈哎,香蕉结果一条心哎,柚子结果抱梳子哎,菠萝结果披鱼鳞哎。[8]
这一类的盘歌都是歌圩场上的歌手们即兴编唱随问随答的,他们皆“临机自撰”、 “不肯蹈袭”,而且往往对答如流,除了歌手们有灵活的头脑、敏捷的诗才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万物及其生长习性有深刻的生态审美感知。正如曾繁仁先生所说的:“生态美学是一种人与自然审美地和谐相处的美学形态,它不同于一般美学之处在于在这种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不是相分的,而是一体的,构成一个紧密不分的共同体;而且人在生态审美过程中也不是孤立静观地审视,而是如现实生活一样是在动态的时间之流中审视。因此,生态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就是一般美学所没有的‘家园意识’。人与自然是一种‘在家’的关系,自然是家中之物,人是家中之人。人感受到一种在家的惬意,与自然万物须臾难离。”[9]岭南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南国属于亚热带地区,雨量充沛,植被繁茂,气候温暖而湿润,动植物种类多样。独特的地形地貌使这里岩溶广布,山岭绵亘,泉涧错综,洞奇石美。人们生息劳作于这美丽的大自然之中,长期地跟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打交道,与它们形成一种须臾难离、和谐共生的“在家”的关系,对它们的千般秀姿万般妩媚有着深刻的生态审美感知和体验,于是自然在歌圩对歌中把其作为歌咏的对象。
其次,山椒水湄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歌圩民歌以物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起了促进作用。比兴手法是中国民歌惯用的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就是比附物之性,也就是比喻,兴就是见物起兴,由所见之景引发某种情绪或情怀。它也是歌圩场上的青年男女试探对方、表露情意的一种重要方式,贯穿于歌圩中的沿路歌、见面歌、求歌、接歌、盘歌、定情歌、盟歌、别歌等阶段。如下面这组“沿路歌”:
男:一路唱歌一路来,一路唱得百花开;花开引得蝴蝶舞,花开引得蜜蜂来。
女:一路唱歌一路来,一路看见百花开;妹的花开香千里,哥是蜜蜂万里来。[6]183
“沿路歌”(又称“游歌”)是人们在赶歌圩的路上常唱的一种歌,歌中以自然界中的百花、蝴蝶、蜜蜂作起兴和比喻,引出男女双方的交情心意。
借物抒怀、借物寓意也是歌圩场上的青年男女表露感情的重要方式,如下面的这一首探情歌:
一条河水绿幽幽,一朵梅花跟水流;妹你有心捞花去,无心无意望花流。[10]
通过“梅花”有意“跟水流”含蓄委婉地试探对方是否有心和自己结交。下面这组别歌则由燕子的春来秋走而引发思恋的情怀,盼望来日的重逢:
男:燕子春来秋又走,只见屋檐空留窝;抬头望燕无踪影,低头想妹心更忧。
女:燕子春来秋又走,竹楼檐下把窝留;有缘不怕四季变,归期自飞哥门楼。[6]209
岭南人们之所以在歌圩对歌中信手拈来地以当地熟悉的自然景物作为起兴和比喻的对象,源于他们亲近自然,长期地融入自然并对自然生命律动有独特的感受和生态审美体验。生态审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就是人对自然万物蓬勃生命力的一种审美的经验。其内涵包含人对自然的本源的亲和性、人与自然须臾不分的共生性、人对自然生命律动的感受性以及人在改造自然中与对象的交融性等等。”[11]在四季如春的南国,山花不分季节地盛开,草木一年四季的葱郁,鸟兽虫鱼一年四季地歌唱,它们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岭南人们现实生活中常处、常乐、常适、常亲的人生伙伴,与人们形成一种须臾不分的交融共生性,人们对它们的蓬勃生命力有一种审美的经验和感受,进而与其产生生命的感通,于是自然在歌圩场上以其作为起兴和比喻来传情达意。
再次,山椒水湄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歌圩民歌独特的韵律特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情韵并重、韵点密集、韵律多样是岭南壮侗等少数民族民歌的重要特点,比如壮民族民歌的特点是“押韵次数密集,换韵频繁灵活,韵律多种多样”[12],其中的腰脚韵就明显具有这种特点。它要求“下句的‘腰’(五字句歌中的第二或第三个字,七字句歌中的第一到第六个字其中的一个),要押上句末字即‘脚’的韵,同时,四句以上的一首歌中,凡偶句的脚韵必须互押,这样,就形成了十分严谨的一首多韵连环式的韵律结构”[6]189。这种独特的民歌韵律配上民族音乐特别的优美动听,如刘锡藩所说的:“壮歌尤悦耳。唱时,一呼疾起,曳声入云,在余音袅袅中,急转直下,再跌再起,长声绕天,回旋不散。若联合多人同声齐唱,抑扬振落,四山回声相应,虽远隔数里,而声彻耳鼓,使人怦然动怀。”[13]
这种韵律特征的形成又与岭南民族迂回曲折、连绵起伏的自然山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这里山岭绵亘、丘陵错综,猫儿山、越城岭、云开大山、岑王老山、大苗山、大瑶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等平地崛起,连绵起伏,西江、漓江、柳江、邕江、明江等迂回曲折,蜿蜒盘旋,形成半封闭半开放的连锁式“∽”形生活环境。这种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对“多韵连环式”的民歌韵律结构以及“一呼疾起,曳声入云,在余音袅袅中,急转直下,再跌再起,长声绕天,回旋不散”的民歌音乐特征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会歌则年岁佳:人与神的和谐共生
目前关于歌圩的起源主要有4种说法:源于乐神说,源于择配说,源于掉念殉情者说,源于刘兰妹传歌说,其中乐神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壮学专家潘其旭先生认为:“古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里举行‘会和男女’一类的活动,是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为原始信仰的一种仪俗。”“歌圩脱胎于原始氏族部落的祭祀活动”[6]78。韦苏文等学者也认为:“祈求丰年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14]4。岭南民族的歌圩活动起初作为一种祭神酬神的巫术礼仪,它所起的主要是沟通神人的作用,以达到消灾祈福、农业丰收、种族绵延之目的,实现人与神的和谐共处。这在历代典籍中多有记载。《说蛮》云:“峒人……春秋场歌,男女会歌为异耳,言会歌则年岁佳,人无疾病”。清乾隆十一年修纂的《镇安府志》载壮人“元宵前后,以大粽、酒淆祭上神,杂坐祠前共饮,唱土歌以祝太平。”《粤西丛载》云:“宾州罗奉岭,去城七里。春秋二社日,士女毕集,男女未婚者,以歌诗相应和,自择婚配。”
这种观念在民众中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据学者们的田野调查得知,在问及为什么要举行歌圩时,人们认为“过‘航单’(广西靖西对歌圩的称谓)就会丰衣足食,有好日子。”[15]“在老一代的观念里,‘航单’时父母带孩子到圩上去可以让他们健康成长。”[16]“棉山的一位社员说,‘俄阿’(广西都安对歌圩的称谓)能够免徐天灾人祸,能使禾苗丰收,虫子不吃庄稼,总之只要唱山歌一切都有办法”[17];“巴马燕洞的一位老人也说,哪一年不搞‘俄呷’(广西巴马对歌圩的称谓)哪一年庄稼就长不好”[16];“龙州县老人们说,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五谷正在生长阶段,哪里要是赶‘歌圩’,哪里的五谷就会获得大丰收。”[16]“传说每年举行一次‘圩蓬’(广西宾阳对歌圩的称谓)之后,当年禾虫少,庄稼生长好。”[18]
在民众意识的深层,歌圩还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龙州县志》载:“相传此墟一禁,即年谷不登,人畜瘟疫。”“(德保县)都安有一年不做 (歌赛),死了十几人”[13],“老人们认为过‘航单’就能有好饭菜”[19],“老人说,带孩子去‘航单’玩可以让他长得健壮”[13]。“2005年农历正月期间,靖西县渠洋镇珍帮村大帮屯的民众恢复了三年一度的‘航单’,因为此前一年,村里发生火灾,导致几十间房屋被烧,他们认为灾难降临的原因是不过‘航单’。”[20]“谁家没有儿子,只要举办一次‘花炮歌圩’,来年便可生儿子。”[13]“大新雷平的老年人说,以前有神农庙时,农人到神农诞生那天在庙前供祭唱歌,后来人越来越多便发展为歌圩。又说谷神也来参加歌圩饮宴,神和我们一起快乐,便会保佑我们丰收。”[21]
人们认为,歌圩中的男女会歌是求得神灵的护佑,以达到“年岁佳”的重要目的。对于岭南稻作民族来说,“年岁佳”既包括稻作农业的丰收,也包括家族的人丁兴旺。因此,人们或是在进行农事活动 (如开耕、插秧、收割时),或是在围绕稻作农耕而举行的节日 (如禾魂节、尝新节、糍粑节等),或是在神灵祀日 (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祭祀蛙神的蛙婆节,正月末到二月初的土地节,二月十九日的花王节,四月初八的牛魂节,八月初二的“众神节”,八月十五祭拜月神的中秋节等),同时举行隆重的峒场歌会,通过男女之间的交往来乐神娱神,感谢神的恩赐和庇佑,以达到农业繁荣和人丁兴旺的目的。而且,为了便于神灵的观看,歌圩场所一般都选择神山、庙宇(或宗祠、社坛)附近的那一带山野、田峒,举行歌圩之前一般都要到庙里 (或宗祠、社坛)祭祀神灵并请里面的“神”来观看,歌圩结束也要入庙祭拜,告谢神灵。
总之,歌圩依托于山清水秀的“峒”和“那”之中,它聚集了“峒”和“那”之上的山山水水、它上空的风雨雷电、岭南人们及其对神灵的信仰,昭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天、地、神、人”的四重性融合统一。
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
“喜乐日子唱欢歌,客人尊主唱赞歌,接待要唱礼仪歌,白事丧葬唱悲歌,野外歌圩唱情歌,嫁女要唱哀怨歌,‘纳福’请来巫道歌。”[22]岭南人们从降生人间直至生命的结束都是在歌声中度过的。正如刘锡藩所说的,“壮乡无论男女,皆认歌唱为其人生之主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 (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即不能通今博古,即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23]他们不但把唱歌作为恋爱择偶的重要手段,而且把它作为交朋结友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更把其视作个人聪明才智的一种标志,衡量社会道德的一种标准,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之美。
(一)歌圩为青年男女提供了自由恋爱择偶的场所,体现了两性之间的和谐之美。
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从相识到婚姻的缔结始终都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进行,他们没有任何自由自主权。婚后,男子可以娶三妻四妾,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这种婚姻制度不仅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的权利,而且强调女子的从属地位和依顺人格,体现了婚恋生活中男女双方在机会、情感、人格上的不对等以及歧视女性的伦理本质。岭南民族的歌圩活动则是以青年男女的倚歌择偶为主要内容的,它为青年男女提供了自由社交、自由恋爱、自择佳偶的场所,体现了婚恋生活中男女两性在机会、情感、人格上的对等与和谐。
“俍人者……其俗自幼即习歌,男女皆倚歌自择配。”[24]“善唱歌者,能博得妇女之欢心,可籍此为媒介而达到最美满之恋爱,进而达到美满结婚之目的”[25]。人们正是通过歌圩对歌的方式自由自主地寻找和发展他们动人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每逢圩期,青年男女皆盛装艳服,从四面八方云集歌场,“以答歌踏青为媒妁”[2],“清歌互答自成亲”。“斯时三五为群,绿荫树下,青草池边,皆会歌盟情之所。此答彼唱,声傲四野。”[26]绣球、扇子、彩蛋等则成了歌圩场上的青年男女自主定情或订婚的信物。如《岭外代答》中记载:“交趾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陀。男女目成,则女受陀而男婚已定。”[18]“溪峒……当春日戴阳,男女互歌谓之浪花歌,又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抛绣笼。绣笼者,彩球也。回旋舞蹈,歌意相洽,即投之报之,返而约聘。”[10]“宾州罗奉岭,去城七里,春秋二社,士女毕集。男女未婚者,以歌诗相应和,自择配偶。各以所执扇帕相博,谓之博扇。归日,父母即与成礼。”[18]这种男女两性相互尊重、自由自主、和谐对等的婚恋形态,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父权制婚恋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歌圩还是岭南人们施展才智、交朋结友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地,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之美。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是生态美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对于以歌代言、以歌相伴的岭南民族来说,歌圩是通达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首先,歌圩是岭南人们施展才智以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鄂温克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个人要靠成为优秀勇敢的猎手才被社会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而也才能满足心理上的需要。而在壮族歌圩文化的环境中,一个人要实现自我价值,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要找到对象,就要成为真正的歌手。”[2]黄秉生先生也指出:“壮人之所以喜欢唱歌,固然有恋爱求偶之需要,更有要通今博古、表现自己的聪明和智慧、以求得社会的肯定和认可的需要,这正是壮族歌圩得以流传的本质所在。”[27]人们通过歌圩来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求得社会的认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其次,歌圩还是岭南人们交朋结友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岭南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之中。这里崇山峻岭,河流纵横,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人们分散居住于千山万岭之间,以自给自足的稻作经济为本,其社会结构多以家庭和村落为主,人们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歌圩的举行则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状态,不同民族、不同村落的人们从方圆几十里之外聚集在一起,通过对歌赛歌,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了解,有的还借此交朋结友、交结“同年”,寻求佳偶。可以说,歌圩这种季节性的集会在加强男女两性之间、不同村落、不同民族的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强化了社会团结,加强了不同族群、不同等级的社区内部、家族或宗族内部以至性别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四、唱歌解得万年愁:个体自我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
“生态美学所关注的生态问题既是物质的、自然的、生理的,更是精神的、社会的、心理的,亦即‘文化’的;它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不单纯是给人以直接的自然性、生物性满足和享受,而是还要给人以真正‘属人’的文化体验、情感满足和精神快乐。”“生态美学所关切的就是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人类生存的诗意化和理想化。”个体自我精神生态的和谐与诗意栖居是生态美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人之所以要追求诗意的生存,缘于人类本身的存在境域。人的存在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又是一种不满于缺陷而追求完善的存在”,“而诗意的人生正是人类克服自身缺陷不断为自己完形的创造性人生,人为自身完形的过程就是对人生的不完善方面进行完善补充的过程。”岭南民族自古就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山歌本是古人留,留给后代解忧愁;三天不把山歌唱,三岁孩童变白头。”民歌是他们在有缺陷的人生中追求“完善的存在”的重要途径,是他们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
首先,山歌是岭南人们超越生活之困苦、人生之艰难的重要途径。岭南先民居住的地方在古代被称为“蛮荒之地”,瘴气重,蛇虫多,野兽出没,人烟稀少,在土地少得可怜的大石山地区,人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生活更加困苦。而且在历史上,岭南诸民族除了长期受到奴隶主、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之外,还受到土官、土司的层层压榨与奴役,千百次的阶级与民族压迫更是使得苗、瑶等民族被迫迁徙到荒无人烟的深山野林中,人们的生存之艰难可见一斑。而山歌可以化解人生中的苦难和忧愁,可以促进人精神生态的平衡。正如广西民歌所唱的:“唱句山歌解个闷,喝口凉水浇心头;凉水浇得心头火,唱歌解得万年愁。”“出路携歌当早饭,赶街唱歌当晚餐。妹穷用歌当茶水,妹贫要歌当酒坛。”人们正是通过山歌超越了贫苦的生活和艰难的人生。
其次,歌圩还是岭南人们用以反抗不自由婚姻以及弥补婚恋生活缺陷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岭南少数民族“婚不用媒聘”,而是以歌为媒,歌圩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的理想场所。自明清以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种前时代自由自主的婚姻逐渐向封建婚制过渡,“门当户对”、“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规范,这种违反人性的婚姻制度造成了许多没有爱情的婚姻,给婚姻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而歌圩这种“歌唱为乐”“倚歌择配”的民俗活动是与封建礼教及道德观念相冲突的,虽然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伤风败俗”而屡遭禁止,但是它一直在岭南乡土社会中世代传承而屡禁不止,它的存在为人们提供了自由恋爱的机会,成为人们在不自由的包办婚姻之外寻找美满的婚姻,在没有爱情的封建婚姻之外寻找真爱的重要途径。许多年轻人对封建包办婚姻非常不满,于是通过歌圩寻找自己钟情的对象,最终实现了美满的婚姻。“如盘阳的盲歌手就是一例,他在十六岁时,经父母包办结了婚,夫妻毫无感情,女方始终不落夫家,最后他坚决离了婚,并通过对歌找到了中意的伴侣。”[27]而很多对包办婚姻或买卖婚姻无能为力的,则通过歌圩结交异性,欢会“同年”,寻找“精神上的伴侣”,以弥补恋爱婚姻生活的空白或缺陷。他们把歌圩视为自己的自由天地,“到歌圩上来还能笑几声,回去只有哭着过活,说不定哪天就活不下去了。”[27]在这种情况下,歌圩成为人们摆脱封建婚姻制度的控制和压抑,寻找鲜活的情与爱的重要途径。通过歌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情爱归宿以及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总之,岭南民族的歌圩活动依托于“峒”和“那”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和谐之美;歌圩是岭南人们祭神娱神以祈求丰年的重要媒介,体现了人与神的和谐之美;歌圩为青年男女提供了自由婚恋的场所,是民族个体与他人、民族与民族之间情感联系、文化交流的场地,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歌圩还是个体自我化解生活中的忧愁,通达诗意生存的重要途径,体现了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之美。
[l]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视野看生态美学的民族性问题[J].社会科学辑刊,2005(6).
[3]黄秉生,袁鼎生.民族生态审美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申扶民.原始艺术的生态审美特征探析— —以广西花山壁画为个案[J].贵州民族研究,2008(3).
[5]隋丽.论生态审美民族性的内涵与表征[J].山东社会科学,2012(5).
[6]潘其旭.壮族歌圩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7]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8]邓凡平.刘三姐剧本集[G].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9]曾繁仁.建设性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J].学术研究,2012(8).
[10]覃录辉.广西壮族“歌圩”情歌的分类[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11]曾繁仁.发现人的生态审美本性与新的生态审美观建设[J].社会科学辑刊,2008(6).
[12]黄革.广西壮族民歌独特的押韵形式[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13]刘锡藩.岭表纪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4]韦苏文,周燕屏.千年流韵——中国壮族歌圩[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5]陆晓芹.歌圩是什么——文人学者视野中的歌圩概念与民间表述[J].广西民族研究,2005(4).
[16]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广西各地歌圩情况[M].1963.
[17]陆晓芹.歌圩的地方性表现及其意义——以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民间节日“航单"为个案[J].百色学院学报,2011(5).
[18]那坡县文化馆.黑衣壮歌谣艺术与传承保护初考(内部资料)[M].
[19](清)陆祚蕃.粤西偶记[Z].山东:齐鲁书社,1997.
[20](明)方瑜,梁炫.南宁府志十一卷(嘉靖四十三年)[Z].桂林图书馆藏书.
[2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Z].民国影印本,桂林图书馆藏书.
[22](清)李文琰,何天祥,等.庆远府志十卷[Z].乾隆二十年(1755年)刻本,桂林图书馆藏书.
[23](清)汪森.粤西丛载三十卷[Z].据上海进步书局民国石印本复印本,桂林图书馆藏书.
[24]陆干波.壮族歌圩文化延续原因初探[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1).
[25]黄秉生.崇智文化根系与壮族的文化生态美[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26]段建军.人:诗意的生存者— —审美创造的个体人类学阐释[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9(1).
[27]张铭远.壮族歌圩的社会基础及观念基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