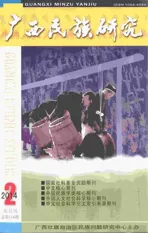藏区水葬习俗的饮食人类学解读——基于金沙江河谷的田野调查
2014-12-12叶远飘
叶远飘
藏族的丧葬类型是目前国内所有少数民族中种类最多的,其丧葬因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一直是学术界青睐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学术界对天葬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对水葬的研究非常少,即便有,也仅仅简单提到藏族对水葬的态度:在盛行天葬的地方,人们习惯把水葬视为一种低贱的葬法,其葬的对象多是经济贫困或死于非命的人。[1]171而在那些缺乏秃鹫的地方,人们盛行水葬。当地认为水葬与天葬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把水葬说成天葬。[2]许多研究笼统认为,这些观念的形成主要受藏传佛教影响。笔者认为,以上解释在推却责任。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佛教主要推行三种葬式:火葬、水葬与野葬。换句话说,水葬也是佛教推行的葬式,那么为什么偏偏在有天葬的地方水葬就变成一种低贱的葬式了呢?为什么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藏人面对同一种葬式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学术界至今未回答的问题。要解答这一疑问,需要从源头搞清藏区水葬的起源,从根本上改变学界长期以来侧重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研究丧葬的做法,从而为丧葬研究开辟新的路径。为此,笔者曾于2010年7-11月前往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沿金沙江畔分布的两个田野点——三岩与羊拉进行为期半年的多点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向学术界全面展示该地区藏民对水葬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将丧葬研究往纵深推进的设想。
一、三岩:牧业经济、苯教信仰与低贱的水葬
三岩处于金沙江峡谷上游,地理位置大致在东经98°40'—98°52',北纬31°02'—30°14'之间,行政上包括今四川省白玉县管辖的山岩乡和西藏贡觉县管辖的克日乡、罗麦乡、沙东乡、敏都乡、雄松乡和木协乡。乡村沿金沙江两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居住人口1万人,属藏族。①数据根据各乡政府提供的土地面积与人口汇总。
该地境内山峰绵延起伏,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最高处是克日乡的勒泼山峰,海拔5400米,最低处是西岸木协乡则达村,海拔2500米,整片地区平均海拔达3700米。“全境多为石山,熟地颇少,计不过千分之七八而已……垦荒地亦属廖廖。”[3]此生态条件决定了农业不可能在当地的经济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岩人目前仍然实行传统的牧业生计模式。由于垂直气候显著,低海拔地区常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影响,而高海拔地区容易受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的影响。三岩人巧妙地利用这种垂直气候将牧场分为春夏牧场与秋冬牧场。在春夏两季,他们主要在海拔3500—4000米的高山垭口放牧,那里不同的坡向地生长着不同的植物,如阴坡有高山柳灌丛,阳坡有草甸,这些都是理想的饲料。但是秋冬以后,高山垭口处的草木枯萎,人们必须把牲畜赶到金沙江的河谷一带放养。那个季节里,河谷一带的草本植物还是郁郁葱葱的,牛羊主要吃的草为早熟禾属、野青茅、须芒草等。
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境内存在多个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但该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大量吸收苯教的仪轨,早就与古老的苯教融为一体,突出表现在僧人可以不出家,不脱离生产,娶妻生子、崇尚咒术,以致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并不认为宁玛派属于佛教。但无论如何,它在三岩人的生活生产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丧葬方面,此地几乎囊括了藏区现有的葬式,其中天葬最流行,水葬最低贱。在三岩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中,水葬经常用来葬那些自杀死亡,或者意外摔死的人,尤其是用来葬那些难产而死的孕妇。水葬程序大体如下:家里有人去世以后打算实行水葬的,家属会刻意把丧事办得低调一些,下葬的速度比较快,如当天去世,第二天可能就会下葬了,省去了长长的念经、守尸等环节。之所以省去这些环节,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死亡不洁,具有非常强的污染性,它可能会像传染病一样把这些晦气传染给那些前来吊唁的人。通常情况下,在敛尸之前,人们也不会替死者洗尸,仅以死者平常睡的一张毛毯将尸体包裹后放入箩筐中就抬往水葬点。到了河流高处,众人将尸体从箩筐中移出,举起尸体往河里投掷,尸体瞬间就被水冲走了,水葬也随之草草结束。如果是冬天,三岩境内的所有金沙江支流的水位都会下降,水流量同时会降低,无法有效冲走一具成年人的尸体,这时候要进行水葬的必须往死者的尸体上绑一块重几十斤的石头,然后把尸体连同石头一起扔到河里。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家属也会请喇嘛来帮助念经。关于水葬的意义,“地方性知识”专家,73岁的啊尼告诉笔者:
自杀、摔死、产妇难产而死是因为他们得罪鲁神的结果,这种神住在水里面,它能导致你患传染病。比如一个人的皮肤溃烂就是因为你得罪它,它往人的身上下药的结果。这种死亡肯定是一种不好的死亡,死者的身体不干净,因此亲属不愿意给死者洗尸,只能把尸体丢在有漩涡的地方,漩涡状的水流只会促使死者的灵魂走向毁灭,这样能够有效把一切传染和人类生活的地方隔离起来。因此,水葬点比坟场还恐怖,因为葬在那里的死者都比较脏,都是厉鬼。①访谈时间:2012年11月。
实地考察发现,三岩的水葬点大都远离居民饮水的水源。比如位于雄松乡的一个水葬点就建在金沙江支流的下游,而这条河不在居民日常生活用水的范围内,甚至不在老百姓生活村庄的视野范围内。若在平日的生产劳动中,老百姓经过这些地方时,经常会绕道而行。在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体系里面,水多与凶神发生联系,水葬点更是不可接触、不可冒犯之地,是凶神、厉鬼居住之所。
不难看出,在三岩老百姓的观念中,水葬的等级非常低,它针对的大都是那些非常差的死亡,老百姓认为这些死者的尸体是不干净的,这种观念与台湾的排湾族相似。在排湾族的死亡观念中,凡蓄意或过失导致的死亡,为非常严重的恶死,女巫无法干涉或行祭仪弥补。人们相信此类死者之魂终将成为恶灵或邪神来危害人间,纵然家属为其献祭,仍无法使之避免成为飘浮不定的坏祖先。[4]403
二、羊拉:农业经济、佛教信仰与流行的水葬
从三岩沿金沙江畔往南走150公里,是本文的第二个田野点——羊拉。羊拉在行政上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管辖,地理坐标为东经99°05'23.7″,北纬28°54'58.8″,全乡约1087平方公里,辖4个行政村,分别是羊拉村、归吾村、甲功村、茂顶村,人口8216人,全部为藏族。②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德钦县羊拉乡政府。
由于此地位于金沙江的下游,气候介于湿润、半湿润之间,河谷地带发育着褐土,土体有机物含量低,碱性反映强,因此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明末以降,世居丽江的纳西族木氏土司西征吐蕃,羊拉曾一度受木氏统治。大批纳西族迁移此地,开垦农田,为羊拉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同时强化了此地人的农业生产观念。目前,羊拉人表现出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他们生产的农作物主要是青稞、大麦、小麦、马铃薯和杂豆等,在靠近金沙江河谷更低的地方还可以种植水稻。因此,羊拉人一年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他们经常通过辨认昆虫的叫声来判断春耕的时间,也会通过观察山峰上雪线所在的位置判断收获的季节。
在宗教信仰方面,羊拉一共有7座藏传佛教寺院,全部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该地佛教信仰气氛浓厚。突出表现在大多村庄名字的命名都与佛事有关,如位于奔子栏附近的“茂顶”村就是一例。在当地的藏语发音中,“茂”就是“经书”的意思,“顶”是上层的意思。“茂顶”一词说的就是“用经书堆起来的村子”。由于热衷于佛事,无论男女老幼每天都把祭佛作为头等大事。每个家庭每个月至少要举行一次家庭念经祈福活动。每个村庄每年最少要集体向寺庙布施一次,凡逢年过节,人人争相到外转经。每年岁末年初,村村也会争先邀请喇嘛到村中讲法。
在丧葬方面,这一带没有天葬,但水葬特别流行。水葬分为两种:一种是整尸水葬;另一种是分肢水葬。整尸水葬的程序大致如下:死者去世以后,亲属将尸体捆成胎儿状,用一张白色的裹尸布将尸体裹起来,然后把这个装有尸体的白色布袋装入一个竹箩筐或者木箩筐里面,用一根直径约3厘米、长约15米的粗麻绳反复穿过箩筐两端的端耳,向上拉紧打结;然后,两个人一组,一前一后抬箩筐前往河流中游水葬点进行水葬。抵达水葬点以后,先在河边浅水处清理出一块地方,供僧人念经超度死者。念经结束后,将装有尸体的箩筐放在浅水处,开始处理尸体。首先是把白色的裹尸布除掉,然后将穿在箩筐耳端的绳子解下,在绳子的一端绑一块重十几斤的石头,将这块石头放进箩筐底部让尸体压住,再用绳子将尸体的头部或者颈部缠绕几圈,目的是让尸体在水葬时不至于浮起。缠绕尸体的绳子还多出十几米长,人们在它的另一端也绑上一块石头。然后捡一些干净的大小不一的石块往箩筐里填充,垒砌尸体。垒砌好后,由一名僧人和死者亲属的一位老者领路,其他十几个年轻人跟在后面拉起绳子的另一端,缓缓地逆流而上,尸体也跟着逐渐进入水中;拉绳的人不断往上游走,绳子也逐渐被水淹没,一直到这根12米长的绳子完全淹没在水中,人们即弃绳而走。上岸以后,人们还会在水葬点的地方竖两根木杆,一根木杆用来挂经幡,将一根长约十几米的细细的反搓而成的白羊毛绳缠绕在另一根木杆上以纪念死者。田野调查中经常发现,一些老妇人在送葬队伍离开以后,她们就会走到水葬点的浅水处,左手不断摇嘛呢经轮,口里不断念诵超度经文,默默为死者祈祷,久久都不离弃。
分肢水葬的程序与整尸水葬大致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到了水葬点以后要对尸体进行肢解。分肢水葬点多在金沙江支流中游河的支流举行,那些地方的水深约0.5米,河水流速不大。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对尸体进行肢解。水葬点旁边有一块面积约6平方米的白色巨石,是为肢解台。肢解尸体前,活佛会坐在石板约2米远的地方为死者念经超度,和尚在一旁协助,送葬的家属也会跟着唱玛尼调。肢解尸体前要先用斧头将棺木劈开,然后将尸体从棺木取出来,解开尸体身上的绳子和衣服,让尸体平整地躺在大石上。从颈部开始,用刀在尸体背面画一些纹路,然后再沿着纹路将尸体肢解,抛入河中。据说整个程序大约要行108刀,待尸体处理干净以后,把尸首、斧头、刀和劈开的棺木一起丢到河里,然后家属在肢解台的旁边立经幡,整个水葬到此结束。整个分肢水葬过程不允许妇女和小孩送葬。
目前,整个羊拉乡比较大的水葬点有10个,其中有6个位于中游河不同的地段。关于水葬的意义,茂顶村的经师拉曲曾告诉笔者:
无论是整尸水葬还是分肢水葬,都是比较好的葬式。我们藏族相信灵魂转世,水葬其实就是做功德,与西藏的天葬是一样的。天葬是死者将尸体向神鸟“布施”,水葬是死者将尸体向河里的鱼虾做“布施”,这些葬式都有利于拯救大自然的动物,是死者向生前所犯的罪恶进行赎罪的方式,有利于加快灵魂的转世。①采访时间:2011年11月。
有理由相信,报道人所言不虚。比如笔者就发现这些水葬点的鱼虾比较多,甚至有长约0.5米的大鱼在河里游动,因此当地人选择这些地方作为水葬点可能确实是出于“布施”,方便鱼类等吞食尸体以免污染下游的举措。由于水葬在当地是一种流行的葬式,因此当地人特别在意人死亡的时间,很多群众就认为发生在冬天的死亡是很差的死亡,原因无非是因为冬天气候寒冷,河水结冰,无法实行水葬。如果某人死亡要实行水葬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老百姓大都将罪归于死者前世所造的孽,当地人也因此称之为“死无葬身之水”,这时候死者的亲属一般都会积极向寺庙和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群众“布施”以赎死者生前的罪恶。羊拉的水葬点还有一个特色——它并没有像三岩那样——远离居民饮水的水源。在一次外出调查过程中,由于天气炎热,报道人与笔者路过一处小溪时就地洗脸甚至喝水,稍后报道人才指了指在离我们5米的下游处,说那就是水葬点,继而说那条河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用水的水源,这令笔者颇感意外。对此,报道人的解释是,金沙江那样浑浊的水不能水葬,有一种“晦气”在里面。水葬点的水一定要清澈透底,才有利于加速死者灵魂的转世。
以上田野资料来自于金沙江流域,在某种程度上与目前藏区群众对水葬的两种态度遥相呼应。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分布在一条大江河畔,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人群对水葬会有明显区别甚至完全相反的态度呢?
三、作为“观念”的水:牧区的水与农区的水
来自三岩的田野材料表明:生活在高寒牧区的牧民对水有着近乎一种“规避”的态度,其理由何在?饮食人类学的理论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在饮食人类学看来,人类的饮食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们选择食物是因为他们看中了食物所负载的信息而非它们含有的热量和蛋白质。一切文化都无意识地传递着食物媒介和制作食物的方式中译成密码的信息。”[5]众所周知,青藏高原的牧民最看重的食物是牦牛。在藏语中,牦牛被称为“诺”,有“财富”之意。的确,在现实的生活中,牦牛一身都是宝,在一定程度上是判断一个家庭贫富程度的最直接的方法。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对此深有感受:到一个家庭去做客,富裕的家庭捧上来的酥油茶表面会结一层厚厚的油,而贫困的家庭打出来的酥油茶往往清澈见底。广大的藏区也一直有“无牦牛不成宴”的说法。在三岩,一个家庭要嫁女儿,通常会送给男方5-8头牦牛。在群体斗殴事件中,伤了一根手指头,会赔给对方10头牦牛;伤了一只眼,会给赔偿对方15头牦牛。甚至在发生诸如杀人此等大事时,民间也还会以赔偿牦牛的方式私了。问题在于,藏民为什么会视牦牛为财富?著名考古学家富雷尔·海门多夫提出的“财富控制论”可以解答这一疑问。这位考古学家在考察早期人类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农产品产出不对等的现象时指出,最早的农业不能导致食物实际产量的任何惊人增长;只有经过若干年或若干世纪的选种才能做到这一点。毋宁说,人们肯定是出于控制食物位置的愿望而开始农耕。[6]13换言之,人类最初之所以从事农作物生产 (包括饲养动物)是出于他们对培育出来的动植物实行控制,将它们当作财富以防止被抢的一种心理。西藏著名的两个考古遗址——曲贡遗址和卡若遗址的早期也先后出土有牦牛的遗骨[7],这说明在青藏高原地区,牦牛很可能是藏民最先驯服的动物之一,这可以解释藏民称呼牦牛为财富的疑问。
事实上,人类最初对动物的分类不可能凭借太多的专业知识,他们只能依据自身所处的空间将自然界的动物大体分为三类:即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和水里游的 (这大体与苯教所倡导的三层宇宙空间观相符合)。对于游牧部落而言,由于长期在牧区生活,他们最先接触到的应该是高原上奔跑的动物,而非水中的动物。当这些在陆地上行走的被驯服的动物被当成个人财富看待以后,为了满足天生的征服欲望,他们还会想办法去驯服那些在陆地上走的其他动物,于是,陆地上走的动物就被视为个人潜在的财富。那么,因意外、病残而失去了牛羊的一群牧民 (失去财富的人)——穷人——为了解决温饱只好到水中去寻觅食物。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被排斥在财富之外——不能捕猎陆地上的动物——于是只能根据生活经验做出判断——相对于天上飞的动物来说,水中游的动物毕竟容易捕获一些。久而久之,在高原牧区,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水中游的动物是穷人、乞丐或者病残的人才吃的。[8]24既然水中的食物是穷人乞丐的食物,就难免会被主流价值观灌以“肮脏”的观念,于是,任何东西被投到水里都会变“脏”。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穷人、乞丐的尸体被投入水中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清乾隆年间的《西藏志》在有关藏区的丧葬就明确提到了“无钱则弃尸于水”的现象,而如今三岩将水葬视为一种低贱的丧葬无疑就是这些观念的延伸。其实,来自世界各地关于牧民民族志的大量材料也有力支持“水”是与“贫穷”、“低贱”这些观点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如生活在尼罗河畔的牧民——努尔人,“他们瞧不起像施鲁克那样的人,他们说,施鲁克人主要以捕鱼、杀河马为生……”[9]86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边生活着一群以捕鱼为业的图尔卡纳人,其居住地与那些看不起他们的牧民总是保持一定距离。[10]295与水中游的动物相反,对于牧民来说,天上飞的动物由于不容易捕获,自然便成高贵的。这便是牧区的牧民将天葬视为高贵,而将水葬视为低贱的观念之缘由。
这种观念形成的确切时间无法考证,但从藏民流传很广的一则传说来看,至少在吐蕃赤年松赞时代这种观念就已经得到强化了。据说吐蕃的赞普赤年松赞曾从达布地区迎娶一位叫秦萨鲁杰的美女为妃,但那位妃子却因为吃不到鱼娃而变丑,赤年松赞知晓此事后派人到达布取鱼给这位妃子吃,她立即恢复了美丽的容貌,赤年松赞认为此物有功效,也想享用,但他吃了以后却立即染上了疾病。[11]从这个传说来看,禁渔是吐蕃王室的传统。但是疑问在于,吐蕃王室发迹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一带而非高原牧区,他们为什么也会禁食水中的食物呢?近年来,考古学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经济类型的演变轨迹是农业向牧业转变而不是相反”[12]有力地回答了这个疑问。随着藏区经济类型的转变,人们对水的思维定式也逐渐发生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苯教由于登上吐蕃“国教”宝座的位置,更是从宗教方面对这种信仰加以强化。苯教认为,有一种叫“鲁”的神,在人格化之前,它泛指居住在水中的一切动物,如蛙、鱼等。苯教的信仰体系里面一般认为,天上住着的是赞神,是善良的,它们主管世间万物,保护人类;陆地上住的是年神,似善非善,喜怒无常,它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厄运,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水中住的鲁神则是世间一切不幸的源泉。[13]6-15在一些苯教经典看来,由“鲁”引起的疾病多达几百种,譬如梅毒、溃疡、麻风等,这些病的特征大多是“传染”、“皮肤溃烂”等,因此水葬专用于葬那些患传染病而亡的人。苯教登上“国教”的位置以后将水葬当作一种惩罚政敌的手段,这一史事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历史文书P.T.1287《赞普传记》中有明确记载:“止贡赞普亦于彼时遇害,尸骸置于有盖能启的铜匣之中,抛于藏布大江之中央。”[14]157有研究表明,止贡赞普遇害,就是因为他支持了一种与苯教为敌的宗教。[15]而考查藏区的宗教历史过程,这种与苯教为敌的宗教无疑就是佛教。这也为后来苯教与佛教在对待水葬截然相反的态度上埋下了伏笔。吐蕃占领金沙江峡谷以后,苯教支配下的观念得以在这些地方强化并延续。从三岩人实行水葬的方式来看——站在悬崖上将尸体高高举起,然后抛入河中,似乎还隐藏着对尸体惩罚的心理。
转向农区,人们对水的观念正好显示出另一面。由于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农业民族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大量接触水 (比如早期人类为了方便生产多将住处建在河流附近),特别是庄稼受惠于水,使得农业民族天生对水产生一种崇拜的心理。例如,在中原农业发达的地区,考古出土的许多彩陶就刻有水的形象。我国民间广泛存在龙神信仰,原因莫过于人们相信天上的龙能够降雨。我国古代的每个朝代都有被称为国师的巫师存在,事实上,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帮助帝王求雨。藏区的考古材料也可以印证农业民族与水的密切联系。就目前藏区挖掘出的考古遗址而言,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多以农业经济类型为主的遗址中都会零星出土一些鱼骨、鱼翅、渔网或者鱼坠,其中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出土的4000年前的曲贡遗址是最有力的说明。[16]3220世纪70年代,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这个遗址一共有两期文化层,其中早期文化层遗址呈现出的是农业经济类型,而晚期文化遗址呈现出的却是游牧经济类型。[17]由于当时考古人员在这个地处澜沧江、渔业资源丰富的遗址中并未发现任何鱼骨头或捕鱼工具,因此一度认为卡若人有禁吃水中食物的习俗。然而,200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在清理早期遗址第五粮食局库区时竟然发现了疑似黄河裸鲤的鱼骨,从而否定了原先的推论。[18]以农业经济类型面貌呈现的曲贡遗址和卡若遗址早期皆出土鱼骨充分说明了农业民族与水的密切关系。对农业民族而言,水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水是农作物顺利成长的保障,它也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观念。在民间,围绕着水也发展出了许多神话,其中“大禹治水”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由于大禹治水有功,也因此受万人敬仰,成为一代名君。魏特曼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对于水影响人类的组织观念做了最充分的论述——基于农业经济而生长的中央集权制政体正是中央通过控制“水”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从田野调查的情况来看,围绕着水,羊拉也发展出了一套水崇拜的文化。在羊拉,藏民甚至有视水为“财富”的观念。譬如每年春节初一,家家户户争先恐后到神山附近的山泉去取水回家存放,他们将第一桶水称为“金水”,将第二桶称为“银水”。据说,能抢到第一桶水的家庭在来年将会发财致富。此外,该地藏民还认为水能治疗不孕不育症。羊拉境内湖泊错综分布,还有大小不一的温泉,其中位于铜矿的叫“格龙”、“散美”的温泉疗效最显著,常年接待那些结婚多年不孕不育的妇女。这种对水崇拜的心理形成后反映在丧葬方面自然会延伸出水葬好的观念。无独有偶,随着佛教传入藏区,佛教也将作为“布施”的水葬传入,两股水葬最终发生合流,从而使农区的水葬蒙上了“布施”的色彩。
四、结论
青藏高原的水葬在牧区与农区确实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但从根本上说,这些观念的形成从来与宗教信仰无关,而是基于人们的生产与饮食发展起来的。当这些观念形成后,与某种宗教信仰的某些教义发生了契合。在高原牧区,水葬更多保留了苯教的色彩;在河谷农区,则更多被佛教教义所涵盖。接下来的问题是,高原牧区是不是更利于苯教信仰的保留,河谷农区是不是更利于佛教的传播?这将成为我们今后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向。
[1]赤列曲扎.西藏风土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2]李志农.文化边缘视野下的云南藏族丧葬习俗解读——以德钦县奔子栏村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09(5).
[3](民国)羊泽.三岩概况[J].康导月刊,1939(1).
[4]许功明.排湾族古楼村丧葬制度之变迁:兼论人的观念[C]//黄应贵:人观、意义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3.
[5][美]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论[M].张海洋,王曼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M].马孆,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7]李建胜.从考古材料看青藏高原原始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历程[J].农业考古,2012(4).
[8]梦煜.藏族食鱼规避的成因与演变[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9][英]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0]Simoons,Frederick J.Eat not this flesh:food avoidance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M].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11]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摘译[J].黄颖,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4).
[12]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J].中国藏学,1993(3).
[13]丹珠昂奔.藏族神灵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4]陈践,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15]孙林.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6).
[16]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17]童恩正,冷建.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J].民族研究,1983(1).
[18]李永宪.遗址动物遗存生业模式分析——橫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J].四川文物,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