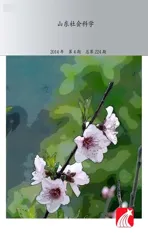中国传统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及其时代价值
——基于闽南地区的调查
2014-12-03高和荣张爱敏
高和荣 张爱敏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互助是在互惠基础上以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乡村互助养老是建立在乡土互助文化基础上的家庭、家族、邻里及村落成员之间的养老互助活动。乡村互助养老是一种蕴藏于乡土社会中的非正式福利制度,长久地存在于传统社会里并发挥着作用。那么,在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日渐完善的今天,这种民间的、非正式的乡村互助养老有哪些新形式和新内容,这对于完善我国养老福利体系有何借鉴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各类人员的养老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早在1982年就有学者从促进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角度对乡村养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在关注“生小”的同时要注重“养老”问题的解决。[注]阎卡林:《发展老年保险和老年服务事业是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战略性措施》,《人口学刊》1982年第5期。一般认为,养老涵盖“谁来养”、“怎么养”及“养得怎么样”等方面[注]王述智、张仕平:《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及其研究的思考》,《人口学刊》2001年第1期。,它构成了人们对乡村养老问题的分析框架。
谁来赡养老人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前提。自古以来主要通过文化与习俗强调要依靠子女实行家庭养老。《孝经·圣治章》写道:“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母生之,续莫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注]《孝经·圣治》第九章。。这表明,子女孝敬并赡养老人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是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亲子关系及儒家孝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亲子关系呈现一种有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反馈模式”[注]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上一代抚养下一代,待上一代年老之时下一代有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为此,《论语》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当然,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国家也要承担养老责任,《礼记·王制》就说过:“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尽管如此,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与主体。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老年人口扶养比增大、代际隔阂不断扩大的冲击,这就需要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办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养老方式是养老问题的重要方面。陈静、葛晓萍认为,家庭养老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我国农村养老最初表现为氏族公社时期的“集体供养”,后来才逐步转变为“家庭供养”[注]葛晓萍、李澍卿、袁丙澍:《中国传统社会养老观的变迁》,《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林兴龙对汉代民间养老方式的考察发现,汉代民间养老以“家庭养老为主,政府支持为补”[注]林兴龙:《汉代民间养老问题与现实思考》,《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沈关宝的研究发现,互助养老是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它与集体、家庭及政府等养老方式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养老的主要方式[注]沈关宝:《从民间互助到社会保障的制度改革与观念转变》,《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3期。,当然这种互助养老方式是在家庭养老及集体养老基础上形成的,它以家族为基础。袁同成对义庄的分析也佐证了沈关宝的观点,古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是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注]袁同成:《“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理论导刊》2009年第4期。。干咏昕对先秦以来民间互助养老形式的考察发现,我国民间互助养老形式包括血亲宗族、宗教、姻缘、地缘及业缘养老互助等形式[注]干咏昕:《中国民间互助养老的福利传统回溯及其现代意义》,《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7期。。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城镇化的兴起,农村空巢家庭的大量出现,并不意味着社会养老就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必然选择,汲取各种养老方式优点采取互助养老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一些学者探讨了乡村养老互助新模式[注]高和荣、蒲新微:《论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西北人口》2003年第3期。,指出在现行乡村养老互助中应当积极发挥乡村社区的养老功能,创建“社区养老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乡村养老资源,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注]周伟文:《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危机与变革——基于冀南前屯村养老方式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崇维祥、安娜青:《乡村社区养老模式探析》,《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赡养内容是养老的重要方面。一般包括“物质供给”、“生活照料”与“精神安慰”三个层面[注]张敏杰:《论“家庭养老”模式》,《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由于物质供给的可度量性以及中国长期处于匮乏性时代,人们往往从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层面进行分析。例如,张仕平等人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养老情况发现,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家庭保障、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养老,经济支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重要考量[注]张仕平、刘丽华:《建国以来农村老年保障的历史沿革、特点及成因》,《人口学刊》2000年第5期。。如今,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农村老龄人口的增多,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得到了重视,人们日益意识到完整的老有所养应当包括物质供给、生活照料及精神安慰,三者不可分割,“任何偏废一方的做法都有损老有所养的质量”。[注]穆光宗:《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社会》1995年第4期。
总体上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挖掘传统养老文化,分析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养老互助的积极功能,总结了宗族、邻里及社区养老互助形式,这对于深化乡村互助养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一定的意义。现有的研究虽然看到了乡村互助养老具有历史文化性,却没有看到乡村互助养老与中国以家为圆心的关系社会能够相嵌入,因而很容易忽视乡村互助养老的时代性价值。不仅如此,现有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田野调查,没有充分挖掘乡村社会里互助养老形式与内容。为此,本文采用访谈法对福建闽南地区乡村养老互助传统进行实地调查,调研对象以年龄大于70周岁的老人为主,请被访者回溯民国以来所形成的互助养老形式与内容,以便存留中国传统乡村养老记忆,并为完善中国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供建议。
二、闽南地区民间互助养老传统形式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在缺乏制度化社会养老保险的时代,家庭自我养老以及民间互助养老就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这种民间互助养老按照血缘关系及空间距离的远近可以划分为宗族型、姻亲型、邻里型以及社区型等四种基本形式。
一是以过继和孝子会为主的宗族型互助养老。宗族型互助养老是以血缘为纽带发展起来的互助养老形式,这是民间社会最基本的互助养老形式,它包括本家族内部各家庭以及本村同一姓氏内部成员向所要帮扶的本族老人提供从食物、护理到丧葬等方面的帮助[注]卞国凤、刘娜:《乡村互助传统及其变化与乡村社会福利建设》,《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6期。,使之能够安度晚年。前者采取“过继”形式赡养老人,后者由本村同姓成员组成的“孝子会”帮助老人。在传统民间社会里,养儿防老是人们的主要养老观念,那些没有生育儿子的老人其养老送终愿望只能采取其他途径予以实现。调查发现,民国以来该镇宗族内部就通行过继儿子的养老做法。所谓“过继”,就是本宗族内部那些没有生育儿子的家庭可以在兄弟或同一宗族内部其他人员的子氏中“认个儿子”,过继时举办宴席,邀请过继者的亲兄弟或宗族成员作为见证人在一种名为“新书帖”的单据上签字,签字后这种过继行为将取得合法性认同,“新书帖”由过继者保存,以便日后宗族内部有人对被过继者身份质疑时充当证据。被过继者承担起养老送终责任,同时继承老人名下的所有遗产。
该镇有位农民叫吴老六,男,1937年生,膝下只育有3个女儿。女儿成年后均已嫁为人妇。吴老六为了实现有子养老送终的愿望,请族长在家族内部为其过继一个儿子。在族长及双方家庭共同协商下,吴老六最终选择了其堂兄的次子吴小三为过继对象。待吴老六年老体弱需他人照顾之时,吴小三承担起了赡养张老六的责任,为老人提供吃穿,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老人去世后,吴小三以儿子的身份为其养老送终,每年清明时节为老人扫墓。作为回馈,他继承了吴老六名下的一套房产和几亩田[注]本文中所列案例均为实地访谈整理所得,此案例访谈时间为2013年8月28日,访谈地点为福建省新罗区大池镇,访谈对象姓名吴某某。。
“孝子会”作为一种互助组织也广泛存在于民国时期该镇各村同一姓氏人家。它以本村同一姓氏家庭为成员,会长由同姓中名望较高的老人担任,本村同姓成员可自愿决定是否加入其中。加入孝子会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每位成员须缴纳一石米作为“会费”。会长将会员缴纳的米进行出租,赚取利息作为孝子会的运作资金。当本族老人出现生活困难问题时可以向孝子会提出申请,会长根据申请人的情况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同时,一旦有老人过世,其他会员要向该家庭缴纳一斗米作为互助资金,以解决该家庭在办理老人丧葬仪式时的资金压力。这种互助是在本村同姓内部成员间的互惠活动,是传统民间社会应对养老问题的解决之道。但是,据老人们回忆,孝子会在上世纪30年代就逐渐消失了。
二是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姻亲型互助养老。表现为外孙过继、招赘、外嫁女儿对于女方父母的赡养等,其中以外孙过继及招赘最为典型。发生在宗族外部成员之间的外孙过继是这个地区较为独特的互助养老形式。对于那些只生有女儿的家庭可以选择将已出嫁的女儿所生儿子过继回来给自己的外公外婆养老送终。通常,外公所在的宗族内部会举行一场过继仪式,外公将自己的几个亲兄弟请来让这几个兄弟轮流在一种名为“新书帖”的单据上签字,以示宗族内部承认这种外孙过继形式,同时将过继回来的外孙之名用红纸书写后贴于宗族的祠堂内并载入家族的族谱当中,进一步强化外孙的身份认同。与家族内部过继相比,这种过继形式对被过继者的要求更高,因为外孙的姓氏要改成外公的姓氏并定居在外公家而不能回到其原来的家庭,否则,即使他承担起了赡养老人义务,也将失去老人财产的继承权。
假设实际上的运动为如图1(a)中小方块从位置a移动到位置b,而摄像机位置c是固定的,而根据运动的相对性可认为的运动关系为如图1(b)中的运动方式,即可认为是摄像机从位置c移动到位置d。
张大坤,男,1933年生,老人育有一女,女儿婚后生下两子。为了实现有子养老送终愿望,老人希望在宗族内部通过过继形式认一个儿子,然而,宗族内部没有合适对象,于是他将自己的外孙作为过继对象以延续其香火,待其去世之时,该子可以获得张大坤老人名下的一套房产。而条件是他的外孙必须更改姓氏后居住在老人家中与老人一起生活。后来,他的外孙不愿居住在老人家中,虽尽到了赡养老人责任,然而他欲将老人房产出售之际遭到了老人及宗族内部人员反对[注]此案例访谈时间为2013年8月30日,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大池镇,采访对象张某某。。
闽南地区特别强调有个男儿在身边为老人养老送终,除宗族内部过继、外孙过继之外,他们还采取招赘方式承担老人的赡养义务。无论是宗族内部过继还是外孙过继都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而招赘则使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连结在一起,实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养老互助,扩大了赡养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女方家庭采取通婚方式让招收上门的女婿扮演起“儿子”的角色。该镇的上门女婿需改姓女方姓氏,这是进入女方家族族谱的条件与依据,一般也需要制作“新书帖”作为凭证。待双方父母年老体弱需他人赡养之时,男方既要承担起亲生父母的赡养责任,也要肩负起为岳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
三是邻里型互助养老。邻里间互助也是乡村养老互助传统的重要形式。它一般是相邻而居、非血缘关系的人们对于那些无法过继或者招赘的老人给予物质供养与生活照料,使老人能够安享晚年,最主要发生在空间相邻的留守老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邻里型互助圈子半径大致为一个“里”,即聚集居住在同一个庐舍或宅院里面的各户人家。从养老内容来看,邻里间养老互助主要体现在对于老人的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两方面,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照顾、陪老人聊天以及丧葬仪式上的互助。这些老人由于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在生活起居方面难免需要一些帮助。此时,邻里间的互助起到了独特优势,相邻而居的人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彼此间基于地域优势转化为一种“朋亲关系”,在称呼上仍可以遵循宗族内部的辈份称呼。在这种“朋亲关系”下的邻里互助本质上也是一种“换工”和“互惠”行为,一种基于获得对等互惠心理而发生的互助。相邻而居的人们对于生活起居较为困难的老人进行照顾比比皆是,为这类老人从集市上捎回一点生活必需品,帮助老人搬弄家具、修理家用品,给老人送上一些时令果蔬等无不洋溢着邻里间尊老敬老的和谐风尚。
传统乡土社会生活清苦,温饱成为了老人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在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较为简单,主要集中在聊天、参加婚嫁庆典等方面。在乡村,经常可以看到三五个老年人坐在房檐屋下聊天的场景,老人们聊聊村里新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谁家娶媳妇生孩子,哪个老人又过世了,自家子女在外状况等。丧葬是乡村社会里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互助养老的最后环节。在该镇,一旦遇上老人过世,主人家不能亲自料理丧葬的相关事宜,必须全权委托其他人进行处理。此时,邻居们一般会主动前来帮忙料理丧葬仪式上的相关事宜,不需要有相应的邀请活动,以换取下次自家遇上类似事件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人同样的帮助。这种邻里间丧葬仪式上的互助行为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以地缘性关系为纽带,本着互惠互利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并发挥功能。
四是以互助基金会为主导的社区型互助养老。乡村互助基金会是以村为单位,由村委会发动建立,鼓励乡村中的富裕家庭向基金会捐款,以便在逢年过节或突发性事件发生时资助本村生活困苦的老人,本村小孩升学或考取功名也能够获得基金会的奖励。捐赠者在捐赠一定金额后可以获得由村委会发放的一本荣誉证书,并刻碑表彰。这种互助基金会最早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该镇一些早年参加国民党的人员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他们到台湾后就组成同乡会联络同乡情谊,同时关注家乡人民的生活,向那些成功人士进行劝募以资助远在家乡的孩子完成学业,解决家乡老人的生活困难,为家乡建立老人活动中心,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福利。
上述情况表明,乡村社会中养老互助风尚盛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这里得到了诠释,它以乡村社区为界,将身处其中的人们通过血缘、姻亲以及地缘而织成一个养老互助的关系网络。这种乡村养老互助呈现三个特点:
首先,闽南地区采取宗族及姻亲互助养老形式解决了农村中无儿子的家庭赡养老人这个难题,通过邻里互助及基金会资助等形式丰富了农村老人的物质供养及生活照料来源。缘于闽南地区较为浓厚的宗族文化,宗族在乡土社会中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通过宗族举行的过继、入赘、孝子会等形式强化了社会对赡养老人的认同,也使得农村无子家庭接受这种赡养形式。从内容上看,乡土社会的养老互助重点从原来的解决温饱问题到现在的老年照顾及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方面。这增进了乡土社会里老年人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其次,纵观闽南地区存在的各种养老形式中,宗族型养老互助尤其是孝子会的功能有所降低,孝子会逐渐与邻里互助及基金会等农村自组织进行整合以便更好地解决老人赡养问题。其中,姻亲型互助养老日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邻里型及社区型互助养老更容易整合乡村资源,这四种互助形式相互交错,构成了乡村养老互助网络,在促进乡村养老互助持续发展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在表现形式上,这些养老互助形式往往通过过继、婚嫁、庆生、丧葬、扫墓、祭拜等仪式得以认同与强化,人们通过各种仪式搭建起了参与者间沟通信息和情感的平台。这些传承于先祖的仪式性活动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维系了乡村社会间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
再次,在制度化社会养老保障普遍缺失的年代,养老互助在解决乡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与乡土经济、乡土文化及乡村生活嵌入在一起而成为功能一体。即便在制度化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形成并日趋成熟的今天,乡村养老互助仍然具有很强的时代调适能力,它弥补了农村制度化养老服务尤其是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普遍不足问题。乡村养老互助成为国家论和市场论福利意识形态之外的“第三种体系”[注]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6页。,与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一道筑成了我国乡村养老福利体系的安全网,共同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三、中国乡村养老互助传统的时代意义
通过对民国以来闽南地区该镇养老互助传统的回溯,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民间互助养老传统在解决中国乡村养老问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在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日臻完善的当代中国农村,这种民间非正式制度安排还是能够有力地克服制度化养老保障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第一,乡村养老互助有助于促进养老问题的全面解决。作为一种正式性的制度安排,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是以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政策的形式被确定下来而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与行政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但是,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更多地侧重于物质供养方面,而以生活照顾及精神安慰为主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很多地方尚未普遍地建立养老服务体系,这就为民间养老互助功能的发挥留出了空间。同时,乡村养老互助功能的有效发挥使得民众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与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进行对比,这就对于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构成了无形压力,促进了农村正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避免了制度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流于形式。因此,农村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与养老互助构成了一张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安全网,促进农村养老问题的全面解决。
第二,乡村养老互助传统是农村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的支撑与补充。一方面,乡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福利安排,是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养老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产物,与乡村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相契合。这种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生活习俗正是制度化养老保障制度形成的社会基础,为制度化养老保障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发挥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人口超过6亿、散居在乡土社会里的广大农民来说,制度化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无法涉及到养老问题的全部,无论是“五保”供养制度抑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保障水平还仅仅在于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时,乡村养老互助在老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方面的功能发挥可以填补制度性养老保障体系的空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完美结合为农村养老问题的全面解决创造了可能性。
第三,乡村养老互助传统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福利水平。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下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有力保障,但它是一种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导向的低层次福利状态。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后会衍生出对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建立在传统养老敬老文化基础之上的民间养老互助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使得整个乡村养老事业更加全面和立体化。同时,乡村养老互助传统的发展有利于整合乡村养老资源,减少农村家庭养老矛盾,促进乡村社会稳定。
在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日臻完善的今天,民间养老互助传统对于我国养老福利的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成为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一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民间互助养老是民间社会解决养老问题的创举与智慧结晶,是贴近民间生活、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应该努力寻求民间养老互助传统与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的最佳结合点,挖掘乡村养老互助传统的合理内核,调动各方资源,充分挖掘民间养老智慧,努力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中国养老福利事业的长足发展,为人类社会福利事业贡献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