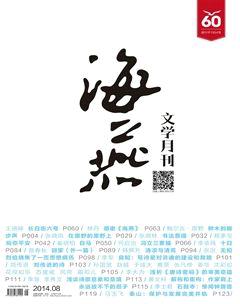冯立三素描
2014-08-15何启治
何启治
一、“启治……是我当年在唐山(地震)废墟前一见而遂定终生之交者。”“互相赏识,彼此敬重,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1992年岁末,我讲述自己在纽约华人餐馆打工经历的体验及见闻感想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教授闯纽约》即将出版,请立三作序。他在写于1993年2月2日的序文《殊堪玩味的唐人街风情》中,开门见山就说:“启治是位重事业又重道义,既有文名又有人望的人,察世敏锐冷静,做事勤奋认真,内心炽烈如火,外表恂然蔼然,是我当年在唐山(地震)废墟前一见而遂定终生之交者。”
立三之序,对我多有策励,“而遂定终生之交者”之说,则让我永远感念于心。
为什么“在唐山废墟前一见而遂定终生之交”呢?
原来,这与我们在唐山大地震11年之后的一次唐山之游有直接的关系。
1987年9月26日,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冯立三等人应友人之邀来到唐山。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凭吊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的唐山7.8级大地震的遗址,面对着大地震的牺牲者和幸存者,肃立在特意保留下来的地震废墟上。
我们在游览中不但亲见了新唐山的建设成就,而且也从一些细微之处体察了新唐山人的文明礼貌和谦让友善。我不由得想起立三曾经不满于唐山抗震纪念碑四周的美术浮雕,批评说这些作品过于直白浅露,没有很好地表现出唐山抗震斗争过程中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建设和大振作。我想立三的批评不无道理。然而,这些宽阔的街道,这些风格多样的新建筑,这么美丽可爱的街头公园,这么友善、乐观、好客的唐山人,这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地震大火中重生的一切,大概可以弥补那些抗震纪念碑四周美术浮雕作品的不足了吧。
当晚,在我们下榻的唐山饭店210号套房里,我和立三有过一次几乎是彻夜的长谈。
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唐山大地震的牺牲者谈到了这些年来在极左路线肆虐中受到政治迫害的牺牲者……
原来,冯立三在北京男四中念书的时候,就是一个品学兼优,不带一点水分的三好学生。1958年,神州大地到处响遍了“大办钢铁”、“赶英(当时年产1070万吨钢)超美”的壮烈口号,城乡处处都冒着小土高炉的滚滚浓烟。此时,年仅17岁的热血少年冯立三也怀着一颗爱国爱党的纯真火热的心,活跃在北京男四中的“炼钢”工地上。一天,这个小班长领着四个同班同学拉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竟然冒冒失失地直奔几十里地之外的石景山钢铁厂去讨要耐火砖。面对这一伙纯朴可爱的少年,工人师傅还真给了他们一车耐火砖。兴奋得意之余,他们竟不愿稍事休息,装好车就往回赶,硬是在星星眨眼的当天夜晚赶回了学校。流了一身汗,可半块砖也没丢。然而毕竟是路远无轻载,何况是满满登登的一车耐火砖,何况是漫长而坎坷的路,又何况是靠凉水冷馒头充饥,身子骨都还没长壮实的几个孩子,把一车砖拉到工地,他们就趴下起不来了。
就这样和着热血少年的汗水炼成了一块块铁疙瘩。然而这心血的结晶却没人收,没人要,终于又成了一堆锈迹斑斑的废物!
随后,冯立三这个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之为“老三”的班长便以超过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的优异成绩通过了高考。然而,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政审通不过,他竟被打入另 册分到了师范学校。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安、治国跑来安慰他。大安像狮子一样咆哮说:“老三从上小学到现在考大学一直当干部,就当成这么一个结果!银质奖章白得了!‘互爱杯足球冠军管屁用!真的不带一点水分的‘三好,这种学生全北京能有几个!他不能上北大,谁能上北大!”他大喊:“虚伪,什么玩意儿!”
立三静静地坐在地上听他喊,默默地垂泪——已经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深深的感动而泪流满面。呵,虽然不是“宴桃园兄弟三结义”,却是“哭四中三人一条心”呀!
师院就师院吧,立三提醒自己决不能自暴自弃!他依然是勤奋好学,依然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当他从一个单纯稚嫩的少年成长为有了专业知识的青年时,在面临大学毕业分配的日子里,想不到更可怕的迫害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认定为“思想反动”的学生而受到有组织的反复批斗。
究竟是些什么罪状呢?
一曰: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原来,是他在学习周恩来总理关于在困难时期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新方针时,痛苦地回顾了“大办钢铁”炼出了一堆废物的事实,而表同情于彭德怀的“得不偿失”论;因热衷于钻研政治经济学,并认为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如不适应则将破坏生产力的立论是个真理,而在师范学院的学生讨论会上说过“人民公社是共产风的母亲”这么一句名言。
二曰:为“右派分子”王蒙鸣冤叫屈。事实是,冯立三在师院中文系读书时(1960~1964),适逢当时被错划为“右派”的王蒙由于当年师范学院院长的关照被安排任王景山教授的助教,曾在他所在的班级任课。立三有幸为王蒙所看重,请他到家里吃过一次饭,倾听了王蒙夫妇含泪所讲的经历。他很同情,也很不平。他实在看不出这位穿着破毛衣与学生一起打乒乓球、赤膊与学生一起劳动、说话和气幽默的青年教师有哪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又听说伟大领袖都关心过他,说过中央有的部的官僚主义比北京市一个区委的官僚主义更严重一类的话,于是就为他,以及他的成名代表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公然作了一些辩解。
三曰:“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这指的是他看了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认为都是好作品。还特别欣赏《静静的顿河》的史诗品格,欣赏它对哥萨克生活描写的无比生动,欣赏格里高利形象深刻的典型意义,竟不同意说它是“修正主义货色”。
四曰:“攻击党的阶级路线。”这指的是他曾经说过“60年高考录取新生有唯成分论的倾向”。这话其实没有说错,事实如此。批判唯成分论,并不是对党的阶级路线的攻击——难道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唯成分论吗?
……
在批判他的会上,他曾经勇敢地自我辩护。他原以为老师和同学听了他的辩护之后能理解他,实事求是地宣布他无罪。他太天真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领导因此反而被激怒了。原定一周的批判延长为两周,连家也不让回了。
一位党的负责人还警告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院党委还可考虑按正常情况分配工作,否则……
面对这些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和以党的化身自诩的负责人的警告,即将大学毕业的冯立三深知等待着他的将是多么严酷的抉择:满腔的热血和良知都告诉他决不能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然而他也完全明白那个“否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又不难想象“反动学生”的帽子将压得他一辈子都翻不过身来!
呵,还能到哪里去申诉?还能跟谁去讲理?他真是百口莫辩,欲哭无泪了。对方有权有势,运动群众,封住了他能言善辩的嘴巴。口号声和申斥声震得他晕头转向,只觉得脚下冰冷的水泥地都在摇晃。
一个黄昏,他在万分痛苦中,急不择路地出了校门,又鬼使神差地奔向离学校最近的深水池——玉渊潭。夕阳如血,流水多情。也许,这里就是他年轻生命的归宿吧。有道是,一了百了,把青春和生命都托付给一池碧水,也就无所谓烦恼,无所谓痛苦,无所谓幸与不幸了。奇怪的是,当他正要纵身跳入深水潭时,微波荡漾的水面上却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墙——由母亲和四个弟妹一道组成的一堵人墙横在了他的面前。是的,左看是这道人墙,右看也是这道人墙。慈爱的母亲的惊慌的面容和稚嫩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熟悉的身影都活生生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们仿佛都在呼喊:孩子,莫轻生啊;哥哥,你死了谁管我们哪?……
他痛苦地蹲在草地上,双手拔扯着自己的头发,终于发出了一声备受戕害的男子汉的深深的叹息。
痛定思痛,他从死神的手里又回到了人间,忍痛在那张差点要了他命的“结论”上签了字。他倔强地紧闭着嘴,不再说话。
然而,可怕的是厄运果然从此伴随着他。他太执拗也太幼稚了。1965年他在劳动实习的时候,居然又声称“重压之下难有真情”,便斗胆上书北京市教育局,洋洋数万言,据理力争,要求甄别。那结果可想而知。
立三说,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便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政治贱民而饱受折磨。“红卫兵团背后有人统计冯立三先后翻案达九次,属于死不改悔!红卫兵接受指导,对我‘大开杀戒。‘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到了兑现自己决心的时候了!我站直,说:‘打吧!但我告诉你们,中央有个16条,谁违背16条,弄出人命,将来也会吃不了兜着走!他们冷笑一声,下手!一次一次下手!皮带、棍棒、铸铁椅子腿,我都品尝过。最后訇然一声,四五腰椎崩裂。试着爬起来,下肢已不听使唤!”
完了,冯立三从此致残!
立三说,我不怨北京市右安门一中。这是城乡交界,流氓无产者意识浓厚,容易接受忽悠——煽动。根子在于1964年那次伤天害理的政治虐杀。否则,何来翻案,又何来镇压翻案!……
后来,主要根据立三受极左政治迫害致残的事实,加上我所知道的,在“文革”中老舍被迫自杀和我在武大中文系的老师刘绶松教授自杀的事例,写成《唐山地震废墟前的沉思》一文,刊发在1989年第1期的《当代》杂志上。
我在此文中,根据自己的思考得出结论说:“政治地震的震源比自然地震的震源更深更远,政治地震后的波及面比自然地震的破坏范围更宽更大,而平息医治政治地震的破坏后果,也显然远较治愈自然地震的创伤要更复杂、更艰难一些。……今后如何防止和根除新的政治灾难、政治地震的发生,实在有赖于我们大家的同心协力呵!”
关于立三,我写道:“他也在拨乱反正历史新时期曙光的照耀下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而且凭着自己的正直果敢和学识才气,成了当今文坛上颇受人敬重的文艺评论家。”又说,“刚直而极富个性的冯君慨然陈辞,从自己的经历谈到了最痛苦时的种种感受。于是,一个坚强而又痛苦的政治迫害的幸存者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至于立三对我,除了本文开头引用的对我备加赞赏、鼓励良多的话之外,关于拙著《中国教授闯纽约》,他在序中还不吝赞美之词说:“简洁而不简陋,轻柔而不轻浮,动人而不刺激,纯洁的感情与纯洁的文字交相辉映,十足的东方情调,确是好手笔。所谓朴素是艺术的高境界,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版我和冯立三、岳建一、章德宁及已故杨志广等五位编辑朋友的散文合集。立三在序言中,在谈到他和我的上述交谊之后,得出结论说:“互相赏识,彼此敬重,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此话甚合我心。
二、“从1980年冯立三进入《光明日报》,到1989年他离开报社,这十年……他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参加过许多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研讨活动,成为活跃的文学评论家。”
以上,主要讲述了冯立三人生成长历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幕:被打致残和自杀未遂。资料来自拙文《唐山地震废墟前的沉思》和冯立三主编的《与子同袍——从北京四中“白屋”走出来的人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0年9月北京第1版)中的《冯立三自述》。
下面,让我们再来简要地回顾一下冯立三的成长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的奋斗历程。
冯立三,1940年生,山东昌乐人。初中毕业于北京一中,高中毕业于北京四中,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
“‘文革后,‘白屋同窗(按,即北京四中首届文科班同学)秦晋一力保举我进《光明日报》文艺部。我时来运转,瞬间天上地下,入党、提干、提职、提级、评奖、分房、入作协、进作协,最后官至正局,职当主编——这不是小人得志,穷显摆,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不会比那些傲慢狂妄的革命派低能!极左政治代表的是愚昧、野蛮,他们才是小人得志!”(见《与子同袍·冯立三自述》)冯立三对极左政治可谓恨之入骨!
冯立三于1980年经秦晋力荐从北京市右安门一中调入《光明日报》文艺部之后,到1989年北京风波《小说选刊》被迫停刊前的10年间的状况,乃久在《莫道人生多变幻,粗缯大布裹生涯——记60届校友冯立三》一文(收入《与子同袍》一书)中, 有简要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