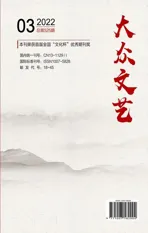浅谈中国“学院派”民族民间舞的困境与出路
2014-07-14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北京100081
刘 柳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北京 100081)
浅谈中国“学院派”民族民间舞的困境与出路
刘 柳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 北京 100081)
学院派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学科性注定了学院派“这一个”的必备天赋即权威性、规范性和类型化。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和精英主义式的姿态冠冕堂皇地高喊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 “源于民间,高于民间,既不失风格又科学规范”时,我们还应调用一种文化批判的眼光和实践的力度来审视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在文化自觉和权力场域中“学院派”与“民族民间舞蹈”在权力关系、文化格局、价值动机及意义指向上的内在悖论及其所可能具有的裂隙与张力,并在反观自照中引发思考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如何在多元文化格局和多级话语拉力中完成新一轮自我更新的重要议题。
学院派;民族民间舞;重要议题
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自诞生的那刻就天然携带着现代性内在的逻辑悖论,它是启蒙现代话语和现代民族意识双重绑架的产物。无论是艺术作品的创作,还是比赛标准的设定,都无不反映狰狞的现代性内部二元结构的对立,表现在中国学院派民族民间舞内部就呈现为“审美失语”“实践萎缩”与“精神分裂”三大症结。
“学院派”民族民间舞作为现代教育体系下的知识类型,始终伴随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并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茁壮成长,因而内在地具有学科化、精英化、技术化和模式化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科学的进步话语漫天飞舞,中国学院派民族民间舞也深受其害。为了被世界文明体系承认,为了实现所谓的“文明”和“先进”,我们抛弃了多元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扰乱多样民族的文化秩序,忽视动态的民族生活与情感,为了赢取外来权力的认证,获得“文明先进”的光荣称号,我们不惜一切地背离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意义泛白和道德缺失中杀死了让自己得以安身立命和生生不息的“神”。于是,“东施效颦”和“不中不洋”就成了当下学院派民族民间舞尴尬和无奈的结局。从时间安排到空间设计,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都深受西方话语和文化的操控,裹挟着浓重的现代化痕迹。
学院派民族民间舞作为一种权力的发明和身份的设置,掺和了权力因素和资本逻辑,不论从作品的制作动机、创作立场、表现手段还是从作品生产消费的途径和评审标准而言,都夹带着不同文化主体对权力伸张和资源争夺的动机,它是现代性话语生成和不同权力主体争夺的场域。
学院派民族民间舞与其说是时间的,不如说是空间的;与其说是文化的,不如说是政治的;与其说是民众的,不如说是精英的,与其说是艺术审美的,不如说是权力修辞的。
总之,当下学院派民族民间舞在“民族、文化、艺术”等这些政治无涉的公共表象下,征用着一套启蒙理性逻辑和发展主义话语来遮蔽强势文化的殖民痕迹,矫揉造作地引用一套民间化的表述,高举文化旗帜进行“狸猫换太子”的游戏。由于过多地专注以知识技术为棋子的权力竞技,从而导致了学院派与民族民间舞蹈的断裂,封压了民族文化自身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在不均称的话语格局中兜售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势文化价值。而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已被20世纪中期的历史给全盘洗劫和污染,其理念根数根植于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进步观。随着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此理念谱系不但移植成功,而且深入民心。导致大多数人在今天都无意识地将“民族舞蹈”等约于少数民族舞蹈,并将“少数民族舞蹈”挂靠在自然原始野蛮的序列之中,极力将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打造出“原生感”与“神秘性”。如此的“刻板”印象反过来又制约着以宏大优美为主导美学理念和以技术规范为主打旗号的“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在整理、加工、提炼和发展素材的空间,引发了不必要的创作焦虑与道德责难,并在不同权力场域发号的所谓 “保护和发展,传统和现代”等二元系列的持续纠缠下,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出现了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陷落在“失语、自闭和分裂”的境地。
然而,学院派民族民间舞的内部尴尬又为学院机构外的不同权力主体提供进行民族文化“另度”创作的可能。以“杨丽萍”为代表的“原生态”映像系列制作为例,其创作不论从舞台定位、命名、设置、演员的选取和动作的编排上,都以“反学院”的方式再次跌进民族文化的定型色板中,顺势地继承了现代性话语的内部传统,再次印证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对“他者”的强制规定。
由上可见,不论在学院内部还是外部,当下民族民间舞蹈的编创,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这一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难以自拔。而历史的复杂与开放却告诉我们,单数的主体与静态的文化从来都是近代以来的政治设计,与其相反的是,生活之树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中有相似,相似中有差异。或许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一个民族是什么,而能做的是通过“民族”这一绑缚了超负荷欲望却又过分失效的主体单位,呈现出我们自身及其时代中的恶与罪。
也就是说,祈求用民族民间舞蹈来体现我们是谁?或他们是谁将会是个天方夜谭的事。因为,没有谁,包括民族内部的人会懂得问题的答案。所以,对文化的理解应该在交流中。因为交流始终都是个历史的过程,在其中谁也无法决定谁,惟有不断缠绕的关系,难解难分的缘分。
笔者认为,由外部发起的民族文化保护运动,及相应的内部民族自觉与意识的激起,造成了民族文化“本质化”,民族舞蹈脸谱化的问题。而尊重他人文化是民族民间舞蹈编创的基本前提,但问题是现在我们尊重的只是自己对他人的愿景。他人被我们形塑成没有历史的“化石”,以致于我们能按图索骥地识别出他人文化的身体样式和精神模式。然而,一旦“身体与精神”进入被用以识别与计算的轨道,“标准化”就成了文化进程和艺术创作的炸弹。
全球化背景下接连不断的民族自觉运动和身份认同需求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动摇着一体化、技术化、程式化为导向的学院派路线,文化多元主义景象对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的“准字号”生产和“画地为牢”的现实提出了难以回避的挑战。除外,在“生态文化”的大语境下生产的“原生态”或“衍生态”也相应引起了以一体化、技术化和模式化为志向的学院派艺术的阵痛和危机,同时也变相地促进了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进入新一轮的自我重估和更新。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技术支持和知识支撑,学院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如何在独断论失效,多元主义范式兴起的情势下重估自身,反思学院派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民族话语权与民族民间舞蹈的关系,进行一场自觉的自我重估与生态更新,将是我们每一位文化学人不可小视的问题。
在重审学院派民族民间舞生成背景和制作策略时,我们除了要意识到学院派民族民间舞的内在悖论外,还要看到体制内部也存在投放和挖掘多样性和创作力的可能。
学院派内部的危机矛盾和模糊两可也是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赢得自我更新和生成的机遇,它提供了学院派一条参与社会实践的别样路径和用以爆发的内在动力,其前提就是我们学院派需进行一个彻底的自我反思和估算,为此才能实现自觉的自我转变和更新。
总之,此次的重估不是反叛,它只意味着在既有范式上的超越和本体语言上的尝试,即对可能性的探索和多样性的追求,它是当下本质主义范式转型的写照,是多元文化主义在艺术创作上的启示,它需要我们在自我批判,自我觉醒和自觉定位中学会自我更新,思考“学院派”民族民间舞蹈的机体结构弹性,思考开拓前景的多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