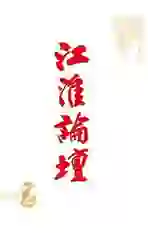庄子与尼采的生命美学比照
2014-05-27刘小兵
刘小兵
摘要:庄子和尼采在通向“逍遥游世”与“醉艺狂欢”的自由之境时,庄子主张个体应依托“心斋”、“坐忘”的方式来荡涤一切违背本性的外在羁绊,达求返璞归真、与道为一、自在逍遥的自然澄明之境;尼采则追求个体要历经从骆驼、狮子、小孩的精神变形,持守本真性灵,最终成为具有强力意志的充满激情与创造活力的生命舞者。庄子的“至人”和尼采的“超人”虽说皆是理想人格模式,但庄子推崇在“清静无为”中彰显性灵,尼采却信奉在“狂放有为”中创造人生。
关键词:庄子;尼采;生命哲学;审美观照
中图分类号:B223.5;B51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099-005
庄子和尼采作为叛逆哲人出于对生命和万物的热爱,皆对传统思想观念作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庄子和尼采虽说是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著名哲学家,面临各自的时代背景却是有着诸多的相似,即二人皆对各自的文化传统提出了彻底的批判,张扬人的自由精神。庄子与尼采生命哲学的主线就是从自由的审美视角去观照生命本体与自然造化,最终追求个性解放与形而上的内在超越和自由佳境。
一、“逍遥”与“狂欢”:体验生命自由的思想特质
庄子和尼采都把“自由”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并信奉人理应摆脱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桎梏,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庄子和尼采都对传统价值理论进行强烈的批判,信奉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但两者毕竟源于迥异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环境。庄子着重抨击儒家伦理压抑人性,强调应该从精神层面上拓展人的视野和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尼采认为基督教理论导致了人的精神颓废故而极力主张突破思想禁区而迈向新的自由领域。
生命哲学倡导更多地关注生命存在的形态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话题,并为生命的完善提供思想和方法论。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1]强调哲学的基本使命是通过反思为人类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关注现实生命存在和探索理想生命形态就是庄子和尼采重要的哲学视野。李泽厚指出:“庄子是最早的反异化的思想家,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个体身心的绝对自由。”[2]庄子祈求的生命自由在实质上是砸碎个体外在枷锁的“出六极而游乎尘垢之外”的绝对精神逍遥。庄子在人类生存方式上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倡导的自由是不受任何束缚的纯粹自由。“逍遥游”的特点就是个体抛开一切依赖和凭借后的“无待”心境。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面对残酷现实环境中的一切倍感失望,不再希冀在现实社会中去寻找自身的价值,而是转向了精神苑囿,并在那里营造出一个性灵避难所。黑格尔说:“现实世界的人们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在彼岸世界里才成为抽象的现实。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内心寻找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有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3]庄子的“逍遥游”只是心游,或是幻化之境。
庄子美学预设的绝对理念称名为“道”。庄子认为“道”是绝对自由无限的存在。整个宇宙万物皆由“道”生发而来并且最终复归于“道”。《庄子·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4]畅言“道”是真实可信的至高无上的存在,孕育天地万物。
庄子与尼采作为时代的叛逆哲人,出于对生命的关注、热爱和颂扬,皆是近似异端的思想者、文明的反叛者、道统的非难者以及生命哲学的崇奉者。他们的确能极为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尼采倡导的昂然的生命力、人格的塑造力、奋发的意志力又与庄子终身信奉的与世无争、逍遥自在、顺应自然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可谓是大异其趣,但他们在各自超越思想中所倡导的个性独立的精神求索无疑为时代演进带来了强烈的心灵呼唤,并体认着一种“人本主义”的自由精神。
庄子和尼采都致力于“人之本性”的复原,但采取的方法却迥然有别。虽说两人尽皆怀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并渴望生命自由,但庄子与尼采对自由的界定却大异其趣。庄子的自由思辨是从“命定论”出发,追求的是绝对无为的自由佳境,要求世人必须内心静养,是由外而内的“收敛式”的自由;尼采竭力倡导用人的本能意志去行动、创造、超越,是自内而外的“发散式”的自由。
尼采崇奉生命,力求成为生命的“拼命感受者和辩护者”,尼采说:“根本我只爱着生命——而且,诚然,当我憎恨生命时也最爱生命!”[5]尼采虽说同庄子一样认可人生道路的确是充满痛苦的征途,却仍愿意挺身而出,力争强力、奋发、有为,追崇蕴含于人体之内的创造欢乐的酒神精神。尼采大声疾呼:“从生存获得最大成果和最大享受的秘密是:生活在险境中,在威苏维火山旁建筑你们的城市。把你们的船只驶向未经探测的海洋,在同旗鼓相当的对手以及同你们自己的战争中生活。”[6]站在生命之上而决不在乎肉体的毁灭,越是濒临消亡越是感受兴奋,积极投入大千世界和人生改造,张扬着在悲切中心怀奋斗的狂欢激情。
现实生命个体大多会感受到世俗的挤压、生存的艰辛、求索的挫折、发展的阻隔,它必然要求个体采取补偿方式加以平衡。庄子看似“无奈游世”的人生态度背后却有着不肯妥协而不断追求生命价值的精神,尼采倡导的“放纵本能”更是一种生命的欢跃姿态,但他们在看似外显的欢快背后皆隐藏着非常深厚的悲剧特质以及对生命的执著、坚持和祈盼。尼采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7]21人的生命唯有在艺术的审美之中才能真正地得到价值认同和存在依据。尼采赋予了艺术一种对生命的形而上的意义,强调这种意义通常源自艺术中的“冲创意志”。认为人世间正是因为有了醉狂艺术的升腾才演绎出生命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稳定性,即只能依托“醉于艺术”方能在审美中感悟生命的力量,观照宇宙的本质精神,获得生命的自由驰骋,从而真正享受到自由、愉悦的生命活力。endprint
马克思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8]劝诫作为现实的人唯有在现实的世界中且使用现实的手段方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庄子与尼采信仰的自由难免会因忽略了实践的根基而陷于近乎虚妄的生命幻想,即单纯强调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的衍生。但两者的自由思想却富含性灵解放与形而上的内在超越的生命意识,它必然启迪世人从自由视角去塑造独立人格、观照生命本体,从而最终使得生命个体能皈依精神乐园。
二、“至人”与“超人”:构建理想生命的风貌形态
庄子和尼采在通向“逍遥无待”与“酒神狂欢”的自由之境时,庄子强调个体应依靠“心斋”、“坐忘”的方式来祛除一切违背本性的外在羁绊,达求返璞归真、与道为一、逍遥自在的自然澄明之境;尼采强调个体要历经从骆驼、狮子、小孩的精神变形,持守本真性灵,最终成为具有强力意志的充满激情与创造活力的生命强者。庄子是“清静无为”中彰显人性,尼采是“狂放有为”中创造人性。庄子的“至人”和尼采的“超人”虽说都是理想人格模式,但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时代渊源,而具有截然不同的审美意蕴。庄子深感世人经常陷入“人为”与“自为”的种种束缚而塑造了“至人”的理想人格,借以冲破桎梏性灵的重重罗网,打通人与外在世界的诸多隔离,使得人与宇宙万物最终达至交感、融合、开放的自由境界。
《逍遥游》中的“至人”是神人、圣人的总和,焕发着大智大慧、无所依赖的旺盛的生命力。庄子之“道”体现着人类与万物相融且与宇宙精神往来的和谐姿态,推崇个体生命在对“道”的顺应中恢复本真之美,体验无限的欢欣悦动的生命力,即所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诗意乐土,从而使得人与外物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圣境。
庄子在《逍遥游》中对理想人格作了形象的描绘:“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9]畅谈至人能“齐生死”、“齐万物”的绝对自由,并能自觉进入“与道同体”的逍遥境界。庄子身处动荡变迁的战乱时代,生命如同白驹过隙,生死无常。正因如此,庄子为世人提供了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谋求内心平静的生存方式,即站在“道”的角度看待、超越、升华生与死的界限,视生死为大道造化,顺其自然地将灵魂与道融为一体,从而最终达至心灵圣境的宁静恬适。庄子表面上似乎不问世事,也决不屈从“专制”的现实生活,生辉的笔下不时洋溢着展翅高飞的大鹏、梦中萦绕的蝴蝶、七窍不通的混沌、得黄龙之珠的象罔、畸形怪异的支离疏、藐姑射的神人等诸多炫丽精彩的故事,生命中呐喊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誓言,但事实上,在那看似冷眼旁观的淡漠中,实则投入了对“天地大美”的诗意关注。
尼采主张人作为宇宙生命,秉承着“强力意志”的日神冲动和酒神冲动,提倡个体生命自觉追求宇宙本体的强力而有所作为。唯有如此,生命才可能具备存在的价值意义。尼采说:“阿波罗是体现个体化原理的神采奕奕的天才。只有通过他才能在表象中获得解脱:而狄奥尼索斯的神秘的欢呼声则打破了个体化的魔力,使通向存在之母、万物核心的道路畅通无阻。”[10]“超人”就是尼采生命主张的典型形象和至高无上的美学形象。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述说“骆驼”蕴含着坚忍负重的精神,“狮子”意味着批判传统而获得创造的自由,“赤子”喻示着新价值创造的伊始。骆驼的沉默强韧、狮子的勇猛冲力、孩童的天真无邪必然导致三者巨大的反差而使生命持续着多极的生存状态。“精神三变形”就是尼采对于人类精神重新获得自由的三个阶段的描绘和思想发展过程的规定。它象征着人类成长中对传统价值的承担、认知、批判、创造,最后一定会进入“超人”的理想境界。
尼采曾大声疾呼:“近代欧洲文明正经历着一条下降的曲线,并且日趋腐败;如今,已经到了一个大时代的门槛,从而应对一切与其有关的价值重新作出估价。”[11]尼采面临现实社会的不堪现状,发出了生命的最强音来呼唤“超人”的现身,并希冀能凭借“权力意志”去升华个体奔放的、燃烧的生命力。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如斯表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2]强调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并充分肯定了人对自由的追求精神。尼采哲学最重要的精神蕴含就是主张哲学的使命必须关注人生,即给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一种合理的解释。为此,尼采提出了建构“理想人生”的哲学思辨,推崇“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征,映射着尼采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人生佳境。于是乎,尼采哲学在当时就被炒作成一种“行动哲学”,即使个人的需求、理念和欲望均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生命哲学。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世界之本体,并赋予其超越性特点,他追求的不是生命本身,不是满足生命的种种欲望,而是超越于求生之上的生命的意志和目的。”[13]归根结底,尼采的“权力意志”蕴积着本体的意义,并以其建构了具有强烈反形而上学意向的崭新的世界观和价值尺度,从而体认了人作为一个类的真实本性的生命实现。尼采塑造的“超人“是拒绝上帝、理性、科学对人的主宰,彰显的是具有鲜明个性、创造性的富含坚强意志和旺盛生命力的新人,“超人”本应立足大地又超越自身,更是一位自由开放的并将成为新价值的估定人和立法者。
尼采塑造的“超人”充满激情欲望,具有坚强意志,更是一位充分挖掘自己潜能的不断超越自我的强者,即是“充满酒神精神的生命的肯定者和生之欢乐的享受者,有着健全生命本能和旺盛的强力意志的强者,有着独特个性的真实的人,超越一切传统道德规范、处于善恶之彼岸、自树价值尺度的创造者,不为现代文明所累的‘未来之子。”[14]尼采说:“整个人生也是一样,透过对于死亡与其他意义的思索,会蓦然发现,我们的‘死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死亡。”[15]诠释了尼采从“超人”和个体性的学说出发而提出的生命自愿死亡观。总体来看,“至人”是以退让的生存方式,立足超越自己、社会、人生,安然接受人世的生死、穷达、荣辱;“超人”则以投入的形式体现,不屑于安命现状,力图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自我主宰,追求克服所遇到的现实困难来创造理想的生存环境。“至人”和“超人”皆具有特殊的超现实的力量,它和现实生命所拥有的现实力量加以融合就会产生综合的效力,并能推动现实生命向理想状态发展,使得现实生命涵盖着理想的生命光环endprint
三、“游世”与“醉艺”:悟化生命美感的践行模式
庄子和尼采都强调精神世界的自由塑造,但不同的是庄子主张清静无为的内敛的精神世界,尼采却要求自我实现的向外的精神世界。庄子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最终皆可归结为对人性的关注,他们不仅承认人生的悲剧现实而且强力主张超越人生的悲剧性。为探求人性的本真风范,庄子把悲剧作为人生的清醒剂,尼采则把悲剧当作人生的兴奋剂,但他们均采取理想的形式对世俗社会所赞美的人格加以彻底地否定,从而显现出在人生超越观上共同的审美取向。
庄子深知人性的局限而力图予以超越,幻想建立一个思想上的自由王国来探求某种逍遥游世的人生佳境。庄子面对生死无常以及无来由的痛苦、疾病、不公,深邃地觉察到困囿人生自由的诸种羁绊大多是来自社会、自然、自我之限,逐步感悟到世人若想保持自由天性就必须涤除诸多障碍。“逍遥游”作为庄子的人生理想就是其自由观的灵魂所在、生命哲学的自然归宿和人生价值观的最高境界。为此,庄子提出了一个内外结合而渐趋摆脱限制的修养历程,即通过“心斋”、“坐忘”来抛弃仁义礼乐、生理欲望、心灵智慧而终将达到“死生一观,物我两忘”。
庄子和尼采皆是在对传统道德进行强有力批判的基础上建构着各自的理想道德人格。尼采提出了“重新估价一切”的抗争口号,自称“第一个反道德者”,是现有的颓废文化堆下的“炸药”,是旧价值体系“彻底的破坏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理想主义道德和基督教道德就是长期窒息生命精神的恶魔。“从根本上来说,在反道德这个名词中,含两种否定。第一,我否定以往被称为最高者那种类型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人;第二,我否定普遍承认所谓道德本身的那种道德——即颓废道德,或者用更不好的名词来说,基督教道德”。[16]
尼采说:“仔细审查一下最优秀、最有成效者的生平,然后反躬自问:一棵参天大树如果昂首于天宇之间,能没有恶劣的气候和暴风雨之助吗?外部的不善和对抗、某种仇恨嫉妒、玩梗疑惑、严酷贪婪和暴戾,是否算顺利环境之因素呢?没有这种顺利的环境,甚至连德性上的巨大长进也不可能。”[17]明晰现实世界,“超人”之路充满血腥气味和恐怖气氛,环境越险恶就越有可能出现“超人”。因此,现实中必然需要一个把现实争斗简化了的外观的艺术境界,并以此来慰藉人生的痛苦磨难。于是乎,尼采提出了“远观”、“独处”的理想道德人格修养途径。“远观”是从远处看待事物和认识自己,并借以超脱万物的束缚。“独处”却是达到艺术境界并以之安顿寂寞心灵的有效途径。
叶朗指出:“坐忘”和“心斋”一样,其核心都是要人们彻底排除外部世界强加给人的一切人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让个体以一颗纯净透明之心来实现对于道的观照,从而达到一种至美至乐的境界,并在其中获得高度的精神自由。这种通过“心斋”、“坐忘”所达到的境界,就是庄子所说的“游”。[18]庄子的体道过程就是一种悟化本真、忘却外物、自由无碍、回归天性的生命征途。
“游”与“醉”可谓是人类本质精神之美的体认佳径,更是生命个体的“大美”感悟。“游”是《庄子》全篇的核心范畴,若想达至“游”的自由生命状态,就必须寻觅某种“虚静”、“忘我”,涤除一切凡间俗世的欲念,全身心地融入自由无拘的宇宙精神,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生命圣境。与之相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借助对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而提出了“酒神精神”,认为酒神精神就是一种趋向于放纵性灵的原始本能的醉狂。尼采推崇的是在艺术中放纵自我的酒神狂欢之“醉”,并竭力主张通过“醉”于艺术来拯救人生的苦难。
尼采主张艺术就像人生的游戏,唯有处于“醉”态回归纯真无杂念的婴孩时期,才能迸发出原始的生命创造力。尼采说:“艺术家倘若有些作为,都一定禀性强健(肉体上也如此),精力过剩,像野兽一般,充满情欲。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当看得更丰满、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和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醉意。”[19]尼采正是以“醉”为标准对艺术家的存在状态作出了最基本的规定,即艺术家必是充满了生命的醉意并洋溢着克服现实阻力的人生欢乐。因此,尼采以极其独特、敏锐、审美的视角来解读悲剧艺术,并从中去寻求、领悟、拓展生命的存在意义。
尼采评说:“一种文化随着这种认识应运而生,我斗胆称之为悲剧文化。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把握。”[7]334由此可见,尼采和庄子一样都认为艺术与宇宙生命最根本、最本质的精神相契合,世人可通过艺术来真正地感知生命之“大美”。
庄子与尼采皆以诗意的哲学言语来描摹自由这一亘古不变的生命哲学主题,遵从人生的审美化与形而上的内在超越,主张依托自由的审美视角去全力观照生命本体,崇奉以持守生命本真来拯救人世间被异化的生命个体,从而纵情地讴歌生命自由精神。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
[3]李牧恒,郭道荣.自事其心:重读庄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1.
[4]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95-96.
[5][德]尼采.查拉特斯图拉如是说[M].徐梵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06.
[6][德]尼采.尼采全集(第5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5.
[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21.
[8][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
[10][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95.
[11][丹麦]勃兰兑斯.弗里德里希·尼采[M].安延明,译.北京:工人出版杜,1986:107.
[12][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13][德]海德格尔.尼采十讲[M].苏隆,译.北京:言实出版社,2002:64.
[14]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17.
[15][德]尼采.快乐的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
[16][德]尼采.瞧这个人[M].刘崎,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109-110.
[17][德]尼采.快乐的智慧[M].王雨,编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103.
[1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4.
[19]周国平.尼采哲学文选:作为艺术的强力意志[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342.
(责任编辑 吴 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