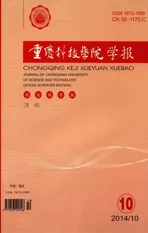香港人价值观变迁及其形态特征分析——以香港社会文化为切入点
2014-03-25徐海波冯庆想
徐海波,冯庆想
香港社会在156年殖民统治与近代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表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这些文化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交融的过程,既反映了香港人价值观的变化图谱,又透露了香港人的文化心理、价值旨归、身份意识与精神风貌的嬗变轨迹。本文以香港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变迁为线索,从香港社会多种文化交织中,尝试揭示香港人价值观的变化规律与其形态特征。
一、香港人价值观变迁与中西文化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下形成的,并且在长期社会历史演变中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笔者认为,香港人价值观的形成既离不开香港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谱系,同时又在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融合了西方现代文化,呈现出成熟的观念形态特征。
(一)香港人价值观的“中西角力”
“香港包括香港岛在成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中华文化进入殖民地时期的。”[1]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文化也随着英殖民者登陆而输入香港社会意识领域,使香港人的价值观系统形成了二重文化分层。西方现代文化是西方价值观的承载者,这种文化的深层结构由“个体”价值支撑,与西方人的生存成长法则紧密相连。“西方人的成长方式是强调‘断裂—分离—个体化’,使个人脱离人生早期的依附状态,以便及早地培养全面掌握一己人生的自我组织的力量。”[2]这种个体价值意识在西方文化形塑下,配合资本向外延展、扩张,形成了取代家族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价值意识——契约精神、法律意识与公平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以纲常伦理、仁义道德为主轴,围绕服从群体秩序、尊重君师权威这些规则运转,传统“人情化”力量在处理中国人际关系中形成一种社交文化默契;在他律的压缩下,自我价值意识缺乏自由伸缩空间。两种文化的异质性与视角差异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张力,致使中西两股文化力量在香港人价值观领域相互角力与较量。
从香港社会文化结构中,我们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对域外文化的反应与态度存在明显差异。除了少数跻身殖民建制的港人精英为了融入英式上流社会而较为认同西方价值观与游戏规则外,从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香港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对西方现代法治文化的态度是漠视的。一方面儒家文化重视人治,轻视法治,人们敬畏人治的威力远胜于法律的效力。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在香港社会管理共识中根深蒂固,它在香港人价值观中发挥主流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熏陶下,港人集体潜意识确信个人良知系统与天地相通相知,将辨别是非黑白的权力尺度让渡给上天和祖宗是合理与正当的。”[3]因而祠堂、宗庙在香港民间社会具有强大公信力,成为审判是非、施行律法的大众平台,替代了英国现代司法系统在香港社会中的作用。邓晓芒教授在谈及中西文化的区别时指出:“在中国,由于私有制的不确立,家庭被束缚于氏族宗法体制之中,未能发展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游离家庭,而国家只不过是氏族宗法的家长制原则的放大。所有这些都不需要有法律意识和公平原则来协调和制衡,而只需由家族习惯的‘礼’‘义’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廉耻’之心来调节,就可以维持大致的社会和谐了。”[4]英殖民统治初期的香港人价值观总体取向正是佐证这些文化规律的例子。另一方面,反映英国上流阶层利益、兴趣的贵族文化与大部分香港人的文化需求呈现明显脱节,究其根源,在于双方经济地位不对等。港英政府及其背后的经济财团掌控香港社会的文化资源,对于处于香港社会中下层的群体来说,并不存在向上流动分享这种资源的权利与渠道。因此,在经济地位与文化供求无法建立联系的前提下,这些文化与香港人生活必然出现脱离,进而反映在香港人的文化偏好与价值取向中。从深层次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间接削弱了殖民建制在香港社会管治的权威性与有效性。西方现代文化在香港人价值观念体系的认受性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支持,其所承载的法治逻辑、工具程序、制度理性在香港社会领域得不到全面的扩张,因而英国政治制度的文化价值在香港社会的话语权与社会功能必然受到严峻的考验。
(二)香港人价值观的“中西交织”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在英殖民统治中期,香港在上层建筑层面的变化远比经济基础变化要慢,港英政府在香港的资本输入与文化输入并不相协调。要改变其文化弱势地位与话语权缺失情况,港英政府必然从文化价值领地着手,通过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介入来实现社会秩序与群体心理的有效控制。首先,在政治制度安排上,港英政府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加快在香港华人精英阶层中吸纳西方价值观的受众,港英政府希望以西方文化来塑造香港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提高他们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受性。并通过这些文化改造过的港人群体来沟通、影响香港社会底层,获取更多对殖民建制合法性的资源支持。正如金耀金先生所认为:“在这个行政吸纳政治模式运作中,英国的统治精英把政府外的,非英国的,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精英,及时地吸纳进不断扩大的行政的决策机构中去,从而,一方面达到了‘精英整合’的效果,一方面取得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5]其次,在社会文化管理策略上,通过支持基督教、天主教在香港社会传教、办学、议政等方式,间接向香港不同社会阶层渗透西方价值观;同时,“港英政府充分利用和吻合香港华人文化传统,将殖民统治寓于香港华人所熟悉并容易接受的传统文化之中,”[6]对当地文化传统放任兼诱导,默认儒家文化价值观对香港人行为举止的制约,发挥当地约定俗成的条例对香港社会秩序维护的功能,这对于辅助和协调英国在香港的价值观输入以及降低香港管治的社会成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西文化双向互动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法治、理性、自由与中国传统的等级、正义、孝道在香港人价值观念体系中形成相互交叉的文化圈,使得潜藏在文化基因里的香港人价值取向呈现“亦中亦西”的雏形。
(三)香港人价值观的“中西融合”
在香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在香港社会的内化与渗透正面冲击着香港本土价值观,分化了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港人群体。香港人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虽然没有发生大动摇,但为了响应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香港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香港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中国传统文化重仁义轻名利的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的商业活动不相协调,儒家思想面临“去中心化”的冲击。现代性的商业化原则在香港社会文化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加快儒家文化解构和重构的变化过程。一是分解、拆离中国传统旧的文化秩序和落后思想,以时装、影视、消费为标志的现代女性文化在香港废除婢女制度之后方兴未艾,促进香港女性价值观念解放,改变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分配倾向男权主义的格局。二是根据香港社会变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发挥儒家文化价值的转化弹性,整合西方价值观念,不断丰富香港人价值观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传达的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价值理念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其所推崇的服从群体秩序、尊重传统权威、忠于家庭伦理,深入到香港人价值观的情感层面,具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这些合理的价值因子在香港社会意义系统稳定地流通。而西方现代文化传译的自由意志、理性逻辑与社会契约精神,契合香港现代商业活动规则的运作,在香港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提供重要的参考指标,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形成互补,形成大多数香港人可以共享与沟通的文化与价值观模式。
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融中,香港人价值观在维护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回应香港商业社会与现代化的变迁,因地制宜进行了转型。香港人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表现出中西融合的观念形态,既遵循自高到低的中国传统等级规范,维系传统的人脉、秩序构建的规则,保持稳定性;又看重科学、理性、效率等价值观,尊重个性扩张与能力延展,展现流动性。香港人价值观就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形成、发展与成熟。
二、香港人价值观的形态特征
“香港的现代文化,是讲求创新与实惠、敬重道义与正气的岭南文化,与强调自由、理性与实用的英美文化,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结合,获得突出的成就。”[7]香港地处岭南地区,香港人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在岭南文化浸润下,呈现岭南文化价值共性,主要表现为重商、务实、开放、包容等。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香港现代文化以岭南文化价值为内核,吸纳西方商业文化,又呈现出香港地域文化价值个性,主要表现为实用性、商业性、消费性、通俗性等。
其一,在香港的现代化进程中,香港本土文化“扩张化”(expansion)与西方现代文化“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双向过程,形成了香港现代文化,塑造了香港人价值观的“香港性”(HongKongness),展现出不同于内地的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与混杂性的观念形态特征。
一方面香港社会发展进程不同于内地,在香港回归以前,由于两地文化、政治上分隔,致使内地主流意识形态对香港的辐射和影响并不强烈,这为本土文化拓展发展空间与西方现代文化“在地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为向导的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本土文化与市场经济建立联系创造了基础条件,也为香港人价值观的商业逻辑的展开注入动力,推动各种价值观念、文化符号、思想意识以商品形式在发达的市场机制运作中生产、分配与流通,为香港人的文化消费提供选择、比较的空间。从内部文化结构来看,香港现代文化表现出高度的流动性。这种文化结构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为香港输入各种价值观念提供了可能性。自香港回归议题提出以来,各种权力话语从各自的立场、视角、态度来阐述香港当代的价值意义,使得香港成为各种价值观博弈的场域。泛民主派推崇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专业主义等理念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建制派提倡爱国爱港、务实重商、和谐稳定等价值理念为香港社会共识的基础;中间派指出核心价值观应该与普世价值观接轨。不同党派、阶层、团体以不同文化视角对共享价值进行诠释,反映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从外部文化环境来看,多元思想文化的争论与共生,回应了香港作为一个全面开放自由港的发展定位,自由宽松的城市环境酝酿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先进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和思想都可以在香港社会找到生存空间。这些文化掺杂各种价值取向,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和发达的商业氛围下,由于缺乏有效的价值观筛选机制,显得内容混杂、层次交错,这也致使香港人价值观呈现不同的“颜色”变化。
其二,在香港社会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同影响下,香港人表现出务实重利的价值观特征与明显的本土身份意识,形成了独特的粤语文化认同。
社会文化具有形成身份意识、输送价值观的功能。岭南文化与英美文化都是务实、重商、重利文化,以财富增长与社会地位上升为追求目标,这对建立香港人与社会身份结构的文化联系,形成香港人追名逐利的务实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一些香港人通过金钱多寡进行社会价值、资历、地位的排序,将自我认同的群体置于价值金字塔的上端,而他者所属群体位于中下端。虽然这种排位价值观念本质上是拆离皇权的封建等级价值观与现代商业文化相结合的变异形态,但在香港人价值观领域依然具有一定受众基础。随着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加速,两地经济价值观差异越发模糊,但是,基于香港社会体制优势形成的价值观“优越感”依然在香港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中有意或无意地显露出来。
以语言认同作为价值归属与群体划分标的是香港人价值观的另一大特征。粤语是承载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译香港人价值观的媒介。粤语与岭南文化紧密联系,在香港人的商业活动、市井生活、社群交际中传达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理想,充当社会意义流动的工具。在香港社会成熟的商业运作下,本土文化工作者把香港人的文化旨趣、生活方式、核心价值进行系统的编码,创造香港本土文化的象征符号,以电影、电视剧、戏剧、歌曲等形式进行文化包装,通过粤语传媒向社会各阶层推广与传播。香港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通过共同语言沟通与交流,对岭南文化符号进行意义解码,透析隐藏在粤语背后的文化意象与意识形态印记。这一过程以重现本土文化意识、集体记忆、生活场景的过程来追寻区别他者文化身份的价值标的,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价值归属,在潜移默化中强化香港人对承载本土价值观的岭南文化的认同,缔造一种“大香港文化”优越感。但香港粤语文化缺乏一种高位文化价值架构,粤语文化资源在工具程序理性与消费主义结合下,形成一种强大密集的文化流通、交易状态,不断追逐商业利益,却逃避了宏观历史文化视野,掩盖了终极性的文化价值目标的询问和思考。因而,相当部分香港粤语文化消费只是缓解经济社会向香港人精神结构施加压力的一种消遣方式,并非一种价值观内化行为。可见,在香港现代化进程中,岭南文化资源与粤语有机融合,在经贸交流、文化互动中共同塑造香港人的身份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形成香港人价值观的独特性。
其三,在岭南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交融中,现代性的世俗化原则与理性化程序不断向香港人价值观念体系延展,并与岭南生活方式、本土政治模式对接,构成大多数香港人共享的政治文化空间,展现了香港人“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价值观的演变动态。
“当代的香港既是维持岭南文化传统的世俗社会,也是公民意识不断成熟的理性社会。”[8]回家喝汤、排队饮茶是富有岭南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香港人习惯以这种微观生活镜像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与价值观念,通过解构依附在小区活动、地标建筑、街道面貌的文化元素,组合群体价值观认同的文化资源。在香港文化界的本土价值论述中,以反映岭南生活方式、习惯和习俗的文化观念包含本土主体的记忆建构与价值选择,修正了精英文化的社会阶层偏见;岭南文化的内在价值由抽象、形而上层面向大众普及层面内化到香港人价值观念体系里,形成香港本土价值意识,反映在香港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诉求中。随着“香港是我家”的主体意识在香港社会群体心理不断膨胀,香港人日常文化活动与政治实践层层相扣,围绕日常权力关系而展开的争取妇女权益、保护环境、关注弱势群体等一系列人本主义诉求,从个人描述性政治目标向社群行动式社会思潮的转变,这既是香港人政治主体价值观成熟的显著表征,又反映香港价值观念与香港人日常生活交合而成的微观政治文化逻辑。公民政治普遍参与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香港人不可避免卷进现代文明秩序构建中。在本土独特的岭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融中,基于理性价值进行民主表达诉求,建构健康的微观政治价值观,寻求适合香港历史和现状的现代性价值表达方式,这是香港人价值观的未来变化趋势。
由上面分析可知,要使香港完全融入祖国大家庭,除了在经济与政治上维持香港繁荣稳定,还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香港社会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与香港人价值观的关联和影响。通过两地文化的有效互动和对话,建构香港与内地在文化和意识层面的认同机制,在“中国梦”的价值导向与共同精神旗帜下,逐步实现内地与香港在核心价值观念、文化认同和社会发展目标上的相互融合。
[1]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3.
[2]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3]徐海波,冯庆想.解构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脉络[J].行政与法,2013(12).
[4]邓晓芒讲演录[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97.
[5]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43-44.
[6]刘曼容.利用与吻合:港英政府借助香港华人文化传统提高施政效率[J].学术研究,2005(12).
[7]何志平,陈云根.文化政策与香港传承[M].北京:中华书局,2008:4.
[8]廖伟棠.波西米亚香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