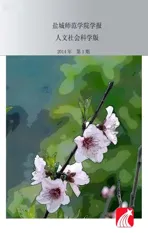赛译《水浒传》“误译”探微*
2014-03-12苏军锋
苏军锋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这要归功于迄今为止的四大英语全译本。它们是赛珍珠(Pearl S. Buck)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杰克逊(J. H. Jackson)译本(Water Margin)、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译本(Outlaws of the Marsh)和登特-杨父子(Dent-Young. J;Dent-Young. A)译本(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其中最早的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于1933年出版的译本(以下简称“赛译本”)。出于对原著的推崇和喜爱,在其恩师龙墨乡先生(M. H. Lung)的帮助下,赛氏精心打磨五年(1927—1932),才向西方读者推出英译本。令她欣慰的是,该译本很受欢迎——“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蹿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1]。然而自赛译本引入我国以来,却“遭到了我国翻译界的猛烈抨击,其‘误译’被频频引证, 被批评指责的次数似乎仅次于赵景深先生的‘牛奶路’”[2]。
综观国内译界对赛译本的评论,焦点在于其对原著的“亦步亦趋”,即对目的语读者来说,赛氏似乎做了太多的“异化”处理。“赛珍珠的译文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类似圣经英文,让人读起来有点‘古味’,又为了有点‘中国味道’,句型结构则完全按照中文逐字逐句地直译。”[3]依笔者之见,就《水浒传》现有的四种译本来看,无论是从翻译策略来看,还是从译作的影响力及其担负的文化使命来说,赛译本最有特点、最具影响力,而这恰恰要归功于所谓的“误译”。本文拟从上述三方面来探析赛译本中“误译”现象背后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赛译本的翻译策略
1.关于书名
如果说书名是“纲”的话,纲举则目张,透过书名读者就能了解文本的概要。赛珍珠把《水浒传》的英文书名转译为AllMenAre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引自《论语·颜渊》中的一句话。之所以藉此翻译,赛氏认为《水浒传》这个书名是“无法单独翻译的(singularly untranslatable)”。若非要直译,那就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在她看来,这样的直译“几乎没有意义(nearly meaningless)”,甚至“会误导英语读者”。所以她就“自行选择了孔子的一句话作为英文标题,这句话含义隽永、内涵丰富,能表现出这帮侠盗的精神”[4]。
诚然,如此处理书名是否准确到位,尚有争议。如有学者主张把《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类比为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罗宾汉,认为二者的侠义精神异曲同工,因此主张把书名译为“The Righteous Brigand”,“A Brotherhood of Righteous Robbers”或简单译为“Liang Shan Po, The Robbers’ Lair”则更加恰当[5]。但以笔者管见,相比之下,在现有的四个英译本中,杰克逊的译名“在水边”和登特-杨父子的“梁山之水边”,都仅仅点明故事的发生地;沙博理的译名“沼泽地上的不法之徒”,亦只是列明故事的人物和地点而已。赛氏的书名翻译则更为妥当,除上述她的解释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理由:其一,必须指出的是,《水浒传》中的人物屡次使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例如: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下称“金评《水浒》”)第一回中陈达和史进的对白及第三回中鲁达和赵员外交谈均直接提及此语。其二,鲜为人知的是,赛译本是在出版前没多久才应出版商的要求定下“All Men Are Brothers”的书名。此前,她尝试过的书名有《侠盗》、《义侠》等[6]。可见,赛译本如此定名是她和出版商博弈后“相互妥协”的结果:她认为该译名能较为准确地传达原著的“忠”、“义”主旨,而出版商也能以此博得读者眼球,争取商业利益最大化。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和出版商达成一致,但赛氏似乎还是觉得不尽如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赛译本封面上除了All Men Are Brothers的译名外,还特地在下边保留了“水浒传”三个汉字及其拼音SHUI HU CHUAN, 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以期具备英汉双语能力的读者能体会该书的要义,特别是标题处理方面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可见其用心良苦。
2.关于采用“直译法”
赛珍珠除转译了原著的书名外,基本是以“直译法”再现原文的。正因如此,赛译本在译界颇受非议,譬如,她把小说中的“放屁”译为“pass your wind”,屡屡被列为典型来批评,乃至被冠以“文化陷阱”“误读”“胡译”“语用失误”等名称[2]。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若客观地从翻译目的、策略、方法等诸方面来透析赛氏的翻译活动,或能解释所谓“误译”的原因。翻译目的学派创始人德国语言学家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指出:“翻译就是做事情……都是一种行为(action)……做出该行为的人必须(有可能)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虽然实际可能有出入),而且行为的真实原因总是能从行为的目标或对目标的阐述中找到答案。”[7]在赛译本的序言中,她就明确指出翻译《水浒传》纯粹是出于对原著精彩情节和叙事方法的喜爱,丝毫不抱任何学术目的。她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使译文与原著相像。出于这样的目的,赛译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如把“牛肉”译为 cow’s flesh;把“早饭”译作 morning meal;把“江湖”处理为river and lake;英译“三寸不烂之舌”为three inches of never failing tongue等等,如此“误译”不胜枚举。试举两例:
(1)两个小头目听了这话,欢天喜地……
The two small chieftains, hearing these words, were glad to Heaven and joyous to earth…
(2)“……哥哥放著常来的一班儿好酒肉弟兄,闲常不睬的是亲兄弟!”
“…Brother has some wine-drinking, meat-eating friends who are here continually, but the one whom he never heeds is his own brother.”
按如今的说法,上述字字对应翻译很“机械”,属于“中式英语”(Chinglish)。但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来看,赛氏有错吗?她就是尽其所能“使译本像原著那样”,并“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感到他们是在读原本”[8]。
作为宏幅巨制,《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梁山泊故事”的结晶[9]。其版本多达五种以上。在上述目的的指引下,赛珍珠选择以“金评《水浒》”为蓝本,原因有二:其一,她认为该版本兼收并蓄,而其他版本后续的“招安”章节乃是出于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缺失“金评《水浒》”彰显的精神和要义。其二,受到胡适先生的影响。胡适对“金评《水浒》”评价颇高,夸赞金圣叹具有“大匠精神与大匠本领”。胡适的识见使赛氏更加坚信她的选择,这在赛译本的序言里可以得到佐证。
赛氏采用保留“原汁原味”的直译策略,还和她独特的思维模式不无关联。她尚在襁褓之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先学说汉语,再学英语,并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了大半辈子。1932年,她的小说《大地》(讲述19世纪一个中国农夫的生存故事)获普利策小说奖。几年后,因“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10],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写中国题材的小说时构想故事内容、人物对话都是以中文思维,然后再翻译为英文,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外国译者中几乎从未出现。而翻译《水浒传》恰巧符合了这种‘特殊’的思维过程,所需的中文已在,直译为英文即可”[11]。她曾说其作品是以地道的汉语为基础的,自己甚至不能肯定文风中是否体现出英语的特点[12]。换言之,赛珍珠“追求的效果是,将中文翻译为与在汉语中具有相同意义的英文,使得英语读者的感受与汉语读者相同。英语读者阅读到的是同样优美的篇章……”[11]
赛珍珠翻译“金评《水浒》”的过程历时五年,呕心沥血,孜孜以“译”。虽然可以说她长期浸淫于中国的语言文化当中,有着很高的双语功底和驾驭能力,但毕竟《水浒传》中的人名、地名,尤其是关于习俗、服饰、武器、俗语等,甚至人物打斗动作,有些国人尚且不甚了了,何况赛氏?所幸她有龙墨乡先生始终如一的鼎力相助。翻译伊始,谙熟中国古典文学的赛氏把原著再次仔细研读,其后她日闻龙墨乡大声朗读原文,这种做法似乎在仿效不懂外文的林纾。然而与林纾不同的是,赛氏在聆听的同时,能尽可能精确地逐句翻译。这种听、译相间的工作方法是她的“最优选择”,既能提高翻译效率,亦能使译文和原文在“词语结构、句式语序自然十分接近”。原作译毕,她还要从头至尾通读原文至少四遍,第一遍独立完成,两次是与龙墨乡先生一起,第四次是与另一位中国朋友一起[13]。可谓倾心打磨,精益求精。
综上可以看出,她的译作与其翻译文本时的初衷、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其翻译过程莫不关联。她只是在创作之余,开创性地向西方读者推介《水浒传》。我们不应对她和她这唯一的长篇译著求全责备。
二、赛译本肩负的文化使命
翻译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不同语言的交流需要,又和文化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14]。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之一,翻译无疑承载着文化传播的使命。翻译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我们需要这个平台,在汲取国外先进文化精髓的同时,也需向国外受众传播和推广我国的灿烂文化。正如许钧先生指出“翻译研究应该关注并推动中外文化之间进行平等、双向的交流[15]”。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地位日益凸显,而相应的文化影响力,客观地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扭转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外译汉为主流的文化单向输入局面,必须把汉译外作为输出中国优秀文化的主要路径,使中国文化更多地“走出去”,在国际文化大家庭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从这种意义上说,赛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为我们树立了标杆。
赛译本和原著相比,在措词、句式和结构等方面有相当的契合度。精心而为的如此契合就是力图向西方读者传达原著的要义及其映射出的中国文化,以便使他们与中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态。无疑,赛译本对“翻译的文化使命”的担当是成功的。对此,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家》上,对赛译本也不吝溢美之词,“认为赛珍珠翻译的这部伟大的中国小说是她代表中国向西方国家呈现的最美的礼物”。她的译作“具有极其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价值。……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16]。称她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人桥”一点都不为过。
三、赛译本的影响力
另外,对于国内译界对赛译本的批评,笔者认为,其一,译文达意与否,最有话语权的非英语读者莫属。那么,目的语读者对赛译本的看法如何呢?沙博理的态度或许具有代表性,“这(赛珍珠的译文)给外国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由于故事本身十分生动,而且我看懂了大部分,因此我很喜欢这部小说”[3]。需要指出的是,沙博理先生是1946年第一次读《水浒传》,囿于他当时的汉语水平,他读的正是赛译本。从他的言论来看,赛氏基本实现了其预期目的。诚然,赛译本确有商榷之处,但既然英语读者“看懂了大部分”,再加上赛氏翻译原著的本意,我们就不应以偏概全,而要客观公允地对待它。第二,如前所述,赛译《水浒传》是史上第一个英语全译本,“很多其他语言的版本也是转译自赛珍珠的英译本”[17]187。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赛译本“误译”百出,那么非英语国家的汉学家们译介的《水浒传》版本都是在以讹传讹吗?这似乎不大可能。其三,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赛译本,而不是以现在的或自我的标准对其进行“道德评判”。赛氏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翻译《水浒传》时,除原著外的参考资料甚少,遑论《水浒词典》和其他《水浒传》专题研究资料了。换言之,赛氏当时的条件有限,她的所做“前无古人,后才有来者”。
在《水浒传》被赛珍珠译介到西方之前,普通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就是刻板,“冷漠、缺乏感情……,走路鬼鬼祟祟,面无表情,还甩着一根长辫子”[18]。而赛氏长期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促使她决意“颠覆”这一歪曲形象,途径之一就是翻译和评论中国文学。经过她的不懈努力,《水浒传》的第一个英译本终于横空出世,且很畅销,陆续再版达十几次。它给西方读者展现的是“一部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民间史,是与宫廷倾轧、士人风雅对立的草根小民的生活史”[17]190。书中的英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及以替天行道之名与腐败的朝廷相抗争的精神,再加上敢作敢为、耿直率真、有勇有谋、光明磊落等性格特征和形象,对西方读者而言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可以说,赛译本“甚至推翻了之前西方的东方想象”[17]190,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四、结语
我们认为应该以整体视角来客观地衡量和评价翻译作品,而不应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抑或断章取义。对赛译《水浒传》的评价亦然如是。它的成功是原著、译者、译作、读者和其他因素等[19],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一言以蔽之,相比而言,赛珍珠对书名的处理可谓匠心独运。赛译本无论是从译者的翻译目的、策略和过程出发,还是从译本的影响力及跨文化价值层面来解读,都非常成功,深受西方读者欢迎,否则就不可能再版多达十余次。当然,赛译本中的有些措辞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对于《水浒传》最早的英译本,也是赛氏唯一的长篇译作,学界应该且需要以包容的态度从更深层次和更广角度去挖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龚放,王运来,袁李来.南大逸事[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230.
[2] 马红军.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3):122-126.
[3] 沙博理.《水浒传》的英译[J].中国翻译,1984(2):29-32.
[4] Buck P S.All Men Are Brothers(SHUI HU CHUAN)[M].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3:v-vi.
[5] Tai Jen.A Chinese Classic[J].The Saturday Review,October7,1933:162.
[6] 顾钧.赛珍珠的英译《水浒传》[J].博览群书,2011(4):104-107.
[7] 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61.
[8] 姚锡佩.从赛珍珠谈鲁迅说起——兼述赛珍珠其人其书[J].鲁迅研究月刊,1990(6):38-42.
[9] 易竹贤.漫评胡适的小说考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4):89-108.
[10] 王运来,罗静.赛珍珠与南京大学(中国名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04-08(6).
[11] 董琇.赛珍珠以汉语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谈赛译《水浒传》[J].中国翻译,2010(2):49-54.
[12] Doyle P A.Pearl S. Buck [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Inc.,1965:40.
[13] Giles L.Review of Books[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34(3):629-636.
[14]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
[15] 许钧.从国家文化发展的角度谈谈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J].中国翻译,2012(4):5-6.
[16] 庄华萍.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114-124.
[17] 朱骅.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8] Buck P S.The Emotional Nature of the Chinese[J].Nation,September22,1926:269.
[19] 钟再强.接受理论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J].兰州学刊,2011(10):10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