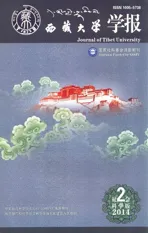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传播与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
2014-03-03王黎刘虹
王 黎 刘 虹
(①乐山师范学院人事处 四川乐山 614000②成都大学档案馆 四川成都 610106)
藏文大藏经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对藏文目录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对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对藏文目录学发展所起的催化作用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藏文大藏经概述
佛教源于印度,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开始向外传播,一向南传至斯里兰卡,形成了巴利语系的大藏经;二向北传至西域各国经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汉地,公元7世纪传入我国西藏。松赞干布时期创制藏文,开始了佛典的藏译活动。自此,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巴利语《大藏经》流传于世界,自成体系。
藏文《大藏经》,是译成藏文的佛经典籍和佛经论著总集,分为《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称为“正藏”,是翻译佛语的译文,即为佛祖释迦牟尼语录译文;《丹珠尔》称为“续藏”,是对佛经注疏和论著的译文,即佛教徒和佛学大师所作论述及注疏的译文,包括经律的阐释、密宗仪轨以及五明杂著等。自松赞干布时起,经历代高僧的翻译、校正、整理、精心甄别至14世纪最终完成,其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其中收录的佛经典籍大部分是8、9、11、13世纪时直接从梵文翻译的,弥补了不少汉文大藏经中没有的内容,因此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对研究藏传佛教、藏族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
二、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传播对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影响
(一)吐蕃藏文佛经典籍和佛教著述的翻译促使藏文三大佛经目录形成
7世纪,松赞干布派心腹大臣吞弥·桑布扎前往印度学习文字。吞弥·桑布扎到印度后,广拜名师,学习梵文、声明学,同时学习佛教经典,游学7年整,大增学识,学成归来,并带回大乘佛典。吞弥·桑布扎一回到吐蕃,在松赞干布委托下开始创制藏文。吞弥·桑布扎以梵文为参照并结合藏语的实际情况,潜心研究,创造性建立了完备的藏文字体系,使藏文翻译佛典成为了可能。
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不久,就和自己的弟子以及汉族僧人大天寿和尚等一起,翻译了《宝云经》、《宝箧经》、《月灯》等部分佛经,开创了用藏文翻译佛经典籍的先河。这时期藏文佛典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推行和传播藏文字,其翻译文体还未确立,因此译本存在词不达意、质量不高的现象。因此藏学学者普遍认为松赞干布时期的佛典翻译无论是影响还是规模都不是很大。
公元8世纪初,赤德祖赞继位,重新与唐朝联姻,迎娶金城公主进藏,并派大臣到唐朝去求取佛典,唐朝皇帝赠予千部金粉书写的经典。种种史料表明,赤德祖赞时期,吐蕃王室重新开始崇尚佛教,并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然而,王室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当地苯教徒的警觉,并予以抵制,致使佛典翻译事业受阻。[2]
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继位,大力弘扬佛教,采取了翦除反佛大臣,派大臣到长安取佛经,迎请汉僧,从印度迎请大佛学家静命和莲花生大师,建立藏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桑耶寺等措施。桑耶寺的创建、藏僧的出现,标志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建立,同时也打开了吐蕃大规模传播佛教的局面。佛经的翻译事业从此得以迅速发展,迎来了兴盛期。为了更好地传播佛教,发展藏传佛教,赤松德赞在桑耶寺开设了专门从事佛经翻译的译经院;为确保佛经翻译质量,制定了整套严密细致的译师选拔制度,对翻译程序和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并从人、财、物、政策等各个方面予以扶持。由于王室对翻译事业的支持,一时间整个佛教典籍不论大小乘教显密宗、禅教尽量吸收,兼收并蓄,盛极一时。根据《丹噶目录》记载,所收经论约有700余种。这时期藏译佛典因其大部分印度原本已失传而显得弥足珍贵,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8世纪末,赤德松赞为提升藏传佛教的地位,鼓励大量译经,推广佛教成果,召集印度、克什米尔、藏区等各地的译师对译经进行了全面的汇集、审定和编纂,并对诸多译语进行统一和规范。
佛经典籍的大规模翻译、整理,为藏文目录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公元9世纪,赤德松赞搜集整理并统一了山南地区佛典,对前译经论进行了校改,编订成函并规定其经文的数量、篇幅及规模,命译师将存放于旁塘宫的佛经按一颂为八个音节,一卷为三百颂分函造册,辑成了藏文佛经典籍的第一部目录《旁塘目录》。此后,译师完德贝则、昆·鲁易旺波松等人把存放于东塘丹噶宫的佛经和论著译成藏文,并经校勘、订正制成《丹噶目录》。之后完德贝则又将存放于青浦宫的所有佛经、论著编辑成《青浦目录》,至此,藏文佛经文献的三大目录产生。旁塘、丹噶、青浦三大目录基本上包含了藏文早期的佛经文献。这些佛典目录成为指导阅读藏文早期的佛经文献、检索佛典的重要工具。
(二)元朝藏文《大藏经》的翻译、编撰、分类、整理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
公元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佛教在吐蕃遭到毁灭性打击,佛教典籍也遭空前浩劫。公元10世纪,藏传佛教“后弘期”到来,阿里、安多等地率先举起复兴藏传佛教的大旗,西藏各地相继出现了宁玛、萨迦、噶当、噶举等教派。各大教派在佛教经典的翻译、阐释、注疏工作中培育了一批学识渊博的佛学和译经大师。他们新译了大量未翻译过的佛教典籍,并对吐蕃时期翻译的经论进行了校订改正。[3]
据《布顿佛教史》记载,这一时期藏地出现了198位著名的大译师,仅从印度来的高僧就有70多位,佛经典籍翻译总量高达2000多种。佛经典籍大规模翻译和系统的分类整理,为藏文目录学形成创造了条件。随着藏文大藏经分类编目、藏文大藏经目录的编制,藏文文献目录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先后出现了《纳塘大藏经目录》、《布顿大藏经目录》(录《宗教源流宝藏》末尾)、《夏鲁丹珠尔目录》、《蔡巴甘珠尔目录》、《乃东丹珠尔目录》。
藏文大藏经的第一次集结是元仁宗时期。1312年,纳塘寺格西嘉木噶拔希邀请上师觉丹热智,与译师索南沃赛等人一起将西藏各地凡能找到的经、律、密咒佛经原本进行搜集和分类编排,并进行了认真的校对,由觉丹热智编写大藏经目录——《论典广说》、甘珠尔目录——《太阳之光》(目录简说)。其学生洛色绛曲益希也编辑了简要目录《甘珠尔》、《丹珠尔》。后按格西嘉木噶拔希要求,以现已编成的目录为准编成了一套完整的大藏经,与原本一起存放在纳塘寺,这样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写本产生。因其是在纳塘寺编制,所以又叫纳塘版《大藏经》。以后各种版本的藏文《大藏经》均在旧纳塘版基础上形成,因此,纳塘版《大藏经》的编制意义重大。
在纳塘版《大藏经》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以下几种藏文大藏经及其目录手抄本。
1322年夏鲁派创始人布顿·仁钦大师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一书,并在该书尾部编写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总目,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次将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
从此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定型,对后世藏文《大藏经》的编纂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部总目,是布顿大师在“丹噶”、“青浦”、“旁塘”三大目录和“纳塘甘珠尔目录”的基础上,增加了各寺未编入的译本和后期译本而成。这部目录全面反映了元朝及元朝之前西藏佛教典籍翻译的全貌,并且因所利用的几种重要目录现已无法看到,更显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藏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
1323-1348年间蔡巴·贡噶多杰请布顿大师校订后编撰《蔡巴甘珠尔》,后来的纳塘新版、德格版、北京康熙版的《甘珠尔》都是依据这个版本。
1334年布顿大师在夏鲁寺,对旧纳塘版《丹珠尔》校订、增补、删除重复部分后,编写《夏鲁丹珠尔》(124函)。布顿大师收集了40个寺院里后世的经论、经疏、译经,翻译了无译文和尚未翻译完的经论,在旧纳塘版基础上,增加了1000种未收录的章节,并将其编写成目录。
1362年,以《夏鲁丹珠尔》为底本,大司徒绛曲坚赞出资,编纂了一套共202函的大藏经,史称《乃东丹珠尔》。
从以上五种藏文大藏经目录不难看到,佛经文献的大量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编排、分类、整理,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三)明、清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传播促使藏文文献目录学完善与成熟
大约11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藏传佛教中诸多单独承袭的教派渐渐形成为藏区几个较大的宗教派系,由于几大教派所传承修持的密法不同,因此他们往往是以所在的寺院、地区、家族为中心,拥有当地的宗教、政治、经济特权,甚至成为这一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集团。继宁玛派后,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的噶当派,11-12世纪形成的希结派、觉域派,以及最晚形成的格鲁派都是显教派别;宁玛、萨迦、香巴噶举、塔波噶举、觉囊、夏鲁派等是密教派别。各派由于其传承和修持的密法不同,在宣传和弘扬本派教义时,表现在各派流传于世的佛教典籍的内容以及编排结构各具特色,从而使各派在编制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时形成了框架、结构、佛经内容不尽相同的版本目录。
藏文大藏经版本目录学源于元末,兴盛于明清。刊刻藏文大藏经自明代开始,之后,随着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藏文大藏经的版本多达十几种。元朝对藏区全面施政,使分裂割据的藏区出现了统一安定的局面,经济迅速发展,文化空前繁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藏区较大的寺院均建起了印经院,印刷了大量的藏文大藏经等典籍。明清时期(1368-191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对佛教典籍、目录学非常重视,藏文大藏经得以多次刊刻,促使大藏经版本目录学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共有15种版本的大藏经刊印,同时产生了15种版本目录,即:《永乐版大藏经目录》、《江孜“天邦玛”目录》、《万历版大藏经目录》、《理塘版甘珠尔目录》、《北京版甘珠尔丹珠尔目录》、《拉萨版丹珠尔目录》、《卓尼版大藏经目录》、《德格版甘珠尔目录》、《纳塘版甘珠尔目录》、《德格丹珠尔目录》、《纳塘版丹珠尔目录》、《卓尼版丹珠尔目录》、《拉萨版甘珠尔目录》、《拉嘉甘珠尔目录》、《蒙古库伦甘珠尔目录》。其中,以北京、纳塘、卓尼、德格版较为著名。[5]
1410年,明成祖朱棣派太监侯显到藏区请回藏文《甘珠尔》底本,在南京刊刻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史称永乐版《甘珠尔》,是第一部刻本藏文大藏经,底本是《蔡巴甘珠尔》古写本,从此开启了藏文大藏经的刻本时代。
1431年,“江孜‘天邦玛’本”甘珠尔目录问世,将不能出寺院的禁书揭示出来,这是寺院藏书半开放的第一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刻印了完整的藏文《甘珠尔》,同时刊刻的还有《丹珠尔》42函。所依底版是永乐版《甘珠尔》,由噶玛巴红帽派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校订。
1623年,在噶举派红帽派系第六世活佛却吉旺秋主持下,刻印了理塘朱印版《甘珠尔》(108函),这是藏区首次刻印甘珠尔。
1683年清康熙帝(康熙二十二年)以夏鲁寺写本为蓝本,在北京刻印了全套《甘珠尔》,称北京版大藏经,也称康熙版,又称“嵩祝寺版”,共计1055部。1724年雍正帝(清雍正二年)刻印了全套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由赞颂部、经疏部、秘经疏部三部分组成,另附补遗、西藏撰述,共计3523余部。有藏、汉、满、蒙古四种文字的总目录。
1721卓尼土司莫索公保以永乐版、纳塘版、西藏版写本为底本,主持刻印了一套完整的大藏经《甘珠尔》,称卓尼版大藏经,其函数与理塘版相同。1753年,卓尼土司丹尚才让以德格版为底本主持刻印了《丹珠尔》大藏经,并由二世嘉木样·晋美旺布编写了目录《丹珠尔目录如意宝贯》,是刻本时期藏文丹珠尔的最后一种版本。
1729-1733年,由四川德格土司丹巴次仁出资以理塘版为底本,在德格印经院刻印了德格版《甘珠尔》。1737-1744年,德格土司丹巴次仁以夏鲁寺的《丹珠尔》为底本,刻印了德格版《丹珠尔》。该版本增补了不少新的论著,对原有的多版本《丹珠尔》进行了校订。
1730-1732年由颇罗鼐·索南多杰主持以旧纳塘版为基础刻成《纳塘甘珠尔》,称纳塘新版大藏经。1741-1742年以第司·桑杰嘉措写本为底本刻印了《纳塘丹珠尔》。
1927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倡导下,喜饶嘉措大师以纳塘新版为底本,参照德格等其它版校勘后刻印拉萨版《甘珠尔》。
1814年青海拉嘉寺活佛洛桑达杰主持,刻印拉嘉版《甘珠尔》(以德格朱印版为底本)。
1908年在由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切仓巡努顿珠拉莫二人倡导,以德格版为底本,刻印《蒙古库伦甘珠尔》,存放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库伦寺。
通过对以上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的比照我们不难发现,各个版本的大藏经在编排部类的次序、经论的函数以及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与不同在《丹珠尔》部分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就是各种版本在主要内容、部类编排次序上大多数依据蔡巴和布顿版,但经论部分函数不同,并在后期的版本中,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时期大藏经版本目录出现了《甘珠尔》目录多于《丹珠尔》目录的现象,这就说明明清时期刊刻的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在蔡巴和布顿大师编目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使目录更加成熟与完善。
虽然,到1737年时编排的德格版《丹珠尔》目录中仍在加入新内容,但这一时期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目录底本较为完善。同时,十五种大藏经版本目录的存在反映了明清时期藏文目录学在藏文大藏经的传播与刊印过程中走向成熟,走向完善。
三、藏文大藏经影响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原因分析
藏文大藏经的传播与翻译,对藏文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原因如下。
(一)藏族地区统治阶级弘扬佛法、信奉佛教,中央政府扶持佛教,重视佛教文化发展。
大藏经的翻译与传播大多出于历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佛教传入吐蕃后,为藏地的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行。为巩固政权、弘扬佛法、教化民众,吐蕃统治阶级大量翻译佛典,到赤松德赞时期形成藏区佛经翻译的高峰期,为藏文大藏经和佛经目录的编制打下了基础。藏地统治阶级在开展大规模的佛经典籍翻译活动时,开始了佛经典籍的分类和编目工作,促使了藏文目录学的形成。
特别是元朝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利用佛教对藏区的影响来巩固对藏区的统治,政治上大力扶持佛教,经济上给予优厚政策,译经成了政府行为,政治上强大的后盾,经费上充裕的保障,确保了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传播。明清时期,大藏经多种版本的刻印和编目同样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关注,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传播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永乐、万历、康熙、乾隆时期分别在南京、北京刊刻了永乐版、万历版、康熙版、乾隆版大藏经。中央政府还积极颁赐佛典。1411年,明朝将在南京刻印的藏文大藏经颁赐各寺珍藏。在大藏经大规模的刻印过程中,作为文化分支的藏文目录学也得到迅速的发展。由此可见,元、明、清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佛教的扶持及尊崇,对藏传佛教典籍的重视,赢得了藏族地区宗教上层阶级的衷心拥护,一定意义上对藏文目录学的发展、成熟和完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因此,藏文目录学在藏文大藏经的翻译与传播中,进一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翻译与编目二者的自然结合,使文献目录学原理在藏文佛经典籍目录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深度的运用和发展。
(二)藏文大藏经在翻译与集结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具有渊博学识的佛学大师,这些佛学大师在对大藏经翻译与集结的过程中,对藏文大藏经进行了校订、修订、编目,成为藏民族最重要的翻译家、目录学家。
据藏学家的研究,仅吐蕃时期,先后参加佛经文献翻译的门徒就超过千人,贤达者上百位,如吞弥·桑布扎、觉若·鲁意坚参、噶瓦·白泽、尚·益西德等。
布顿大师是夏鲁派的创始人,博学、精通五明,渊博的知识使他30岁就开始在藏传佛教寺院从事翻译、著述、讲经和编制、校订大藏经等工作。1322年撰写了举世闻名的著作《佛教史大宝藏论》,该书全面地反映了元及元以前西藏翻译佛经典籍的全貌,布顿大师在书尾编制了著名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录,第一次将藏文大藏经合编在一起。
总目录内容除经律论外,还有因、声、医方、工巧明等。类目的上位与下位区分明显,层次分明。在目录的编排上,布顿大师采用的是部类区分法、次序排列法。按佛经原文的翻译以及佛经注疏和论著的翻译分为《甘珠尔》、《丹珠尔》两大类,再按论述的内容划分为显密宗外加密宗总续8类。8类外按因、声、医方、工巧、小五明类分,小五明又分为修辞、辞藻、韵律、戏剧、星象学共计9类著述,另分全集、零散著作两类,《甘珠尔》、《丹珠尔》总目共分19大类。[6]
之后,布顿大师又编制了《续部总录》、《论典目录·如意摩尼自在王璧》、《论典目录·如意摩尼宝筐》。在这几种目录中,布顿大师对原有佛经译典中的编次、卷数、分类,旧目录的著录进行了考订、修正。经布顿大师编制、考订、修正后的完整而系统的佛经典籍目录,成为后世各种版本《大藏经》的底本。他所创造的分类法,成为后世编订藏文大藏经目录定本。
集翻译家、佛学家、目录学家为一身的布顿大师以其深广的学术思想、目录学思想参与到目录实践活动中,使藏文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目录学思想丰富的内涵和有序的组织排列,揭示了藏文佛典精深的学术内容和亘古的文化渊源。
通过布顿大师,我们看到了在藏文大藏经翻译传播历史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藏族佛学大师、翻译家、目录学家们在藏文大藏经翻译传播过程中,为创制推行藏文目录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正是他们的翻译学、目录学实践促使了藏文目录学的发展、成熟、完善。
(三)藏文大藏经在形成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这种体系深刻地影响了藏文目录学的发展。
佛教有自己的文化系统,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说大藏经是藏文目录学发展的催化剂。藏文大藏经成了藏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的有系统的早期最大部头的著作。译经促使佛经典籍目录的产生,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非常实用的工具。
纵观藏文目录学体系,藏学佛经文献目录大体有以下几种分类法。
喜饶嘉措大师的分类。历史和传记类、菩提道次第修心、中观、现观、庄严、俱舍论、律经、释量论、教派;密集、阎摩敌、胜乐;时轮、大轮、喜金刚、各种修行轮、声明;诗歌辞藻学、工艺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医方明全集共21类。
拉卜楞寺分类。甘珠尔、丹珠尔、医方明、声明、韵律学、工艺学、星象学、诗歌、辞藻学、戏剧学、文法、佛教源流史、传记、全集、性相学、菩提道次第修心、密咒共17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分类。甘珠尔部:律经经藏俱舍论续部零;丹珠尔部:律经经藏俱舍论续部零医方明;全集部:显宗密宗明处类法事;综合部:佛教教义;明处类法事大藏经行本、苯教部;大藏经甘珠尔部大藏经丹珠尔部散著作共20类。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分类。甘珠尔、丹珠尔、声明、工巧明、医方明、诗歌、辞藻学、音乐律学、戏剧学、星象学、历史类、目录、性相学、教派、菩提道次第修心、新密咒、全集、各种零散著作共19类。
以上类目的编排基本遵循以下规律:将甘珠尔与丹珠尔立于类目之首;按照经律论密宗八部和大五明小五明的学科进行分类;按照史传全集形式分类。[7]
从以上藏文文献目录分类看,藏文大藏经目录体系为藏文目录学的精髓所在。因此,藏文目录学中的分类、编目体系深深地打下了藏文大藏经分类编目的印记。
[1]桑吉扎西.藏文版大藏经概述[J].法音,2003(2).
[2]才项多杰.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述略[J].中国藏学,2009(4).
[3][5]余光会.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历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1).
[4]李冀诚.西藏佛教夏鲁派祖师布顿大师及其著述[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4).
[6]东·华尔丹.略论藏族历史上布顿大师对藏文文献目录学的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6).
[7]王黎,朱俊波.论藏学佛经文献目录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J].图书馆,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