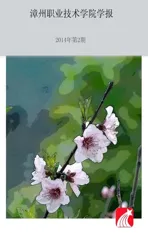六朝画论对庾信前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2014-02-05伊赛梅
伊赛梅
六朝画论对庾信前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伊赛梅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漳州分校, 福建 漳州 363000)
庾信前期作品,虽说总体上不脱离宫体的窠臼, 但清新之作随处可见。在萧氏兄弟力主革新的文风影响下,诗人借鉴六朝绘画理论,把画学的原则和技巧用之于诗,创造出绮丽、清新的诗境,并由此形成了许多新鲜的艺术技巧和手法,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庾信;前期创作;六朝画论;文学背景
庾信(513-581年),是南北朝文学集大成者,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庾信42岁时由南入北,其诗作也因此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庾信的诗歌,历来的评价是前期形式绮艳,内容空洞,而后期则清新绮丽、内容丰富、形式刚健,表现深刻。特别是对其前期的宫体诗作,大多评论家抱着贬斥的态度,斥其“轻佻”“淫靡”等。这些评价因人因时而异,有些论点往往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庾信前期诗歌虽然总体上显示着绮丽浮艳的风格,但是不乏清新之句,蕴含着许多值得关注的新变因素。六朝画论探讨的一些原则和技巧被庾信用之于诗,其诗具有布局精巧、疏密相宜、形象生动、色彩明丽和谐的画面美。本文拟从六朝画论对庾信前期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
一、六朝画论概述
中国文学理论的出现远早于绘画理论。到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更是出现了《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文心雕龙》、《诗品》这样一些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是,当时的文学理论或探讨各类文体的特点、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论文》),或开创性地研究作家创作的心理过程(《文赋》)。即使《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巨著,也只是系统地探讨了文学的起源问题、各体作品的特点与写作要求等问题。对于当时创作中具体而迫切的实践问题,文学理论还缺乏必要的研究和论述。而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六朝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画山水序》、《古画品录》等著述,总结绘画经验,探讨绘画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些绘画理论显示了不同于文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六朝的画论较少对绘画的本质、特征、起源等“形而上”的问题进行探讨,而较多的对“形而下”的问题即具体的艺术问题作出总结和研究。
如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的绘画观,作为他论评画家和自己创作的艺术标准。他在《论画》一文中指出《小列子》一画“作女子尤丽,衣髻俯仰中,一点一画,皆相与成其艳姿”,《醉客》一画“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漫)之,亦以助醉神耳”。这里指出要用衣服发髻来衬托人物的神貌动势;又提出要“临见妙裁”,“置阵布势”,用景物渲染、烘托人物,制造氛围。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更谈到了艺术构思,全图布局,细节处理等等。[1]
此外,宗炳《画山水序》提出写山水之神,还讨论了“远小近大”的透视原理。谢赫《古画品录》总结了绘画六法,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萧绎的《山水松石格》,也对山水的具体画法作了深入地研究,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见解。如“设奇巧之体势,写山水之纵横”,即对客观事物要有取舍、不能极目所见尽入画面,又说“褒茂林之幽趣,割杂草之芳情”,就是要在山水景物中蕴含作者的思想情趣。
可见,六朝画论确实总结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艺术原则、原理、技巧和方法,可补文学理论研究的空白和不足,并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二、庾信早期创作的文学背景
庾信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庾信集序》)的官僚世族家庭,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敏俊迈,博览群书。父亲肩吾是著名的文学之士,深得萧纲的赏接,与萧绎的关系也很密切。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萧统薨,萧纲立为太子,“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2]这标志着新的一代文学之士崛起于梁代文坛,而萧纲、萧绎兄弟,则以太子之尊和亲王之贵隐然充当着他们的领袖。
以萧氏兄弟为首的新一代文人,在知识结构和艺术修养方面,和他们的父兄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一代文学新人不仅好读书、熟悉经史,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擅长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绘画。如湘东王萧绎“聪悟俊朗,博极群书,工书善画”,[3]兼擅人物和山水。他对绘画理论也有深入地研究,画论《山水松石格》在绘画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萧绎的儿子方等也“尤能写真”,简文帝第五子大连“雅好巧思,妙达音乐,善丹青”。[4]萧贲、刘孝先、刘灵等文学之士也有很高的“写真”技巧。庾肩吾精通书法,模仿了画论的评论方式作《书品》,把历代书法家分为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进行品评。可见,庾肩吾也是深谙绘画理论的。而庾信也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善行书和草书。在同一代文人当中,有那么多人特别是文坛领袖和创作中坚,都具有这样的艺术专长,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他们的艺术眼光及当时绘画理论所探讨的问题,无疑会对他们的艺术思维发生作用,影响到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
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在文学发展上自有其积极作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清代贺贻孙《水田居诗筏》云:“观康乐诗,深密有余,疏淡不足,虽有佳句,痴重伤气”,批评谢诗过于雕琢字句,作风生涩,景物描写堆垛沉闷而无灵气流动。然谢诗一起,后起仿效者代不乏人,而且还“总把所模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了来”。[5]对于山水诗的传统和梁代文学界的弊病,当然受到了以文坛领袖自许而又锐意创新的萧纲兄弟的批评乃至贬斥。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称为创作的缘故,就是因为它绝不是对以往创作的重复。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后人多从运字造句、以诗谈玄、缺乏真实情感等方面来批评谢诗。但以萧纲兄弟为首的新一代文人看来,这一诗风的主要弊病,更在于缺乏对自然景物的裁剪选择,不能抓住最能表现对象特征的东西来写,不懂得烘染衬托,制造氛围,因而缺乏“篇什之美”。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就来努力实现这些东西。应该说,萧纲们的诗歌,确实一洗晋宋诗风的滞重雍塞,开了一派写人描物鲜明生动、构图造境富丽清新的新气象。而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当时绘画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所达到的水平,与他们画家或画学理论家的修养,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现存的庾信集中所收他早期的作品,大都可以在萧纲的作品中找到同题之作,可见这些都是庾信在文德省中与萧钢及其文学学士的唱和之作。这样,庾信作为一个文学新人,真正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就处于萧纲、萧绎兄弟革新繁冗滞重的晋宋诗风、追求描人写物清新生动、敷彩设色鲜丽绮艳的潮流之中,他的创作完全受这种文学风气的影响乃至支配,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三、六朝画论对庾信前期诗歌创作的影响
那么,庾信是如何在这种文学风气的影响下,以画法做诗,融画境入诗的呢?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 以形写神、突出动势
六朝画论强调对描绘对象作周密观察的重要性,如宗炳《画山水序》提出必须身入其境,目揣心摩,使对象烂熟于心:“身所盘桓,目所绸缪”,“应目会心以为理”。庾信正是在画论的这种要求影响之下,对所要描写的环境及人物观察精熟,然后选取最能表现对象特征的东西入诗。如下面这首诗,诗人从衫袂、鬟髻等容易飘动、颤动的部分来衬托和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的动势:
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疎节,低鬟逐上声。步转行初进,衫飘曲未成。鸾回镜欲满,鹤顾市应倾。已曾天上学,讵是世中生。——《和咏舞》[6]
在花烛齐明,笙簧悦耳的“洞房”中,一个舞女随着乐曲翩翩起舞,或低首、或转步、或舞动衫袖、或顿足踏地。诗人突出了“逐声”的“鬟”、“随节”的“履”、飘动的衣衫,来增强她舞蹈时霎那间的动势,给人一个具体细腻的动的形象,舞女娴熟的舞技、轻盈的身姿、婀娜的体态如在眼前,笔法非常细致,形象描摹精细逼真,美感令人回味。
再如《夜听捣衣》中的四句:
花鬟醉眼缬,龙子细文红。湿折通夕露,吹衣一夜风。[6]
诗人特别突出花鬟随风飘动,头发的细缕散逸出来,被露打湿,贴在泪眼上面的细节。这就把捣衣女寅夜捣衣的劳苦憔悴和思远不归的悲哀愁惨表现得细腻而独特,而笔墨又十分经济。诗人深入精细的观察和描写能力可见一斑。这显然借鉴了顾恺之认为要用衣衫发髻等来衬托人物神情动势的探讨。
再如《奉和山池》一诗,就充分显示了诗人在穷形写态方面的本领:
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茄凌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舒。
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6]
这首诗首四句叙事,其余六句是对景物的描绘。诗中有动态“鸣茄凌绝浪,飞盖历飞渠”,有静态“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舒”;有近景:桂亭之花、桐门之叶;有远景:日落、云归;更有细节:风惊浴鸟、桥聚行鱼。特别是“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二句,一惊一聚,诗人捕捉瞬间的眼力令人称奇。诗人把镜头定格在鸟惊鱼游的瞬间动势,化动为静,表现了如民间剪纸似的图案美。这两句也一直被后人称道有加。
以具体、典型的动势来刻画人物或描绘景物,是庾信早期作品的一个特点。再看下面这首诗:
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
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侠客行》[6]
这首诗截取侠客醉后跑马上桥的一个场面,借助细节的描写和氛围的渲染生动的反映了侠客的剽悍、粗豪的醉态和骄气。侠客痛饮归来,纵马并辔而驰,路上尘土障目,路边树上的花瓣被惊得纷纷飘落。这是以“细尘”“惊花”“汗马”来旁衬侠客酒后的洋洋自得和满不在乎。最后,诗人选取了一个带有强烈动势的镜头——“争路上河桥”,活现出侠客们勒马上桥、互不相让、意气相争的情景。如果说前面数句组成了这幅画的背景的话,那么这最后一句写的勒马上桥的形象,就由于它的强烈的动势感而在这背景前面格外地鲜明和突出,而侠客的剽悍、粗豪也毕现无疑。
(二) 运用光色,渲染烘托
绘画艺术中的设色法又称色彩法,就是指物象色彩之浓淡、明暗、冷暖、素艳的调配。到了南朝梁代,人们对敷彩设色更为重视。谢赫的六法论,把“随类赋彩”的重要性提到骨法用笔,应物象形同等的高度。稍后的姚最作《续画品》,则干脆用“丹青”用来作了绘画的代称。[7]而萧绎的《山水松石格》对色彩感觉作了专门的研究,总结出“炎悱寒碧”的规律。正是绘画领域中审美趣味的这种变化扩展和渗透到文学领域,因而以庾信为代表的宫体诗创作才会格外注重色彩的视觉效果。
如下面这首诗:
拭啼辞戚里,回顾望昭阳。镜失菱花影,钗除却月梁。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绿衫承马汗,红袖拂秋霜。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张。——《王昭君》[6]
诗中“绿衫承马汗,红袖拂秋霜”二句,“红”、“绿”表面看是字面上的色彩搭配,但再深入体味我们就会发现:“秋霜”色白,为冷色调,给人萧杀、阴森、冷酷的感觉;“红”为暖色调,有温暖、光明、生命的感觉。另外,“马汗”表热,“秋霜”表寒,这“热”和“寒”又形成一种对立,衬托和加强了前面两种色调冷暖感觉的对立,使之更加强烈和难以忍受;从而使昭君的形象在这冰天雪地当中更加孤立无援,茫然无所凭藉,更显昭君的哀怨和凄凉。
再看《昭君辞应诏》:
敛眉光禄塞,还望夫人城。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6]
首先是昭君形象的特写,红颜红妆,鲜艳夺目;“敛眉”、“还望”、泪眼双流,表现昭君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悲愤、怨叹。接着镜头拉开,展现出塞外寒冬的整幅画面:雪路隐约,冰河蜿蜒,天地之间,浑白一片。一面是明艳的色彩,美丽柔弱的女性,一面是“冰河”“雪路”“胡风”“夜月”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诗人以充满画面的冷色调与比例极小的暖色调的尖锐的反衬对照,来象征强大而冥然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对红颜弱女的摧毁性打击。但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夜月照心明”一句,写哀怨中的昭君从这永恒而皎洁的月光里,突然感到了一种对秘不可测的命运的了悟。寒风过后,一轮皎洁的明月把一切都照得晶莹透亮,而红颜红妆连同心胸,也在这月光的映照下变得冰清玉洁,纤尘无染,与月光下的冰雪世界融为一体,而悲愤怨叹也在这冰清玉洁的月光中升华为一种对残酷命运的坦然镇静的接受。于是,“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昭君调弦抚琴,唱起悲凉慷慨的胡歌来。诗人正是借鉴了绘画中的设色艺术,对诗歌语言色彩精心选择和调配,点染出一种冷艳冰清的色彩氛围,刻画了形象,升华了主题。
(三) 经营位置、构图巧妙
“经营位置”是谢赫总结的画学六法之一,是画家的基本功。指的是画家通过经营位置把许多个别的迹象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表现一个主旨或某些意趣。庾信前期诗歌的结构布局,也有不少创新之处。他运用画家“经营位置”的方法,使作品的结构紧凑,布局合理,无拖沓繁密之嫌;人与景的描写也能互相映衬,不滞不隔。如下面这首诗:
紫阁旦朝罢,中台夕奏稀。无复千金笑,徒劳五日归。
步檐朝未扫,兰房昼掩扉。菭生理曲处,网积回文机。
故瑟余弦断,歌梁秋燕飞。朝云虽可望,夜帐定难依。
愿凭甘露入,方假慧灯辉。宁知洛城晚,还泪独沾衣。——《仰和何仆射还宅故诗》[6]
这首诗写丧妻之痛。“步檐”以下六句,写主人公罢朝归来跨进家门所见的景物:未曾打扫的步檐、白昼紧闭的房门、青苔、蛛网、还有断弦的故瑟、梁上的秋雁,景物似乎散乱而零碎。但细细体味发现,这些景物的视角是一致的,都是主人公进门所见;这些景物所蕴含的情调也是一致的,都是败落荒废,无人料理。这样,一幅人亡楼空,凄凉冷寂的画面就活现在我们面前。看似散乱而零碎的景物被恰当的统一在一起,件件都缺少不得。
再从全诗结构看,开头四句写上朝归来,想到家中的妻子已亡,回家也是徒然无欢;次六句写回家所见,满目凄凉冷寂;最后六句写面对这一景象的心理活动:丧妻后孤独寂寞,忍得过早晨,也熬不了夜晚;还不如借了“慧灯”的光亮,从“甘露门”入黄泉找她去!但想到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不仅泪湿衣襟。全诗层层推进,结构十分紧凑。
再如庾信的这首《赠周处士》诗,在构思方面也是很巧妙的:
九丹开石室,三径没荒林。仙人翻可见,隐士更难寻。
篱下黄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叶酒,自和游仙吟。[6]
画家在作画之前往往要考虑画面的布局,哪些地方该落墨,哪些地方该置实,哪些地方该留白。诗歌创作也有一个构思布局问题。从“仙人翻可见,隐士更难寻”二句,可知画面上并无人物出现,然而诗人写石室、荒林、篱下菊、丘中琴,又无一不暗示着隐士其人的存在,构思非常巧妙,最后两句是诗人揣想隐士刚刚在这里饮了松叶酒、吟了游仙诗。这样的想象,是对上述画面容量的丰富和延展。这与古代画师以“深山藏古寺”为题选徒的掌故有异曲同工之妙。被选中的画家只画了嶙峋的怪石、飞流直下的瀑布、下方一小和尚正弯腰提水。画家的高明处在于没有直接画出古寺,留下了形象的空白,但却给欣赏者创造了一个更奇妙、更幽美、更神秘的古寺形象。诗画虽不同,但均得画理,各领其境,正合山水画“妙在无处”的境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或许可以从六朝画论这一特定角度对庾信作品“清新”、“绮丽”风格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因其借鉴经营位置、取景设势的画法做诗,一扫晋宋诗风写物平滞繁冗的弊病,故其作品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景物描写疏密得宜,形成了“清”的特色。又由于受六朝画论的影响,其艺术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前代,所以在创作中不是一味的沿袭化用,而是出自手眼,自创新格,这就形成了“新”的特色,使他的诗歌创作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清新流丽”便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而且这种文风到他入北以后也一直延续着。又由于其借鉴了画学的色彩原则和着色技巧,利用色彩的冷暖对比、明暗对比、浓淡对比等,来烘托人物心境,加强景物氛围,所以作品的氛围感十分强烈,画面鲜艳明丽、浓淡得宜,这就形成了“绮丽”的风格。庾信之所以成为南北朝文坛的典范,与他在南朝时功底深厚的创作技法和语言的驾驭能力是分不开的。正是青年庾信及其一族对绘画理论的吸收和借鉴,拓宽了文学视野,在景物、人物描写中手眼创新,对入诗的山水景物进行提纯和净化,刊落了那些繁冗无意义的东西,从而创造出绮丽、清新的诗境,并由此形成了许多新鲜的艺术技巧和手法,为唐代诗人进一步前进提供了基础和借鉴。就这一点,庾信及其宫体诗人一族的努力是不容抹杀的。
[1] 伍蠡甫. 读顾恺之<画云台山记>[M]//中国画论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 姚思廉. 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李延寿. 南史卷八:梁元帝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李延寿. 南史卷五十四:梁简文帝诸子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钱钟书. 宋诗选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 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 庾子山集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陈传席. 六朝画论研究 [M].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马圳炜)
The Influence of Painting Theory of the Six Dynasties on Yu Xin’ Early Creation
YI Sai-mei
(Fujian Radio & TV University,Zhangzhou Branch, Zhangzhou,Fujian, 363000)
Generally speaking, Yu Xin’s early creation didn’t break away from the style of imperial court but refreshingly lucid style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his poe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ets Xiao Gang and Xiao Yi, who advocated to reform writing mode, Yu Xin used painting theory in the Six Dynasties for reference. He successfully combined the painting skill with art principle in his poems and created beautiful and refreshing poetic flavor. His many new art skills and writing methods provided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cre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Yu Xin; early creation; painting theory in the Six Dynasties(AD220—589);literary background
2014-04-27
伊赛梅(1972—),女,福建三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1673-1417(2014)02-0043-06
10.13908/j.cnki.issn1673-1417.2014.02.0009
I207.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