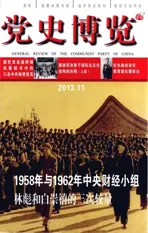饥饿和寒冷是抗联最大的敌人
2013-12-19史义军
■ 史义军
1938年以后,对于东北抗日联军来说,那可真是困难到了极点。据统计,有些部队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无斤米粒粮。其处境之惨,生活之苦,战斗之残酷,难以用语言进行描述。
饥寒交迫比凶恶的敌人还要可怕
1940年3月,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力进行了会谈,并由周保中根据会谈内容于3月19日整理出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涉及粮食问题的: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春,东北抗日联军各部人员极其减低,其原因不是完全由于战斗的损失,而是由于粮食受敌人封锁,农村征发来源断绝,军队常陷入饥饿疲乏状态。常因给养缺乏造成军事行动上的损失,大部分战斗员由于饥饿而叛逃,甚至暗藏奸细分子,借机会造成叛乱投降敌人,许多部队整个瓦解。这不能不归罪于许多领导干部缺乏非常时期的各种准备,特别是由于没有能够适当地解决粮食补给。
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游击队到处能够“因粮就食”,得到农民的广泛的援助,并且能够大量征发,许多游击队不懂粮食储备,更不懂得在军队中应进行严格的粮食管理,不节省,无政府状态的浪费,不知道对每个战斗员应该进行粮食问题的教育,不懂限制和调节食量,一旦困难来临,目瞪口呆,形成军队的严重动摇。现在条件转变,对解决粮食问题应有以下注意办法:
第一,每个活动单位部队,应在其活动区域,或另外不同之地域执行严格秘密的自耕计划和代耕计划。
第二,敌兵守备薄弱和兵力不大的水陆运输、集团采伐场、金矿、煤矿以及山边集团部落等等,应向这些地方进行有利的袭击夺取其粮食牲畜。
第三,农村秋收时期,游击队组成专门征发队,直接到地主富农田中去自己收获运输粗粮。
第四,就有薪炭作业及散种农民进行劝募式给资代购。
第五,强制征发及军事行政征发人民所痛恨的地主富农之剩余粮食等。
上述为目前解决粮食的一般办法,各军历年斗争,应利用经验和环境去努力克服粮食供给的困难,对于游击队巩固发展非常重要,同时必须指出,不但要会解决粮食需要,并且要实行严格的军队粮食管理规则。对于储藏方面,不但要严防为敌人、内奸、叛徒所破坏,并且要防止飞禽走兽、风雨潮湿的侵蚀损害。
这个《提纲草案》详尽论述了征收粮食的重要意义。这些都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1938年以后,饥饿的阴云时时刻刻笼罩在抗联干部和战士们的心头。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鹤北林区小兴安岭山脉密营中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写了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讲了面临的困难和部队克服困难自己动手种地的事情。他说:
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最主要的是给养问题,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问题。所以,我们队伍自己要到山里找秘密地带,要尽可能地多种地 (苞米、倭瓜、萝卜、昔田谷、土豆,等等)。
昔田谷很密地种到地下,从小苗就能吃,长大时可以吃叶,秋天收获吃子;土豆容易保存,还不怕冻,冻时可以吃面子,能有很多吃法;萝卜也可以晒干子,冻了也能吃;倭瓜冻了也能吃;苞米当然吃法很多,但苞米种在山里较高地带,到秋有时不容易收获,种时必须找到洼下地带。
可以设法尽可能捉鱼,夏季尽可能晒野菜或党参等,这些都是候补给养。
到了冬季大雪封山,饥寒交迫比凶恶的敌人还要可怕。当然,有了夏季储存要好得多。
粮食,粮食,还是粮食。
粮食成了抗联各部队和各省省委会议研究的重要议题。
1938年底,三路军的主力西征去了,远在下江的留守部队大都是东北抗日联军六军的人员。1938年冬天就要到来的时候,松花江开始封江了,在富锦境内的一个大江通子上,抗联第六军二十三团一个连被敌人包围了,战了一昼夜,敌人退走了,接着开始跑冰排了,敌人上不来,我们也出不去,抗联战士饿了半个多月。
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二十五卷第19页至22页的《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七次常委会以来的工作及吉东党的情况(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一文中也提到了这次战斗:“去年冬月,六军在松花江江通子里被敌包围半个月,断粮已久……”
饥饿和寒冷使部队官兵不得不越境进入苏联,有的动摇投降,部队大量减员。在这危急关头,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不得不写信向北满临时省委说明留守部队的情况。
1939年1月21日,北满临时省委在写给高禹民的指示信中说:
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的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的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同志们,战斗起来哟!祖国和民族将展开绚烂的前途!……
当时,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有这样高昂的斗志,还能写出这样富有感染力的战斗的诗句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激情荡漾。
冬天到了,太难熬了,想打猎,枪里却没有一粒子弹
1938年12月29日,李兆麟率领的西征部队到了绥棱境内。李兆麟先派遣耿殿君率领一支小部队,到八道林子与六军三师后方联系。1939年1月2日,六军教导队长于大发和许交通员来到八道林子,给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送来了李兆麟的信,信的内容是:“我带领的第三批西征部队已到达白皮营。要火速送粮,以解燃眉之急!”每个字旁边都画着圈,表示焦急万分。王明贵立即集中了30匹马,驮着粮食送往白皮营。
粮食,粮食,还是粮食。
2012年春节前,笔者在汤原县采访了抗联老战士潘兆会。他给笔者讲了1938年底1939年初他们在山里忍饥挨饿的情况:
那时,吃啥呀,夏天吃的是野菜,战马死了吃马肉,马肉吃完了,吃马皮。1938年、1939年啊,太难了。冬天到了,太难熬了,想打猎,枪里却没有一粒子弹。
潘老在讲述的过程中多次提到了苏联,好像是下意识的,苏联……苏联,嘴唇哆哆嗦嗦。
那时,轻手利脚的受不了饥饿的人都跑到苏联去了,苏联那时就是天堂。为了防止部队成员大量越境,高禹民还不得不开展反越境斗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给高禹民的指示信中说:
省委完全同意你在六军二十九团开展反越境斗争。汤 (原)萝 (北)北黑 (密营),我们在任何困难情况之下,我们必须有一部分队伍支持活动。饥饿寒冻逼迫下的六军一师一团,现在当然是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你们必须拿出布尔什维克的坚毅忠勇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展开反越境的斗争,及切实地、耐心地找到方法来克服饥饿的困难。
……
亲爱的禹民同志:紧急的关头、巨艰的局面,没有骨头分子的动摇、叛离常常会发生的。而且这样的事件发生,会破坏我们的计划和行动,会增加我们的困难。西部战线年来的血的经验,是证明了这一点!
饥寒交迫的一师一团,如果情况继续严重,这种事件之产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你们不仅要开展反越境斗争,同时又要开展反动摇叛离斗争!你们要处处提防和预防这些事件之产生 (如注意秘密工作等)。
你们要成为群众的模范,你们要沉着耐心,你们要非常爱护和顾虑队员,这是政治工作中的主要部分。目前巨艰局面之下,领导工作作风常常决定一切。
从以上指示信的文本来看,这应该是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的手笔,因为在他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充满理想的词句,可以看到他对未来充满信心。面对饥饿,1939年3月2日,他以北满临时省委的名义在给高禹民的指示信中说:
只要 “头尚存,血犹温”,为了民族和祖国,誓死坚持我们的艰巨工作!
仅仅不害怕困难,那还不够!还应该“拿出勇气和找到方法去战胜困难”,战胜饥饿!
北满临时省委充分肯定了高禹民在下江留守部队中自己种地解决粮食困难的做法。北满临时省委在指示信中说:
我们认为你们的老幼残弱、伤人、冻伤(者),如果失去抗日战斗及劳动效能 (如不能种地的)而一时不能恢复者不必分配×营,可以送过界外,这样的话,还可以利用×营来分配队员散天种地。这样可以减少队伍的累赘和困难。
种地的问题你们必须以布尔什维克高度的积极性去实现之。事先准备耕地、种子、用器、食粮耕具等,必须极秘密地布置之。
你们必须准备食粮作为军事上必需时之用,在非必需时,无论在任何挨饿条件下不得任意动用,并须秘密安插于各地。现在敌人常常以长追圈围的进攻方式来对待我军,而我军如果陷于这样状况,那只有绕出敌人包围作远距大圈之游击。如果没有粮食而陷于敌人长追圈围中,那么内部可能发生问题,或者束手待毙 (如三军二师),所以应该注意之。
1939年6月,日伪军不断向富锦、宝清七星河左岸出扰,并实行粮食封锁。由于敌情严峻,五军总部及警卫队无从征发粮食,购买亦不易,部队粮食不足成为最大的问题。因恐给养断绝,部队早晚均改为粥餐。“千死敢当,一饥难忍。”饥肠饿肚的滋味异常难受。给养缺乏,农民被日伪强迫归入大屯,受到严密监视,即使有心支援抗联,也难以实现。为解决部队给养,抗联战士只有袭击敌人据点及其监护下的交通线、木业点、“集团部落”、采金场等,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此外,五军的官兵还用松子、野果、树皮、野菜充饥,如山韭菜、山菠菜、山芹菜、蕨菜、蘑菇、木耳等。
在小兴安岭和完达山林区,山野菜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山坡、林间、沟塘、河边,均有分布。
在春、夏、秋三季,抗联六军的女战士们一有空就到河边、山边采黄花,采来的黄花用滚水一烫,拌上盐,就是最好吃的下饭菜。采花的女战士一边采花一边唱歌:
碧草萧萧,树叶青青,
满山野花颜色新,
清香扑鼻,鲜艳吐芬芳。
一阵清脆嘹亮的歌声,
山前唱,山后应,
真是快乐的歌声。
月峰高,月峰美,
我们登越青林,
山菜嫩,山菜香,
姑娘们笑声扬。
玉手采采,采呀采满筐,
日落西山头,采完快回营,篝火晚餐忙。
饿死冻死的战士,远远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数字
抗联老战士刘淑珍给笔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记得有一次,没有吃的,女战士小李子为了摘狗枣子,爬上了大树,掉下来又骨碌到深沟里,摔死了。小李子没有死在鬼子的枪下,却为了能吃上狗枣子,摔死在深山里。
王铁环出生于1927年,是东北抗日联军七军中岁数最小的女兵之一。2012年5月18日,笔者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的全体人员采访了王铁环。她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老妈妈啊!当我们问到那些牺牲的她的长辈和战友时,她的眼里噙满了泪花。她说:
1938年以前,抗联七军可以在密林中宿营,粮食可以自行解决,生活不是那么艰苦。1938年以后,生活异常艰苦,冬天到山里只好挖洞躲藏,夏天就到沼泽地,因为沼泽地里有水泡子,水泡子里有鱼有虾,靠它们也可以填饱肚子。那时候,我小,领导让我看守两根鱼线,别让上钩的鱼把鱼线拽跑了。我就把鱼线拴在了我的脚踝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忽然觉得脚踝勒得疼。惊醒之后,看到水泡子里一个东西翻滚搅起好大的浪花,吓得我大喊大叫起来。一会儿,听到我的喊声,来了好多战士,大家七手八脚把水里的东西弄了上来,原来是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鲇鱼。战士们开玩笑地说,好悬没把王铁环当了鱼饵。
大自然有时比敌人的机枪大炮更可怕,但恰恰是因为敌人来了,才把本来生活在和平安宁环境中的中国人逼进了山林沼泽。
抗联老战士单立志说:
1939年冬季,抗联经历的饥饿和寒冷的考验更为严峻。一连几个月也吃不到一粒粮食,全靠山菜、木耳、蘑菇、橡子等充饥。由于长期吃不上盐,全身浮肿,肿得连眼皮都睁不开。衣服破烂到不能遮身,补上麻袋片,用椴树皮打麻鞋穿。怕冻掉耳朵,用破布条把长得很长的头发拢起来,把耳朵绑上。有多少个长夜,是在冰天雪地里围着篝火度过的。一冬来,饿死冻死的战士,远远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数字。活下来的,很多人至今留有残疾。我现在还不敢轻易早脱掉棉鞋,几十年的冻伤给我留下了遗累啊!
1939年底,严冬早已降临,梧桐河流域的小兴安岭山区早已是冰天雪地。赵尚志等司令部人员自6月份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也没有等来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来开会。尽管望眼欲穿,依然是音信皆无。此时,粮食、食盐均已吃光,战士们靠猎取狍子肉为食。战士们衣着单薄,难以御寒,晚上睡觉时,大家只好把从西梧桐河日军测量队手中缴获的帐篷当被子盖在身上。呼啸的北风阵阵袭来,严寒砭人肌骨,处境极为艰难。
1939年11月末,赵尚志带领几名战士离开西梧桐,往老白山找关系去了,陈雷等在原地驻守了几天。12月5日,他给赵尚志写了一封信,通过交通送给赵尚志,信中描述了他们在等待赵尚志归来的情况:
自与你分手后,我们未能离开与你分手的地点,到今天已在这里过了五夜,都很平安。在这五六天中,我们多半是吃狍肉,因为这里狍子非常多,这也是我们未离开此地原因之一。 (在十二月一日那天,张副官、赵海、葛青林每人各打住狍子一个;二日,张、葛二同志又各打住狍子一个;三日,张副官自己打狍一个,昨天空空如也)根据此地狍子多,每天如果能打住二个,便能够吃,因此,在这几天中,给养并未耗费多少,从现在计算,给养还能吃四五天。如果这里给养吃绝,狍子再打不住,那就只有想另外办法去解决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能等待你的关系,至于若找买东西的关系,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在这附近,在现在时期接近老百姓,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的队伍,同志们中间互相的关系,是比较改善一些,但是也有几个人表现萎靡不振,我当然使用各种办法来提高他们的精神和兴趣,现在虽然比较好些,但是那种颓靡现象还是没有铲草除根地消灭。至于他们工作方面也是有相当的缺点和弱点,譬如劳动工作的依赖性。……这种现象,当然也是领导上的缺点,最近他们昏昏沉沉的现象,是比较少些了。我们的住处,现在我们就要搬,至于和你关系的规定,不必在信中写,可询问交通员便知。……如果我们现在天天能打住狍子的话,吃的当然是暂时的算能解决,但是咸盐或者要成问题的,如果狍子再打不住 (当然那是碰事,你是知道的,那是指不上的),当然给养问题,便成严重的问题了。最后我们希望你顺利地迅速解决了问题,以便开展和转变东北新形势,这是我们期待的。临别指示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定能遵照办理。此致革命敬礼!
笔者多次采访过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她也多次给笔者讲过关于饥饿的故事。1941年9月,她和小分队回国执行任务。她说:
由于挠力河发大水,淹没了草甸子,无法行军,部队只好绕道上游,多走了一个多月的路程。但我们只准备了七天的粮食,后二十多天没有粮食吃,大家饿得走不动,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我们捡蘑菇、挖野菜、摘刺梅果,还吃树叶、树皮、草根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找来吃。
一天,队伍走到小团子山。这里地势较高,春天有人在这里种过大烟,夏天割完大烟,人就走了。我们在地里找到些零星的菜,如倭瓜、角瓜、萝卜,还有点儿大烟子,总算吃了一顿正经粮食,救了我们的命。小团子山周围一片汪洋,但部队继续前进。姜信泰 (又名姜健)政委带一些人去找给养,碰上敌人的一队骑兵。队伍转移时,李呈祥失踪了。王队长把队伍集合的地点记错了,我们和姜政委的人没有接上头,队伍分散后,人更少了。
有一次,部队要找休息的地点,那里恰巧离抗联早期活动时住过的炭窑不远。王队长派指导员李在民和中队长李忠彦去看看有没有人,但只有李忠彦一个人回来了。他汇报说:炭窑没有人,李在民已经饿倒在炭窑门口,说: “我走不动了,不行了。你回去告诉王队长,我誓死也不叛变,要革命到底!”听了李在民指导员的临终遗言,我们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在艰苦战斗中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过挠力河,我们开始割柳条做筏子。二十多天没有吃粮食,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同志们拼尽全力,做好筏子渡过了挠力河。过河后,大家咬着牙继续前进,饿得实在走不动,一天只能行军五六里路。保合同志也有几次要倒下去了,但仍以顽强的毅力背着沉重的电台坚持着。有一次,他倒在水甸子里,硬拄着棍子爬起来,是强烈的责任心在支撑着他极度虚弱的身体,他想,不能因为我的死使部队同指挥部失掉联系,致使全队有行动失败的危险。有四五个同志把全身的力气耗完了,倒在路边一动也不能动了。队伍中仅有我一个女同志,因饭量小,少吃点还顶得住,就把采来的野果、野菜分给饭量大的同志。我们的司务长老王 (王喜刚)三十多岁,原是个伐木工人,身体高大强壮。他饭量大,平时两个我这样的人的饭也不够他一个人吃。他为了大家,到处找吃的东西,找到点儿吃的,自己不吃,先给同志们吃。我见他饿得不行,有时省下点儿吃的给他,可根本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不幸的是,老王和另一个炊事员同志又一次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我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含着泪,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树丛里。我心里暗暗发誓:安息吧战友,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完成任务,为你们报仇!
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默默告别了永远长眠在挠力河畔的司务长,又踏上了征程。
……
到了冬季,是抗联战士最难熬的。2012年11月,笔者在广州采访抗联老战士卢连峰时,他给笔者讲了这样一个细节:
到了冬季吃的是个大问题,我们吃过草子、冻野菜,还吃过松树皮,把老皮弄掉,把里边的皮放在水里泡,晾干后砸碎磨成面,吃进去大便出不来,要抠才行。
刘淑珍说:
我跟随抗联转战整整四年。四年,一千四百多天,我们第三军全体官兵没有住过一次火炕,没有盖过一次被子,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
在西征的路上,抗联饿死、冻死了很多人
笔者采访过一些抗联老战士,他们都说那个年代最难熬的是冬天:大雪纷飞,朔风凛冽,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是经常的,寒冷的天气断指裂肤;行军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峡谷间,狂风怒吼,树木摇曳,白毛风夹着大烟泡刮得大树呜呜作响,有的树枝不堪狂风的肆虐咔吧咔吧断折倒地。战士们经常走在大雪齐腰的老林子中,有的扛不住冻饿倒在地下,几分钟后就变为化石般的僵尸。有的战士临死前产生了幻觉,抱着枫桦——枫桦的皮是红颜色的,他以为那是一缕温暖的火。他脱掉棉衣,光着上身,紧紧搂着枫桦,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死了。
自1938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大部分部队一年四季都是在露天宿营。天大房子地大炕,围着火堆把歌唱,这就是抗联战士乐观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难的具体表现。篝火取暖和驱除蚊子叮咬,成为抗联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火是抗联最亲密的朋友,一天也离不开它。火不但解决了取暖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有了火,吃得虽少,不觉太饿;穿得单薄,不觉太冷。所以,在抗联著名的歌曲《露营之歌》中,春、夏、秋、冬四季的描述中,都着重提到了火。在春天,“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在夏天,“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在秋天,“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在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在最寒冷的季节,大、小兴安岭的夜晚都是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白天尚可,太阳一落山,真是冷风刺骨,点篝火,火都不愿意燃烧,只是吱吱啦啦地响着,火焰极微,仿佛被凛冽的寒风征服了,虽有干柴,而无烈火,人们面面相觑,也无能为力!
2012年11月,笔者在广州采访抗联老战士卢连峰时,他给笔者讲了1938年冬天抗联西征的事情。
关东军对小兴安岭根据地实施破坏,不让老百姓接触抗联,成立部落,实行保甲连坐,收买叛徒特务。抗联受不了关东军的“围剿”,为保存实力决定西征。抗联领导在伊春还专门开了一个会,决定到松嫩平原开辟新的根据地,还有准备联系在热河八路军的意愿,这是一次战略转移。到了1938年11月份,在萝北的老等山根据地,李兆麟带着我们西征。开始有马,还有一个交通姓林,在原始森林由东往西穿,几个月后我们到了海伦的四方台,王明贵带着六军在那,李兆麟叫他把粮食拿出来给我们吃,见到王明贵后我们才吃了一顿饱饭。
在长征的路上最困难的是粮食和棉衣,脚穿的是靰鞡鞋裹的乌拉草,雪太大,都到大腿根,靰鞡底一整就掉了。我记得有一个叫韩晨的警卫员,他的靰鞡底就掉了,用马皮裹着靰鞡继续走,手和脸都冻黑了。冬天多冷!都露着肉啊,没办法!我才十六七岁,在鹤立岗弄得小孩棉袄,鞋也不跟脚,脚后跟也冻坏了,隋团长提醒我:小卢好好的,一定要坚持!
到了冬季吃的是个大问题,我们吃过草子、冻野菜,还吃过松树皮,把老皮弄掉,把里边的皮放在水里泡,晾干后砸碎磨成面……实在没有吃的就杀马。杀了马,马鞍子还要背着,换着背,一天就走10多公里,1000公里走了好几个月。
晚上拢火过夜,一堆火四个人,真的就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那时我们都有各种手工锯,在林子里专找 “站干”烧,“爆码子”不行,点着火它梆梆地响,火星子乱飞,人睡着了一整棉衣就被烧着了。
在西征路上,抗联饿死、冻死了很多人,人一死就像木头一样,一扒拉就倒啦。
……
冬天,在林海雪原中行军,必须挑年轻力壮的队员作尖兵在前面开道,后面一个接一个踩着脚印走,最后一个人用树枝埋脚印。渴了吞雪团,饿了嚼柳树条子。除了要战胜严寒,还要战胜饥饿、疲乏、瞌睡的折磨。有的战士在行军的路上休息时,抱着枪背靠着树根便长眠了。有时候掉队的战士死了,尸体就被野兽吃了。那时,大、小兴安岭里狼多,狼群来了,饥饿疲劳的战士连端枪的力气也没有了,等后续的战友过来时,就剩下了一副凌乱的骨头架子,没有肉的手还紧紧握着枪。
1939年秋后,日本关东军制定了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确定关东军第六六九部队野副昌德少将为司令官,并纠集日伪警特7.5万人,对东南满地区进行联合大“讨伐”。敌人采取“日伪军警合为一体”的办法,成立了“工作队”“挺进队”“工作班”“宣抚班”,并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等毒辣手段,对抗联加紧了严密的封锁围困,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抗联部队完全失去了根据地,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之中,陷于异常困苦的境地。
2008年4月底的小兴安岭,冰雪已经融化,树木露出了新叶,笔者回到鹤北。在萝北二十里河、鹤岗桶子沟一带,笔者寻找到了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经过询问,在鹤北林业局的跃峰林场,笔者找到了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种地的一些地方。地垄沟依稀可以辨认,在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树木已经长到了碗口粗了,周围山头上的散兵坑和地窨子的遗迹也清晰可辨。
站在这片东北抗日联军战斗过的土地上,微风吹拂,林涛声声,笔者的眼前浮现出了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陈翰章、高禹民等等抗日将领坚毅的面孔;笔者的耳畔又响起了一首首鲜血凝成的战歌:“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万里长征,山路重重,热血奔腾,哪怕山路,崎岖峥嵘,饥寒交迫,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