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三种式样——比较周作人、张中行、张昌华的民国人物书写
2013-11-05冯仰操
冯仰操
自古以来记述人的文字太多了,甚至形成了固定的体裁,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列传状一类,章学诚《文史通义》列传记一类,林纾《春觉斋论文》列史传一类,所指相同,除主流的古文外,尚有笔记体,如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所列轶事类、历史琐闻类多是。至民国,古文淡出文坛,尚有徐一士、黄濬、瞿兑之等撰著笔记,其中多记有清一代人物,但终被新文学的潮流遮蔽,胡适、郁达夫等人鼓吹的传记文学自此大行于世。一时代均有责任对前代人物进行追忆、品评,自古如此,今世亦然,在台有刘绍唐等主编《传记文学》等长期发掘民国人物,在大陆对民国的重评则方兴未艾。述说民国人物应是一种严肃的事业,如柳鸣九所说“记述他们为文,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怀念,也不仅是机械的简单记录,更不是讲套话式的应景,而应该是‘一桩精神文化的使命’”。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温故书坊”系列,所“温”者多为民国人物,其中有张昌华的文集多种,如《曾经风雅》、《民国风景》、《故人风清》等,堪为代表。
往事非烟,同一传主,因材料、立场及用笔的各异,各人所呈现的风景自然不同。本文试图用比较的方法,给张昌华所撰人物传记的特色一个恰当的位置。当下民国人物传记热之前,早有若干先驱者做了相同的工作,如周作人《知堂随想录·北大感旧录》、张中行《负暄琐话》系列,他们所写的人物多有重复,如辜鸿铭、章太炎等人,而呈现的面貌各异,这就给本文的比较提供了可能。周作人、张中行自民国走来,带着深刻的民国印记,而张昌华亦是“旧派人”风范,喜书法印章、乐书窗读月。虽然都是怀旧,却因各人的境遇、天赋不同,而呈现的“旧”各不相同。下面以他们对辜鸿铭的记述为焦点,谈谈怀旧的三种式样。
周作人虽然常谈“寿则多辱”,却从晚清、民国直挨到了“文革”前夕,其一生所见所闻可谓多矣。他晚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与写回忆文章,以1960年开始写的《知堂回想录》最著名,其中涉及北大故交,如《卯字号的名人》、《北大感旧录》等,均短而有趣。歌德曾著自传《诗与真》,周作人从这里受到了启示,认为自传均有诗(虚构)与真实(事实)两种成分,话锋一转,强调自己的文章“里面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排斥诗歌的感叹与小说的描写。周作人一生以散文为业,而非诗与小说,早在1920年代重编其译文《空大鼓》时已表露对尼采的戏剧式抒情风格的排斥,作文追求平易,到晚年更返璞归真。因此以真实为旗帜,周作人在材料的选择上便以个人见闻为主,且看他对辜鸿铭的记述,正是《北大感旧录》的第一位。
他先描述了大家对辜鸿铭的印象,“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紧接着描述其外貌、履历。履历是这样写的,“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话至此,周作人谨慎的加了按语,“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之下又讲了两件亲历的轶事。从全章看来,周作人基本做到了求真的要求,甚至排除了个人的主观评价,如辜鸿铭从新党到守旧派的形象转变本是关键的问题,但他一笔带过不予评论。他这一平实风格的自觉,可与其1950年的同题文章《辜鸿铭》做个比较,那是他为《亦报》写的小杂感,其中有辛辣的讽刺,认为辜鸿铭缺乏热诚,没有革命家的骨气,该文最后笔锋一荡,竟然呼吁去国的林语堂与傅斯年归来,显然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
与周作人这一写法相对的,可举温源宁《辜鸿铭先生》,从头至尾全是主观的评价,诸如“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等判语处处可见。温源宁用英文写作,其机智的议论更多受英国essay的影响,但要给周作人的文章找一种比较近的典范,大概是明清的笔记了。周作人是现代“美文”的倡导者,最早鼓吹英法随笔,但自三十年代以来,他阅读和品评更多的是明清笔记,这一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风,乃至产生了独特的“文抄公体”。传统的笔记内容“杂”,不拘类别,形式“散”,长短不拘,因此笔记作为小专题写作,仅是局部的琐屑的记录。如徐一士所著笔记《凌霄一士随笔》中有“辜鸿铭之文多诙谐语”一则,仅仅摘引辜鸿铭《幕府纪闻》若干条,呈现对象的一斑而非全貌。周作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再抄引别人的文章,而是以回忆为材料,所呈现的辜鸿铭仅仅是一个侧面,即通过亲闻的两个轶事凸显辜鸿铭怪的一面,而无意于做整体的评判。
虽然是记录琐事,周作人仍有独特的别择,“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别择的条件之一是趣味。周作人向来不板着面孔做文章,创作《知堂回想录》更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如与曹聚仁通信时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最所不能,这回写的恐怕更是上边是大学生不要看,下边是中学生看不懂,弄得两面不讨好,奈何”。无论如何,周作人最后呈现的文章多趣味,文字多质朴流畅,如写辜鸿铭的车夫一段,“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不禁让人捧腹。其语言虽偶尔点染若干文言词,句式却是充分欧化了的,用长句,多从句,却层次分明,不失为现代语文的范本。
张中行的文风晚成,是周作人的学生辈,虽继承了前辈的许多特征,仍有自家的面貌。周作人喜写民风民俗,张中行写名人更写市井人物,分明是一路下来的。他也写辜鸿铭,列在《负暄续话》的第一位,篇幅是周作人的近十倍,严谨详实。张中行难逃周作人所言的诗与真的两难困境,却更为洒脱,坦白“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
张中行与辜鸿铭素未谋面,在史料层面,很难依赖个人经验,他的工作起步于周作人所止步的地方,如周作人谈辜鸿铭的怪,却不讲其原因,只是一句“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带过,而张中行所探讨的恰是“怪”背后的原因。张中行的文章没有周作人那么随意,虽有闲话插叙,更多严谨的铺排,如谈辜鸿铭的“ 怪”从外到内或由小而大,从“ 字”、“ 文”、“ 性格”直谈到“思想”,层层递进,尽力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他所用的材料小半来自前人记忆,大半引自传主的文字,就篇幅言,所引的文章占了全文的一半,正继承了周作人“文抄公体”的传统。即便是引前人记述的材料,张中行大多加以考辨,文章内部形成了众多的对话关系。其中有呼应的,如引《辜鸿铭特辑》中陈昌华谈辜鸿铭中文字古怪的例子,之下用自己的藏书加以印证;有商榷的,如引温源宁《辜鸿铭先生》的一个论断,之下提出相反的可能性。在众多引文与考辨之后,张中行的结论更为平实可取,如论“用处世的通例来衡量,确是过于怪,甚至过于狂;如果换为用事理人情来衡量,那就会成为,其言其人都不无可取,即使仍须称之为怪物也好”。除了对材料的辨析外,张中行同周作人一样有选择性,如启功所言“那种勾魂摄魄之功,更重要的还有不屑一写的部分和不傻装糊涂的部分”。张中行熟悉辜鸿铭的各种掌故,对不确的材料尽量略过,还有的如“有关妇女的脚的,因为欠雅驯,从略”。
写史却不忘诗,“新潮”的周作人对“保守”的辜鸿铭很难有了解之同情,而张中行作为历史的观望者,对民国知识分子群落有深广的怀念,正如吕冀平从中读到的“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张中行开篇便直抒对辜鸿铭怪的偏爱,认为“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我们常人怎么能不刮目相看呢?”直至篇末,仍止不住地重复,“这可爱还可以找到更为有力的理由,是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成为广陵散了”。这一广陵散式的怅惘几乎出现在每篇文章里,这是张中行不同于周作人趣味的热的表现吧。
周作人晚年作文不拘一格,不忌讳用欧化长句,张中行的文字则别有风味,多用短句,初读质木无文,细读方能感受其源于口语却精练含蓄的魅力。张中行对语言的运用有强烈的自觉,其《文言和口语》推崇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造就的白话文,认为其成就是与口语“不即不离”,要求在口语的“鲜明流利”外加上“深沉委曲”,“这深沉委曲,是来自内容的精粹和深远,以及表达方面的精炼和典重”。张中行的文章正是朝这个方向去的,正因此,方获得了大批读者的青睐吧。
与周作人、张中行的文学成绩或声望相比,张昌华只能叨陪末座了,但其文仍有其独特性与不可替代的作用。张昌华对民国的纪事是有计划的工作,其文章结集者自2002年《书香人和》至2012年《故人风清》有六七种之多,均以民国人物为对象,虽各集有重收,却有了上百位人物传记的规模。他写民国人物传记,虽然全是名人,领域却很广,从艺术到科学,从文人到武将,以小型传记的规模一一道来,影响甚至更远。张昌华在自序中提及一件琐事,有年轻读者称他为“扫盲教师”,由此可见一斑。他写过《 辜鸿铭的东西南北》,占了《 曾经风雅》的头一位,篇幅又远超张中行,因倾向于通俗与普及,使得材料、立场及用笔又与前辈们不同。
周作人偏史,张中行诗史并重,那么张昌华则重诗。他详细介绍传主一生的趣闻轶事,乃至有浮泛的成分。关于辜鸿铭的传记材料已经出了多种,如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书社,1988年)、宋炳辉编《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黄兴涛编《名人笔下的辜鸿铭、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等,张昌华文晚出,所用材料均出自以上各书。上述二手材料多出于印象式观察,不能完全信赖,但张昌华的文章引用过于频繁,且不加批驳,自然会有所失察。此外,多轶事的罗列,但很少对传主本人的功绩实在的考辨,因此文章有搜罗奇珍的趣味,却很难真正进入传主的深处,萧乾早在《书香人和》中指出“惟恐不足的是,‘书香人和’,论人有余,品书不足”,即便到后来,张昌华对传主著作的评介仍是有限的。
张昌华写的是诗,而且是赞美的诗,虽有材料的不足,却自有其功绩。周作人、张中行的文章深刻却不流行,其他的传记材料丰富却难分辨,而张昌华能够占有大量的材料加以深入浅出,为普通读者说法。他写民国人物,多选择一些有趣的角度,如辜鸿铭则依次介绍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扬我中华”、“名士风流、独领风骚”等。张中行写诗却非常含蓄,张昌华写诗却充满激情甚至止不住地现身说法,如赞美辜鸿铭“‘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等等随处可见。张昌华的集子愈晚出者愈好,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重史料的如《蒋梦麟二题》、《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选题精的如《“ 不如青史尽成灰”:刘绍唐和他的〈传记文学〉》、《“ 脚编辑”余大雄和他的“晶报”》,开篇奇的如《诗酒台静农》、《 闲话西滢》等。
民国离我们并不遥远,却横看成岭侧成峰,尤其是对民国人物的追忆,作者站的或高或低所呈现的风景迥异。就站的位置说,周作人几乎是俯视的,只是以有趣的态度看辜鸿铭的怪,张中行却是直视的,不彰善隐恶,展现其全貌,而张昌华离民国更远了,则将民国理想化了,仰视各位名人雅士,呈现的是理想的激情。他们怀旧的式样各异,对于今天的人们却都是必要的,正因他们,人们才逐渐地接触那段并非一团漆黑反而光芒四射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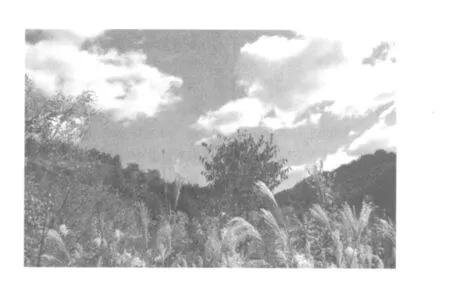
【注释】
①参见柳鸣九《名士风流:中国当代“翰林”纪事》前言,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②参见董桥《名家翰墨》序,收张昌华《名家翰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③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后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④参见周作人《辜鸿铭》,《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794-795页。
⑤参见温源宁《我的朋友胡适之——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南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⑥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⑦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⑧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后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333页。
⑨周作人:《与曹聚仁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136页。
⑩张中行:《负暄琐话》小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⑪参见张中行《负暄续话》启功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
⑫吕冀平:《负暄琐话》序,收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⑬参见张中行《文言和白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7-341页。
⑭参见张昌华《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自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⑮萧乾:《书香人和》序,收张昌华《书香人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