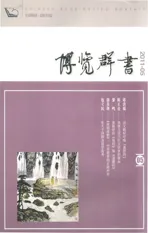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
2013-10-24○许力
○许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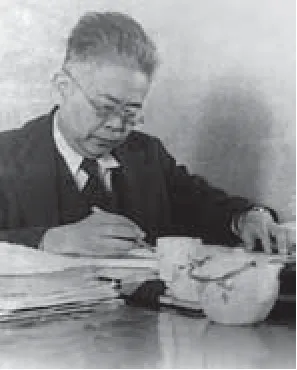
近日,笔者在研读“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相当多的论著在谈到“史料学即史学”这个论断时,往往认为,“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历史研究宗旨。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题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这里所说的“史料学即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
“史料学即史学”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提出来的。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 集中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是: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明明白白说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将“近代史学”与“古世中世”的“著史”作比较,说明“近代史学”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没有泛泛而谈“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而更系统阐述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的“史料略论”篇、“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篇详细地阐明了傅斯年对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认识,由此可窥见傅斯年的史观。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19 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工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傅斯年先生更进一步说明,“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虽然认为中国史学发达甚早,并将宋代史学的诸多特征指为新史学,实际上却是以欧洲近代的新史学作为标准,来反证中国的史学发展程度。
那么,傅斯年认为的新史学是如何呢?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曾留学英、德,学习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傅斯年先生的史观是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分支。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要想探明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们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史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这样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
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傅斯年先生有着那个时代学者特有的教育经历。幼时在私塾学习中国传统的“经”“史”,在北大上学时被胡适“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深深折服,以后留学欧洲,亲身体验“欧风美雨”的洗礼,接受着当时最“时髦”的思潮。在深深地理解了几千年来中国旧史学被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所束缚,中国知识分子被奴化的现实后,傅斯年坚决主张,旧史学是把史学作为传道的工具,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以维护封建统治,而新史学就是要打破旧史学,实实在在地做学问,不再沦为封建伦理的附庸。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想流派都被介绍进入中国,它们相互交锋,激烈争论。傅斯年反对利用史学为普及这个运动、那个主义服务,力图保持历史学的纯粹的科学认识功能,“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因此他强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反对对史料妄加解释,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在面对几千年的旧史学和各种花样的新思潮时,在对中西史学的对比思考中,傅斯年找到了他所认为正确的史观,即实证主义史观,并在回国后在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中,积极鼓吹,希望“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方法论确立了,具体应如何操作呢?傅斯年先生说:
我们可以把一句很平实的话作一个很概括的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在这里,傅斯年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新史学发展的建议:研究直接材料、扩张研究材料与扩充研究工具。
许多批判傅斯年“史料即史学”史观的学人,往往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他的“史学只是材料的堆积”,“……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是资产阶级的唯物史观的和形而上学,有些不可知论的嫌疑,不可能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也谈不上史论的进一步结合。更有学人将“只讲微观认识一些个别的历史现象”作为傅斯年的“史料学即是史学”论断的弊病,这多少有些曲解了他的本意,因为他虽然反复强调史料的作用,但从未否定史观,只是他从不空谈史观。在傅斯年1935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对此有所阐述。他说:编历史教科书与编算学、物理等教科书有绝不同之处,“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所谓‘天命’(庞加赉,Henri Poincare,认为可以重复出现的事实,如元素、种类,使科学得以发展),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据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由此可见,傅斯年不是“轻视理论指导”,而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历史事实是特殊、个别的事例,事实之间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套在史学研究中。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能自己想当然,凡事都硬往上套。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在展开了对“史料即是史学”的批判之后曾刮起一阵“以论带史”之风,对史实的研究全套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对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如今,史学界已经对这种倾向有了强烈的反思,但是还不够,如果能将傅斯年先生“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的话真正落实,“史学即是史料学”将不再是对“史料学派”的批判,而是史学发展的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