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不成样子的阅读
2013-10-24○赵勇
○赵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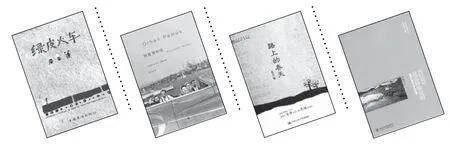
说到2012 的读书总结,我感到惭愧。总的来说,这一年读的书不多,而读的不多的原因之一是有本书读得太多了。
这本书是布莱斯勒(Charles E.Bressler)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 》(Literary Criticism: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第5 版。一个偶然的原因,我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与我的几位学生一道上了翻译这条“贼船”。春节之后,我除自己翻译的那部分外,开始投入到逐字逐句的校译之中,就这样一直折腾到9月中。既然大半年反反复复都在读这本书,我似乎应该谈一谈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还是留点神秘感吧。这里我只是把瑞恩(Z.A.Rhone)在“序言”中的结尾段拿过来,做个广告:
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布莱斯勒的这部著作已上升为美国文学批评方面最畅销的入门书之一。学生与教师均已发现,布莱斯勒对于文学理论与批评中许多抽象且艰涩的理论概念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我相信,这个新出的第五版不仅为错综复杂的文学理论界提供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批判性视角,而且也为理论运用到文本与课堂之中打开了方便之门。
翻译和校译之余,我认真读过的书大概只有三本:《路上的春天》(聂尔著),《纯真博物馆》(帕慕克著)和《〈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钱振文著)。
我记得读聂尔的第二本散文集《最后一班地铁》时,其中的一个句子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我来说,所有的感情都不单纯。它们不光是感情,它们也凝结着思想的血。它们需要细致,曲折,独特的表达方式。”让思想之血充盈于散文之中,这大概也是聂尔散文写作的秘密,如此一来,他的散文便有了筋骨、味道和嚼头,好读而且耐读。这种散文观常常让我想起萨特的那个说法:“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某些事情,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而散文的价值当然在于它的风格。”(《什么是文学?》)萨特所谓的散文与聂尔笔下的散文肯定不是一回事,但我却总觉得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什么关联。
因为《路上的春天》的出版,我邀请聂尔来北京做了次讲座。聂尔在举例时提到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他说他被这本小说感动了。于是我立刻决定买回这本小说瞧瞧。结果可想而知,我也被感动了。
当凯末尔“顺”走了芙颂用过的许多物件(包括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和芙颂抽过的4213 个烟头等)来治疗他的爱情之痛时,精神分析学家估计有了用武之地,但小说的魅力却也由此显示出来。现代小说似乎已不像古典小说那样能够包罗万象了,它们往往选择人性的一个部位,开凿钻探,直到把这口井打出水为止。深水井里的水显然更好吃,而被它感动似乎也就容易解释了。
为了弄清楚帕慕克的文学观,我又读了他的《别样的色彩》和《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的一些篇章,约略了解了《纯真博物馆》的写作过程。作者先是在楚库尔主麻区买下了一座废弃的建筑,然后开始改造成一个博物馆空间。然后他开始在二手商店和跳蚤市场搜集那个虚构家庭中使用过的种种物品。有一天,他“发现一件浅色的裙子,上面装饰有橘色玫瑰和绿叶子。我认为这正好适合小说女主人公芙颂,我把裙子摆在眼前,开始写芙颂身穿这个裙子学开车的场景细节”。这种写小说的过程让我感到奇特,作者似乎是要重建“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场景,让想象有了对应物、或让物品激发了自己的想象之后,方才运思落笔。而这种写法和做法也诞生了两个作品——作为小说的《纯真博物馆》和现实世界那座实实在在的“纯真博物馆”,后者已于2012 的4月27日正式开张。
我在十一长假读完了周云蓬的两本书:《绿皮火车》和《春天责备》。
我是在2008年知道周云蓬的,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盲人歌手。后来我在《独唱团》里读到了他的《绿皮火车》,大为惊异。他在篇幅不长的散文里把人生况味写得跌宕起伏,五味俱全,让人叹服。而读他这两本书,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先前那种模糊的感觉:这位盲人歌手不光在诗(歌词)里、歌里有出色的艺术感觉,而且文字的感觉也不同凡响。比如,因为纪念邓丽君,他曾写过这样一个文案:
邓丽君,我们音乐的后娘,我们色情的大姐姐,如果你生在21 世纪的北京,一定会成为若干地下乐队的女主唱。北京的沙尘暴将使你的支气管无比坚韧,北京强悍的摇滚音乐人绝不允许你至死未嫁抱恨终生。(《春天责备》,P229)
关于这两本书,我也想写一写书评,但刚写了一半,莫言获奖了。而我所在的学校为了强化与莫言的关系,也频频出招。于是,Beijing Nomal University(北京师范大学——编者注)被网友欢快地称作Beijing Nobel University(北京诺贝尔大学——编者注),我所在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被称作诺贝尔奖培养基地,我的导师成为“莫言导师”,我的同学被称作“莫言好友”。一位美国朋友写文章时引用了我的一些说法,并称我“很多年里一直是莫言的粉丝,写过不少莫言评论,而且在不计其数的文学场合与莫言有过接触”,我读后吓了一跳,立刻写邮件纠正她的错误说法。我说我与莫言有过接触,但极为有限,真正面对面似只有一次,“不计其数”太夸张了;我只写过两篇关于莫言的评论,谈不上“不少”;我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但算不上粉丝。如此纠正时,我一方面是要还原一个基本事实,另一方面我也深知,粉丝的情感指向一般都是非理性的,一旦把谁说成是谁谁谁的粉丝,他的价值判断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后来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北大中文系邵燕君的一句高论:路遥是有粉丝的,但莫言没有。这个说法让我沉思良久,她不经意间点出了两种类型的作家作品最终会催生出怎样的文学受众。
我不是莫言的粉丝,但我确实读过他的不少作品。当然也有漏网之鱼,比如长篇中的《生死疲劳》,当年我只读了一半;而那本《酒国》我也只是有所耳闻,却并没有下决心找来一读。伴随着莫言获奖的喧嚣,我决定把这两本书读完补课,顺便搭配着读他那本52 万字的《莫言对话新录》。而这两本小说读完,莫言的长篇我就全部读过了。
我现在得承认,《生死疲劳》当年之所以只读到了“猪撒欢”,是因为尽管它形式新颖,但内容却相对贫乏。我读小说读到这个年龄,可能对花里胡哨玩形式的实验已心生厌倦。我想从小说中读出点干货,如果它不能满足我的期待,我干嘛要把时间搭进去呢?但莫言获奖之后我听到一种说法:因为《生死疲劳》去年刚好翻译成了瑞典文,评委写出的那两句话很可能就是从这本小说中概括出来的。这么说,我当年的阅读状态是不是有问题?我没把它读完,怎么能肯定它后半部没干货呢?自我检讨一番之后,我立刻拿起这本书,调整好阅读状态,把它从头读到了尾。但遗憾的是,我依然没读出多少干货。接着我又读了《酒国》。读这部长篇我也充满了某种期待,因为《莫言对话新录》中说:“在我目前所有的创作里面,下刀最狠的是《酒国》。因为它所触及的问题是极其尖锐的,而且是在那么一个时期。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场学生的运动,最早的起因是对社会腐败现象极其强烈的不满。”又记得莫言刚获奖时在媒体见面会上说,《酒国》等作品,是“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种说法更是让我好奇,我期待着能在这部作品中读出一种批判效果。
但读过之后,我却依然比较失望。莫言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并说“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莫言的这部长篇确实展示了结构的才华,小说(《酒国》)里套小说(李一斗的各种小说实验),莫言(真实作者)写莫言(真真假假的虚构人物),集荒诞、魔幻、戏仿、侦探、黑色幽默、超现实叙事于一体,把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吃人(红烧婴儿)的案件写得风生水起。但说实在话,这部长篇我只看到了精致的结构,却没看到多少政治。这是不是意味着结构挤压了政治,结构放逐了政治?
不过,《莫言对话新录》我觉得是本值得一读的书。如果说作者在小说中藏得很深,那么在与评论家、汉学家、大江健三郎、记者等人的对谈中,莫言却敞开了心扉。我读莫言时遇到的一些困惑差不多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比如,莫言与多人对谈时曾经说过,他钦佩左拉那种敢于发出“我控诉”的声音的作家,但具体到他本人,他却不愿意站到作品之外说话,之所以如此,是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生存状态、个人性格等等使然。他说:“我的性格可能不太合适扮演这种台前角色,以非文学的方式扮演社会良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既如此,我们在《讲故事的人》中听不到我们想听到的东西也就可以释然了。
但问题马上接踵而至:这究竟是莫言一个人的性格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集体性格?如果是前者,为什么当代作家大都只愿在作品中说话?大概是要寻找答案,我读了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邢小群的《我们曾历经沧桑》。其中还夹杂着阅读江飞的散文集《纸上还乡》、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莫利斯的《裸猿三部曲》等,它们构成了我在2012年年底颇为凌乱的阅读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