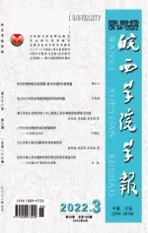从徽州民谣看明清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2013-08-15张浩
张 浩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231131)
一、民谣与徽州民谣
民谣,是民间歌谣的俗称,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歌﹑谣分称,最早见于《诗经·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1]歌与谣是不同的,“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古人对歌与谣常联用,统称为“歌谣”,简称为“民歌”或“民谣”。民谣是一种带有个体情感的创作,源于生活,来自底层、口耳相传于民间,最接近生活实态,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信息。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吟诵、口传心记的民间口头艺术,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珍宝,是写在徽州人心中、流传于民间的另类重要的“徽州文书”。徽州民谣在地域上包括歙县、绩溪、休宁、黟县和祁门等地的民谣;内容上有徽商民谣、生活民谣、劳动民谣、爱情民谣、时政民谣和游戏民谣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性、题材的多样性和艺术的独创性等特点[2]。徽州民谣是徽州社会民间生活的鲜活见证,从中可以真切地认识古徽州人所具有的人生、婚姻、生活、教育、是非和审美观念,是认识徽州民间社会和人生的一把钥匙。
徽州民谣尤其是徽商民谣历史上曾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是徽商历史的真实写照,具有特别的认识价值和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通过对徽州民谣的分析和解读,再现明清时期徽商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探究徽商产生、发展、壮大的文化根源。
二、徽州人从商的原因及生活观念的转变
(一)徽商——徽州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道路崎岖,交通闭塞,地理环境恶劣。“江西老表,挑粪刈稻。挑上石塔,一跤跌煞。来到徽州,算我眼瞎!”这首绩溪民谣《江西老表》写的是一个外乡人在徽州挑石头因为山路崎岖而摔倒后的抱怨,生动地反映了徽州山区恶劣的地理环境。
徽州山多地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这仅有的土地也“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明清时期,随着徽州人口的剧增,粮食常常难以自济。“水渣青,饿断肚肠筋。水渣红,饿煞人。水渣烂,白米饭。”《水渣红》反映的是旧时徽州人每年断粮的苦楚,水渣红时,正是存粮吃尽,在稻子没有成熟青黄不接之时,水渣野果的色彩成了可怕的断粮信号。生存的压力迫使大量的徽州人只有逃离故土,外出谋生。“一担挑三头,屁股在外头。做煞做死,做不出个鸡子。”《一担挑三头》讲的是一户被迫逃荒的徽州人家,担着儿女,流落四方的悲惨故事,“做煞做死,做不出个鸡子”,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即便再怎么勤劳,也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深深的叹息道出了古徽州人背井离乡的无奈。
徽商是徽州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正如清人许承尧所说:“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3]于是就出现了“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独特现象。
(二)从被迫“求生存”到主动“图发展”的转变
徽州人外出从商经历了由被迫走出大山到主动闯荡天下的转变。如果说外出“求生存”是徽商产生的客观原因,那么渴望自我实现“图发展”则是他们经营天下的内在动力。从少儿时代起,“中状元”、“造金屋”、“建祠堂”的思想就根深蒂固地烙印在徽州人的观念中,渴望功名富贵、发家致富和光宗耀祖的强烈意识,成为徽州人毅然从商的不竭动力。《牵三哥》、《摇篮谣》、《青竹叶青啾啾》这些民谣无不展现了徽州人的“富贵梦”。《牵三哥》:“牵三哥,卖三郎,打发仔,进学堂。读得三年书,中个状元郎;前门竖旗杆,后门做祠堂。金屋柱,银屋梁;珍珠壁,象牙床,绣花枕上一对好鸳鸯。”《摇篮谣》(节选):“宝宝宝宝,快快地长大,进学堂呀,考个状元郎。有朝一日做了官,衣锦还乡回家里。”《青竹叶青啾啾》:“青竹叶,青啾啾,写封信,上徽州。徽州路上一眼塘,两个姑娘洗衣裳。金檬槌,槌衣裳,银檬槌,槌草穰。金打屋柱银打梁,珍珠元宝砌明堂。阁上点灯阁下亮,阁上阁下亮厅堂”。
事实上,在文教发达的徽州,与从商相比,读书还是被人们视为出人头地的第一出路,他们认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4]若是不能学而优则仕,退而求其次那就只有选择经商了。
然而,从商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国策,商人作为“士农工商”这“四民”之末,在社会上饱受歧视,很多人更是羞于言商。可是为生存所迫的徽州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主动把商业作为求生存、图发展的出路,正是这种敢于冲破世俗的勇气和对旧观念的革新与转变,才成就了日后从商之风的兴盛。明清时期,徽州从商人口众多,达到成年男子70%左右,“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利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这首《丈夫志四方》反映的就是当时身怀理想的徽州人闯荡天下、经商成风的盛况。
(三)宁静淡泊、知足常乐——留守徽州人的人生观念
与外出求发展的徽州人略有不同,依然扎根于本土的徽州人在观念上则流露出另一种隐逸般的情怀:他们安土重迁,追求一种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流传于休宁和绩溪的《手捏苞芦馃》唱道:“手捧苞芦馃,脚踏硬炭火,除开皇帝就是我。”“手捏苞芦馃,脚踏树桩火;无忧又无虑,皇帝不抵我”。这种略显盲目和狭隘的满足无疑带着浓厚的山里人意识,虽然其中多少也包含了对富贵权势的淡薄,但主要还是体现了立足本土的徽州人宁静淡泊、知足常乐的人生哲理。
三、徽商初创业的生存状态
(一)艰辛与屈辱——少年徽商“伙头”的磨砺
徽州民谣中有大量反映徽商创业的内容,如流传于歙县的《前世不修》、祁门的《天光下饶州》和绩溪的《徽馆学生意》、《写封信啊上徽州》、《甜竹叶》、《火萤虫啊低低飞》等,反映了初出家门的少年徽商起步的艰辛和日后发展的必然性。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只要是对徽州历史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对这首《前世不修》都不陌生,这首民谣明显饱含了哀怨之情:一是徽州人对自身命运的感叹,充满了一种浓厚的宿命论的意识,正是因为“前世”的“不修”,所以“今生”注定要生在穷僻的徽州。二是徽州人对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早早“丢”出去讨生活的哀叹。当别的地方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在朗朗诵读或是在天真无忧的嬉戏时,徽州的孩子却被父母狠心地“往外一丢”了,小小年纪便踏上自立的征程。据明清笔记小说《豆棚闲话》载,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三四岁,就要跟随乡族长辈出外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也就是俗称的“做伙头”。下面两首歌谣反映的就是少年徽商的学徒生活:
《学徒苦》:“学徒苦,学徒愁;头上戴栗色,背脊驼拳头。三餐白米饭,两个咸鱼头。”《甜竹叶》:“甜竹叶,朵朵娇,写封信,上徽州。俺在杭州做伙头;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咸菜头。手磨铁火箝,嘴磨铁犁尖。手像乌鸡爪,脚如黑柴头。你要到杭州来看俺,拿个布袋背骨头。”
从上面两首歌谣可以管窥少年徽商“伙头”生活的艰辛和屈辱。这种生活对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可谓残酷,他们却毫无怨言,因为这正是一个担“大任”成“大业”的磨砺过程。
徽州儒教盛行,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创业精神因素大都源于“儒道”。儒道在创业上向来提倡“劳而不怨”。他们认为“发大财”就是自己将要承担的“大任”。要担“大任”、成“大业”就要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自身,承受一切苦难,就要吃苦耐劳,甘心做“徽骆驼”。
(二)徽商的精神重负——亲情的压抑与家庭经济的压力
少年徽商不仅在生活上饱尝艰辛,在情感上,还要长期承受着精神的重负——来自亲情的压抑和家庭经济的压力。亲情的压抑首先体现在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与牵挂。少小离家,艰辛备尝,山高路远,书信成了亲情维系的唯一纽带。徽州民谣有很多关于信的字样,信的内容多是对家乡的思念、对父母的宽慰、对苦难的倾诉和对自我的激励,其中包含的孝道、隐忍和励志读来尤为让人感动。如《火萤虫啊低低飞》:“火萤虫,低低飞,写封信,到徽州。一劝爷娘别牵挂,二劝哥嫂不要愁。一日三餐锅焦饭,一餐两个腌菜头。面孔烟抹黑,两手乌溜溜。日子过得好可怜!可怜!可怜!好儿不低头。今朝吃的苦中苦,好的日子在后头!出了头,当老板,赚大钱,回家做屋又买田。”
信,有时候不仅意味着亲人的讯息,还是全家希望的寄托。《信客到》:“烘炉笑,信客到,爹爹寄钞票;寄钞票,做么呢,买糖买饼给俺吃”。在山路遥遥的徽州,对信的期盼不仅代表了孩子们对远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还寄托了家人对外出的亲人赚钱养家的期望,所以说家庭经济压力是徽商背上的另一副重担。
歙县有另一版本的《前世不修》:“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三年吃苦,拼搏出头。发达是爷,落泊是狗。”祁门有一首《天光下饶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半夜收包袱,天光下饶州。赚得钱来心头肉,赚不钱来骂‘天收’”。这里的“赚得钱来心头肉,赚不钱来骂‘天收’”,与前面的“发达是爷,落泊歙狗”一样,都应了徽州西递古村落中“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的联语所指。“效好便好”,经商总是要讲效益的,“效”不好自然一切不会好。命系于商,“赚不钱来”真的连天理都不容!正如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说的:“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簿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里所说的恰与歌谣的内容相对应,令人想来唏嘘不已。
(三)不做“茴香萝卜干”——敬业精神的内在动力
正因为如此,背负着亲人的重托与压力的徽州游子,也只有义无反顾地走到底了。要么发达,要么落泊,别无选择。《写封信啊上徽州》(节选)就唱到:“叫爹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伙头。儿在外头学生意,心中记住爹娘话:“茴香萝卜干”,不能自己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好了生意,我再上徽州。天啊地啊老子娘啊,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徽州人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5]
长期的亲情压抑和家庭经济压力,锻造了徽州人倔强的性格。“天啊地啊老子娘啊,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这悲壮而震撼的呐喊,喊出了少年徽商伙计做人的骨气和尊严,这种不做“茴香萝卜干”的决心和勇气,这种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敬业精神,成为徽商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四、徽商的情感生活
(一)“乡思”与“相思”的双重煎熬
如果说少年学徒承受的情感压抑主要还是“乡思”的话,那么成年徽商的感情压抑更甚,因为除了乡思之外还要承受漫长的“相思”。徽州习俗,男子十三四岁外出当学徒,十七八岁遵父母之命回乡完婚,短暂的新婚欢聚之后,便要远走他乡。顾炎武《肇域志·徽州府》中说“(徽州人)取妇数月则外出。”[6]民国《歙县志》亦有“邑俗重商,商必外出……新婚之别,习为故常”的记载。燕尔新婚,欢聚短暂,更痛苦的是他们婚后相聚的时间也极少,有的夫妻一辈子团聚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几年时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俗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漫长的思念与等待无论是对徽商妇还是徽商来说,都是巨大的折磨和考验。
徽州民谣中直接反映徽商情感生活的不多,而反映徽商妇辛酸和哀怨的民谣却十分丰富,我们可以通过解读这类民谣间接地了解徽商的情感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徽商并不是徽州女人择偶的首选,因为谁都知道,嫁作徽商妇就意味着要面对长期别离的残酷现实,面对富贵和贫贱,她们有时宁可贫贱而长相厮守,也不要富贵而长别离。《高兴嫁个种田郎》把这部分徽州妇女的心态表露得淋漓尽致:“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在田里夜坐房,日陪公婆堂前坐,夜伴郎哥上花床”。徽商的爱情是甜美而苦涩的。甜美在于徽州女人的贤惠多情,爱情双方的情深意笃;苦涩在于聚少离多和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
“三送郎,送到槛闼(窗)边,开开槛闼看看天。有风有雨快点落,留我的郎哥歇夜添。四送郎,送到房门边,左手摸门闩,右手摸门闩,不晓得门闩往哪边。五送郎,送到阁桥(楼梯)头,左手搭栏杆,眼泪往那流;右手提起罗裙揩眼泪;放下罗裙透地拖……七送郎,送到后门头,望望后门一棵好石榴。心想摘个石榴给郎吃,吃着味道好回头。……九送郎,送到灯笼店。别做灯笼千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这首流传于歙县的《十送郎》(节选)表现的是徽商妇送别丈夫时的依依惜别的情怀,在这里既有对远行的丈夫的百般依恋,又有对早日返回团聚的美好期盼,更有对丈夫“要学蜡烛一条心”的反复劝诫。
再看这首《送郎远行》:“怨我哥哥要出门,一把扇,两面红,送给姐姐打蠓虫。姐姐摇扇心里疼,怨我哥哥要出门。叫声姐姐不要急,三月五月就回程。车打斗斗打碓,我和姐姐不离分!”这首歌中,青年徽商温言软语地安慰着自己的爱人,明知归期难定,却要哄意中人宽心,先含糊地说“三月五月即回程”,进而以“潦车打斗斗打碓”比喻,说他和她不会分离。歌中的“姐姐”担心的是“哥哥”出门后会变心,“哥哥”一句“不离分”的誓言,无疑是对“姐姐”最好的安慰。
(二)移情别恋的无奈
然而,长久的漂泊,有的徽商终于难耐寂寞与孤独,移情别恋,在外另立家室。“一纸书,到南京,丈夫出门没良心。家里娶个细细黄花女,外头娶个大大狐狸精。搽粉搽一斗,胭脂涂半斤;红头绳,扎四两,绿头绳扎一斤。”这首《一纸书,到南京》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矛盾。
现在来看,徽商在外另娶既有社会风气影响的原因,又有个人所处环境使然。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三妻四妾”的现象在明清时期属于常态,社会对多妻现象十分宽容。此外,徽商长年孤身在外,奔波于繁华市井、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场所,与外界接触广,再加上和家人长期音讯难通,有些徽商出于情感的慰藉,常常在外面另成家室,这或许是徽商继创业不成长期不归家的另外一个原因。
五、结语
徽州民谣是认识徽商的一面镜子,是徽商历史的真实写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徽商是徽州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外出从商是他们求生存、图发展的必然选择;徽商的起步和发展充满了艰辛和屈辱,这种苦难对他们来说正是成就辉煌的磨砺;徽商长期承受着来自亲情和家庭经济的压力,这种压力锻造了徽州人倔强的性格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以及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的敬业精神,这些品质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关键;在情感上,徽商充满了乡土和孝的理念,饱尝爱情的相思与孤独,挣扎于忠贞与背叛的矛盾之中。
[1]金开诚.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方 静.徽州民谣[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3]许承尧.歙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
[4]汪良发.徽州文化十二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5]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民国歙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5.
[6]顾炎武.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