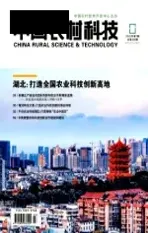松江模式的探索
2013-08-02李慎宁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李慎宁
对于农业,人们常关心两大难题,一是千家万户的“散户”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如何破解;二是农业后继乏人的难题如何破解。而上海家庭农场模式,正借助都市农业的优势尝试解答。
家庭农场作为上海松江区发展现代农业和粮食生产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改革探索,是继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后提升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又一积极尝试。
家庭农场试水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般一户农户拥有地少则两三亩,多则七八亩。当前,大多数农户耕种的面积规模偏小,虽然国家免征农业税,并给予种粮补贴,但随着农业成本上升,一旦除去自家的口粮,实际卖粮收入只能满足日常家用。加上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长此以往,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村土地被浪费了。为此,松江区曾经建立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种植收益,将农民种植的承包田以不同方式入了合作社,但由于其经营模式存在不确定性,经济收益并不高,直接导致了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
在奉贤、金山、浦东等多个郊区,70岁以上的老人竟成了主要劳动力。在金山的一家蔬菜生产合作社里,除了社长和部分管理人员在50岁上下,其他在蔬菜大棚里劳作的一线农民都已经年过70了。相关负责人表示,并非他们贪图人工费便宜而找老人,而是实在招不到青壮年。“只要不是在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呆在农村,下田劳作既辛苦收入又少,现在我们除了找老人做些采摘蔬菜、看守大棚的工作,还不得不从云南等地找农民过来,但终究还是劳动力缺乏。”
面对严峻的形势,甚至有业内人士担忧:“20年以后,上海还能有谁来种地?”
奉贤区农委主任吴四军认为:“从市场需求来看,农业可说是最稳定的产业。”只要承包土地政策不变、农地经营权能适度流动、经营者有体面的收入,再把农业生态循环起来,“农业就不会矮人一头”。
5年前沪郊的松江开始探索家庭农场,就是为了充分发挥都市型农业劳动力转移充分、城市“反哺”能力较大的优势,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将土地流转到专业农民手中,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吴四军所说的这几个“只要”,其实就是家庭农场模式的几个“主要素”。
5年来,作为上海农业现代化的创新探索,松江家庭农场模式备受各方关注。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介绍说,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家庭农场的优势已逐步显现。首先,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从原来的户均粮食产量1.8万公斤提高到现在的6.6万公斤,提高了2.5倍。其次,家庭农场农民收入大幅提升。农民粮食种植亩均净收入866元,增加了56.1%,家庭农场户均年收入达到近10万元;部分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甚至可以达到人均近8万元的年收入水平。同时,农业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收入的提高,种田成为一份比较体面的职业,农民从犹豫观望已发展为争相种田。
村民回流种田
36岁的沈万英在一家外资电子公司工作了13年,成为月收入五六千元的生产管理人员。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效益下降,村里承包家庭农场的人却纷纷致富,她毅然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钻进田头,安心种起了田。沈万英承包了115亩土地,进行家庭农场式经营。虽然只干了三个年头,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所种作物的亩产量年年超过全区平均水平。
“原本想自己创业,但看着父亲劳作了一辈子的田头,就想我的事业或许也能从这里开始。”沈万英说,和原本的办公室生活相比,如今的农场工作辛苦不少,只有1.58米、并不强壮的她,几乎一个人就要负担起115亩的农田,这在以男人为壮劳力的农村很少见。但她说:“现在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一个女人也能种好田。”
这位戴着眼镜、一脸书卷气的种田能手表示,还是要靠学习,多参加培训,“父辈种田靠经验,现在种田得靠科学技术。”她说,仅2011年一年,她就参加了好几次培训,每次学成归来,都觉得收获很大。

松江的家庭农场别出心裁,是高度“计划性”的“定人定产”农场,规模在100亩到200亩之间,农场主是本地职业化的家庭成员,基本不超过3人,只从事粮食生产和养猪。
在松江,像沈万英这样回流种田的人还有好多,顾良辉也是其中一位。他种过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镇上的工厂里上过班,也曾跑到市区当起泥水匠,还做过一阵子小生意,从事过的行当不少,但从2009年开始,他安安心心回归农田,和老伴一起办起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种田养猪一年能挣20万元,远超打工时的收入。
顾良辉承包的家庭农场还是区内37户种养结合的农场之一,包括146亩的农田和每批500头的生猪养殖,一年平均可以养上2.2批。2011年,松江区粮田每亩净收益866元,每头猪的代养费则为50元左右,一年下来,顾良辉和老伴的年收入可以达到近20万元,远远超过他当年打工的收入。
“过去打工做泥瓦匠,工资一年一结,收入不稳定,还要担心包工头不给工钱,家庭农场却能保证收入。”他掰着手指说着,“每年种植的大麦、小麦和水稻,都有政府免费提供的种子,使用的农药、化肥也是由政府先送来,年底结账。稻谷成熟后就有区里的粮食公司按照统一粮价收购,即使是风险较大的养猪也因为有龙头企业托底而不再危险。”既不用关心猪价波动,又不用担心疫病来袭,猪粪猪尿还能用作有机肥,省下了近一半的肥料开支,现在的顾良辉美美的在家做起了猪倌。
如今,在沪郊,粮田里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松江区农委主任封坚强手里有一份最新的调研报告:松江家庭农场经营者49岁及以下的达475户,占比达40%以上;50岁至60岁的达629户,占比为53%以上。60岁以上的仅为69户,占比不到6%。
据了解,松江的家庭农场目前正在试行一种“老年农民退休制度”,确立了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准入条件,其中主要一条是年龄限制,规定男性在25周岁至60周岁,女性在25周岁至55周岁。只有在务农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年龄才可以适当放宽。
制度背后的秘密
农业是永续型产业,有着“天然的生命力”。如何让这种生命力充满生机,需要体制机制的不断探索。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千亩大农场年产量惊人,粮食水果均大量出口。松江的家庭农场是否以此作为发展目标?是不是“越大越好”?封坚强等人十分肯定地回答:绝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中,比较适合的还是以家庭为单位,适度规模化,否则管理容易失控。
对此,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松江的家庭农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机械化程度,都能和日本媲美,但从国情出发,大型农场并非我们的目标,提高产值、增加收益才是关键。
上海市的家庭农场正是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探索实行农民土地委托村委会统一流转的方式,从而集中农民土地,将土地交给真正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经营。村民与村委会签订统一格式的土地流转授权委托书,再由村委会与家庭农场经营者签订统一格式的土地流转合同。如果老年农民自愿出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养老金将每月增加150元。同时禁止农民将土地私自转租,禁止家庭农场经营者将土地再转包。
在农用地流入环节,建立了准入考核机制,在农民自愿提出经营申请的基础上,由村委会严格按照家庭农场准入条件,采取村民议事、民主讨论、集体协商等方式选拔家庭农场经营者,选择的标准包括吃苦耐劳、钻研技术、善于经营等多方面内容。每年三次对家庭农场进行生产经营管理考核,实行淘汰退出机制,从而提高家庭农场的准入门槛。
与一般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相比,家庭农场制度有三个明显不同:一是“经营主体”不同。家庭农场落脚点是“当地专业农民和种田能手、镇村干部和技术人员等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业经营者”,以当地农户家庭为单位;二是因地制宜、适度规模,以农户家庭实际经营能力定规模;第三,也是相当要紧的一条,即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签订市统一流转合同文本,同时承包经营者除支付每亩500元(含政府补贴)的土地转让金给转让土地的农民外,还必须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承诺书,保证不抛荒、不转包。
家庭农场的运转,还有一个“内外循环”的基本平台,其内生动力与社会化服务、政府扶持等外部因素紧密结合。松江针对家庭农场加强了政策扶持,建立土地流转费补贴调节机制,实行生产考核性补贴,并出台家庭农场土地流转费的指导价格,以每亩250公斤稻谷实物折价,从而平衡流出土地农民和家庭农场之间的利益关系,调节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同时,还积极推广种养结合补贴,增加农机补助,给予家庭农场贴息贷款扶持,家庭农场的水稻保险费等也由区级财政给予扶持。这样,平均下来家庭农场的亩均净收入可达600~800元。
家庭农场制度让一家一户的小块农田向家庭农场集中,不但解决了土地分散经营效益低下、市场风险高的矛盾,还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和社会化组织程度。松江的家庭农场之所以受到农民欢迎,在于它符合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了农民的愿望。松江让种粮收入集中到那些“种田大户”身上,切切实实让他们感受到了种粮能赚钱。实践证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