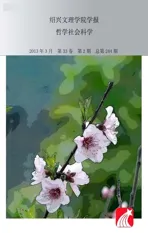永远的儿子和弱者
——论卡夫卡之“精神未成年”
2013-04-11王一然
王一然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美国诗人奥登这么评价:“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1]259
弗兰兹·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家中的长子。从小喜爱戏剧、文学,最初学习文学、化学,后转学法律,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保险公司工作。尽管一生中有多次订婚史,但却终生未娶。于41岁因肺痨过世。
孩童般的敏感,一贯的“弱者”姿态以及灵魂的最终无解——这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挣扎,形成了卡夫卡极具悖谬性的文学风格,他以此为我们提供一个“城堡”式的文学世界。卡夫卡精神上的“未成年”出神地诠释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精神生存困境,直至如今,他的小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表现出更为惊人的艺术魅力和价值长盛不衰。
父亲:“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我像一个孩子,在成年人中流浪。[2]242
——卡夫卡
马克斯·勃罗德这样说,卡夫卡“想把他所有的文学作品聚集在一起,作为他的一种‘从我的父亲身边逃脱出来的尝试’”[3]24。
“我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曾问我,为什么我声称在你的面前我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4]461-501这是1919年卡夫卡给他父亲写的那封著名的长信的开头,这封长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卡夫卡一直沉郁在自己心头的复杂的“父亲情节”。
国内专家叶廷芳先生说:“熟悉卡夫卡的人大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浓重的投影。”[5]87试图理解卡夫卡的世界也应该由他与父亲的关系谈起,或者更甚者,卡夫卡的生活、写作甚至于与女友的关系也同时溯源于他与父亲的关系,无论是书信,还是卡夫卡自身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卡夫卡的生命中父亲的作用有多么巨大——其实正如卡夫卡在信中想要传达给父亲的消息一样,“你远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对我影响深刻——我乐于夸大这种效果”[4]461-501。
《致父亲》倾诉了卡夫卡从童年以来对于父亲粗鲁无礼的教育方式的控诉和抗议。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赫尔曼·卡夫卡一直期望把儿子培养成坚强勇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定下了许多严格的规定去要求孩子,比如他要求孩子吃饭时不能说话,要吃得又快又干净,可是自己却在饭桌上毫无顾忌。在卡夫卡眼中,父亲就像是一位全能的独裁者,从小他就感受到了父亲精神上的强大、无可抗拒和绝对主宰,或者可以说,父亲本身就是法律。从幼年开始,卡夫卡从内心上对父亲就有难以消除的畏惧感,他甚至于无法顺利与父亲交谈。卡夫卡在信中清晰地回忆起童年时期父亲对他的巨大影响:“我那时已经有了一种自卑感,它不断地压抑着我”,“给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的勇气、决心、信心,以及各种乐趣……无影无踪了。”但就是这样,父亲“还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在父亲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我的负罪意识扩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更不可理解了……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4]461-501这几乎就是在小说《变形记》中所描绘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生存处境,由于他丧失了语言这一与人类沟通的最基本的工具,这意味着他就失去了被理解的最基本的条件。
卡夫卡对于母亲采取的怀柔政策也表示不认同。在卡夫卡看来,母亲的关爱无疑加重了自己内心的负担,使自己更加无法反抗父亲的权威。“母亲对我无限宠爱……母亲不自觉地扮演着围猎时驱赶鸟兽以供人射击的角色。如果说您用制造执拗、厌恶或者甚至憎恨的感情,在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来教育人——还有可能会将我培养成为一个能够独立的人的话,那么,母亲用宠爱、理智的谈话——说情把这又给抵消掉了。我也就被逐回到您的囚笼,我采取对您我都没有好处的行动,本来也许会冲破这个囚笼的。”[4]461-501
“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6]411卡夫卡不止一次地这样意味深长地抱怨:“不幸的童年几乎毁了我的一生”。[4]461-501
“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相当程度上来自他对他所在的家庭的看法,说得更确切些,个人的体验和人生经历,尤其是童年时代的生命感觉(印象),决定了他日后的世界观。一个人会最终脱离对母亲的依赖和父亲的权威,成为自己的父母,从而使人的灵魂成长,达到成熟。”[7]53费洛姆的观点在卡夫卡身上很说明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卡夫卡从未真正意义上地长大和成年,他绝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强者。他不自主地受到父亲的巨大影响,深陷其中;他终生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父亲巨大影响的无可逃匿。
莱恩在《分裂的自我》一书中写道:“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的回忆……否则他会感到没有生存的权利,他会感到自己从未降生……一旦有了这种爱,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受到什么伤害,人始终能够回顾过去……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可能被摧毁……”[8]32
罗杰斯曾经指出,“个体会随着成长产生另外两种需要,即得到别人积极评价的需要和自尊的需要,它们来自于人的自我实现倾向。在孩子寻求积极的经验时,有一种是受他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体验,还有一种是受到他人尊重而产生的体验……他人的关怀与尊重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体现着父母和社会的价值观”,罗杰斯称这种条件为“价值条件”,“儿童通过自己的行为不断体验到这些价值条件,不自觉地将这些本属于父母或他人的价值观内化,变成自我结构的一部分……被父母压制、与自我相疏离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价值条件化作用”。[9]159
荷妮的观点也是相通的:“从一开始儿童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儿童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对此,我称之为基本焦虑”。[10]2“他不再是一个‘追求者’,而是一个‘被迫者’。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使他感到软弱,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加强了他与自我的疏离。”“或者说,他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对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感到焦虑,并将这种焦虑带到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感到自己在别人眼中没有价值、很容易就会被抛弃……个人觉得世界无比强大,能压倒一切,而且危险重重,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10]3
费洛姆这样描述父亲的爱,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我爱你,因为你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爱你,因为你尽到了你的职责;我爱你,因为你像我。”[7]59-61可惜,天生羸弱且宣称自己是“最瘦的人”的卡夫卡与父亲心中的期望相差甚远。
如卡夫卡所说,父亲是卡夫卡“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一将自己体质与父亲对比,卡夫卡就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就像他信中“譬如,我们时常一起在更衣室脱衣服的情景……我瘦削、弱小、肩窄,您强壮、高大、肩宽。在更衣室里,我就觉得我是够可怜的了,而且不单单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4]461-501
这是卡夫卡父子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父亲的强大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卡夫卡,他甚至希望成为像父亲一样果断而强有力的人,父亲事实上已经成为卡夫卡人生的标尺,他一生都渴望得到父亲的重视,认可和理解,即使当发现自己无法成为父亲期许的人时,卡夫卡仍然走不出父亲的阴影。父亲赫尔曼出身贫寒,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历人事,闯荡生活。他的这种经历便造就了他果断自信,甚至可以说刚愎自用的性格。很自然,从小羸弱,似乎天生不是商人个性的卡夫卡在父亲看来注定是个失败者,卡夫卡自己也承认自己与父亲的期许,父亲爱他的条件和原则相背离。
在爱的作用上,弗洛姆认为“父亲不体现任何一种自然渊源,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7]59-61“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7]59-61
父亲对卡夫卡的影响使得他得不到正常的长大——卡夫卡在精神上是为父亲的强大所慑服的,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折磨,他清楚自己的弱点,他也恨自己无法满足父亲爱他的条件,不能成熟强大到被父亲重视和尊重。同时,他内心深处的挫败感和自卑感让他在父亲的世界里更加渺小和无助。
卡夫卡父子关系的痛苦之处在于:卡夫卡无法成为父亲,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更不可能用父亲的标准来衡量自己那个完全迥异的世界,而卡夫卡显然一生都受困于此;父亲的蛮横无理击溃了卡夫卡,以至于他认为一切困难都可以击倒他;而父亲粗暴的爱也并没有教会卡夫卡责任和承担,教会他勇敢地选择并为之付出代价。卡夫卡无法在内心树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强大形象,并达到最终真正的成长。
崩溃的世界:反抗,恐惧,逃避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11]550
——卡夫卡
卡夫卡在《致父亲》中谈到一件小事:“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要惹恼你,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一些强烈的威胁不生效后,您把我从床上拽出来,抱到阳台上去,关紧了门,让我独自一人穿着衬衣在那儿站了一阵子……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的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4]461-501赫尔曼在卡夫卡心中几乎是专制和暴君的象征,卡夫卡对于世界的看法与父亲对他的影响有着很深的联系——这是卡夫卡父子关系的另一重要部分。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不可阻挡地影响了卡夫卡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充斥了被动、无助、和“弱”。
卡夫卡与父亲关系的奇特之处在于,“A给B一个坦率的、与他的人生观相符的、不太美的、但却是今天在城市里很有普遍意义的、也许能防止健康受损的建议。这个建议对B在道德上没有多大鼓舞力量,但他难道就不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从这种损伤中摆脱出来吗?再说,他并不是非听从这个建议不可的,何况仅仅在这个建议中也看不出促使B的整个未来世界将崩溃的因素。但事情偏偏还是这样发生了,原因仅仅在于;你是这个A,我是这个B”[4]461-501。
在父亲的影响面前,卡夫卡的处境就像是这段话中所表达的那样——偏偏还是发生了。卡夫卡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很荒谬的态度,那就是,他“让”父亲击溃了他的世界。卡夫卡如同手足无措的孩子般无法主导自己的世界,直到生理上长大到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摆脱父亲的影响,他还是选择沉浸在父亲的“余毒”中。接下来的人生,卡夫卡唯一做的,就是持续地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抗父亲,来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不满。
“对抗父亲”——这是卡夫卡精神未成年的重要体现。
卡夫卡与父亲站在了对立的两方面,这种对立和反抗甚至于从未从卡夫卡的人生中消失。尽管卡夫卡本身很清楚这场抗战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却忍不住还是像孩子一般地把这种反抗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细读卡夫卡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比如《判决》、《变形记》中的父亲形象,《在流放地》中的司令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自己的父亲赫尔曼为原型的,他们都享有绝对的权威,儿子在他们面前都孱弱无力,所能做的只有放弃反抗,乖乖地去执行父亲下达的各种有理或者无理的命令。如果不了解卡夫卡的父子关系,就无法理解这些象征着“儿子”的人物形象上所表达出来的软弱和恐惧,还有对于父亲的宣泄。与彻头彻尾的反叛者所不同的是,卡夫卡没有办法恨透父亲而与之抗战。卡夫卡在这一点上完完全全是一个内心柔软,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仍然爱着父亲,无法割断对父亲的感情和希望;即使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父亲的示好也会让他既感动又痛苦,因为在卡夫卡看来,这种和蔼美好的印象会加重他的犯罪意识,让他觉得世界无法理解。比如《判决》中的儿子本德曼一直尽心竭力地为家庭奔波,却依旧得不到亲生父亲的理解,结尾时竟然莫名其妙地被判投河自杀。就像是卡夫卡对于父亲的感受:“即使这是最后一点力气,但对付你是绰绰有余的。”[12]100儿子由此获知自己的弱者身份——“一个被剥夺继承权的儿子”,儿子们唯一拥有的权力,就是爱和服从自己的父亲。
这种“弱者”身份不仅揭示出了作为“儿子”的困境,同时也道出了卡夫卡复杂的“父亲情节”。一方面他们始终在进行着逃离父亲的尝试,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无法离开代表权威的父亲,因为一旦脱离了父亲,他们也就不再是儿子了;一方面,儿子们希望离开父亲们的管制,因为这种管制使得他们难以长大,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总是渴望得到父亲对于自己的肯定和确认;一方面儿子们无法停止反抗父亲,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内心对父亲的依赖……
这就是卡夫卡的世界——那个在他看来“更加不能理解”的世界——他清楚地明白自己无法为之妥协,却同时无法果断地与这个世界决裂,甚至对抗中还交杂着爱和依赖,还有负罪意识。这种复杂的爱恨使得卡夫卡更加无法找到自己和属于自己的出路,决绝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
同时,随着卡夫卡思想上的成熟,他内心深处的犹太文化觉醒后,他内心中一直畏惧的父亲形象开始渗入上帝的影子,父亲的“惧怕”和作为犹太人对于上帝耶和华的“敬畏”是并生的,成为了卡夫卡精神上的绝对统治。卡夫卡甚至于这么说:“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4]461-501
卡夫卡对父亲对抗上了瘾,这种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卡夫卡的心理需要。“对抗”以一种证明存在的方式存在——无论是对抗父亲,还是对抗世界。当然与这种反抗共同存在的是恐惧、躲避和逃跑。
“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4]461-501然而逃跑尝试的失败,不仅让卡夫卡进一步丧失自信,同时也在他心中形成了夹杂着复杂社会文化内涵和私人情感因素,与人的原罪直接相联系的“恐惧”。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恐惧”中,卡夫卡不仅获得了存在感和安全感,而且由衷地生发出对于“父亲”的一种近似于“愤怒”的依恋,卡夫卡对于父亲的决不妥协中饱含着对于父亲的爱和惧,就像《致父亲》的结尾部分一样。
事实上,卡夫卡心中的父亲形象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伦理概念范畴而开始具有宗教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的含义,他把对父亲的感受和现实世界的运行机制关联起来,由此在他心中也形成了一种蕴含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个人情感的体验。卡夫卡的父亲形象与他所认知的世界有着深远的联系,对于父亲形象的描绘和建构,来自于卡夫卡作为一个敏感作家的亲身生存体验,也来自于他的文化记忆和积淀,成为了一个关于现实世界的绝妙比喻。这也是为什么在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中,世界就像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窥视到全貌,弄清楚结构的错综复杂的迷宫,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接近它,却又无时无处不感受到它的威严和压迫。
爱与惧并生,反抗夹杂依赖,而这种“恐惧”和“弱”成为了卡夫卡面对世界的直接感受,也成为了卡夫卡荒诞精神世界的组成。“父亲/上帝”这一意象就如同卡夫卡笔下神秘的难以接近的城堡,让他深感压迫,永远无法得到庇护,成为永远的失败者和囚犯。父亲的强大显然击败了卡夫卡,让卡夫卡永远以弱者自居,在精神上最终还是无法成长为一个成熟者和决定者。在他不长的人生旅途中,他不由自主地在许多问题上摇摆不定,恐惧逃避,自相矛盾。越是长大,对自己弱者的情状的认识越清楚,卡夫卡就越陷入这种矛盾和彻底的绝望中……而这种精神上未长成的痛苦不堪也贯穿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
写作:无望的救赎
首先,卡夫卡很快找到了一条灵魂拯救之路——写作。通过写作,卡夫卡发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天马行空的思想得以自由驰骋,压抑的自我得以充分释放,暂时远离了现实的各种压力,卡夫卡很快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个世界。写作成为了“一种祈祷的形式”[13]117-137和“砸碎我们心中冰海的斧子”[13]117-137“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推进”的手段[13]117-137。他感觉到唯有写作才是“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13]117-137,是“巨大的幸福”。[11]524
于是,卡夫卡这样决绝地在日记中表示:“要不顾一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来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11]536“我写作,所以我存在”。“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11]536
事实上,写作成了卡夫卡向父亲宣示反抗的方式,成了卡夫卡精神未长成的“奶嘴”,“奶嘴”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让卡夫卡不禁把它当成了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甚至超过婚姻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的处境:上帝不让我去写,但是我偏写,我必须写。如此而成为永久的拉锯战,而最终上帝毕竟更强大,其中的苦恼之多已超出你所能够想象的。”[11]536写作本身意味着对父亲的反叛和逃离,抒发了他渴望独立自由的愿望,同时又饱含着他对父亲无法割舍的依恋;写作是在卡夫卡看来获得灵魂拯救的唯一途径,也是使他陷入恐惧和孤独的根源。卡夫卡曾模仿父亲的口气哂笑自己:“写作的唯一目的,不过是拯救自己的灵魂或者罚入地狱。”[13]117-137他认为父亲非常“正确”地看到了这点。
写作,对于卡夫卡而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存在?拯救灵魂,或者是罚入地狱?
《饥饿艺术家》更像是关于拯救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喻体。饥饿艺术家把自己像一只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不吃不喝,以这种自虐展览作为自己的饥饿艺术。刚开始,好奇的人们还像举行盛大仪式那样围在他笼子前观看。很快,热情褪去的人们就开始对他熟视无睹,没有几个人愿意在他的笼子前停留;即使是专门为他饥饿艺术记数的工作人员都忘记了他的存在,直到他死去了才被人发现。
卡夫卡在这里展示了这样的一种生存悖论,饥饿艺术家的生存意义来自于他所谓的“饥饿艺术”,而一旦深深迷恋上这种“艺术”而“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最终结果无外乎就是死亡。《饥饿艺术家》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卡夫卡是在赞颂饥饿艺术家的执著呢,还是在讽刺饥饿艺术家的荒唐?卡夫卡的那句“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可以倒着来解析《饥饿艺术家》——“我存在着,却活不下去”。饥饿艺术家的困境也就是卡夫卡的困境,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生存的绝望感和对无意义的焦虑。
像微型小说《启程》中表达的那样,在卡夫卡的世界里,人的诞生就是一种“出发”[14]402,而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一次通向未知的旅行。在这条路上,人找不到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人生只能是不断重复的“出发”,为了努力奔向无可预知的远方,直到死亡将其终结。我们身外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甚至不能通过对外在的行动的选择来确定自我存在的意义。“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15]219,“向死而生”成了卡夫卡小说人物普遍选择的一种结局。和《等待戈多》式的“虚无”的等待中所隐含的希望不同的是,卡夫卡笔下的生存虚无是一种更加彻底的东西。
知道目标是虚无和不真实的,却无法说服自己停止追求;知道目标毫无价值可言,却无法停止达不到目标所带来的生存焦虑和痛苦——这是一种生存悖论。
拯救还是惩罚?在写作中,卡夫卡又一次不可自拔地陷入了困境。卡夫卡从来不曾想到自己的文学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他甚至无法承认自己的文学。卡夫卡看不清自己,看不清自己的世界,找不到真正可以寄托的东西。他在“弱者”和“儿子”的影响下不可自拔,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标准时间。而这种拯救耗尽卡夫卡一生,却无法给他指示明路。
写作凝结了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饱含着卡夫卡无望的拯救。卡夫卡曾经说过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这种孤独的创作,就像是饥饿艺术家的理想生活方式是表演饥饿艺术一样。卡夫卡因为写作拒绝了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执着于自己所惧怕的孤独。卡夫卡的创作不以发表和成名为目的,无关于时事,只是作为抒发思想情感的手段和灵魂的独白。他临死前希望所有的日记、手稿“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16]453,因为他对于创作追求完美近乎于绝望,无法容忍任何世俗观点对其创作的玷污。作为小说家的卡夫卡虽然表现出智者的成熟,但写作作为卡夫卡的理想生活形式,却是一种浸透着孤独和绝望的存在。卡夫卡本身就是一部绝望的作品,正如饥饿艺术家——笼子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性,而进入笼子却是饥饿艺术家自己的选择。这是一种如同火上花一样的绝望又炽热的艺术人生。
结婚:放弃的尝试
卡夫卡做了另一种逃离父亲的尝试——结婚。“事实上结婚的图谋变成了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自救尝试。尝试是惊心动魄的,其失败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4]461-501
婚恋不像友谊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责任和义务,而这又是卡夫卡一直恐惧的东西,卡夫卡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境地。结婚意味着逃出父亲的阴影,组成自己的家庭,过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而且,在卡夫卡看来,有一个类似朋友的妻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从卡夫卡日记中所描述的来看,菲利斯不漂亮也不可爱,没有什么特别吸引卡夫卡的地方,但他还是决定凑合着与她交朋友,因为卡夫卡认为菲利斯是一个可靠又平静的人,和他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一样,自己可以对她畅所欲言,这点从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的信中可见一斑。
但是随着与菲莉斯恋爱关系的推进,卡夫卡对于婚姻带来的伦理关系和肉体关系的恐惧逐渐增加。在日记中他剖析自己“恐惧结合,恐惧失落于对方”[13]117-137,用他自己的说法,除写作之外,他几乎恐惧一切。
卡夫卡曾经给菲利斯的父亲写信求婚,但是不等回信就拟了第二封:“从我看到的来说,她跟我一起生活是不会幸福的。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不仅是因为有外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我内在的原因,我的性格内向、沉默,不善社交,而且,我并不把这看成是我的不幸,因为这些性格特点反映了我的生活目的……我对一切不是文学的东西都感到无聊、厌恶,因为它们打扰我,或者说耽误我,尽管我也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13]117-137
接着在与密伦娜的恋爱中,卡夫卡留下了《致密伦娜情书》,在这场特殊的恋爱中,婚姻伦理关系大大减弱,卡夫卡更像是在与一位知心朋友探讨和分享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卡夫卡在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恐惧,甚至不仅仅单单关于爱情和婚姻:“你应当明白,密伦娜,我的年龄、我的暮气、特别是我的恐惧……我的恐惧与日俱增……”“此外我的本质是:恐惧。”[17]268“……这种恐惧并不是我私人的恐惧,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信仰的恐惧。”[17]268
而倾诉恐惧的另一方面是孩子般的依恋:“……我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站在你的面前,这孩子干了很坏的事,现在站在母亲面前,哭着,哭着,我发誓再也不做坏事了”,“在这场谈话中,我像一个孩子那样诚实、严肃,你像一个母亲那样宽容、严肃(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孩子或者这么一位母亲)……”“……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17]268卡夫卡在《致密伦娜情书》中把后者称为“密伦娜妈妈”。
卡夫卡的婚恋显然并非一般意义的,他更像是在找寻一位依赖对象,找寻自己灵魂的出口。某种程度上,卡夫卡试图通过婚姻来缓和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以此来完成对自我的拯救。但很显然,在这几段婚恋关系中,无论是从过程还是结果上来说,卡夫卡“在精神上显然没有能力结婚”。[4]461-501
卡夫卡生前曾一再把自己称作“洞中鼠人”,1913年,他在给恋人菲利斯的信中就已经这样说了:“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写作用品和灯具,住进一个大大的、这个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14]383两年后,他再度与菲利斯相恋的时候还是这样说:“只有我从自己的洞里走出来……我才有爱你的权利。”[13]117-137
对于最终的毁婚,卡夫卡提出的重要借口仍然是写作。卡夫卡越来越多强调写作对他的重要性,他认为占据他内心世界的只有写作,即使是爱情,也要为他的写作让路。正如他对菲利斯的表白:“一旦我不写作,我就立刻被击倒在地,像一堆垃圾……如果没有这种力量,那么我就什么都不是,会突然间被扔在可怕的虚空之中……”[13]117-137可是他又渴望爱情,他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就像他生命中的许多时候,卡夫卡总是不能明确地做出决定。文学写作本来是卡夫卡用以反叛父亲的主要方式,因为“你一开始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却例外地受到我的欢迎……实际上我感到舒服。”[4]461-501可是现在他却用它作为理由来喝止自己逃离父亲的尝试——结婚。这个举动,也恰恰反映了卡夫卡内心深处悖谬性的精神结构,结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卡夫卡必须离开他与父亲之间的实实在在的紧张性关系,离开他时时刻刻都必须与之相伴的极为复杂的“恐惧”——长久以来,卡夫卡依赖这种让自己成为“儿子”和“弱者”的影响力,卡夫卡深知这种“恐惧”对自己的重要意义。
“其实,恐惧就是我的组成部分。或许还是我身上最好的那一部分。正因为它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所以它兴许也就是仅有的你最喜爱的东西。否则,在我身上找得到什么值得你爱的东西呢?不过它的确值得爱的。”[17]355卡夫卡已不再恐惧“恐惧”了,反而由衷地表示了对于“恐惧”的好感:“完全承认恐惧的合理存在,所承认的要比恐惧本身所要求的还要多,我如此做不是由于任何压力,而是欣喜若狂,我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向于他。”[17]355
实质上,卡夫卡从第一次毁约开始,就已经在内心深处放弃了这样的尝试。所以,1917年下半年,当卡夫卡得知自己患上了肺结核而随即与菲利斯解除婚约时,内心丝毫没有痛苦和内疚。他对马克斯暗示自己对这能够帮助解除婚约的疾病早有预知:“我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你还记得《乡村医生》中那开裂的伤口吗?”[16]43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遇到朵拉之后所发生的恋爱也许是最接近一般意义的婚恋关系。在遇到朵拉之后,卡夫卡完全变成了模范病人,他拼命想活下去,当得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高兴得哭了。马克斯也这样写道:“卡夫卡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他不再是某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家长了。……我发现,卡夫卡和女伴在一起,正过着真正愉快的生活……”[2]242确实,无力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做出承担、精神上不够强大也注定了他永远跨不出追求自己人生幸福的那一步,而朵拉发自内心的爱,或者是病情的加重……无论什么原因,这或许是卡夫卡一生中不多见的精神强大的时刻了。这一次他也许终于走出了洞穴,可是却已经失去了爱的权利。
结语
可以这么说,卡夫卡依赖父亲,依赖写作,也同样依赖爱情。而这种种“依赖”显然是孩子气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恪尽职守地做一个小职员,却终生人在曹营心在汉;业余写作占用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是他心灵的释放、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延伸,却在最后要求烧毁所有的作品;想要对抗父亲来宣告自己的独立和存在,却最终在“爱”和“惧”中痛苦不堪;想要得到爱情完成婚姻来做最后走出洞穴逃离父亲的尝试,却中途流产,如同弱者一般地放弃和退缩。卡夫卡在精神上显然是不够强大的,他从来都不曾有过强大果断的否定,割裂或弃绝。童年时代缺少的父爱也许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卡夫卡在人格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而卡夫卡后来对于父亲、写作、婚姻三者的关系都表现出了,他始终无法长大成为“家长”或者“成人”。
刘小枫认为:“卡夫卡的受苦是自己性情中的两个世界的紧张引起的,他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世界的紧张之间的绳索”。[18]184-229的确如此,卡夫卡像一个孩子,一个不愿意妥协的未成年,在这两个世界中辗转,无法像英雄一样面对其中任何一个,承担生命的责任。卡夫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卡夫卡一直在这种矛盾中痛苦着,在归宿中挣扎着,直到无家可归,无路可走。卡夫卡用敏锐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用柔软的内心感知到了这个世界,可是上下求索而不得的他最后却给不出答案——“这世界是我们的迷雾。”[19]132
但这就是我们的卡夫卡,他绝不是英雄和巨人,他是“弱者”和“儿子”;他绝不是像托尔斯泰、尼采那样说话明亮又干脆,掷地有声,一落千丈的救世者,他只是一个精神不够强大,敏感而忧郁的“未成年”——他的恐惧、懦弱和挣扎不会比我们少多少。在所有这些用尽毕生向我们展示世界是什么和如何面对世界的作家们中,卡夫卡所表达的世界最直接、最本真,事实上也最珍贵。卡夫卡是让我们感动的,他恐惧着我们的恐惧,矛盾着我们的矛盾,在这部分他是最接近我们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和卡夫卡一样,都是精神未成年的不强大的“儿子”和“弱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那个灵魂挣扎的脆弱的自己。
参考文献:
[1]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259.
[2][德]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M].周建明,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42.
[3][奥]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M].叶廷芳,黎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4.
[4][奥]弗兰兹·卡夫卡.致父亲[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461-501.
[5]黄卓越,叶廷芳.二十世纪艺术精神[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87.
[6][奥]弗兰兹·卡夫卡.致卡尔·鲍威尔[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411.
[7][美]E.弗洛姆.爱的艺术[M].萨茹菲,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53,59-61.
[8][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M].林和生,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32.
[9][美]卡尔·R·罗杰斯.个人形成论[M].杨广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9.
[10][美]卡尔·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M].陈收,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2-3.
[11][奥]弗兰兹·卡夫卡.日记[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550,524,536.
[12][奥]弗兰兹·卡夫卡.判决[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100.
[13][奥]弗兰兹·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黎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17-137.
[14][奥]弗兰兹·卡夫卡.致菲利斯·鲍威尔[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402,383.
[15][奥]弗兰兹·卡夫卡.箴言[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219.
[16][奥]弗兰兹·卡夫卡.致马克斯·勃罗德[M]//叶廷芳.卡夫卡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453,431.
[17][奥]弗兰兹·卡夫卡著,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第十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68,355.
[18]刘小枫.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M]//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84-229.
[19]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