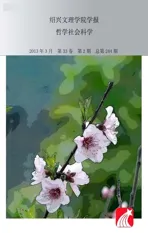就陆游“初仕瑞安”与邹志方先生商榷
2013-04-11谢公望
谢公望
( 瑞安市二轻工业局,浙江 瑞安325200)
近日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邹志方先生所著《陆游研究》一书,其中竟有陆游 “初仕瑞安” 一节。文章从生平考察,作品考察,相关材料考察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文章多处以推理、猜想的方式,草率地下结论。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则以 “应该承认是史实”“应作于”“肯定会”“似乎不大可能”来搪塞。例如 “曾幾的口许要两年半才实现,似乎不大可能”“二十六年冬出仕即官瑞安主簿的可能性,则相对大一些”①等等。拜读之余,惊诧不已。为此顺着邹先生的三方面,就陆游有否“初仕瑞安”与邹先生商榷。
一、关于陆游的生平
记载陆游生平的史料非常丰富,《宋史》有陆游传,清代钱竹汀(大昕)著有《陆放翁先生年谱》,赵瓯北(翼)著有《陆放翁年谱》,近代则有于北山先生著的《陆游年谱》,邱鸣皋先生著的《陆游评传》,还有陆游本人的著作《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以及陆氏宗谱族谱等,对陆游的“初仕”早有定论,而邹先生置历史公论于不顾,别出心裁地,以陆游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向其师曾幾,知台州召赴行在前,在《送曾学士赴行在》诗中提出“士生恨不用,得位忍辞责”,希望曾幾向朝廷推荐自己,并认为曾幾 “不但心许,而且已经口许了” 为依据,作出结论: “试想一下,要是陆游到绍兴二十八年冬季才出仕为福建宁德县主簿,曾幾的口许要两年半才实现,似乎不大可能。二十六年冬出仕即官瑞安主簿的可能性,则相对大一些”。②这里邹先生似乎认定曾幾有自主任命陆游为主簿的权力。其实陆游的出仕,不仅仅因曾幾极力推荐,更有某些王公大臣的协助才让陆游走上仕途的。
陆游的出仕,绝不是邹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陆游当时是没有“出身”的人,直到孝宗时才获得“赐进士出身”,虽世宦门第,其祖上的门生故吏,那时所剩无几。他父亲落职较早,后来仅得个“奉祠洞霄宫”的头衔。况且陆家都是主战派人物。秦桧两踞相位近二十年,一时忠臣良将诛锄殆尽。直至秦桧死后,忠良正直之臣才渐集于朝。因此,即使做一个县主簿的小官也是很难的。仅凭曾幾一个人的能力,还是不够的。陆游《贺礼部曾侍郎启》的结尾处,有几句很微妙的话:“某顷陶善诱,尝辱异知,虽借势于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唯侍坐先生长者,尚梦寐之不忘。”③从中已委婉透露出陆游这次出仕的蛛丝马迹。虽然没有明指哪几个王公大人,但陆游的《上辛给事书》就与陆游出仕宁德主簿有着因果关系。
总之,陆游的出仕,并不像邹先生所猜想的 “曾幾的口许要两年半才实现,似乎不大可能” 那样简单。
其实,佐证陆游生平的资料,只有下列最具代表性。
1. 《剑南诗稿》卷六十四《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而朱孝闻景参作尉,情好甚笃。后十余年景参下世,今又几四十年,忽梦见之若平生,觉而感叹不已》诗曰:“白鹤峰前试吏时,尉曹诗酒乐新知。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峬村折荔枝。”该诗开禧元年(1205)作于山阴,此时陆游已八十岁,但对四十多年前,初仕宁德主簿的情景却记忆犹新。这首诗,他直白地向读者表明,自己是从官宁德主簿开始进入仕途的。一是“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二是“白鹤峰前试吏时”, 白鹤峰为宁德境内的最高山峰。“试吏时”,试是尝试,说明此前从未有过。按宋制,主簿只是一个从九品的小吏。从诗题到诗的内容都相呼应地阐明自己是从宁德主簿任上开始踏上仕宦之途。
2. 《山阴陆氏族谱》:陆游“力学不仕,尝至临安,有诗云:‘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都人传入禁中,高宗称赏不止,由是名振京师。高宗虽慕公才,为桧所阻,不能用。及桧死,始除敕令所删定官,出赴福州宁德主簿……”④
3. 《陆游年谱》(于北山著),绍兴二十八年(1158):“七月,曾幾为礼部侍郎,有贺启。八月,王师心来为绍兴守,对务观颇加礼遇,陈棠由山阴应召赴临安,赋诗送之,……。冬季,始出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簿。”⑤
另外,绍兴二十七年(1157),二月,曾幾自台州内召,四月还任,务观有诗送行,曾幾有次韵。七月,曾幾为礼部侍郎,有贺启。八月王师心在绍兴对务观颇加礼遇,陈棠赴临安有诗送之。看来绍兴二十七年陆游官瑞安主簿是分身乏术的了。以上关键还是陆游的“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不知邹先生对此将作何解释?
二、关于陆游的作品
能够佐证陆游初仕的作品很多,诸如《云门寿圣院记》《老学庵笔记》等等,然而邹先生却选择《留题云门草堂》和《泛瑞安江风涛贴然》两首诗。
一是《留题云门草堂》:
小住初为旬月期,二年留滞未应非。
寻碑野寺云生屦,送客溪桥雪满衣。
亲涤砚池余墨渍,卧看炉面散烟霏。
他年游宦应无此,早买渔蓑未老归。
邹先生说,秦桧死后,陆游 “急于出仕的心迹,在这首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并将这首作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的诗, “不妨看作是陆游出仕前向云门的告别”。既然邹先生将这首诗看作是“告别”之作,那么绍兴二十七年(1157)春,陆游就应该出仕的了。因此,邹先生紧接着说“这里涉及《送陈德邵宫教赴行在二十韵》《朱子云园中观花》《酬妙湛闍梨见赠》《次韵鲁山新居绝句》《寄陈鲁山》等诗的编排问题,笔者(邹志方)以为,这些诗均作于出仕前,即绍兴二十六年冬日前。”⑥然而,查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诗均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作于山阴。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曾幾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二月,自台州内召,四月还任,陆游有诗送行,曾幾有次韵,即《还守台州次陆务观赠行韵》(详于北山《陆游年谱》第62页)。陆游送行诗《剑南诗稿》未收。但曾幾的这首《还守台州次陆务观赠行韵》末尾有:“新诗中律吕,虽美无人听。鸣声勿浪出,坐待轩皇伶。”大意是,陆游的诗里行间所表达的观点、建议都很适合时宜,但执政者一时还听不进去。并劝慰他不要轻易发牢骚,耐心等待朝廷的任命。《陆游评传》作者邱鸣皋分析“坐待轩皇伶”句:曾幾有可能向朝廷推荐过陆游,并已经获得朝廷将起用陆游的信息,因而予以透露。⑦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绍兴二十七年)陆游尚未得到朝廷的起用。
二是《戏题江心寺僧房壁》和《泛瑞安江风涛贴然》诗:
史君千骑驻霜天,主簿孤舟冷不眠。(《孤屿志》“冷”作吟)
也与史君同快意,卧听鼓角大江边。(《孤屿志》“快”作惬)
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
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
邹先生说: “此两诗应作于瑞安主簿任上”。并对前一首陆游的“是夕新永嘉守亦宿此寺”(陆游)自注的理解,全盘接受了瑞安革命老前辈高圻祥先生的观点,即: “永嘉新守是张九成 ”。⑧
邹先生只知其二,而不知其三。无论是温州本地的史料记载也好,或是《剑南诗稿校注》本也好,陆游在写《戏题江心寺僧房壁》诗之后,不仅仅写了《泛瑞安江风涛贴然》,紧接着还在平阳写了《平阳驿舍梅花》诗。《剑南诗稿校注》则明确注解,这三首诗都是陆游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冬奔赴宁德主簿任路上,经永嘉、瑞安、平阳时所作。《平阳驿舍梅花》诗为:
江路轻阴未成雨,梅花欲过半沾泥。
远来不负东皇意,一绝清诗手自题。
把三首诗连贯起来赏析,不难看出陆游当时内心无限兴奋,以及急于报效朝廷的心境。“蓬莱定不远”,表示诗人此番的目的地不会很远的了,不日就会到达。而“远来不负东皇意”,既说明诗人不是从瑞安的任上来,而是从山阴一路而来,并且从内心迸发出绝不辜负朝廷对他的期望的决心。
至于《戏题江心寺僧房壁》诗中的史君是谁,邹先生说: “高圻祥先生认为是张九成,是一个新发现,是正确的。” 这显然是错误的!张九成是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以左朝散郎复秘阁修撰知温州,同年十月,以表求去。⑨沈克成先生的《温州历史年表》则称:“是年(绍兴二十六年),张九成辑成《南雁荡山图志》,此为平阳第一部山志。”
试问邹志方先生,假设你的推理成立的话,即绍兴二十七年(1157),张九成还能称新守吗?
根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记载,张九成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去职后,同年十一月,王大宝(字元龟,湖州人)以直敷文阁知温州。至二十八年(1158)七月离任。同年七月底,黄仁荣(字释之,福建浦城人),以右朝请大夫知温州。假设陆游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初仕瑞安”,王大宝也已经算不上新守的了。只有二十八年(1158)冬,陆游初仕宁德主簿,路过永嘉遇到刚上任不久的黄仁荣,才能称黄为新守。
三、关于相关材料
在这一部分,邹先生举证了三个材料。一是陆游《云门寿圣院记》,二是明《弘治温州府志》,三是民国版《瑞安县志稿》。除了第二条外,一、三条资料都只能佐证陆游初仕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陆游并没有担任过瑞安主簿。
1.关于陆游《云门寿圣院记》。记中写到“今年,予来南,而四五人者相与送予至新溪,且曰:‘吾寺旧无记,愿得君之文,摩刻崖石’。予异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与为记。……绍兴丁丑岁十一月十七日,吴郡陸某记。”⑩这不仅说明陆游在绍兴(丁丑)二十七年十一月止一直仍在故乡,而且文末尚无系衔,但书“吴郡陸某记”。这就不可辩驳地证明,那时的陆游还未进入仕途。云门寿圣院在云门山,坐落在绍兴南三十里,故云“吾来南”。而邹先生不仅将“吴郡陸某记”删掉,更可笑的是将“予来南”,理解为“予南来”。他说: “‘予来南’,即从南方回来。瑞安在绍兴之南,故此语不虚” 。“予来南”是北往南,即北面的绍兴到南面的云门寺。如果陆游称“予南来”,才是从南到北。这是常识,用不着多解释。陆游表达的是从绍兴到云门寺。
2.关于《弘治温州府志》。《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名宦”收黄度、王公济、陆游、汪季良、陈容、范寅孙、吴兴祖、仰仁谦和霍蠡九名宦,除陆游外,其余八人,均记有到任年份,并有宦迹事例。如“范寅孙,姑苏人,文正公之曾孙也。绍兴十七年(1147)为平阳县丞,治政勤能,急于民事,兴修水利,人多赖之”。再如“吴兴祖,绍定元年主平阳簿。肃恭明锐,留心政事,一邑藉之。修理学校,延诸生讲校经难,文义彬彬,士皆奋发”。范、吴两人均既有任职时间,又有业绩例子。范寅孙的“兴修水利”,吴兴祖的“修理学校,延诸生讲校经难”都是实有其事。这样的史料才是不容置疑的铁证。而陆游的这段记词,既无到任日期,又无褒扬依据,这种不实之词只能说是以讹传讹之流言。历来方家对这类不实之词都是遵循“宁信其无、不信其有”的准则的。
3.关于民国版《瑞安县志稿》。在《瑞安县志稿》中,像邹志方先生大作中 “故《民国瑞安县志稿》明确记载:“宋安固令张进之,……知县陈良翰,主簿陆游。”这样的句子是没有的,这是邹先生臆造出来的。而《瑞安县志稿》中关于陆游的记载并不是没有,但不是邹先生所引述的这样。在卷十八《政教篇·职宦门》中,“主簿”栏目有这样的记载:“陆游,案游未为瑞安簿,姑沿旧志。”在卷二十七《文献篇·古迹门》中“放翁亭”条最后一段称:“按陆游并未为瑞安主簿,集中有渡瑞安江一绝。盖为福建宁德主簿路经云江而作也,后人遂附会以主簿此邦,于主簿废署内建亭并祠祀之。民国二十一年,邑人将主簿署址改为公园,重修此亭。取瑞安江五绝中字,名桥曰仰青,池曰明镜,山曰蓬莱,厅曰一帆等,目不备录”。显然,民国版《瑞安县志稿》编纂期间,对陆游官瑞安主簿是已经下过结论的。陆游并没有在瑞安担任过主簿。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要再问:邹志方先生究竟有否查对过《瑞安县志稿》?
笔者认为,对历史悬案作出结论,特别是要推翻一个已经被公认了的史实,必须有足以令人信服和无可辩驳的佐证史料。既要还历史本来面目,更要对今人、后人负责。然而,邹志方先生这短短的 “初仕瑞安” 一节,使得早在清嘉庆版《瑞安县志》,民国版《瑞安县志稿》都已下了结论(未担任瑞安主簿)的话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制造了历史悬案。特此提供上述史实和本人的认识,与邹志方先生商榷,如有不当之处,祈望斧正。
注释:
③《渭南文集》第六卷,《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21页。
④《山阴陆氏族谱》,上海图书馆藏本。
⑤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⑦邹鸣皋《陆游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⑨李之亮《东西浙路郡守年表·温州·瑞安府》,巴蜀书社,2001年版。
⑩见《渭南文集》第十七卷,《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