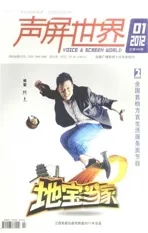以“信号”为逻辑起点的广播组织权内容研究
2012-11-22金雷宇
□金雷宇
邻接权与著作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保护客体的显著差异,后者保护的对象是作品,而前者保护的对象是对于作品的某种行为。无论是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还是广播组织,其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对于作品的传播。①
关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将其作为“节目”来对待,那是囿于其没有邻接权这一概念所致,因此笼统以作品版权的形式予以保护。我国许多学者也一度认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是节目。但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邻接权概念的认知,如果节目的内容本身已有著作权保护,那么广播组织的权利应仅限于其传播与组织行为的利益回报,因此将“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只有信号最能体现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经修订的基础提案草案》(以下简称“《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曾明确提出,该条约所保护的是“广播”(broadcasts),即承载节目的信号(program-carrying signals)。我国1990年的《著作权法》将客体定位为“节目”的误解,已经在 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得到了很好地纠正。因为所谓“广播、电视”,其实就是指节目与信号的结合,如果节目不经信号播放这一程序,那就不能称之为“广播、电视”了。据此,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的缺漏,《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规定的广播组织权内容,以及以信号为逻辑起点的权利内容,借以说明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背景下,广播组织权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广播组织权内容的缺漏
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有三项:转播权、录制权和复制权。这里面,最重要的当属转播权。之所以作此判断,是因为录制权和复制权的涵盖范围比较简明而少争议,而转播权却要复杂得多。
按照 《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规定,“广播”仅指无线方式,而在《著作权法》中,没有规定转播是通过无线还是有线。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目前有线电视发展很快,应增加规定有线方式的播放权。同时要求将“重播”改为“转播”。因此,修订后的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为“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根据这一表述,可以认为转播不仅指无线方式,也包括有线方式。
从上述表述看,我国《著作权法》的转播方式应该已经包括了无线、有线乃至卫星转播方式,但显然并未包括网播的方式。“网播”系指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通过计算机网络,使公众能基本同时得到所播送的声音,或图像,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此种播送如果加密,只要网播组织或经其同意向公众提供解密的手段,即应被视为“网播”。②2009年除夕夜,优搜网络公司通过技术手段,截取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信号,在其网站上同步直播。央视诉优搜网络公司侵犯其著作权并要求赔偿。此案中,央视诉称其著作权和网络传播权被侵犯,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③即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方式,而优搜网的网播行为是一种点对多的、同时异地获得信号的转播方式。由于我国的转播权并未包括这种网络转播,于是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虽然不能包含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下,但完全可以被“广播权”所覆盖。优搜网是通过有线电视线路截取了“春晚”节目信号,但提供该信号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无疑是从中央电视台接受的无线电波信号,故认定侵犯了其广播权是没有问题的。④该结论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无线电波信号”被以有线的方式播放,因此属于广播权规范的范围。笔者认为这个论断在逻辑上靠不住。第一,广播权针对的对象是“作品”,不是电波信号,而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是信号。春晚的节目作为邻接权来看,属于信号而非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罗马公约》所称的广播(broadcasting)是指无线电传播,因此要求各成员国保护的是一种无线电磁信号(包括激光、伽马射线等),而非信号所承载的内容;第二,就算广播的晚会是作品,那么非法以“有线方式”播放的组织也首先是有线电视运营商,而不是网播组织;第三,如果侵犯广播权的说法成立,那么春节晚会就变成了一个“现场表演”的“作品”,这既达不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因为晚会只是各种表演的简单集合),也会让邻接权变得很尴尬,因为事实上就不需要邻接权了。
此案的问题其实是 《著作权法》的问题,即上文所说的,超出了现行著作权法的范围。因此,本案最后以调解告终。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广播组织的某些基于节目“信号”的权利可能受到了损害,新《著作权法》应该考虑将其包括在内。
《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所规定的权利内容
由于世界范围内广播组织对于加强对其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经过多年讨论,于2006年出台了《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其中所涵盖的广播组织的权利内容远远超出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比《罗马公约》也要多出三项,总共达到了七项。
转播权。《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五条第(d)项解释了转播的概念,即有线或无线,其中包括有线与无线合并的方式,进行的一切形式的转播,包括转播、以无线或有线方式转播以及通过计算机网络转播。该条实际上沿用了《罗马公约》第三条第一款第(七)项,但是多了计算机网络转播这一点。尽管存在一定争议,但计算机网络对广播信号的转播被纳入转播权,符合大多数国家的预期。如果按照这一规定,前述央视诉优搜网的案子就非常简单了。
向公众传播权。根据草案第五条(e)项,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系指在公共场所使公众能听到,或看到,或能听到并看到本条(a)、(c)或(d)项规定中所述的播送内容。它参照了《罗马公约》第十三条“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的提法。⑤但是,其对象多了广播电台的节目信号。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权,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
录制权。草案第五条(f)项规定了“录制”的定义,“录制”系指对声音,或图像,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的体现,从而可通过某种装置使之被感觉、复制或传播。该定义参考了阿根廷、美国等国的提案,参照WPPT中的定义,但是增加了“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这一概念。该定义相较于《罗马公约》已经宽泛多了,《罗马公约》强调录制的载体能够长时间保存,但该定义却把使用任何手段或介质将信号录制下来都包括在内,比如网络环境下的广播节目暂时录制等。
复制权。《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十二条备选方案: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对其广播节目的录制品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复制的专有权。由于这一条款争议颇多,因此该草案允许缔约国自主选择复制权的保护方式。
发行权。发行权对于广播组织来说是全新的权利,显然针对“节目”而非“信号”。《罗马公约》和TRIPs协议都没有规定这一权利。《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十三条提供了发行权的三个备选方案,其核心内容为“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录制品的原件和复制品的专有权”。无论哪一个备选方案获得通过,都将大大增强广播组织的权利。
录制后播放权。录制后播放权其实也就是重播权。《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在其广播节目被录制后播送此种广播节目的专有权。由于录制后播放的前提是要先录制甚至复制才能实现,因此这一权利对于广播组织来说是很容易控制的。
已录制节目的提供权。用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来解释,已录制节目的提供权就等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也是一种针对节目的权利,是广播组织的信号所承载的节目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权利。
应该说,《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有关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非但保留并拓宽了《罗马公约》已有的四项权利,还增加了发行权、录制后播放权和向公众提供权,极大地提高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水平,同时对著作权的行使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出台困难重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下设的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从1998年至2011年6月连续召开了22届会议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从最近的情况看,各国达成一致的前景依然不明。
基于信号客体的广播组织权内容分析
由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是 “信号”这一结论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因此可以认为,广播组织的权利仅限于对于其组织并播放信号的经济性投入的回报,而决不能影响著作权人以及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对于《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所列的权利内容,如果从保护信号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可以分成三类:针对信号的权利、将信号固定的权利、固定后信号的使用权利。
针对信号的权利——转播权、向公众传播权。转播权的对象包括“广播信号”和“广播前信号”。因为如果广播的信号是广播组织的核心利益所在,那么在广播前为了广播而准备的传输行为就必须得到保护,否则当另外的广播组织截获这一信号而直接予以抢先播放的话,原广播组织的利益就会落空。转播权是广播组织权的核心,是基于保护客体是“载有节目的信号”这个逻辑起点,只有这样才能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和著作权的客体区分开来,⑥并明确广播组织的权利仅是对于组织广播信号的经济回报。对于我国著作权法而言,增加禁止网络转播的权利是有必要的,否则,正如上文央视春晚的案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广播组织的权利将难以保障。
我国著作权法中目前没有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权,这是基于尽可能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目的。但是著作权人和表演者有向公众传播的完整权利,因此,如果不给广播组织以向公众传播权,则应对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此种权利予以廓清。否则,广播组织可以利用合同授权,使前二者的权利自然让渡给自身,从而在实质上控制了节目的向公众传播权。
将信号固定的权利——录制权。录制是针对信号的录制,因此,从逻辑上讲,仍然应该是广播组织权的控制范围。同时,《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对此定义所作的拓展,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我国《著作权法》对于广播组织录制权的定义可以部分参考该草案。但是,由于录制行为本身更多时候是一种合理使用,因此对“录制”的准确定义并非当务之急。
固定后信号的权利——复制权,录制后播放权,发行权,向公众提供权。此四种权利中,复制权已经包括在我国著作权法之内。照此前基于信号的逻辑,复制已经不是针对信号的行为。但是根据《伯尔尼公约》,该“复制”与“录制”一样,是指广播机构使用自己的设备并为自己播送之用而进行临时录制或复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录制、复制权仅限于为播放而为之,不意味着可以不经著作权和其他相关权人的许可,将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发行。可见,这种复制权仍然与广播组织的广播行为本身息息相关,本质上仍然是针对信号使用的行为,应该得到保护。
邻接权意义上的 “转播”是指几乎同时播出广播信号的行为。而录制后的播放,其实相当于滞后一点的转播,也就是“重播”。如果不对重播行为予以保护,那么对于信号“首次播放后50年”的保护期看起来就会很莫名其妙。因为转播和录制后广播这两种行为之间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在发生时间上存有间隔。⑦对于广播组织来说,录制和复制如果不是用于播放,那么对其本身权利的损害并不大。因此,只要控制了录制后的播放权,很大程度上就保障了录制与复制的权利。
发行权及向公众提供权就其本质而言,所保护的已经不是节目信号,而是节目本身了。可以说,此权利在实践中很可能会对著作权的行使产生负面影响。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含有著作权保护内容的节目被非法发行或者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共提供,假使著作权人就是广播组织,广播组织会以著作权人的身份还是以邻接权人的身份,去寻求法律救济?答案很显然会是前者,因为法律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要比邻接权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随意增加邻接权的内容,可能会有“叠床架屋”的嫌疑。⑧只有信号本身才能受保护,这意味着广播组织既不可能授权对信号载有的内容进行使用,也不可能禁止对节目内容并非是传送信号的非法使用。⑨
结语
应当看到,在我国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真正超出现有立法范围的案例并不多见,本文提到的央视诉优搜网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除此之外,一般涉及广播组织的著作权及邻接权侵权事件,在我国法的现有框架内都能得以规范。因此,将广播组织的邻接权严格置于“广播信号”这一客体之上,是一种对著作权保护应有的审慎态度。广播组织的活动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活动一样,属于技术、组织性的活动,立法工作应该致力于保障广播组织在其经济投入方面的回报,弥补明显的缺漏。要从实际的国情出发,而不是“被外部因素牵着鼻子走”,对那些根据著作权法已然能得到保护的内容进行重复保护。这也符合《著作权法》修订工作所要求的“独立性原则”。⑩因此,就现阶段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修订而言,应该在目前内容的基础上,主要致力于完善转播权,同时增加录制后播放权。
注释:
①表演者权有多种理论,如认为表演是一种作品,或者表演是对作品的改编等等。但是均不妨碍把表演作为一种传播的职能来看待。
② W IPO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关于保护广播组织的条约合并案文》,SCCR/11/3,2004年2月29日。
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④ 刘春田,熊文聪:《著作权抑或邻接权——综艺晚会网络直播版权的法理探析》,《电视研究》,2010(4)。
⑤《罗马公约》第13条: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由被要求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⑥胡开忠等:《广播组织权保护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⑦孙 雷:《邻接权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⑧李明德:《邻接权研究》序言。
⑨韦尔纳·伦普霍斯特:《广播组织的邻接权竟然如此复杂》,《版权公报》,2006(3)。
⑩见《〈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启动》,http://www.ncac.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