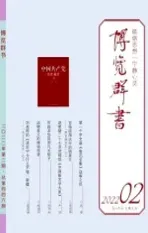梦里萦回伯克利
2012-08-04刘舒曼
○刘舒曼

主图书馆阅览室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 i fornia,Berkeley,常缩写为UC Berkeley或UCB)成立于1868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中最古老的一所,也是所有加州分校中唯一以California为校名的,简称Cal。每年的学校开放日,就能看见学生挥舞着蓝底金字的“Cal”大旗,在主图书馆(DOE)前的草坪上来回奔跑。伯克利的吉祥物是熊,学生也自称金熊(Golden Bear)。学校位置极佳,在旧金山东湾伯克利市的山丘上,距旧金山市区半小时车程。若登上山顶的劳伦斯实验室,可以俯瞰整个湾区的美景。
我来到伯克利的4月初,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雨季结束,校园里樱花盛开,映衬在加州的蓝天艳阳下,格外惹眼。在伯克利工作三个月,我几乎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至今,桉树林的香味,仍会在梦里时时萦回。伯克利如同一本精彩的大书,我所能解读的,只是寥寥数页。
号称最自由的大学
伯克利和旧金山这座城市一样,面向大洋,因多元而包容。在这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和放荡不羁的嬉皮士,获得诺贝尔奖的知识精英和背着睡袋的流浪汉,皆能和平共处。因为开放自由,所以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伯克利车位之紧张,人所共知,诺贝尔奖得主在校内享有的唯一特权,是标注 NL(Nobel Laureate,诺贝尔桂冠得主)的蓝色免费停车位,其他再无额外奖励。多一位获奖者,校长还要头疼又少了一个免费车位。除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另一种在校园有充足车位保证的是残障人士。
我所工作的东亚馆,隔三岔五便有携带全部家当的流浪汉光顾,在大厅里使用电脑,消磨一天半日,并无人管。除了借书需要证件,进出和阅览都是自由的。学校的档案馆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亦无需特别证件,人人皆可前往调阅,一视同仁。校园内的另一类“常住人口”是松鼠,数量众多,绝不怕人。我曾亲见一只小家伙抱着女生的脚趾猛啃,想是饿昏了。
学校的南门萨瑟门(Sather Gate),铜绿的门楣镌刻着拉丁文“要有光(Fiat Lux)”,指的是自由与智慧之光。我在这个校门听过两场很棒的无伴奏人声合唱。唱的人自由自在,无比欣悦;听的人席地而坐,满面笑容。从南门走出去,即进入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l Plaza)。去年年底,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被清场,伯克利学生以“占领伯克利”响应,在斯普劳尔广场搭建帐篷,抗议学校费用上涨和华尔街大公司的贪婪。
说起来,“占领”运动的鼻祖应该在伯克利。这里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70年代反战运动的策源地。1964年12月2日,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在斯普劳尔广场发表了著名的“直面齿轮机(Put Your Bodies Upon The Gears)”演讲,是以伯克利为开端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的高潮。学校的本科生图书馆(Undergraduate Library)内,有家咖啡馆专为纪念这一运动而命名为“言论自由运动咖啡馆”。咖啡馆外的报栏里有世界各地的报纸英文头版,每天更换,表明伯克利虽自由散漫,却绝非不问世事。店内有当年运动的照片和历史介绍,如无人提起,配着本科生图书馆灰扑扑、毫不起眼的外墙,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一家咖啡小店。这也是全校唯一需要出示ID卡才可入内的图书馆。

萨瑟塔
伯克利校园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小咖啡馆,装修风格各有特色,简单亲切为主。从车站走到学校,除了在美国星罗棋布的星巴克,就是些小咖啡店。我最喜欢的还是北门的那家咖啡馆,离东亚馆近,咖啡也香。老板是德国人,西班牙伙计非常热情,手脚极快。几乎你刚点完单,咖啡就送到手上。每次去这家咖啡馆,都是满满的人,看书、写东西、谈天。随时都有教授和学生在讨论问题,拼起两张桌子就是课堂,气氛松弛又热烈。其实我爱闻咖啡的香味更甚啜饮,经常在倦怠的午后,买一杯烫嘴的咖啡,沿着斜坡慢慢走到法学院的小庭院,在紫藤花架下静静喝完,再穿过草坪去档案馆查阅档案。很多学生的早餐就是一杯咖啡,吃什么似乎倒不重要了。咖啡馆在伯克利日常生活中,是香浓的滋养。
音乐陪伴心灵
初到旧金山,东亚馆的同事剑叶和丽敏到机场接我。过海湾大桥时,远远看见一座尖塔,剑叶说那就是伯克利标志性的钟楼。事实上,只要湾区没有雾气,方圆十数英里之内,总能看见这座高塔。此塔名为萨瑟塔(Sather Tower),因其建筑风格酷似威尼斯圣马可钟楼,更多被称为Campanile(意大利语,钟楼)。塔的设计者是环境设计学院创始人约翰·盖伦·霍华德。萨瑟塔建成于1914年,塔高307英尺(93.6米),为世界第三高报时钟楼。塔建成后,拉丁语系教授Leon J.R ichardson致信英国拉夫堡(Loughborough)的 John Taylor铸钟厂,订做12只铜钟。由于一战的缘故,1917年4月方才运抵旧金山。最大的一只重达4118磅,镌刻着当时伯克利希腊语教授Issac Flagg所作铭文——We ring,we chime,we toll,Lend ye the silent part,Some answer in the heart,Some echo in the soul。(试译如下:吾等欢唱/吾等谐响/吾等哀鸣/汝等侧耳静听兮/或心脉暗通/或灵魂激荡。)颇具禅意。
12口铜钟第一次奏响在1917年11月3日下午2点。钟声回荡在校园95年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演奏者当属Margaret Murdock女士,她从1923年一直弹到1982年,整整59年。12只钟对演奏来说是不够的,1976年,1928级学生集资15万美金,向母校捐赠36只铜钟,这批铜钟在法国铸钟厂完成。1983年,1928级的Jerry Chambers携夫人又捐赠了13只铜钟,钟琴数量遂增至现在的61只。这61只钟组成了完整的音乐会钟琴,音阶达到5个八度。伯克利的现任键盘手Jeff Davis,从2000年开始任职至今,他的办公室就在塔里。音乐系亦开设有专门课程,教授钟琴演奏。
演奏时间在春秋两季的学期内是固定的,周一至周五,每天三次,上午7点50分,正午12点,傍晚6点,每次持续10分钟。周六只有中午和晚上两次,周日则从下午两点开始,有长达45分钟的演奏。我听得最多的是正午这次,随着报时钟声结束,键盘手开始弹奏,众钟齐鸣,余音袅袅,响彻校园上空。在午后登上钟楼极目远眺,辽阔的蓝天下,旧金山状如棋盘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楼群,远处海湾里嬉戏的点点白帆,身姿奇美的金门大桥尽收眼底。长风吹来,令人宠辱皆忘。
伯克利的学生耳朵有福,除了朝夕可闻的钟乐,校园里的各类演出丰富多彩。价格十分可人(很多演出持学生证最低票价10美金),甚至免费,水平却是世界一流。那是一个6月的傍晚,原本打算去音乐系购买钢琴音乐会的门票,快走到教授俱乐部前的草坪时,忽听得鼓声温柔,自四面八方阵阵袭来,似不经意,却自有节奏。走近仔细一看,二十多位乐手散布在草坪的各个方向,除了鼓,还有钹、鸟笛、汽笛、砂纸、海螺壳等乐器。演奏者和观众都在随意走动,从没见过这样自由的音乐会。向工作人员索取了节目单,演奏的是John Luther Adams的室外音乐曲目Inuksuit。这位作曲家以打击乐著称,Inkusuit可以安置在不同的空间里演出,演奏者的数量可根据空间大小变更,非常灵活。
除了世界各地前来表演的艺术家,学校音乐系周三中午举办的免费音乐会,更是全校师生的福利。伯克利音乐系全美排名前三,人才济济。音乐会12点开始,匆匆吃点快餐填肚子,赶往Hertz Hall。印象中有一场是珀耳塞福涅(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界之后)之歌的表演,曲目皆为17世纪意大利和法国歌剧中的咏叹调或康塔塔(适合歌唱及演奏的短小音乐作品)。如卡契尼(Guil io Caccini)的《朝圣之女》(La Pel legrina),佩里(Jacopo Peri) 的 《 尤 丽 狄 茜 》(Euridice),蒙 特 威 尔 第(Claudio Monteverdi)的《奥菲欧》(Or feo),吕利(Jean-Baptiste Lul ly)的泊尔塞福涅(Proserpine)等。由于歌剧唱词都是古意大利语或法语,在每段演唱开始之前,由学生担任的主唱都要解释所唱内容,言语风趣,经常逗笑观众。在演唱的过程中,剧场内鸦雀无声。音乐在伯克利的日常生活中,是心灵的陪伴。
东亚馆深厚的历史积淀

钟琴
博尔赫斯在《天赋之诗》中写道:“在我的黑暗里/那 虚 浮的 冥 色/我用一把迟疑的手杖慢慢摸 索/我/总是在想象着天 堂/是 一座图书馆的模样。”最后两句,在人们说到图书馆的时候总是被提起。博尔赫斯从助理馆员做起,一直到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天堂是什么模样,无人知晓。地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图书馆。“拥书权拜小诸侯”,坐拥书城,随手抽取一册阅读的喜悦,想必每个读书人都曾有过。
此次赴美,是与伯克利东亚馆合作一个项目。在伯克利全校20余所的图书馆中,东亚馆是最年轻的,2007年才正式投入使用。设计兼具中国古典美和现代实用性,轩敞的阅览室,柚木色的地板,落地大窗可以远眺山景。各个研究小间里时常可以听见学生热烈的探讨。如有问题需要当面咨询馆员,可以提前预约。来自中、日、韩三国的馆员,提供不同语言的咨询服务。东亚馆的新馆建筑虽然年轻,历史却不短,与近代很多名人的渊源也颇为深厚。

东亚馆外观
它的第一批藏书来自伯克利东方语言学系教授傅兰雅的遗赠。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出生于肯特郡海斯镇的穷苦牧师家庭,从1868年到1896年的28年间,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管,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与工程学读本。在中国近代科学知识输入史上,他创造了多个第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学校格致书院,主编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清廷为表彰傅兰雅,特赐他三品头衔。1895年,傅兰雅举办时新小说竞赛,强调参赛小说要显示鸦片、时文和缠足的祸害,可见傅氏对中国现实的关切与痛心。傅兰雅自称:“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诚哉斯言。1896年,傅兰雅离开江南制造局,受聘于伯克利,成为东方语言系第一位系主任,直至1914年75岁退休。他和中国的缘分一直在继续。1912年,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盲童学校,开中国特殊教育之先河。1928年,傅兰雅病逝,遗嘱将2000册个人手稿和书籍捐赠给伯克利,其中包括时新小说比赛的原稿,现已由东亚馆整理出版。
1949年1月,张充和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丈夫傅汉思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远赴美国。1949年至1959年的十年间,傅汉思任教于伯克利,张充和则在东亚馆工作。在东亚馆的特藏室,鲁德修博士指着一排黄绫函套的佛经说,这些题签都是张充和写的,字迹十分娟秀。1956年秋,胡适到伯克利任客座教授一学期,期间经常到张家写字。据张充和回忆,图书馆的人并不知道胡适,让他填表。胡适填不好,张充和就帮忙给他拿书。别人请胡适写东西,胡也是到张家,磨墨写字,吃顿便饭。张充和《曲人鸿爪》册页里,有胡适在张家写下的元代曲家贯酸斋《清江引·惜别》一曲,上款是“写给充和汉思”。“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恬淡自如的人生态度,与图书馆的宁静气氛很是相得。
与东亚馆有关的名人还有很多,江亢虎、赵元任、张爱玲、宋楚瑜等。有一天我外出访友,回来剑叶告诉我,来过一位女士,说是台湾翻译《源氏物语》的第一人。那么,我错过了林文月。在伯克利期间,除了在东亚馆和档案馆工作,我几乎拜访了校园所有的分馆。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没有图书馆的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做升旗手,纪念品是两张明信片,夜色下的金门桥和蓝天里的悉尼歌剧院。澳洲至今尚无缘前往,伯克利之行则是意外之喜。那天晚上,朋友开车,载我和房东去南湾听音乐会。回程在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停车,欣赏旧金山夜景。那张明信片中的景色突然出现在眼前,人生的际遇,又岂能预料。“If you going to San Francisco,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in your hair.”(若你去旧金山,勿忘在发际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