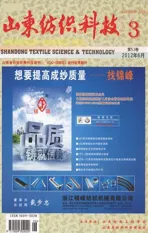论六朝的丝织技术与丝织物
2012-04-14徐晓慧
徐晓慧
(临沂大学,山东临沂 276000)
服装服饰
论六朝的丝织技术与丝织物
徐晓慧
(临沂大学,山东临沂 276000)
文章总结了六朝丝织技术的发展,介绍了六朝丝织物品种及艺术特色。
六朝;江南;丝织技术;丝织物
六朝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定都于建康的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南方王朝,处于汉唐之间的转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的过渡阶段。与南方传统纺织业麻葛纺织相比,六朝丝绸的发展成就虽然不是那么突出,但其意义重大。从产地来看,三国以来,南方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桑蚕丝织迅速发展,为唐中期以后江南丝绸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丝绸还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战略物资,如蜀锦生产就是蜀国军需的主要来源。
1 六朝丝织技术的发展
1.1 织机的改革
六朝丝织业的发展与丝织技术的革新密切相关,三国时,魏国马钧就对多综多蹑机进行了改革。马钧对绫机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了蹑的根数,将脚踏杆从五十、六十根减少到十二根,综多蹑少,也就是用一个蹑来控制多片综,既达到了多蹑的效果又使得操作简化。东晋时还发明了脚踏纺车,成为此后纺织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工具。至陈朝,徐陵的《咏织妇》诗说:“振镊开交缕,停梭续断丝”,观其诗意,当为以一镊牵动数综的织法,比之前代,又有了很大改进。《隋书·地理志》载:江州的豫章郡,“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1]可见当时妇女的丝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
1.2 养蚕技术的进步
史料表明,孙吴政权中曾设立丝织业的专业管理机构,丝织业除分散在农村以外,政府有自己的“织络”作坊,作坊内拥有大量的奴隶,专为统治者们织造奢侈的丝织品。会稽人杨泉依据农家养蚕缫织的经验,著有《蚕赋》和《织机赋》,反映了当时丝织业的兴起。干宝《搜神记》也载:吴时,“见一女人,年可三十余,上著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绨丝履。”[2]其服饰所用丝织品至少已可染成青、紫白、丹(红)三种颜色,可见当时丝织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左思《吴都赋》云:“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又引《永嘉郡记》曰:永嘉(今温州)一带,“有八辈蚕”。《永嘉郡记》所载“八辈蚕”,是将蚕卵藏于瓮中,复盖器口,置冷水,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是以人工低温抑制蚕卵,使之延期孵化的方法,一期蚕种在一年里连续不断地孵化好几代,促使蚕茧产量提高。此外,南朝人已用盐渍之法贮藏蚕茧,《本草纲目》载陶弘景语:“东海盐官盐白草粒细……而藏茧必用盐官者。”[3]妇女从事的桑蚕事业,是六朝时期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因而受到执政者的特别重视。另外,两汉时期形成的亲蚕之礼也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于丝织业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桑蚕生产。
东晋南朝的桑蚕业虽逐渐兴起,但丝织品产量仍远落后于麻织物,尽管如此,南朝时,丝织品已经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中国丝绸除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东南亚,甚至远至西亚、罗马、北非等地,如南齐时,张景真“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
2 六朝丝织物品种及艺术特色
六朝丝织物的实物资料相当匮乏,文献资料的记载可见于正史及唐宋笔记。南方地区(主要为东晋时期的墓葬)的考古发现获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即随葬“衣物疏”,如湖南长沙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周氏夫妇墓所出“衣物券”,与丝织物有关的内容为:“故持绮方衣一要,故练梁衣一要,故绢梁衣一要,故练衫二领,故帛罗缩两当一领,古縠缩两当一领,……故紫纱夹裙一要……故黄縠襦一领故紫绫半裕一领,故紫纱縠罗一领……故练手巾四枚,故帛绢手巾二枚,故练袜一量……故五縠囊五枚,故黄绮枕一枚……。”[4]根据这些文字资料可知东晋丝织物的种类主要有绮、练、绢、罗、縠、纱、绫等。
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六朝时期丝织物的品种主要有纱、縠、罗、绫、绮、锦、织成、刺绣等,与同时期北方的各个朝代相比,六朝丝绸的文化背景相对单纯,丝绸艺术风格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2.1 纱縠罗
六朝时,普通的平纹绢类织物有练、纨、纱、縠、素、绡、缣等。纱、縠质地比较轻薄,在气候炎热的南方数量较多,织造水平也较高。常规的罗本不是轻薄型的织物,但一些高档的罗往往特别轻薄,在南方数量居多。三国时的纱、罗、縠已具备很高的织造水平,传说东吴孙权夫人赵氏曾织造一种轻薄纤细的罗縠,用它做帐幔,轻盈如烟气飘动,而其内凉气自生。东晋南朝人对这类轻薄织物甚为喜爱,用以制衫、裙、襦等衣物,如东晋谢尚有紫罗襦,谢玄好佩紫罗香囊,吐鲁番曾出土东晋的彩条纹罗等。南朝天子朝服有绛纱袍、绛纱裙,杂服有五色纱裙,朱纱袍还成为听政之服。刘宋时纱、罗、素、绡、縠同样是妇女服饰的主要面料,一般裁作襦、衫和裙。
2.2 绫绮
今人看来,绫、绮都是指本色提花(即暗花)织物。二者的区别在于,绫是在斜纹地(或变形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绮却是在平纹地上起斜纹花[5]。魏晋之际,在诗赋小说中尚能见到“绮”字,如《东宫旧事》中记载的绫、绮织物名目甚多,有绛碧结绫、七彩杯文绮、熟绛绫帐、长命绮、紫棋文绮、七彩文绮等。相反在正式记录里,绮已不多见。另一方面,南方地区还能较多地看到绮,但北方却极少。如升平五年湖南长沙周芳之妻潘氏墓随葬绫、绮织物较多,有“绮方衣、紫绫半裕、黄绮枕、绮飞衣”等织物[6],但吐鲁番文书中则基本只有绫,不见绮。对此,许新国、赵丰在《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指出,此时绮的概念范围已大大缩小,平纹地暗花织物也可归为绫类。至唐代,绮的地位更是远远落后于绫,绫至今还是丝绸大类中的一种,而绮织物已不复存在了。
在六朝丝织物中,绫的地位尤为重要。晋代,绫与锦一道被纳入禁令,不准私自织造,也不准六品以下官员服用。绫、绮是仅次于锦的高级织物,依据律令,其服用有所限制。刘宋时,朝廷曾下令第三品以下不得服“杂采衣、杯文绮、齐绣黼”,六品以下不得服“绫、锦、锦绣、七缘绮”,八品以下不得服“罗、纨、绮、縠”[7]。
2.3 锦
锦是“织彩为文”的彩色提花丝织物,在古代丝织物中有特殊的地位,它体现了丝绸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平。东晋刘裕设斗场锦署之后,江南织锦业兴起。南北朝时,江南广陵、四川成都与北方定州成为高级织物的三大中心。
六朝时期织锦图案题材,与同时代的北方各代不同,文献记载不多,出土织物更是罕见。但是从仅有的文献记载可知,汉代的丝绸图案题材在魏晋南北朝时仍然延续,吴主赵夫人所织的“云霞龙蛇锦”便是带有汉式云气动物纹锦风格的织锦。汉代流行的祥瑞题材织锦图案在六朝时也风行不衰。梁元帝诗中曾提到“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证明龙、凤纹仍是南朝的主要织锦图案题材。在汉代被认为是瑞兽的鹿纹在南朝的织锦图案中仍然存在,如南齐高帝时曾有“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柽柏床、牙箱笼杂物、彩帛作屏鄣、锦缘荐席”的规定,其中的“鹿行锦”可能就是织有鹿纹的锦[8]。汉代的棋纹、水波纹、杯纹等几何纹样也继续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文化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异域文明对古老的中国大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同时期的北方各国尤为明显。然而由于南北交流,南方六朝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新型织锦图案题材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南齐书》记载,南齐时,宫中流行“射猎锦文”,射猎题材的图案显然也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射猎题材是波斯常见的图案主题。南齐萧道度年幼时,其生母区贵人曾剪刻锦绣中倒炬、凤凰、莲芰、星月等图案给他玩耍,莲芰是南朝时新出现在丝绸上的植物纹样,即中国本土的莲花。
有学者考证,被称为中国织锦艺术“活化石”的南京云锦乃是发源于六朝时期,六朝时期的南京织锦乃是后来一直被选作皇家服饰专用品的南京云锦的滥觞,六朝时织锦业的发展为后来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的丝织业中心奠定了基础。
2.4 刺绣
孙吴时期,江南妇女的刺绣是十分传统的手工艺,刺绣在江南颇为流行,文献记载:“妇人为绮糜之饰,……并绣文黼黻,转相效仿”。《初学记·卷二十七·绣第七》引梁代张率《绣赋》对精美绣品的描述:“龟龙为文,神仙为像,……总五色而极思,藉罗纨而发想,具万物之有状,尽众化之为形……间绿竹与蘅牡,杂青松与芳树。”[9]《南部烟花记》中也提到,梁武帝造五色绣裙,并加朱绳珍珠为饰,甚为华美。经赵丰考证,此物其实即为后世之穿珠绣。另外,南北朝时佛教的盛行也拓宽了刺绣的题材,南齐陈夫人曾绣无量寿佛像。《吴越钱氏志》里还提到齐、梁时,在织物上镶嵌金箔,并织出各种精美的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极穷巧妙,不可言状。”这些都反映了六朝时期刺绣工艺的进步。
2.5 织成
六朝文献中不乏“织成”二字的出现,可见在六朝时织成还是比较盛行的,起码在统治阶级内部受到了广泛的追捧。由于织成劳工费时,属于奢侈品,六朝各代都曾颁布禁令,尽管如此,因其华贵,六朝帝王仍以织成为重,如《南齐书》卷十七《舆服志》载:“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为天衣。”[10]齐武帝辞世时特别嘱咐“应诸器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
3 结语
总之,中国南方丝织业在六朝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得长期以来江南在中国丝织业中默默无闻的局面开始改观。在中国丝织史上,南方后来超过北方,这一转折的起点,无疑应追溯到六朝时期。六朝丝织业的发展成就既是我国南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纺织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对中国封建经济中心南移这一历史性转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方高峰.“鸡鸣布”是绢布,不是麻布[J].益阳师专学报,1999,(2):61.
[2]干宝著,黄涤明注译.搜神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许 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4]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J].考古通讯,1956,(3):97—99.
[5]朱新予.中国丝绸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
[6]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J].考古通讯,1956,(3):97-99.
[7](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赵丰.中国丝绸通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9](唐)徐坚.初学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10](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Discussion on Silk Weaving Techniques and Silk Fabric in Six Dynasties
XuXiaohui
(Linyi University,Linyi 276000,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ilk weaving techniques in Six Dynasties was summarized.The types and art feature of silk fabrics in Six Dynasties were introduced.
Six Dynasties,Jiangnan,silk wearing technique,silk fabric
TS941-09
A
1009-3028(2012)03-0035-03
2012-04-06
徐晓慧(1983—),女,山东临沂人,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