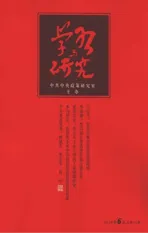论沈光文诗歌的乡愁书写
2012-01-27张如安
张如安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00)
在人类的情感域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情感莫过于亲情与乡情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但同时总有一部分文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故乡,地理上、身心上与故乡双重隔绝的生存状态,不断地煎熬着诗人的心灵,于是我国历代文坛的“乡愁”书写层出不穷,构成了历久弥新的普遍主题。明末清初的鄞籍诗人沈光文(1612~1688)一生遭遇坎坷,后半生流寓台湾,直到生命的尽头都在怀乡。沈光文居台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可惜后来沈光文诗文严重散佚,全祖望认为保存于《诸罗志》中的诗歌,“似非其至者”。①从现存的沈光文不多的诗作看,其最为人称道的,便是抒写乡愁的那一部分作品。
一、乡愁书写之丰富意蕴
乡愁是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也是漂泊他乡的诗人无法解开的情结。自1647年沈光文离开浙东辗转南下后,乡愁与日俱增,诗歌便成为其寄寓乡愁的有效工具。沈光文早在大陆坚持抗清斗争的岁月中,就已经开始抒发了怀乡之情。如《葛衣吟》云:“岁月复相从,中原起战烽。难违昔日志,未能一时踪。故国山河远,他乡幽恨重。葛衣宁敢弃,有逊鲁家佣。”此诗自序云:“余绍兴出奔,亦只衣葛,今已两载。”所谓“绍兴出奔”,是指丙戌(1647)年绍兴鲁王监国溃败,沈光文乘桴南来闽海,从“今已两载”推算,《葛衣吟》当作于1649年。据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二记载,明代建文帝逊国之时,有鲁家佣穿着葛衣乞食金城,北国的冬天非常寒冷,可他坚持“衣其故葛”熬过冬天。沈光文绍兴出奔的经历与建文帝逊国时的经历何其相似。毫无疑问,沈光文乡愁的产生,是与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清斗争紧密相联系的。是抗清斗争中的背井离乡,酿造了他最初的乡思乡愁。“衣其故葛”不仅仅是贫困之故,更是眷恋故国的忠贞意志的象征,这就是作者在诗中表达的“难违昔日志”。沈光文在寓居福建金、厦之时,创作的诗歌中亦时露乡愁之感。如《秋日和陈文生韵》云:“秋声方动处,怪是客偏闻。东国书难去,西山饿早分。知还同倦鸟,不碍等闲云。惭愧故人意,传言战血殷。”客游之地初闻秋声,自然令人惊心,诗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故乡。当秋声乍临之时,南明小朝廷的政治形势也越发危急了,不但寄书信给家乡已很困难,而且粮食吃紧,大家早就在忍饥挨饿了。战乱中的家书抵得上万金,可现在家书难寄,倦还无由,此刻诗人的乡愁亦如秋意般萧飒。戊戌(1654)仲冬,沈光文作《隩草》组诗,第一首即云:“宁不怀乡国,并州说暂居。无枝空绕树,弹铗又歌鱼。炼骨危疑集,盈头珍惜梳。感追无限际,悔绝昔年裾。”此组诗大约是作者流寓金、厦或南澳时所作,原本以为离开乡国是暂时的,没想到一别“故国十三春”,暂居遂成了久住,令他情何以堪!久驻异乡的经历,使他产生了绕枝三匝无所依的感觉,不知人生的旅程何处是归宿。此刻他的心漂泊无依,不禁后悔当年离开乡国太过坚决,这才有了“感追无限际,悔绝昔年裾”之句。久驻濒海尚且如此,那么永居海外,追怀乡国之情更是扰扰难宁了。沈光文漂寓台湾后,孤独感、无助感更加强烈,乡愁亦愈益深化。有学者指出:“乡愁人皆有之,但其浓烈,莫甚于漂泊海外的华人了。”②事实确实如此。沈光文的乡愁诗并非是单纯的抒发乡愁,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漂移海外的遗民志士的乡愁。天崩地解的时代变动,离家去国的心灵剧痛,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拉大了与故乡的地理距离,家山暌隔,归期茫茫,使沈光文的乡愁愈益浓烈,正如其《至湾匝月》诗所说:“闭门只是爱深山,梦里家乡夜夜还。”白日闭门外出,留连于深山之中,足可忘掉一切,但到晚上,却是归思难收,每夜做梦都要回到故乡,足见其备受乡愁的折磨了。
沈光文的乡愁书写还表现在对故乡事物的眷恋和追忆上。故乡的饮食,那是刻在他心里的永远记忆。身处物质极度贫乏的异乡,故乡美食的记忆所勾起的感觉通常是异常强烈的。沈光文也有这方面的体验,如《思归》之三云:“家乡昔日太平事,晚稻告我紫蟹肥。”紫蟹乃河蟹珍品,蟹黄饱满肥腴,味极鲜美,令人垂涎。唐代诗人唐彦谦有《蟹》诗云:“湖田十月清霜堕,晚稻初香蟹如虎。”可见晚稻初香正是蟹壮可啖的时节。沈光文的诗用一“告”字,将物拟人,仿佛亲见晚稻丰收在望,晚稻能作人语,较之唐彦谦“晚稻初香蟹如虎”的平述来更为生动形象。作者追忆的是甬上家园的丰收景象,用金灿灿的晚稻预告紫蟹之肥鲜,喜悦的心情伴随着舌尖上快感的幻觉,并将其放置在“太平”的时代环境下来呈现,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向往明代太平的家园生活的心态。“都说‘乡愁’美就美在‘愁’的思量,其实,真正的‘美’却在于时空滤过那‘乡’的重现。”③沈光文在心灵中清晰重现的是记忆中故乡原野的生态景观,那令人心醉的美,却无法在异乡得到真实的重现和复制,这正是他难以承受的痛楚。至于故乡的风俗,也是无法令游子忘怀的。沈光文《己亥除夕》云:“爆竹声喧似故乡,繁华满目总堪伤。起去看天天未晓,鸡声一唱残年了。”写异乡守岁的复杂心情。除夕之夜,声声爆竹,顿然唤起了诗人对故乡的记忆。一“似”字将台、甬两地连接起来,故乡曾历的喧闹和繁华,都已成为过去,异乡眼前的相似景象,只能带给诗人深切的忧伤。诗人正是在这种复杂心情的支配下,送走了残年。饮食也好,习俗也好,都是少小之时,身处故乡,原本司空见惯的东西,一旦漂泊蛮方异域,在境遇的强烈反差下,它对生命的意义即刻凸显出来了,这就难怪诗人将其视作“乡愁”的追忆性场域而歌之咏之了。
古人秉持家国一体的理念,故乡情结很容易延展为故国情结。沈光文的乡愁诗中,在“暂来”与“淹留”不断纠结的背后,寄寓着一颗复国无望的痛苦灵魂。如《归望》诗云:“归望频年阻,徒欢梦舞斑。在原嗟鸟散,杖策效鳞攀。”一二句说的是归家梦破,三四句说的是国破后追随鲁王,不断流亡。在家破和国亡的双重打击下,诗人不禁“镜里头多白,风前泪积殷”。他又有《思归》之六云:“暂言放浪樵渔共,久作栖迟贫病兼。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这里的“故国”兼有旧国和故乡的双重含义。他的乡愁总是与故国纠缠在一起,不时地透出报国无门的凄伤之情,从而赋予了其乡愁诗以更为广泛的政治含义。全祖望指出:“吾乡残明遗臣葬于闽中者三:钱忠介公在古田,尚称内地;陈光禄在鼓浪屿,则濒海矣;沈太仆在诸罗,则海外矣。……夫三公之勋业有大小,其名亦有显晦,然其依恋故国则一也。”④毫无疑问,沈光文对“故国”的怀念,是对民族之根的一种认同,同时也与其孤贞的品格联接在一起。其《山居》八首之三云:“念此朝宗义,孤衷每郁寥。未能支厦屋,只可托渔樵。冀作云中鹤,来听海上潮。长安难得去,不是为途遥。”首联是说想起国家残破,无法再现上朝觐见之礼,孤单的心里愈发感到郁闷寂寥。颔联谓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未能”两字表达了复明之努力付诸东流的深深遗憾。诗人不得已渔樵于江渚之上,但他多么希望能够化成云中之鹤,也时不时地来到海边听潮。无论是幻想的“冀作”,还是现实的“来听”,都暗含了思乡之情。化鹤不是为了超脱,而是寄希望于能像丁令威那样能化鹤飞归故乡;至于台湾的海潮更与浙江潮相通,所谓“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足见其听潮的用意了。这就逼出最后两句:“长安难得去,不是为途遥。”长安代指旧都。有家之所以不能归,“路遥”的地理原因固然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最根本的,其所隐含的自然是政治和文化的原因,那就是故土信美,却已经改朝换代了。全祖望记沈光文之叹云:“吾廿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⑤这确实表达出了沈光文漂泊他乡的遗民心迹。故乡既然已为异族所占领,归乡就等于臣服于异族,这自是海外遗民所不取的。不能归乡的游子,无时无刻都会涌起的乡愁,更加强化了异域羁旅的悲凉境遇。这使他的乡愁诗显得十分厚重,充满着浓浓的兴衰感和苍凉感。
沈光文的乡愁诗,不仅书写出了其个人的典型情绪,也透出了海外遗民集体性的情绪,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乡愁诗在特殊的时代和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的延续和变奏。历史上台湾岛上的汉族文人,身虽流寓,而心系故土,莫不皆有怀乡情结,这使得台湾文学的乡愁之音绵延不绝。沈光文的这类诗歌,确实可以看做是台湾源远流长的乡愁文学的先河。
沈光文并未一味沉溺于乡愁中不能自拔。为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求得“衣冠海外留”,他的乡愁转而化为对现实土地的认同,这正是他一方面抒发近乎绝望的乡愁,另一方面又在台湾登山问水的深层原因。但是即便是写台湾的物产,作者也不忘以中原的物产相陪衬。如《释迦果》云:“称名颇似足夸人,不是中原大谷珍。端为上林栽未得,只应海岛作安身。”台湾特产释迦果,由荷兰人自爪哇引进,最初种植于台南。范咸《台湾府志》卷十八记载云:“释迦果:树高出墙,实大如柿,碧色,纹绉如释迦头,味甘而腻,熟于夏秋之间。”释迦果一名番梨,因此诗人用中原夏梨作陪衬。诗中所说的“大谷”在洛阳东南万安山,其地以产梨著名。潘岳《闲居赋》云:“张公大谷之梨。”《文选》刘良注云:“洛阳有张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内唯此一树。”此诗的前两句是说释迦果并非中原培育出来的珍果,光是说出其奇特之名就足以向人夸耀一番了。诗人既赞美释迦果的无比珍异,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勾起了对中原物色的怀念之情。他之所以特别在意于中原之“珍”,实是基于其骨子里缠结着的“念兹在此”的故国之思。此诗又提到了汉代皇家园囿上林苑,意谓上林苑地理环境优越,虽然多植奇果异木,但却种不出释迦果,此果只能安身立命于海岛台湾。细加品味,诗人在释迦果中打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他以释迦果寄身海岛的命运,自喻其流寓台湾的遭遇,暗示其无法回到中原施展才华,报效故国。他又有《番橘》云:“种出蛮方味作酸,熟来包灿小金丸。假如移向中原去,雪压庭前亦可看。”台湾所产的番橘原种来自荷兰,肉酸皮苦,可作酸浆。诗人目睹这种蛮方物产,产生了“移向中原”的假想,并由此引发了“雪压庭前亦可看”的审美幻觉。从《释迦果》不能栖身中原,只能安身海岛,到《番橘》中忽发由海岛“移向中原”的奇想,小小果实的反向运思,隐含了诗人怀乡的焦虑。
二、乡愁书写之意象呈现
乡愁本是人们所普遍体验到的却难以捕捉的情绪,需要借助于典型的意象群来传递之,而梦、月、鹤、流水、时间等着情之物,正是中国文学中传递乡愁的传统意象。沈光文的乡愁诗,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这一意象传统,总是借助于梦、水、月等典型而传统的意象群来表现,其乡愁的煎熬,无论梦中梦醒,无论耳闻目见,都无往而不在,并随着时间的推进积聚起强度和浓度。
故乡总是让漂泊异域的游子梦魂牵萦,诗人尽管“岁岁思归思不穷”,但唯一的实现方式只能是“梦里家乡夜夜还”(《至湾匝月》)。他有《归望》诗云:“归望频年阻,徒欢梦舞斑。”这里,“梦舞斑”运用了老莱子七十岁穿五彩斑斓之衣娱亲的典故,归家孝亲的欢乐只有在梦境中出现,现实的处境却将娱亲之“欢”击得粉碎。《山居》之四云:“正作还乡梦,虚窗竹乱敲。”梦中回乡,正沉浸在与家人团聚的欢乐中,然而窗外的响声,无情地惊破了好梦。梦醒后,诗人听着窗外,秋风无情地乱敲着竹子,亦如无情地乱敲在他的心头。《思归》之六云:“山空客睡欲厌厌,可奈愁思梦里添。”客居空旷的山中,做还乡之梦反而平添无穷的愁思。《感怀》之七云:“隐心随倦羽,寒梦绕归槎。”这里,“隐心随倦羽”即“鸟倦飞而知还”之意,驶向家乡的归船,更让诗人梦魂牵绕。沈光文笔下,在梦境的不断闪回中,透出了诗人丰富细微的乡愁世界的窗口。
沈光文尤其惯于凭借水与月的意象来抒发乡愁。一湾海水无情相隔,诗人每每望洋兴叹,望月生哀。如《赠友人归武林》诗云:“却有机缘在,相逢意气同。来看云起处,共话月明中。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这首乡愁小诗,是以友人归浙为触点,在赠别的特定时刻乡愁顿然发酵。作者巧妙地将闽台海峡的海潮与浙江的钱塘潮联系起来,不但聊以慰藉万里的相思之苦,而且更有“天涯若比邻”的意味。沈光文在永历庚戌(1670)冬所作的《怀乡》诗云:“万里程何远,萦回思不穷。安平江上水,汹涌海潮通。”一方面,作者身处安平江畔,心却追逐汹涌的海潮,神驰于万里之外,此刻他的乡愁亦如那江水海潮那样绵绵不绝,汹涌起伏。另一方面,作者所处的安平外台江之水可以自由地接通连接故乡的海水,但故乡反倒成为人为隔绝的异域。作者又一次用江水与潮水的相通,抒发了萦回无穷的乡思。
至于月亮,自古就是寄托乡愁的媒介。对海外遗民来说,月亮不仅易于触发浓烈的乡愁,更会触发对大明帝国的怀念之情,因此一轮明月成了维系着海外遗民乡愁情感的最重要寄托物。沈光文的诗歌亦惯于运用“月”的意象来传递乡国之愁。《思归》六首是沈光文最重要的乡愁组诗,从“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看,此乃作者居台十年时所作,其中就有四首借月抒情。其第二首云:“霜飞北岸天分界,月照家园晚渡江。”这里的“北岸”,指的是台湾海峡,极目远眺,那里不仅是地理感觉上的天分界,同时也构成了人为形成的往来阻绝的界限。诗人只有仰望着一轮明月,看它冉冉渡江,照耀着家园,诗人的心恨不得随着月亮横渡台湾海峡。其第五首云:“絺绤自看还敝甚,无衣空捣月明砧。”每到秋天,家人总要为远方的游子或征人制作寒衣。在黯淡萧条的秋景和暮色中,听闻女子们此起彼落的捣衣声,交织成一片人为的秋声,无疑平添了客子的愁绪。而在沈光文的笔下,则是葛衣破烂,无衣可捣,但诗人却说虽然无衣,仍要“空捣月明砧”,在明月的夜晚,通过空自捣砧,人为地制造秋声,以引发浓浓的归思。第五首云:“民习耕渔因土瘠,天留风月纪尘侵。”身居异域,土地瘠薄,民风古朴,生活艰难,老天用风月记录了岁月流逝的刻痕,渐渐老去的诗人因此更加思归不已。第六首云:“竹和风声幽戛籁,桐筛月影静穿帘。”这是写梦醒后的景象:风声和着竹叶相击之声,其声幽幽;经稀疏的梧桐树叶筛下的月影,悄无声息地穿过窗帘。一个“筛”字,将月影细碎化。“竹和风声”的有声是恼人的,“桐筛月影”的无声同样是恼人的。此处借景烘托,梦醒之后,耳畔所闻、眼中所见,无一不是惹人愁思之物。他的《望月》诗,写出了他的无穷乡愁:“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湾。自当安蹇劣,常有好容颜。旅况不如意,衡门亦早关。每逢北来客,借问几时还?”遥望就是等待,与遥望相伴的是乡愁的侵袭。他的《中秋夜坐》云:“果然今夜月,不与别宵同。环岛风光净,随潮水气通。欢凭人共赏,兴属我何穷。却笑清樽竭,年年沧海中。”对一个流寓异乡为异客的人来说,中秋赏月,只能徒增伤感之情。诗人仰望明月,不禁由衷赞叹:今夜之月,果然与往常不同!月光的清辉洒满整个宝岛,显得格外的清净。月光倒影在水中,随着潮水的高涨,漫上来的水气亦被月光穿透。这真是一个幽美恬静的美妙世界。这个晚上,有多少家庭享受团聚之乐,又有多少游子相望而不相闻,兴起不绝如缕的思念。诗人越是将宝岛的中秋月夜写得美妙无比,就越是会勾起思念家乡的情绪。颈联写出了一种月色,两样心情。任凭他人赏月欢乐无比,而自己所拥有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兴发感触。诗人以己之无趣观他人之欢赏,可谓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了。
沈光文的乡愁书写,水与月的意象是相互交织的,而在时间的作用、磨荡之下,乡愁总能不断地发酵,达致饱满的程度。从以上的论析看,沈光文对传统意象群的运用是非常纯熟的。
三、乡愁书写之“苦趣交集”
苦趣作为情趣的一种,乃是“苦”的人生境况与“趣”的美学意味的有机结合,“就是于诙谐、幽默、俏皮、欢愉之中,透露出哀感和苦情。”苦趣就是苦中有趣,趣中藏苦,“这苦情与别趣,似乎是相矛盾的,但唯其矛盾,才正好给‘苦’笼罩上一层喜剧气氛”,⑥于是这对矛盾的统一体就形成了苦趣美。明末清初的浙东诗人常常不约而同地追求“苦趣”,如黄宗羲自言《诗历》逼真地记录了自己生命的历程,“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谓不逼真耳”。⑦他的弟弟黄宗会更惯于表现“苦趣”,其《潭上苦旱》诗有“苦趣穷如剥笋根”之句。沈光文也是一位善于表现“苦趣”的浙东籍诗人,可惜这一点几乎被所有的研究者所忽略。
在明末清初浙东诗人的语境中,“苦趣”有时只指苦处,乃是一种使人感到痛苦、苦恼的意味。沈光文在入台之前借居金、厦时所作的《寄迹效人吟》中写道:“忆自丙戌乘桴,南来闽海,或经年泛宅,或偶寄枝栖,忧从中来,兴亦时有,每假题咏,聊混居诸。”这里的“兴”便是呈现的一种心态,属于生命的感发,也是一种审美兴趣,它与“忧”结合在一起,“忧”成为诗人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也唤起了他的审美兴趣。“忧”的缺失性体验,既是沈光文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激发了他的心灵,既是诗人独特的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也成为他走上审美之路的强大推手,使其内在生命的冲动获得最充分的满足,故能做到“登山问水,靡不有诗”。“忧从中来,兴亦时有”八字,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对“苦趣”内涵的诠释,也是对传统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文学思想的发展。沈光文在入台后所作《中秋夜坐》诗有句云:“欢凭人共赏,兴属我何穷。”这里的“兴属”,当亦寓有“忧从中来,兴亦时有”之意。他在《题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诗文序》中更是明确写道:“忆余飘泊台湾三十余载,苦趣交集,则托之于诗。”此处的“苦趣交集”,显然是指“苦”与“趣”两者的交集,其中“苦”是基调,“趣”是旁衬;“苦”是主料,“趣”是调料。“苦”与“趣”相反相成,存在于作者内在生命的精神结构中。沈光文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应与他秉持“热肠知未冷”(《隩草》)的人生趣尚有关。在人世“积忧忡”中尚存一副“未冷”的“热肠”,使他能即时地去寻找并进而确立自我的生命意义,采取“自适”的生存策略,从而使个体生命不至于走向枯寂的境地。同时他还需要有“放弃”的姿态,所谓“放弃成吾逸”(《感怀》),这里的“放弃”是对功名利欲的放弃,“逸”则是个体生命达致“自适”的具体形态。
“苦”与“趣”的交集一直伴随着沈光文入台后的生活,也渗入到其诗的各类题材中。如他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方面不断地痛陈断炊之虞,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精神会餐的方式,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一点与浙派诗人黄宗会的诗歌颇为相似。他有《发新港途中即事》诗云:“隐心甘作苦,逐逐却难禁。计拙忧成老,身闲喜独吟。尘嚣浑欲脱,山水试相寻。满路芙蓉发,秋光已觉深。”一面苦于路途的逐逐,一面又主动相寻山水;一面感叹“计拙忧成老”,一面又说老而身闲,良非得已,却反而因此赢得了独吟自娱的好时光,不禁自喜;一面欣赏着一路上相伴的芙蓉花,一面又从芙蓉花的旺发中感叹秋光已经很深。这首诗在结构安排上,几乎就是“苦”与“趣”的双重合奏,真可以说是“苦趣交集”了。他的《偶成》诗云:“客窗诗苦囊兼涩,旅梦春浓老不知。”因为囊中羞涩,故作诗也多苦语,而在旅梦中,诗人竟流连春色,不知身之已老,所谓“作梦偏多欣喜时”(《自疑》)是也。梦中越是醉心于浓浓春色,越能反衬出梦醒后的凄凉境况。“囊兼涩”是“苦”,“旅梦春浓”是“趣”,苦中作趣,趣中见苦,颇堪玩味。
“苦趣交集”几乎构成了沈光文诗歌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当然也表现在其创作的乡愁题材上。他居于金、厦时创作的《寄迹效人吟》云:“共说暂来耳,淹留可奈何?驱羊防叱石,反舍拟挥戈。我耻先施倦,人间遍谪多。旅途宜自适,慨当以长歌。”(此诗与《山间》八首之五大同小异)此诗透出了淹留难回的内心焦虑,“遍谪”一词更有被迫放逐的意味,故人在旅途,不能不苦,但诗人却偏求旅途的“自适”,以此来平衡内心的痛苦。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文修养中,向有“自适”的精神,身居海外的沈光文很好地予以了发挥。“旅途宜自适”的夫子自道,正好透露出沈光文诗歌在忧患中生发趣味的精神来源。沈光文乡愁诗中的“苦趣”,在结构上常表现为忧乐的同场共振。他有《感忆》诗云:“暂将一苇向南溟,来往随波总未宁。忽见游云归别坞,又看飞雁落前汀。梦中尚有娇儿女,灯下惟余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记忆,临晨独眺远山青。”此诗的颈联说,乖巧可爱的“娇儿女”只能在梦中一见,醒来后仍是孑然一身,唯有青灯伴我瘦削的形影。梦里梦外的强烈对比,更见现实人生之可悲。但诗人在述梦之时,却用了“尚有”一词,意谓儿女仅仅只是在距离上疏远了,梦中照样可以团聚,如此读来,不仅毫无悲凄之感,反倒充满了几多温馨之趣。这两句在构联上,一“趣”一“苦”,无疑是其“苦趣交集”的人生体验在诗歌中的生动呈现。这种记忆中的“苦趣”时时浮现,就会构成心理上的沉重负担,此即所谓“苦趣不堪重记忆”,他只有将审美注意力转移到青青的远山身上。然而,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远望可以当归”,如此则“临晨独眺远山青”又是别一种“苦趣”了。再如他的《思归》诗之三颈联云:“诗瘦自怜同骨瘦,身微却喜共名微。”这两句使用拈连的修辞手法,“诗瘦”指诗风的清癯孤寂,实与乡愁相关联,而“骨瘦”自然是由物质匮乏、营养高度不良引起;自己的身影是那么的微弱,好在名声亦如身子一般微不足道。此处由“自怜”转向“却喜”,是以苦中作趣的方式,诠释了“我贵何妨知我希”的品格。紧接着的尾联“家乡昔日太平事,晚稻香新紫蟹肥”,撷取记忆中的故乡秋景,更是趣味盎然,在痴想中为人生留住了青少年的快乐镜头。《思归》之五云:“山容渐老添诗料,海气凝寒动客心。”这里的“山容渐老”,意指渐入深秋。草木摇落而见衰,增添的本应该是愁料,但诗人偏说增添了“诗料”。其实“诗料”所呈现的无非是乡愁,从本质上说仍是“愁料”,但用“诗料”代替“愁料”,却呈现出“苦趣”的审美意味。《望月》:“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湾。自当安蹇劣,常有好容颜。”眼前的境况明明是“蹇劣”,又明明受到乡愁的折磨,但他偏说安于现状,反而能保持好的容颜,此亦即其《思归》诗所谓“久安寂寞道心开”了。沈光文对痛苦与无奈的超越,已经渐渐达致了融苦于趣的人生境界。
结语
综上所述,沈光文有着剪不断的乡思情结,他的乡愁书写内涵丰富,感情真挚,抛弃了任何伪饰面具。沈光文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延续了他在大陆抗清时的乡愁书写,最早运用传统而典型的意象群,鲜明地表达了乡愁情绪。他把乡愁诗从大陆拓展到了台湾的土地上,传递了开台汉族遗民的共同心声,深化了传统乡愁的意蕴。沈光文的乡愁书写“苦趣交集”,独具特色,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也为台湾乡愁诗开拓出艺术上的新天地。
[注释]
① [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15《沈太仆光文》,方祖猷、魏得良等点校本,第408页,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黄万华《乡愁是一种美学》,《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③ 陈瑞琳《他乡明月》,林非、李晓虹、王兆胜选编《百年经典散文·挚爱卷》,第318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清]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15《从亡诸公之二》,方祖猷、魏得良等点校本,第397页,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⑤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7《沈太仆传》。
⑥ 陈世明《诗美学论集·论诗的别趣美(二)》,第10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 [清]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2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