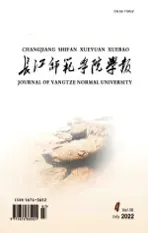羊城革命的史诗叙事
——《三家巷》的艺术传奇故事
2011-08-15黄贤君
黄贤君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红色经典辨伪
羊城革命的史诗叙事
——《三家巷》的艺术传奇故事
黄贤君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主持人语]在所有“红色经典”作品当中,小说《三家巷》题材是否独特。作者以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为历史背景,描写了三个家庭青年人的思想成长与阶级分化,作者欧阳山以其丰富的想象和巨大的热情,史诗般地再现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艰难历程。欧阳山本人并没有亲自参加过广州大革命,但他究竟是怎样写出这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文学作品呢?我想通过读一读黄贤君的这篇文章,人们一定会若有所思颇有收获,因为她不仅细致考证了《三家巷》的历史成因,而且更深刻地揭示了“红色经典”的传奇品性。年轻新锐们那种充满着批判理性的深邃眼光,使我们完全有信心去期待中国学术的美好未来。
小说《三家巷》不是红色经典中最富有影响力,但却是独具特色的。这是首部反映岭南革命历史的南方红色经典,因被认为真实地描绘了“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革命事件,塑造了周炳等动人工人形象而深入人心。事实上,诞生于“万里江山一片红”年代的《三家巷》在描写二十年代广州革命事件与塑造工人群体的时候,必定对“虽败犹荣”的历史进行一定的艺术改写,对当时尚且稚弱的党与工人给予美化夸饰,历史与真实相去甚远。这既是革命家欧阳山对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独特理解,也是其富有高度政治意识的重要体现,更是那个特殊年代所有红色经典作家都会普遍遵循的艺术法则。
《三家巷》;艺术改写;历史美化;真实性
1959年8 月3日,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开始在《羊城晚报》副刊上连载;而广州人争相去看《三家巷》,也几乎成为了一种社会时尚,欧阳山更是因此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不完全统计,《三家巷》已先后发行超过了100万册,虽说还不能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相媲美,但这对于偏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岭南而言,已经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了。后来,《三家巷》又被改编成连环画、话剧、粤剧和电影,从而使“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等革命历史事件,以及周炳与区桃等生动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流传久远并载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成为了一部具有南方特色的红色经典。《三家巷》凝聚着欧阳山对于广州这座古老城市的深刻理解,以及一个革命者对于羊城这座英雄城市的独特认识。欧阳山以他聪明过人的艺术才气,激情书写了岭南地区风卷红旗如画的历史场面;同时又以其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热情讴歌了工人阶级动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特殊的革命政治时代,是造就《三家巷》对于革命历史的艺术传奇化演绎的根本原因。
《三家巷》取名于广州一条普通的街头小巷,至于历史上究竟是否真正有过这条小巷,广州人曾为此去进行过毫无结果的考证与寻找,最终只能是按照小说再造了一个艺术想象的怀旧场景。小说里的《三家巷》,住着不同背景的三户人家,即:小手工业者的周家、买办资本家的陈家和官僚资本家的何家。作者着重去描写这三个家庭中的青年一代,他们在大革命时代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与政治信仰,并通过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三家后代中学毕业之后,他们都曾共同立志盟誓,要为强国富民而去奋斗;但当革命遭遇了严重挫折时,他们少年气盛的一时冲动,顷刻间便烟消云散土崩瓦解——“三家巷”里的三姓青年,其政治立场截然分化,人生追求也各有归宿,命中注定要子承父业:其中周家的后人周炳,加入了码头工人的行列;陈家的后人陈文雄,做起了兴昌洋行的经理;何家的后人何守仁,则当上了教育局的科长!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世俗逻辑,以“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宿命论思想,去合理张扬着出身决定一切的阶级论思想,进而使红色叙事被涂抹上了十分浓厚的封建色彩。
《三家巷》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革命小说,它以革命史诗般的宏大气魄,以主人公周炳参加革命的人生转变,“真实而生动的再现”了“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震惊世界的广州起义”[1]。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习惯于把《三家巷》看作是真实历史的艺术复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它们都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故很容易形成小说对历史的覆盖关系。但小说毕竟是艺术虚构,欧阳山自己也承认,《三家巷》只是艺术真实,而不可能是历史真实。“沙基惨案”发生的时候,欧阳山已北上求学不在广州,显而易见他不可能亲眼目睹过“沙基惨案”。欧阳山自己曾回忆说,《风暴》一章中那种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示威场面,是他对上海“五卅惨案”20余万工人大罢工的印象记忆,即便是到了晚年他仍旧是念念不忘感慨万千:“你们没有亲眼见到过那么壮观的游行示威场面,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民众力量之伟岸,就不懂得中国革命!”[2]“五卅惨案”与“沙基惨案”性质相同,都是当游行队伍到了公共租界时,外籍士兵公然开枪打死我游行人员。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推断,没有见过“沙基惨案”的欧阳山,除了凭借一些史料信息之外,完全是把“五卅惨案”的亲历体验,移植到当年广州革命的历史场景,并生动地塑造了周炳与区桃等一批工人的鲜活形象。欧阳山不仅没有亲自经历“沙基惨案”,就是“广州起义”时他也没有亲临斗争前线。1927年广州起义期间,欧阳山虽然身在广州,但我们翻遍所有欧阳山评传或回忆资料,都没有发现关于他亲自参加起义的任何记载。由此来推断,欧阳山对于“广州起义”的动人描述,也只能是“亲闻”而绝不是什么“亲历”。小说《三家巷》正是通过艺术传奇,想象性地刻画了“广州起义”中工人赤卫队的英雄壮举,并以主人公周炳“攻打公安局”、参加“广州苏维埃群众大会”以及“血战观音山”等重大历史事件,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工人阶级在战斗中成长的光辉业绩。这篇伟大的羊城史诗是那个特殊年代火红政治叙述的又一经典代表。
周炳无疑是《三家巷》里最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其中既寓意着作者对于政治英雄的无比崇拜,同时也寓意着作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深刻理解。曾经一度有人把欧阳山本人,认定为是主人公周炳的人物原型,但实事求是来讲,在周炳与欧阳山之间,却并无必然性的历史联系。欧阳山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就曾对周炳的生活原型问题,公开向公众做出过解答,他说:
他是很多人的概括……当时的一些手工业工人是很少有机会读书的,但是其中一部分人通过各种办法也能读到一些书。周炳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一方面有手工业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因为生活上和各行各业的工人接近;但是他又有知识分子的气味,例如要求个性解放,想通过读书向上爬等。周炳就是那样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着的人物。[3]
周炳在欧阳山的笔下,显然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出身工人家庭,又读过几年书,不仅貌似潘安颇有女人缘,并且向往革命立场坚定。这几重复杂身份的巧妙组合,无疑是象征着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化,它即体现着欧阳山对《讲话》精神的深刻感悟,又反映了《三家巷》世界观改造的政治主题。欧阳山也是工人家庭出身,他也念过中学并热心社会活动,欧阳山的女儿曾回忆说,1926年欧阳山在学校里,担任过“校学生会出版部的干事,负责全校学生的宣传工作”,同时还“帮助从香港回来的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们组织夜校,上政治课,兴办扫盲识字班普及文化教育,联络社会各界筹措文艺义演和爱国募捐活动”。最后,他被校方以“操行不良,难期造就”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学籍。[4]在《三家巷》的创作中,他把自己这些人生经历,都投射到了周炳身上,于是读者便看到了两者的相似性,就连周炳被学校开除之罪名,也是如出一辙:“操行不良,难期造就”。
欧阳山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他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讲话》精神,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敏感与透彻理解,这就使得主人公周炳的人物塑造更加具有深度。周炳既不同于《红岩》中许云峰与江姐的高大完美,也不同于《林海雪原》中杨子荣那般骁勇善战,作者让他以工人阶级的知识化身份,生活于社会底层成长于阶级斗争,这样不仅人为地消解了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同时更是展示了工农革命者的政治智慧!作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杰出代表,小人物周炳遵循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虚心学习认真改造不断进步终成正果,用欧阳山本人的话来说就是:
人民也有缺点。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5]
欧阳山对周炳形象的身份定位,“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这85章里面还不是党员,他参加革命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反抗,他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也做了一些错事,他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有些亲戚、邻居、同学的关系,但是他要继续革命”[6]。毫无疑问,工人阶级之身躯与知识分子之灵魂,主人公周炳在战斗中成长的人生历程,恰恰是作者有关世界观改造的主题设计——只不过这种世界观的彻底改造,更富有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罢了。
为了表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主题,《三家巷》对于主人公周炳的思想成长,应该说作者是做了煞费苦心的精心设计:他出生于一个铁匠世家,先天就具有泾渭分明的革命素质;他头圆眼大英俊漂亮,出场便带有一种虎虎生威的英雄气质;他情感丰富心地善良,为人处事总是一副侠肝义胆的豪放性格。欧阳山把他对工人阶级的全部理解,都倾注在了周炳这一人物形象的身上,让他敢爱敢恨救危扶困,让他率直刚烈激情四射,比如:为了抗议老师把穷人说成是“蠢如鹿”,他宁愿被人当作是“傻子”也不去听课;为了能和区桃演出一场“貂蝉拜月”,即使是被剪刀铺老板辞退也心甘情愿;为了同情一位使女的不幸遭遇,他得罪了干爹陈万利被撵了出来;为了能够保持尊严人格独立,他又因顶撞林开泰而被南关商会歇了工!周炳这种颇具传奇色彩的曲折经历,既被三家巷里的人看成是倒霉的“秃尾龙”,同时也使他同底层平民结下深厚情谊。由于还没有“党”的介入和引导,周炳此时更像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在三家巷的女儿堆里浪荡厮混,也像是《水浒传》里的武松或李逵,行走于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尽管作者试图去揭示他作为工人阶级的朴实品质,但令人看后总觉得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典型形象。直到“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周炳的人生才出现了转折。欧阳山让周炳在斗争中成长,其主观想法当然并没有错;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否都是从流氓无产者过渡而来的?如果回答“是”,那么又是谁在引导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这是一个目前仍未得到合理解释的哲学命题,故欧阳山笔下所描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就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
按照政治理想去重新改写历史,这是小说《三家巷》的创作立场。历史上的“沙基惨案”,原本是由国民党领导广州各界群众,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参与者主要是市民而非工人。但小说却将“沙基惨案”中的“国民革命”,改写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工运事件”,陡然改变了客观历史的原有性质,这几乎是所有“红色经典”都刻意遵守的重构原则。为了突出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欧阳山对游行队伍做了纯化处理——将商人和军人这两种敏感成分完全剔除出,只描写到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的爱国热情;甚至于为了突出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作者还将最先受到枪击的是学生和湘军的历史真相,改写为“受到损害的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广州工人队伍”!小说《三家巷》中的“沙基惨案”,作者让工人阶级尽显其英雄本色:
队伍乱了一下,有些人继续往前冲,有些人向两旁分散,有些人向后面倒退。整个十万人的队伍也就顿挫了一下。几秒钟之后,人们理解了这枪声的意义,就骚动起来,沸腾起来,狂怒起来,离开了队伍往前走,往前挤,往前窜。
有些人自动叫出了新的口号:“铲平沙面!”“把帝国主者消灭光!”“广州工人万岁!”(引自《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8页,下同)
小说中工人遇袭后,怒火燃烧愤怒反抗,场面热烈气势宏大,但却并非历史真实。据亲历者回忆说,当时敌人炮火猛烈,游行人员“秩序大乱,悲呼之声,惨不忍睹”,[7]根本就没有小说里那种情景发生。历史上国民党就曾借用“沙基惨案”,去对全民进行反帝革命的情感教育,[8]可《三家巷》中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党早已销声匿迹,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动员对象,也被巧妙地转化成以周炳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小说中“沙基惨案”的最大意义,就是用区桃的悲壮之死,促成了周炳人生的彻底转变。“沙基惨案”使周炳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而区桃之死则又激起了他坚决复仇的革命决心!原本就具有革命素质的工人知识分子周炳,在经历了“沙基惨案”的磨炼之后,其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仰,也已发展到了一种职业革命家的痴迷程度。
“广州起义”是工人革命家周炳的辉煌起点。在“攻打公安局”的战斗中他表现神奇作战英勇,他和赤卫队小分队队员们与反动军警浴血厮杀,高唱着《国际歌》冲锋在前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与历史真实截然相反,小说《三家巷》中“攻打公安局”的那场战斗,工人赤卫队被描写成是发动进攻的绝对主力,他们不仅武器精良而且训练有素。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才使广州暴动提前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工人赤卫队取代国民革命军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宰中国现代历史命运的真正主人,那么“成千上百”名工人赤卫队员的客观身份,就必须进行颠覆历史真相的全面改写:工人赤卫队员已不再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而是弹药充足后援不断意志顽强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虽然小北门手榴弹转运点被敌人破获,但中队长麦荣还是神奇地“抱了一大捧手榴弹过来,每个人发了五个”,再加上周炳原有的“一支驳壳枪和十几支步枪”,这足够令敌人闻风丧胆,怪不得他们会落荒而逃。但艺术虚构永远也成不了历史真实,广州起义的领导人黄平就曾回忆道:“在广州暴动前夕,工人赤卫队连一枝手枪都没有,步枪更不用说了。唯一的一所制造炸弹的场所因爆炸而被破获了”[9]。而在赤卫队第一联队担任军事参谋工作的刘楚杰也说:“十日晚,即将所有赤卫队在公安局附近集合,决定在十一日上午三点半钟动作。工友并无枪支,全有尖串,炸弹仅四枚。”[10]两人回忆数目虽稍有差异,但都讲出了当时武器匮乏的严峻现实。然而,小说《三家巷》中工人赤卫队传奇还并不仅于此,其骁勇之战斗力与严明之纪律性都被作者做了艺术强化:他们是一切听从党召唤,专捡重担挑在肩,而且身手了得,就连抛手榴弹都落点惊人,“有些没有爆炸的,就像石头一般砸在敌人脑袋上”,他们甚至还能潜行前进翻墙擒敌灭敌于悄无声息之中!工人阶级良好的组织纪律性,也被集中投射于赤卫队员身上,提前起义他们并无丝毫慌乱,“大家都严格遵守纪律,不笑,不闹,不说话”。当战斗任务完成以后,他们又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井条有序且又戒备森严,俨然一支正规军队。欧阳山写工人赤卫队是写得过瘾痛快,而徐向前元帅却在回忆中痛苦无比:
工人队伍和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军队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一说胜利就以为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各家吃饭去了。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我们这个联队总算是个战斗单位,还能把多数人拢在一起;有些地方连个战斗单位都形不成,工人们像“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起义很仓促,组织工作比较乱。[11]
作为广州起义的参加者,徐向前说出了一个历史实情:一支仓促编队没有武器的工人赤卫队,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同时又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如果单凭这种队伍想去获取革命胜利,那无疑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三家巷》中的“沙基惨案”,其重点不是刻意表现打仗,而是表现周炳的思想进步,进而使其完成人生道路的彻底转型。在初上战场之时,他对革命的全部理解,还只限于为区桃报仇,可随着“广州起义”的爆发,经过工人共产党员李恩的思想开导,他终于懂得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理想。从“个人复仇”到“阶级解放”的思想认识,使他瞬间便爆发出了十分惊人的神性力量:他高声吟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之曲,冲锋时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投手”。
他渴望消灭在门拱下面的,敌人的机关枪阵地,就是用全身的力量,投出了第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的落点很好,几乎在敌人的机关枪阵地的中心爆炸了。轰隆一声,火光一闪,有什么人尖叫了一声,机关枪不响了。(小说《三家巷》,第322页)
很难想象第一次参加战斗,周炳就臂力过人弹无虚发!这种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神奇想象,虽然能够增强读者阅读的审美快感,同时也能使主人公形象变得高大完美,但却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武侠小说的渗透影响。
“观音山防御战”是“广州起义”历史上,最为激烈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战斗。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在敌我力量悬殊、战斗技巧及水平差距甚大的情况之下,以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曲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悲壮赞歌。但在小说《三家巷》里,却变成了一场千余名工人赤卫队员,同敌人正规军八千之众的殊死对决,他们不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畏惧之色,相反能神奇地出现耍猴一般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情形:
敌人又展开了全面的进攻。这回敌人的打法很奇怪。这里打一阵机关枪,几十个人冲过来,可是没冲上,一下子就退了。那边又打一阵机关枪,又有几十个人冲过去,也没冲过去,又退了。一共有那么十几个地方,敌人都只是冲一冲,就退回去,好像小孩子玩耍一般。周炳心里觉着好笑。(小说《三家巷》,第371-372页)
欧阳山这种敌“弱”我“强”、敌“狠”我“勇”、敌“蠢”我“智”、敌“败”我“胜”的对比手法,显然就是要去充分论证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天才论断!此时此刻,周炳已经不再是为报一己私仇的伤感少年,而是一名解放全中国放眼全世界的革命战士;他也不再去思念那个令其魂牵梦绕的少女区桃,而是想起了张太雷、杨承辉、李恩等一系列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他感叹那些“可怜无父无母的红色孤儿”,忧虑那些“可怜无依无靠的老人家”,英雄济世弃之儿女情长代之以关爱苍生,这恰是导致主人公周炳骁勇善战的力量源泉。凭借着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突然获得的战时所思所想已经超越个人反抗而具有集体主义觉悟。从“没有这样接近过敌人”的勇士周炳,面对着三个敌人士兵手握武器的步步逼近,他居然“凭感觉就能准确地找到刺杀的对象”,自己毫发无损便轻松地消灭了那三个敌人,你尽可以瞠目结舌大跌眼镜,但信不信由你。与周炳一同并肩作战的工人赤卫队员,也都被描写成能够熟练地使用刺刀,把敌人杀得是鬼哭狼嚎的行家里手。然而,事实上那时“大家还不大会拼刺刀,就用枪托打,用石头砸……参加战斗的手车夫们,大都把鲜血洒在了观音山,最后没有几个活着冲出来。”[12]观音山肉搏之战的惨痛失败,被欧阳山书写成了一曲失败者的胜利颂歌,这既是政治理想主义的意志体现,也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这种现象在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中,几乎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作为“广州起义”的参加者之一,聂荣臻元帅曾痛心疾首地反省说,由于党组织的领导错误,为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十二日晚军事紧急的时候,几位同志开会决定退却,但并没有下退却命令而先去。各部分军事同志和赤卫队负责同志甚至红军总指挥也不知道。结果教导团方面大部分自己向北江退却了,但是赤卫队始终不知道退却,十三日敌人四面包围着,欲退已不能退了!工农群众死亡的数目竟逾数千,大部分原因在此。”[13]这本是个值得反思的历史问题,但欧阳山却为了消除对党不利的负面影响,突出党与工人阶级心心相印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人为地对这一事件做了违反历史的全面修改——《三家巷》中的工人赤卫队,不仅接到了党组织发来的撤退命令,而且更是按照党组织的计划安排顺利撤离:
代理中队长冼鉴到联队里开完会回来,用一种枯燥的调子对大家说:“老朋友,组织上已经决定,咱们要撤退了!”
对周炳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而且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不假思索地说:“不,相反!我们要进攻!咱们要出击!”……
“这就奇怪了!咱们并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也没有丢过一寸土地!”……
“就是饥饿和疲倦,也没有叫咱们失去勇气,咱们的战斗意志还十分旺盛!”
(小说《三家巷》,第374页)
看到同志们斗志这么旺盛,冼鉴只能耐心对大家解释道:
没有人敢怀疑咱们的勇敢和壮烈,没有人敢怀疑咱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没有人敢怀疑咱们对广大民众的关怀和热爱,但是咱们必须有更大的勇气来对付目前的局面,来组织一次有计划的退却。咱们占领了一个大城市,但是咱们守不住它……再守下去,牺牲会更大,也没有什么意义。总是,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小说《三家巷》第375页)
以上有关撤退场景的生动描写,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冼鉴不仅能够从容地突出敌人重围去市中心开会,而且还能够安全地回来组织工人赤卫队撤退;工人赤卫队员则更是士气正高欲与强敌决一雌雄,表现出了可歌可泣令人敬佩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主人公周炳与部分战友们的成功撤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所留下的深深遗憾,而冼鉴那一句“占领了一个大城市,但是咱们守不住它”的肺腑之言,显然又是作者在极力颂扬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为了突出党所建立的新生政权备受人民拥护,欧阳山夸张性地描写了广州苏维埃群众大会的空前盛况,将这场历史上只有“三四百人”[14]参加的冷清会议,渲染成是人头攒动万众欢腾一派喜庆气氛,不仅有来自前线的大部分战士,还有工人、农民、妇女、学生和市民等,场内“两套狮子鼓在广场缘上来回走着,他们的鼓声压倒了珠江上的炮声和近郊的枪声”!一派胜利庆贺的喜人之景。可聂荣臻似乎并不给欧阳山面子,他在追忆中说:“十二日上午,不顾枪声炮声到处在响,起义的领导机关就十分仓促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自然有顾虑,直到中午时分,到会人数仍不是很多”。[15]当然了,小说不是历史,虚构与夸张是允许的,欧阳山正是充分利用了小说艺术的这一特点,把他对革命历史的美好想象,做了他认为是合理的艺术加工。比如为了凸显党对“广州起义”的绝对领导,小说还在攻打公安局战斗取得胜利以后,不惜让党代表们纷纷以真姓名亮相,并以主人公周炳在一旁观察的主观视角,多次去呈现他们相聚一起的开会场景:
张太雷和一大群人从外面走进来。这些人里面,有教导团团长叶剑英,红军总司令叶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领导警卫团起义的蔡申熙和……,广州市的市委书记吴毅,还有苏维埃政府的肃反委员杨殷,司法委员陈郁,秘书长恽代英……
(小说《三家巷》,第329页)
张太雷、杨殷、周文雍、陈郁、恽代英这些人围着长桌,坐在圈手藤椅上;叶挺、叶剑英……这几个人站在地图旁边。
(小说《三家巷》,第331页)
在这两幅“默契配合、运筹帷幄”并最终决定了起义胜利的英雄合照中,事实上只有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三人才是真正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叶挺与叶剑英等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仓促而来,并且根本也没有受到起义组织者的高度重视。即使是领导者张太雷、黄平和周文雍这三个不懂军事的文弱书生,他们平时也几乎是很少联系难得碰面,所以聂荣臻后来便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在暴动的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之外,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的机关来指导一切。”[16]同样是为了维护党组织的高度纯洁,在小说《三家巷》里那份领导人的名单中,欧阳山人为地删掉在“广州起义”中犯有过错,1932年在天津被捕后又叛变了革命的黄平,这真可谓英雄者此一时彼一时也。小说《三家巷》的故事情节中,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周炳与党的高级领导人会面恳谈的艺术场景,以便去强化党关爱主人公周炳思想成长的合理性与可信度:
苏兆征同志看起来三十多岁年纪,瘦瘦的中等身材,神气清朗,待人十分亲切。他一见周炳就抓着他的手说:“我听说你工作很努力,大家都很喜欢你。你演戏演的很好,不是么?我们要把你从庶务部调到游艺部,你给我们演一出戏,好不好?”
(小说《三家巷》,第157页)
他看张太雷同志,约莫三十岁的年纪,脸孔长得又英俊、又严肃……宽阔的前额下面,有一双深沉而明亮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线条,都刻画出这个人的性格是多么的端正、热情和刚强……他走到他身边,对他醇厚地微笑着,说:“哦,一个人背了两根枪,不累么?——很好,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生,身体很棒,很好很好……你看国民党多绝!把这样一个好后生迫得无路可走……从今天起,全世界的路都让你自由自在地走,你喜欢怎么样走就怎么样走!现在你临时给这里帮帮忙。这里缺一个忠实可靠的通讯员,你就来做这个事,怎么样……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革命者的牺牲,是什么地方需要他,他就到什么地方去。”
(小说《三家巷》,第328-329页)
叶剑英走到周炳身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会动脑筋。好材料!你这么年轻就参加革命,比我们幸福多了!”
(小说《三家巷》,第330页)
由此可见,党对工人阶级的关爱,无处不在无微不至!正是因为有了党组织的深切关怀,还不是党员的周炳开始了他的革命道路:他为罢工工人演出《雨过天晴》,他为组织编印《红旗日报》,他拿起武器积极参加战斗,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党组织!“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虽然是电影《雷锋》中的主题歌,何尝又不是发自欧阳山的内心之声。
小说《三家巷》的艺术传奇,与欧阳山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初衷密切相关。欧阳山是跨越现当代的革命老作家。四十年代,他不仅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还为毛泽东的《讲话》出台提出过宝贵意见。他在延安期间多有成就,文章《活在新社会里》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而小说《高干大》则更是在延安及解放区享有盛誉。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欧阳山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和认识,于是他想用《革命与反革命》为题,去写一部反映历史变迁的“史诗”小说[17]。但欧阳山发现时机没有成熟,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解放,革命与反革命正在殊死较量,未来政治形势仍不十分清晰,故他忧虑重重不敢动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两条道路斗争到这时有了结果,眉目清楚了”[18],此时欧阳山审时度势,在革命胜利已“眉目清楚”的大前提下,终于一鼓作气写出了长篇巨著《三家巷》,使人不能不佩服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与稳健。《三家巷》的创作宗旨,是要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所以他决定把最能体现工人阶级革命本质的“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等历史事件,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情节,并通过塑造主人公周炳的成长历程,去真实地再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画卷。不过,《三家巷》虽然写得“万木霜天红烂漫”,但它毕竟只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还比较幼稚,其势力弱小难以担当革命大任,农民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绝对主力。所以,虽然《三家巷》中的历史事件和部分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但总体来说仍是艺术真实大于历史真实。
《三家巷》只是一个艺术经典,但却曾经是外地人认识广州的一个标志,如今也更成为了广州人怀旧情绪的一个记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小说《三家巷》刚一出版,就调动起了广州人去寻找“三家巷”的巨大兴趣;欧阳山还特意为此举办过一个“竞猜”活动,让大家去猜猜小说中所描写的三家巷究竟在哪个位置。而著名作家莫言在90年代第一次来羊城,就充满着激情去探访他想象中的那个“三家巷”,可“窜遍大街小巷想找区桃,可到头来连个胡杏也没有碰到。”到了2004年,与区桃无甚关系的“区家祠”,更是时逢机缘备受关注名声大噪;而到了2009年,《南方都市报》又发表了署名张丹萍的一篇文章,题为《“三家巷”:一桩文学/地理迷案》,带着积攒了几十年的读者疑问,根据小说按图索骥考察了广州的大街小巷,可最终也没有考证出一条与欧阳山笔下一模一样的“三家巷”。这些都说明了人们对于《三家巷》真实性的执着认知。一部传奇化的《三家巷》,它不是历史却变成了历史。而真正反映“广州起义”的历史资料,却只出版印刷了数千册。更有甚者是它对广州革命的艺术描述,早已被当作了广州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19],这种“红色经典”历史真实化的社会宣传,实际上完全遮蔽了革命历史的事实真相。对此,人们是否应该去进行深刻地自我检讨呢?
无论如何,性格执着的广州人始终坚信“三家巷”一定存在,他们要求政府在2010年广州旧城改造之际,理应按照小说《三家巷》里的结构布局,去恢复性地再造一座令几代广州人都魂牵梦绕的“三家巷”——于是在广州的六榕街上,一座“三家巷”正在拔地而起。我们固然可以把这件事看作是聪明的广州人,在利用红色经典去捕捉一个商机;但我们更倾向于这是广州人民对于西关风情,对于自己那段光荣历史难以磨灭的永恒祭奠!也许伴随着时间的逐步流失,人民会渐渐忘却欧阳山;但无论如何广州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们还有一个同“羊城”一样的历史符号——“三家巷”!这就是欧阳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
[1]欧阳山.三家巷[M].香港:香港三联出版社,1959.
[2][4]田海蓝.百年欧阳山·欧阳山评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3]欧阳山谈《三家巷》——《羊城晚报》专访[A].欧阳山文集(第十卷)论文及其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4117.
[5][6]欧阳山《三家巷》、《苦斗》再版前记[J].广东文艺,1978,(5).
[7]钱义璋.沙基痛史[M].台北:文海出版社,1925.11.
[8]李志毓.沙基惨案:一场革命的“情感动员”[J].粤海风,2010,(4).
[9]黄 平.广州暴动[A].广州起义[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25.
[10]刘楚杰.关于广州暴动情形致斌兄信(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A].广州起义[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05.
[11]徐向前.参加广州起义[A].广州起义[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18.
[12][18]徐 雁.广州起义全纪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316、334.
[13][16]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A].广州起义[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77、174.
[14]立三给中央的报告(节录)[A].广州起义[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37.
[15]聂荣臻回忆广州起义[A].广州起义[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11.
[17]欧阳山谈《三家巷》——《羊城晚报》专访[A].欧阳山文集(第十卷)论文及其他[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4119.
[19]王国梁.从“三家巷”里看广州起义的真实性[J].广东党史,2008,(6).
Epic Narration of Guangzhou Revolution——An Artistic Legend of The Three Family Alley
HUANG Xian-jun
(Chinese Depart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Among red classics,the novelThe Three Family Alleyis not the most influential,but it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It is the first red classic in southern China to reflect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Lingnan.It enjoys popular support as it is believed to have authentically depicted such revolutionary events as“Shaji Massacre” and“Guangzhou Uprising” by molding touching images of workers like Zhou Bing.In fact,in describing the Guangzhou revolutionary events and molding worker groups,The Three Family Alley,written in the age when the whole country was all red,had to make artistic adaptation to the history of“feeling proud even in defeat”,and to exaggeratedly beautify the Party and workers that were then weak in strength.As a result,there is a great gap between the 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truth.This is the revolutionist and writer’s unusual understanding of Guangzhou,the heroes’city,and it highly embodies the writer’s profou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Besides,it is an artistic rule that was universally followed by all the red classic writers during that special age.
The Three Family Alley;artistic adaptation;historical beautification;truth
I206.7
A
1674-3652(2011)03-0001-08
2011-03-09
黄贤君(1986- ),女,暨南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爱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