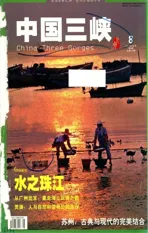从广州出发: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2011-01-17王英华
王英华
从广州出发: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王英华

左:夕照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广东徐闻。摄影/黄/CFP

右:2006年2月12日上午,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泉州仿古“迎蕃货”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繁华盛况。摄影/陈紫玄/CFP
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它肇始于秦汉,发展于三国至隋,繁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
近年来,随着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日受重视,沉寂已久的丝绸之路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2010年11月,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丝绸之路赫然名列其上。这条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长的商贸及文化线路,再度热闹起来。
中国东部即太平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作为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大洋,是中国东部的天然屏障;作为连接海外众多国家的大洋,它又是中国交往对外的重要载体。是把它作为退守的屏障,还是远航探险满足政治经济的需求?2000多年来,历代王朝是以怎样的心态来权衡取舍的?
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利用祖辈积累下来的雄厚实力,北拒匈奴,西通西域,东营辽海,南平闽粤等地,使汉帝国的国土面积较秦代增加一倍多。这不仅为国内交通的开拓奠定了基础,且实现了国内与国际交通的衔接。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派船队自今广州起航,沿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外港出海,沿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半岛航行,直通印度洋腹地,最远可达斯里兰卡。这是正史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
据《汉书》记载,汉帝国的使者携带的是贵金属黄金和丝织物杂缯。可知,这一时期,输出物是黄金和绢帛并列,而以黄金为主。《盐铁论》中也有一种说法,“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换来的则是明珠、琉璃和奇石异物等。
东汉:与西方大国罗马的跨洋接触
东汉时,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向西延伸至欧洲罗马。
东汉与罗马两大帝国的最初接触仅限于双方商人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既不在东汉本土也不在罗马,而是在位于两国之间的印度、斯里兰卡进行。在这一时期的罗马文献中,开始出现关于中国人的描述,“其人诚实,世界无比。善于经商,可以不面对面贸易,遗货于沙碛中。”

罗马人首次踏上中国领土是通过缅甸国王实现的,且是非官方的。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汉安帝接见了缅甸国王派来的艺术表演者,其中一位魔术师来自罗马帝国,“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这是正史记载中罗马人留给中国人的最初印象。
为实现两国间的直航,东汉与罗马政府都在想方设法寻找通道。早在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抵达条支(今叙利亚)后,因古波斯人欲通过向罗马贩卖中国彩缯而获利,极力夸大前往罗马海道的艰险,甘英等人面临波斯湾大海却步而止。同时,罗马皇帝也试图遣使通汉,也因古波斯人的阻挠而不得行。延熹九年(公元166),罗马皇帝马可·安东尼派将攻打安息国,将美索不达米亚重新纳入罗马版图,扫清了自波斯湾前往东方海道的障碍。是年,安东尼派使者来中国觐见汉桓帝。
其路线大致是,罗马船至印度后,环绕亚洲大陆南部,通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直抵中国南部的交趾(今越南)等七郡,然后沿北部湾经合浦、徐闻到达今广州。至此,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汉与罗马东西方两大帝国终于跨越茫茫的大海相见。
这一时期,罗马人开始了解到中国丝绸的原料并非想象中的植物,而是蚕虫,并关注养蚕之法。“赛里斯(即中国)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
三国魏晋南北朝:“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兵燹不断,西域交通要道屡被阻断,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与西方各国的往来主要通过海路,海上贸易日益繁盛,渐至于凌驾汉代,所谓“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2007年5月,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在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南海一号”存放在该馆水晶宫内的效果图。 摄影/钮一新/CFP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拥有吴会闽越交广等地,对沟通海外事宜非常重视。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接待了来自罗马的商人秦论,并详细询问那里的“方土风俗”,这是留名于中国正史中的第一位罗马人。秦论回国时,孙权派使者护送。此外,孙权还派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康泰出使南洋,二人“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并于回国后著书记述东南亚、南亚诸国的风土人情。
据《南史》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已确知的南洋国家共15个。时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之一。“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轫积王府”。
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晋代高僧法显自陆路前往印度、斯里兰卡求经学法数年,返回时携带大批佛经典籍随商船至广州归国。所著《佛国记》,记述了当时到广州经商的东罗马、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十五个国家。
与海上交通繁忙景象相应,中外交流内容也日渐丰富。最值一提的是佛教的传播。早在汉末桓、灵二帝时,在外来僧侣的主持下已开始翻译佛经,如康居人康僧会曾于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自海路来至南京,翻译佛经。
此后,中国僧侣日渐不满于外来僧侣传译的经典,于是亲往印度等地求经学法,法显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此后往来南洋的僧人,根据《高僧传》考证,约有十人。十人的行程各不相同,目的地北至山东东莱等,南迄广州。其中四人抵达广州,二人溯江而上至扬州。同时,佛教又通过海上交通自中国向高句丽、日本等国传播。
就物资交流而言,丝绸仍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则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琉璃、珠玑等。
这一时期,中国的养蚕之法远传至印度和罗马。根据希腊历史学家普罗科匹阿斯(公元500-565年)的记载,为得重赏,几个印度僧人偷偷从中国取走蚕卵,跑到拜占庭献给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折思丁,“由是罗马境内亦知制丝方法”。日本则聘请中国纺织工匠前往授艺。
至公元5世纪,西方先进的玻璃器皿制造法开始传至中国南京一带。三国东吴使者康泰在印尼爪哇岛上注意到当地纺织的“白叠花布”。白叠花即棉花,宋末元初传入中国,引发纺织业的巨大变革。
时外侨定居中国者甚多。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元魏时期定居洛阳的外国僧侣达三千余人,还有远自罗马而来的非佛教僧侣;外侨住宅区则多达“万有余家”。其中,有不少自海上而来者。
隋唐:海上丝路逐渐取代陆路的地位
隋唐时期,尤其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力强盛,国门洞开,加之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交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逐渐取代陆路交通的地位。这一时期,自广州出发通往欧洲甚至东非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隋炀帝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即位之初就在京都设四方馆接待各国来使。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带着丝毛织物,从广州启航出使今马来西亚。
唐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素喜地理,凡各国使者来访或迎送其回国时,必细询其山川形势,因而熟知中外交通情况。他总结认为,唐代“入四夷之路”主要有七条,陆路五条,海路二条:一是自登州入高丽,一是广州出发往西方各国。

游客在广东阳江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观赏文物。摄影/梁文栋/CFP
自广州出发的航线大体可分为四段:广州至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至斯里兰卡;沿印度半岛西部西北行至波斯湾头;自东非沿海北溯至波斯湾头。海上交通进一步延伸至东非。
唐中期后,日本船只不必再绕行朝鲜西海岸、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海岸,可由九州直航长江口,抵达宁波、扬州等地,中日间航程大为缩短。因此,日本官方使团、中国官方派出的商船频繁往来于两国。
据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学习内容之丰富,堪称中日交流史上的盛举。
广州是唐代最为繁盛的海外贸易港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昆仑(根据张星烺的考证,唐代文献中的“昆仑国”即为今非洲)等国船舶屯聚广州城下,中国商船也大多由广州出发赴南洋和南亚一带,甚至远航欧洲和东非。
由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叹曰:“广州素为众舶所凑”。著名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被风漂流至海南岛,北经广州回归时,但见“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侨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很多,时广州居民共25万人,外侨人数达1万余人。
唐代通过海路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侣再度将佛教的传播推向高潮。此外,唐代,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袄教等陆续传入中国。
由于唐代是中国史上最为繁盛的时代,威震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各国均以“唐”称中国。至宋代,皇帝曾试图通过诏令强行各国改称,终无实效。明代仍复如此,根据《明史》的记载,“唐人者,诸藩呼华人之称,凡海外诸国尽然”。
宋代: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海外交往与贸易的朝代,“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宋时期始终奉行的基本外交政策。
为促进对外贸易,增加政府税收,宋代在重要港口设市舶司,负责“藩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先是在广州,后相继于宁波、杭州、泉州等地设市舶司。
据统计,至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仅广州、宁波和杭州三处市舶的乳香贸易收入就达89万多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仅广州港的市舶收入就高达110万缗,加上泉州、宁波,高达200多万缗,占当年全国商业税的五分之一。
对此,宋高宗由衷地叹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当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这是南宋在外有强敌压境且需向金年年纳贡,内有庞大官僚需求的情况下,仍能支撑一个半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特别是南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不仅使政府获利甚丰,且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唐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0余个,到宋代增至40余个,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区。
时广州是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港口,所谓“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其次是泉州,时“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
宋代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还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宋徽宗时有两艘出使高丽的海船装载量达一千一百吨。还首创隔舱技术,当时所造大型海船有上下四层,五六十间客房和仓房。舱与舱之间用双层隔板,一舱破损漏水,不影响邻舱的正常使用,且便于维修。航海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海船上装有磁石指南针,采用干支定位术。这一时期,指南针连同印刷、造纸和火药等中国四大发明西传入欧洲。
宋代,外侨定居中国沿海一带的现象最盛。时广州、泉州和杭州等通商口岸都有大量外侨定居。北宋末,在通商口岸城外划定地段,名曰藩坊,专供外侨居住,设官管理。并允许外侨在城内建寺,如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等。与此同时,肇始于隋朝的华侨海外发展现象,至此已有一定规模。

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展出的郑和雕像。摄影/史训锋/CFP

2005年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将每年七月十一日确定为中国法定的“航海日”。图为郑和航海暨国际海洋博览会上展出的东海长三角海域模型图。摄影/史训锋/CFP
明代:“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
明代,政府支持下的郑和下西洋铸就了世界航海史和中外交流史上一段传奇,而对本国商人实施的严厉海禁政策则拉开了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序幕。同时,为获取财富和奴隶的欧洲航海探险家们也来到中国,这一切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至为深远。
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年至1433年),在朝廷的支持下,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最多时拥有船只300余艘,每船长44丈,宽18丈,可容千余人。所用铁锚,往往需用二三百人才能抬起。船员27800人,除军士外,还包括各种行政和后勤人员,如医官、文书、翻译、船长等。
据晁中辰的研究,郑和的船队一般是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先到福建五虎门,再南下越南南部、马来西亚和爪哇等国,穿过马六甲海峡继续向西。前三次出使的终点站都是印度半岛南端,自第四次开始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达波斯湾沿岸,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国进行交往。最初,郑和的船队沿海岸线航行,后来便由印度半岛南端横渡印度洋,直达红海口和非洲东岸各国。
在私人海外贸易方面,明代一改宋元时期鼓励海外贸易发展的做法,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太祖朱元璋并将之立为“祖训”。有明一代,海外贸易间有松弛,但终以严禁为主流。至嘉靖年间,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以王直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对禁海政策的反抗达到高潮,并酿成历史上著名的“倭寇之乱”。
郑和下西洋半个世纪后,即15世纪末至16世纪,西欧各国为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富庶的东方国家成为他们的目标。相信地球是圆形的欧洲水手们坚信,由欧洲西海岸向西一直航行就能够到达中国和南洋各国。
于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人相继开辟新航线,创造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葡萄牙人首先来到南洋一带,并与中国发生关系。西班牙和荷兰人紧随其后,相继来到中国。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海水湿了货物,希望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受贿,允许他们在澳门登岸。最初,葡萄牙人在澳门只搭盖临时性茅棚数十间,后来偷运砖瓦木石,建造永久性的房屋,聚落而居,使澳门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的主要据点。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人将台湾占为己有。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时代的高潮,也是终结。郑和船队的规模之大和技术之先进让当时的世界为之瞩目,诚如李约瑟所说,“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
船队每到一地,郑和都遵循“厚往薄来”的明代朝贡贸易惯例,代表中国皇帝对当地王公大臣进行赏赐,并接受回赠礼物,同时开展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等。这在客观上推行了和平外交的政策,给所到国家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没有引领中国历史进入新的时代。
而且,这种由政治需求而非经济利益驱动的海外交流,不具有可持续性。终因花费太大,加之明政府海外政策保守倾向占据主流,而成千古绝唱。梁启超由此叹曰:“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个世纪后欧洲海洋探险的组织实施者往往是国王、海盗和商人三位一体,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直通印度的航线,结果却发现了“新大陆”,虽由此开始了包含着罪恶与血腥的对财富与奴隶的掠夺,但却为欧洲发展赢得了必须的资本,并促进了美洲的开发。
明代私人海外贸易在艰难中冲破出海禁令,仍获得很大的发展,由此导致白银大量内流,彻底改变了明初以来白银紧缺的状况,使银本位制得以确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商人大量外移,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的华侨社会初步形成。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士也由海路来到中国,在布道的同时也介绍西方的科技文化,由此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其中,利玛窦是最著名的一位。万历十一年(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先来到中国。四年后,把正在印度果阿传教的利玛窦调来当助手,两人从澳门来到广州,还送给当地官员一幅世界地图,使时人耳目一新。另一位传教士马礼逊在曾广州编撰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收录汉字4万多个。
清代:由“海禁”到“闭关”
清代实行较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海外贸易进一步萎缩消沉,并达到闭关锁国的地步。
清初,著名的海上抗清力量郑成功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赶走荷兰人,进据台湾。为截断郑成功父子与大陆的联系,清政府下“迁海令”,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一律迁于内地”,数千里滨海地区五十里内不许住人,不得有大小船只。虽然此次海禁主要出于军事的需要,并无排外的目的,但在实际上阻碍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外贸易发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解除部分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和连云港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负责管理对日本和欧洲各国的贸易。英国、葡萄牙和荷兰等国都与清政府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关系。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华的欧洲船只达29艘,运来的货物中以自鸣钟、呢绒、玻璃等工业品为主,带走的仍是茶、丝和瓷器等。这是清代海外贸易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的回光返照。
至乾隆朝,四个海关中撤去三个,仅留广州一口与外洋通商。并陆续制定各种严格措施,于广州专设洋货十三行,作为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此种情形下,外国政府和商人很难与中国官府接触。
与明代类似,清政府在解除部分海禁的同时,仍严禁商民私自出海贸易和侨居海外,定居海外的侨民则严禁归国。这些禁令,历经康雍乾至道光朝,百余年来,愈演愈严。如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菲律宾巴城大肆屠杀华人,“挨门排户”,不论男女老幼,屠杀近万人,清廷认为这些华人“实与彼地藩种无异”,听其屠戮。


这种漠然视之的态度,使得在外华商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伤。而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严禁与西方国家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预言性地警示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英国工业革命后,经济实力逐渐强大,亟需打开中国市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数百余人的庞大使团前往中国,向乾隆帝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设立英使馆及减免课税等请求,企图敲开中国紧闭的大门。
这是中英两国间的首次正式通使。然而,乾隆帝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坚决地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全部要求,并因朝见礼仪问题而与使团发生严重分歧,双方不欢而散。
马戛尔尼虽未完成英王的使命,却于来往途中留心勘察记录大清帝国的山川地形和风俗人情,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而大清帝国君臣对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众多展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礼品,尤其是枪炮战舰等的模型,似乎没有什么印象。
马戛尔尼郁郁而去二十三年后,英国第二次派遣访华使团,英使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而遭驱逐。又过了二十四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前者康熙帝的预言性警示,不幸而言中。
放眼世界,回顾历史,面对未来,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辉煌时刻与屈辱事件的相互交织的事实所体现出来的政策、观念,甚至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反思。
王英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
(编辑/于翔汉)